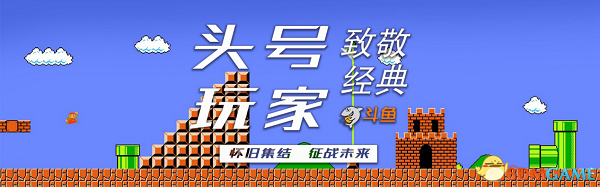譯/MelroseRui
編/Kaogaiyi
FromThe New Yorker
斯皮爾伯格的《頭號玩家》(Ready Player One)可不是一部關注影片遊戲的反烏托邦少年歷險記。它是一部恐怖片,充滿了心靈空洞的精神僵屍。他們的靈魂被一代又一代的官方文化製造者蠶食,在片中又借流行文化懷舊之名被重置。
導演將電影設定為抗爭財閥暴政的故事,但實際上影片卻展現了另一種暴政何以不朽——頌揚極權主義的掠奪者以娛樂至死洗腦俘獲的閱聽人。如此令人窒息的恐怖,斯皮爾伯格卻視而不見,無疑是雪上加霜。

《頭號玩家》的故事發生於2045年,主人公韋德•沃茲(泰伊•謝裡丹飾)幼年失怙,與姑姑和其暴虐成性的男友一起生活在俄亥俄州哥倫布的貧民區。韋德同所有居民一樣,將虛擬現實程式“綠洲”作為娛樂方式和經濟來源。
遊戲中的金錢流動會實時反映在玩家現實中的銀行账戶上。韋德還同許多玩家一樣(可能有上百萬),為了不菲的報酬參與進了“綠洲”的新競爭中——尋找虛擬遊戲中的三枚彩蛋。

這場遊戲中的遊戲是綠洲的創始人和發明者詹姆士•哈利迪(馬克•裡朗斯飾)留下的身後遺作。他在遊戲中規定,解出三道謎題的玩家將成為綠洲的新主人,繼承價值五千億美元的財富。哈利迪不僅是流行文化的創造者,他也是流行文化的癡迷者。
他癡迷於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流行文化,並將這種癡迷化為了解謎的關鍵(他的人生經歷是另一個關鍵)。在遊戲中化身為虛擬角色帕西法爾的韋德在這兩個方面佔據了絕對優勢。韋德同樣癡迷於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流行影像和遊戲製品,這種癡迷甚至擴大到了對哈利迪的人格和人生經歷的探索。

生於八十年代,長於九十年代的哈利迪將他的兒時嗜好往後拖拽了整整半個世紀,讓他們改頭換面成了二十世紀中葉流行文化的核心。《頭號玩家》中內嵌了數以百十計的流行文化引用,它們或一掠而過抖機靈,或緩緩移動填充整個場景(影片中有一系列鏡頭建構於《閃靈》(Shining)的布景重現上,然而得到重現的只有幾個標識性物體,這不免使整個重現場景如同主題公園般傻氣)。
這些引用共同營造了一種可悲又虛假的回響——在極客和宅男的潮流天堂裡,一種狹隘的觀點不斷地被鞏固;二十世紀晚期關注的是商業消費而非真正重要的議題。

在哈利迪或者說斯皮爾伯格的幻想世界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沒有斯派克•李(Spike Lee),沒有吉姆•賈木許(Jim Jarmusch),沒有約翰•卡索維茨(John Cassavetes),沒有科恩兄弟(Coen brothers),更沒有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和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年代;八十年代蓬勃發展的嘻哈,朋克,搖滾通通不見蹤影。在韋德生活的世界裡,反主流文化和獨立藝術是不存在的,在綠洲的虛擬世界中更是如此。

《頭號玩家》珍之愛之的八十年代忠實地避之不談其特立獨行的反叛因子。凱瑟琳•柯林斯(Kathleen Collins)的《迷失之地》(Losing Ground)從未發行;小萬戴爾•哈裡斯(Wendell B. Harris, Jr.)、朱莉•戴什(Julie Dash)、瑞秋•阿莫迪歐(Rachel Amodeo)均未著一墨;伊萊恩•梅(Elaine May)扼於刻薄之言。影片得標志性的致敬場面展現了一場荒謬的活死人狂歡,缺位的不止是活生生的肉體,還有原作的歷史和延展。

影片中的另一致敬場景還原了《周末夜狂熱》(Saturday Night Fever)的鬥舞情節,閃耀的迪斯科舞廳地板逼真奪目,可惜支撐起原作的實質內容——種族幫派鬥爭、關於墮胎正當性的爭議、性騷擾引起的爭論無一被提及。
簡而言之,《頭號玩家》描繪了一個精心矯飾的虛擬時空,在這裡任何比斯皮爾伯格及其作品更前衛、更大膽、更深刻的藝術家和作品都被過濾捨棄。而令人齒冷的是,片中輻射深廣的虛擬現實和充實其中的懷舊事物並未作為影片的反烏托邦預設被賦予專製和恐怖的意味。急於重現兒時戀物的哈利迪創造的世界中,只有腦中塞滿了哈利迪癡迷之物的年輕人,精神世界仿佛克隆而來,全然不在意實際憂患。

而對那些精神消費僅限於爆米花電影、商業影片遊戲和大眾流行音樂的觀眾來說,《頭號玩家》帶來的啟示是熨帖順心的。無需畏懼,這些東西給你帶來的足矣,有了它們你足以成為宇宙的主宰。
但是這令人寬慰的保證背後藏著致命又麻木人心的自我滿足。永遠隻滿足於最易上手的,不去思考廣告宣傳和算法篩選的真正意圖;視利潤不菲而又無關緊要的競技遊戲的提供者和傳銷者為偶像,真正的英雄卻無人問津。斯皮爾伯格的電影生涯正是基於這樣的信條——大眾流行藝術是高尚的。

在片中,帕西法爾正借用了導演的終極信條來辱罵反派索倫托,“真正的粉絲一眼就能看出黑粉”。《頭號玩家》以哈利迪的形象將斯皮爾伯格塑造成了終極酷老爸,韋德的英雄主義也成了一系列以誠孝為中心的美德(對酷老爸的誠孝)和對流行文化的虔誠。
只是在酷的包裝之下,《頭號玩家》真正講述的卻是一個可怖的故事。一代又一代面貌慈藹的文化創造者,延續鞏固著他們日薄西山,暮氣沉沉的統治,蠶食著年輕一代的心智。狂熱的粉絲辨不清狂熱的邪異因他身在其中。

影片中唯一堪稱影響深遠的靈光一現卻是斯皮爾伯格和自己的超級老爸纏鬥的結果。斯皮爾伯格在片中有意挑選了好萊塢獨立製作巨匠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s)展開爭論。後者的奠基之作斯皮爾伯格愛之又恨之,愛之不可多得,也恨之難以相匹的獨創性。
影片中,帕西法爾一直試圖從哈利迪的人生軌跡中找到謎底的蛛絲馬跡。為了研究他的人生經歷,帕西法爾頻繁拜訪哈利迪檔案館(Halliday Journals)。在館中,哈利迪生命中的時時刻刻以全息投影的方式在玻璃牆後反覆反映。

館長則負責影像播放的暫停、快進和回放。這與《公民凱恩》(Citizen Kane)中的圖書館一幕頗為相似,在館中逝去主人公的記憶再次鮮活起來。這一幕在《頭號玩家》中的重製是斯皮爾伯格在片中為數不多的靈感迸發的時刻。哈利迪終於擺脫了僵化的懷舊之父的形象;通過那些讓他顫抖、迷茫、傷懷的人生片段,觀眾得以一窺他人性裡的脆弱和真實,探尋這位創造者內心的隱秘。
但斯皮爾伯格的靈感似乎只能帶他走到這裡,他所刻畫的哈利迪的掙扎和自我矛盾是無關緊要,毫無新意的。在影片的結尾,韋德和哈利迪的對話揭示了這一切;而對“玫瑰花蕾”這一意象的借用更顯窘迫難堪。

點擊關鍵詞查看往期精選
歡迎為深焦口碑榜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