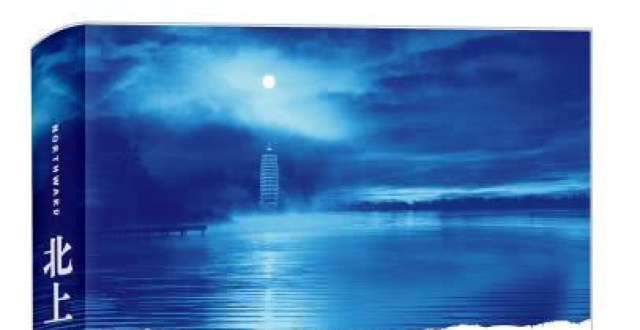張貴興祖籍廣東龍川,1956年生於馬來西亞砂勞越,1976年中學畢業後赴台升學,英語系畢業後留在台灣擔任中學英文老師。作品多以故鄉婆羅洲雨林為背景,處理外來移民與當地土著間的愛恨情仇。文字風格強烈,以濃豔華麗的詩性修辭,鏤刻雨林的凶猛、暴烈與精彩。代表作有《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賽蓮之歌》《頑皮家族》《野豬渡河》等。《猴杯》近日在內地出版
晚上,卡夫卡的寫作總要持續很久。創作於1912年的短篇小說《審判》,便是他一口氣從晚上10點到次日清晨6點寫出來的。第二天,他在日記中寫道:“只有以這種方式才能夠寫作;只有以這種連貫性,才能夠完全打開身心。”工人意外保險機構的工作使卡夫卡沒法在白天寫作。他會在早上8點帶著一身困倦去上班。儘管很早就乾完工作,剩下的時間卻被午飯、長午覺、鍛煉、散步和晚飯填滿。一直到晚上10點。
同樣的困境落在馬來西亞作家張貴興身上。可喜的是,他今年已64歲,理論上應該比卡夫卡擁有更多的時間;窘迫的是,他過去四十多年都在台灣教書,忙著和即將上高中的學生們一起受製於考試和升學壓力。偶爾沒課,就跑到學校附近每個座位都有插座的咖啡廳,招呼也不敢和老闆打,生怕熟了之後會找他聊天,佔據本就少得可憐的寫作時間。有時實在著急,只能見縫插針地在辦公室甚至直接在教室邊看早自習邊伏於講台前動筆。
因此,實際上,他的寫作時間非常少,以至於1998至2001年,他緊迫地完成了“雨林”三部曲後,整整停擱17年沒有發表任何作品。直到2016年7月,他提前一年退休,此後花了一年多,寫出《野豬渡河》。

這本書自2018年年底面世,至今所向披靡,斬獲了包括部落格來(台灣最大網絡書店)年度選書、台灣文學金典獎、聯合報文學大獎、紅樓夢獎等十多個獎項。在台灣,文學類書籍一般一次印刷兩千本,能賣完一刷便算不錯,聯經出版社的編輯黃榮慶自豪地說,“《野豬渡河》目前是六刷了,算是我做過的書裡最暢銷且得獎最多的。”
聚光燈下的男主角本人,倒是對此看得很淡。他不喜歡談論舊作(無論出版多久),每當看到Facebook上有人把多年前的剪報貼出來,他都十分不解,想起自己十幾歲時在馬來報刊上發表的關於背著吉他去雨林看書、彈唱等風花雪月的小說,恨不得立刻掏出遺囑,寫上“不可以出版我在馬來西亞的少作”,“否則我會變成鬼來找你們”!
他一方面仍為過去迫於生活的選擇而耿耿於懷,苦笑著說在台灣當職業作家大概會餓死,“不要忘記台灣只有2300萬的人口,其中有一大部分人是不太讀書的,除非你寫一些非常通俗的言情、武俠小說”;其後又認命似的陷入難以修改的無奈,“沒辦法,你總要生活,那我只能夠繼續教書。但它佔據了我大部分腦力最清楚、最強壯的時間,其實傷害很大。”
另一方面,他越發感到“時日無多”,終於自由的日子,只想埋首於預計2020年年底寫完的科幻小說,以及一部將要提筆的、以台灣為背景的長篇創作,因此不願為其他的事情浪費心思。演講邀約盡量推辭,雜誌拍攝或非去不可的頒獎典禮,一律隨意套上圓領T恤出席;編輯把設計好的書籍封面拿給他過目,每次都會收到“都可以,你們決定就好”的回復。

2019年8月,張貴興回到家鄉領取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一度因為穿著隨意而被攔在場館之外,之後只好換上襯衫
《野豬渡河》以二戰時期日軍侵略為背景,講述戰亂年代的流離和求生,其中不乏屠殺、肢解、強暴、斬首的情節,雖不是抗戰小說,但也同樣血腥殘酷。寫完後,張貴興一度覺得自己像滿手血腥的劊子手,從暗無天日裡走出來,重回人間。據此,很難聯想到寫下這些的作者在生活中這般隨和,如果不是他主動坦露,在哈姆雷特、賈寶玉、方鴻漸等文學人物身上感到共鳴的優柔寡斷更難捕捉。
“賈寶玉對待女人的那種態度,很深刻地影響到我。對女孩子非常地欣賞,非常(心)軟,就好像對學生一樣非常(心)軟。”一天下午他在家裡的躺椅上看《紅樓夢》,看到一半睡著了,夢見自己變成了賈寶玉。大觀園裡面看不到一個人,只聽見外面傳來絲竹聲、女孩子嬉笑玩樂的聲音,心想,誒?黛玉、寶釵,你們到底去哪裡?怎麽你們自己在玩,不來找我?最後在焦慮的踱步中醒了過來。回憶完,他自己都覺得驚訝,用常年累日兩杯咖啡入喉形成的嘶啞聲音驚呼,“天啊,已經四十多年了,我還記得非常清楚。”
從他講述的另一個故事中,可以更明顯感知到這份細膩與柔情。1940年代,馬來當地許多妙齡女子到處相親、急著出嫁,以免因未婚被日軍搶去做慰安婦。張貴興的父親一次與一名溫婉美好得如同從瓊瑤小說走出的長髮女子在茶館相親,彼此都十分滿意。快結束時,七八月裡突然一陣猛烈的西南風刮過,女子露出半邊臉大的胎疤,一段姻緣從此中斷。
不善言談的父親,唯獨將這件事向子女說過很多次,帶著些悔恨與不捨地喃喃,“後來她怎麽樣了呢?”張貴興也不禁浮想,並將她化作女主角寫進了《野豬渡河》裡。他體察到生命的巧合與微弱,帶著南洋的意象,“如果沒有日本人,沒有那股灼熱的西南風,可能也不會有我。”
創作中,他自認不走通俗路線,不會是討喜的作者,“讀者能不能進入我的世界,這個不是我能夠控制的。”於是將多愁善感的一面隱藏起來,隻讓讀者感受到認真嚴謹就好了。“我寫的時候,如果我覺得這種寫法太通俗,不是很好的表達方式,我就不去用它。因為寫長篇小說很容易不小心就灌水,很多不必要的東西就寫進去了,所以我盡量提醒自己,這個東西如果能夠寫成一個句子,我就不要寫兩到三個句子,如果要寫兩到三個句子,描寫得冗長,那一定是有特別的、值得我去書寫的地方。”
遲來二十年的錯愕
在海峽的另一端,對他的關注來得更加緩慢,代表作《猴杯》時隔20年才於近日在內地出版,無論是熱帶雨林的文學地理,還是華麗奇詭的美學風格與鮮為人道的拓荒秘史,都令絕大多數大陸讀者錯愕不已。那種熾烈濃稠、潮濕多汁,恨不得要從紙張裡滴出來。
出生地是小說家難以繞開的命題,人物、故事的氣息indivisible地沾染著對初始環境的記憶。愛爾蘭的陰鬱、壓抑一再為馬丁·麥克唐納提供書寫凶殺案的靈感;成長於美國西北部蒙大拿州的梅爾·梅洛,筆下彌漫的情緒也同樣空曠寂寥,漫無邊際;更不用說馬爾克斯的南美、沈從文的湘西。
而當你細看張貴興書頁中的熱帶奇象,就像親身被綁在巨大的芭蕉樹上,老鷹從你額前滑過,大蜥蜴逡巡眼底,身後傳來樹葉撥動的聲響,也許猴子和穿山甲正上躥下爬。你感到悶熱、焦灼,在快要被水汽吞沒前大口呼吸,卻又難敵墜感和應接不暇的雨林誘惑,不由得睜大雙眼,再看一看。

婆羅洲的熱帶雨林
翻完這三百多頁,就連負責此書在內地出版的編輯都大呼累。“他會用很多你從來沒有想象過的形容詞去描述一件東西,讀的時候有很強烈的畫面感,但不是馬上浮現,要運用你的想象力。讀起來很費勁,但讀下來的感覺很暢快。”
像徹夜跳急促的探戈,筋疲力盡又興奮難耐。你得撇開過往的閱讀習慣,逐漸適應最長時一口氣近40字的長句、前所未聞的動植物名詞,以及人作獸、獸作人的眼花繚亂的顛倒比喻,有人劫後餘生般感慨,“密不透風、濃鬱瘮人。”
追溯這一風格的形成,要先講一講張貴興的高中時期。他就讀於馬來當地的英文中學,英國文學課要求反覆閱讀《哈姆雷特》《李爾王》《麥克白》《暴風雨》《仲夏夜之夢》等原著,好些對白一度倒背如流。多年後,他依然視莎士比亞為“最早引導我走入文學殿堂的大師”,甚至“初戀情人”,“帶給人的那種感情和激勵,是不能夠變的。”
等到他開始寫作時,莎士比亞“每個句子都有比喻,非常華麗”的特性根深蒂固地流淌到他這兒。萬物不再如初,雲不能僅僅是白雲——它原本脆燥,這時竟濕軟得像稠粥。灰雲如同紫菜,朝長屋(雨林中沿河而建的木屋)上空飄來的雨雲則形似蜂巢、蟻窩、象糞;動物也情緒飽滿——豬做出初長成的女兒嬌樣,鴨一臉閨怨,雞像僧侶敷禪,狗肺怒張;甚至難以名狀的語言都能用同樣無影無蹤的味覺、嗅覺來形容——米酒、香料、辣椒醃製的馬來語、印尼語、印度語、達雅克語;充滿樹皮、草荄和泥土腥味的華語、廣東語、客家語、福建語;雪茄、酒精和鉛味混合的英語和荷蘭語。
在新北市生活四十多年後,張貴興早已染上純熟的台灣腔,會把“蝸牛”念成“瓜牛”。八九十年代他和太太回故鄉,被攤販當作日本人;十多年後又被當地人用英文問,你是韓國人嗎;2013年在機場,在經濟浪潮的推動下,被認作大陸人。
自從父母親過世,他回鄉的頻次越來越少。以前網絡不發達時,他會特意叮囑家裡人將平日訂閱的中文報紙收好,等他回去後要全部快速地翻一遍;如今他對家鄉的牽掛絲毫沒有減少,每天都會透過網絡閱讀砂拉越當地的三份華文報紙,並通過谷歌街景探視故鄉。
容納兩三千人的小鎮完全變了模樣,木質高腳屋替換成了水泥洋房,商店、商場等現代化設施衝散了曾經的蠻荒感,在張貴興看來,最明顯的還是自然環境的改變。
打小居住的浮腳樓,四面八方圍繞著鳳梨園、玉米園、香蕉園、胡椒園和菜園,後方是一望無際的芒草叢和雨林。以前茂密的榴蓮樹、菠蘿蜜、紅毛丹、香蕉樹,如今已罕見。少年時期露營時看到的婆羅洲鐵木、龍腦香科樹種,還有箭毒樹,現在也只能深入雨林才得目睹。書名“猴杯”即monkey cups,源自一種他童年常見的熱帶肉食植物,因捕蟲瓶裡的汁液清涼可口、猴子愛喝而得名,又叫忘憂草、豬籠草。

時隔20年、近日於內地出版的《猴杯》封面由台灣知名設計師蔡南昇設計,他曾提出用豬籠草的形象,後來在編輯王介平建議下,結合書中祖父跟小女朋友逃亡時看到蕈類發光的片段,選用了叢林中發光的蕈菇來表現迷幻與超現實感
植物的衰萎勢必導致棲息其間的動物的銳減,《猴杯》裡描寫的動物大部分也來自張貴興的童年生活。他清晰記得兒時從窗口隨便就能望見大蜥蜴,抬頭就能看到老鷹,水源被石油開採汙染前,河裡遊著數量眾多的孔雀魚、攀木魚、馬甲魚。按照長輩或客家人的習俗,闖入家園的動物是不吉祥的,每當看到老鷹在屋頂盤旋,一家人就得趕緊拿個破銅爛鐵用力敲打,或者用力呐喊、驅趕。到了夜晚,常有迷路的豪豬或奇怪的鳥類進門,張貴興笑著說,“若不是母親阻攔,我家裡大概可以開一個小型動物園。”
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他常常不自覺地在小說中切換成動物視角。《猴杯》的主人公名為雉,他的弟弟叫鴒,“我發覺我喜歡用動物的名字來幫人類取名字。當然,除了增加動物性,也希望可以拉近人跟動物的距離。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說過,我們形容一個人的殘暴,喜歡說他跟動物一樣的殘暴,但是這樣子講,對動物是不公平的,是很扭曲的。因為動物雖然殘暴,但它不像人類的殘暴,人類殘暴是藝術性的,非常精致的,非常巧妙。”
用動物的名字稱呼人,對張貴興來說,可以看作是對人類的一種排斥。他認為,人類基本上跟豬籠草一樣,也是一種肉食生物,只不過獅子、老虎是生吃,而人類搞了很多花樣,把這個叫作文明。反之,用人的名字去給動物取名,在他心裡,其實是把動物的地位給拉低了。
書中著墨較多的一頭犀牛,他取名為總督。“總督的原文是Rajah,在馬來文裡是國王、酋長,甚至獨裁者的意思。Rajah是統治砂拉越的第一代英國人,我特別用這個名字來取名犀牛,代表他統治的、狂野的、非常野蠻的、沒有人性的那一部分。”
歷史越混沌,越適合小說家進場
清末民初,大量華人勞工來到馬來半島和婆羅洲,在他們的艱苦勞作下,一片片原始森林和沼澤泥潭被開發為種植園和礦區,市鎮也隨之建立。在此背景下,馬華作家創作了一批表現華人艱苦拓荒的小說。然而,種植園主在不斷開墾周圍雨林荒地的過程中,必然侵犯到原住民的生活領地。張貴興借助《猴杯》,聚焦華人拓荒史上的黑暗一面,即華人資本家對底層勞工的剝削與對土著居民的侵害,從而讓馬華文學中的拓荒史書寫更為完整。
他的靈感來自一位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黃乃裳。這位華僑領袖曾帶領福州移民開墾馬來西亞砂拉越的詩巫(又稱“新福州”),他與鄉親們櫛風沐雨地在荒涼的土地上白手起家,播種薯蔬五穀,引種橡膠,蓋學校,修公路,建廠房,把當年人跡罕至的蠻荒之地,變成了砂拉越重要城鎮和經濟文化中心。黃乃裳終身與不良風氣做鬥爭,在他的墾植廠,嚴格禁止吸食鴉片、賭博、賣淫,最終他被驅逐出境回到中國。
看完黃的歷史資料後,張貴興覺得這個人物似乎太正面了。“他之所以禁絕賭博、鴉片、賣淫,當然就表示當地的墾植廠原來就有這些東西。所以我書寫這麽一個反面的故事,覺得這樣子的話會更有可看性,更能夠帶出比較深刻的問題。”

砂勞越,伊班人村莊(資料圖片)
史料的缺乏,造成婆羅洲的歷史模糊不清,包括婆羅洲有兩個華人建立的王國,一個叫蘭芳王國,一個叫戴燕王國,都是成立了將近100年,後來被荷蘭人消滅。這兩個王國的資料也非常欠缺。不過在張貴興看來,歷史的空白恰恰成了小說家的優勢,因為沒有人真正知道發生過什麽事情,小說的價值得以凸顯,可以天馬行空地去填補細節,書寫這一段失落、斷裂的歷史。
“強大的民族都有陰暗面,殖民主義讓原住民淪為二三等人,東南亞華人被歧視,這些都成為了原罪。偉人、紀念碑有人寫,但我更想描寫枯骨與地獄陰暗。世界模糊,文獻也不一定完全正確,歷史人物都像幽靈,這時有人提著燈籠,希望能夠照亮裡面看不清楚的、非常黑暗的一部分,這個人就是寫小說的家夥。”
他著迷於書寫黑暗面,希望借此能夠更清楚地看清黑暗。歷史越混沌,越適合小說家進場。但他無意梳理歷史,一再強調“我寫的不是歷史,我寫的是小說”。
雨林為他提供了生猛旺盛的滋養,種種私密、珍貴的兒時見聞與成年的自己血肉相連,甚至可以相伴一生。他承認,《猴杯》有很大的自傳成分。但這個自傳並不局限於現實生活中吸食鴉片的祖父、混跡森林的原住民同學、一輩子沒有頭髮的女鄰居等情節上的相承,更多的,是精神上獨一無二的、僅屬個人的雨林感受和經驗,就仿佛隱約覺得另有一個“你”活在那個時代。
在當地文壇,許多人覺得張貴興書寫的砂拉越跟他們認識的砂拉越不太一樣,他們甚至說,這不是他們認識的砂拉越。他解釋過很多遍,他寫的是童年跟青年時代的記憶,就好像有些讀者因為仰慕莫言就到高密縣去看,卻因與小說描寫相差甚遠而大失所望。莫言說,他寫的是文學的高密,不是地理的高密。同理,張貴興也常常說,“我寫的是文學的砂拉越,而不是地理的砂拉越。”
莫言大部分作品他都看過,最喜歡的還是《透明的紅蘿卜》,“充滿了生命力。你可以發覺他並不是為了寫作而寫作,而是好像真的想要寫一些東西,沒有考慮太多就寫出來了,這種寫作方式充滿著原始力量。所以我寫作的時候,我一定要告訴自己,我還有沒有那種非常原始的創作欲望,推動我寫一部作品,而不是為了寫一個長篇而寫,那種原始力量是完全憑感覺去揣摩。”
這種力量該如何保持、不被生活吞噬?張貴興將過往17年不得已的暫停當成儲備期,“這個力量很重要,就是要靠不斷地閱讀、思考、做筆記、寫日記等等來維系。等你存積了一定的能量,覺得不寫也不行,就一定會爆發出來。”
南方人物周刊 孫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