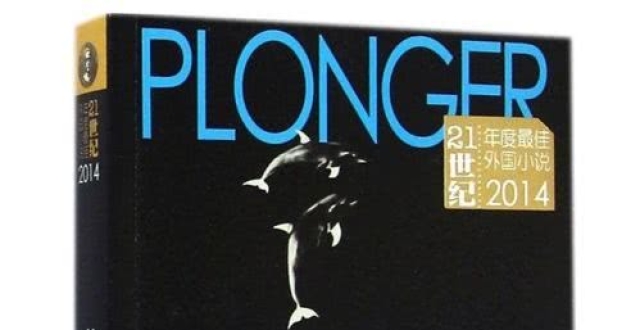畢飛宇是一位出色的小說家。從1991年發表處女作到現在他已經寫了近三十年,而從他寫作起步算,這個時間還要大大提前。他得獎無數,長中短篇小說都獲得過中國文學的最高獎。著名評論家李敬澤說他是“一個刀光閃閃的家夥”,他可以“把一團亂麻清晰地講述出來,精確流暢”。畢飛宇最著名的作品是寫盲人的生存與內心的小說《推拿》,他的寫作就像一束投射到現實世界的光,讓讀者清晰地看見或許不曾留意的幽暗之中的一切。

畢飛宇
1964年生於江蘇,代表作有《哺乳期的女人》,中篇小說《青衣》《玉米》,長篇小說《平原》《推拿》,獲得魯迅文學獎和茅盾文學獎等多種文學獎項。
寫作是投射到現實世界的一束溫暖的光
——訪畢飛宇
文丨《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程青
Q
1994年你寫了短篇小說《哺乳期的女人》,當年就獲得多種文學獎,並在1997年獲得了第一屆魯迅文學獎,作為一個小說家可謂出手不凡,你是怎樣捕捉到小男孩旺旺這個人物形象的?

畢飛宇:實際上我是一個對思想潮流很敏感的人,讀大學的時候就是這樣。1994年,中國離所謂的現代化還很遙遠,而在西方,反思現代化卻早就開始了。我很感謝那個時代的《讀書》,它幫助我建立了一個非常好的心理習慣,那就是無論做什麽都伴隨著反思。那個時候的中國正大踏步地走在現代化的路上,但是,如何現代化?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可以借鑒什麽?避免什麽?這個是我很關心的。《哺乳期的女人》的寫作動機完全是一個意外,那就是我在一個小鎮上問路,一路上,我只能遇上孩子和老人,沒有一個會說國語的人。我第一次在中國的大地上感受一種異樣的現實,也就是“空鎮”。雖說“空鎮”“空村”“空巢”這些概念當時在我們的語匯裡還沒有出現,但是,對一個30歲的年輕人來說,它是觸目驚心的。對我來說,我用不著去捕捉,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我只需要幾秒鐘就可以看見三個人物:一個小男孩,也就是旺旺,一個鰥居的爺爺,還有一個回家生孩子的少婦,他們處在一個封閉而又空洞的現實之中,這就是一個小說家的直覺。事實上,對未來的中國而言,他們不是“人”,而是一個巨大的問題。我們這一代作家都有這樣一個心理趨勢,我們關注社會,關注生活在其中的人,我們總是在小處看,在大處想。
Q
你是什麽時候開始寫作的,通過寫作你發現或者說悟到了什麽?
畢飛宇:何時開始寫作,這個說來話長,首先要看是什麽意義上的寫作。如果從產生寫作的願望算起,我七八歲就開始寫作了。我父母是教師,那時候我最愛乾的事情就是拿著鐵釘在操場和土基牆上胡亂地書寫。我書寫的願望是那樣地蓬勃,許多字都不會寫,村子裡卻到處都是我的字,當然還有句子,具體的內容記不得了,隻記得我受到了父親的訓斥,他擔心我寫出什麽不好的東西。我的父親是因為語言倒霉的,所以,他對我的語言表達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覺。可我的書寫像野草一樣,他哪裡攔得住?到了高中我就開始投稿,當然,一個字也沒有發表過。我的退稿被語文老師發現了,他告訴了我父親。那時我就發現要寫作很難,寫作其實就是抗爭。1983年,我的寫作終於有了陽光——我開始寫詩,成了揚州師范學院的校園詩人,帶著一幫師兄和師姐,我們辦詩社,還出詩刊,刊物的名字叫《流螢》,這份刊物到現在都在。真正意義上的寫作,也就是想做小說家的寫作,始於1987年的秋天,那時候我大學畢業了,知道自己成不了詩人,想踏踏實實地做一個小說家。
寫作對我的幫助是無與倫比的。首先是改變了對語言的認知。我所接受的教育是這樣的——語言是工具。然而寫作讓我知道了語言不是工具,它是本質。所謂對自己的精神負責,就是對自己的語言負責,反過來也一樣。一個小說家擁有語言,就是擁有生命。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說我在使用語言寫作,不如說寫作是在捍衛我所使用的語言。
Q
在《哺乳期的女人》前後你寫了《是誰在深夜說話》《雨天的棉花糖》,2000年之後寫出了影響很大的《青衣》,隨後又寫出了《玉米》《玉秀》《玉秧》三個分量很重的中篇,請問這些小說有沒有什麽內在的關聯?或者說,你心中有沒有一個創作的主題,你一直著力在寫的是什麽?
畢飛宇:寫作的人其實也混沌,他就那麽懵懵懂懂地,僅僅依靠他近乎偏執的愛,他九死不悔的同情心,加上他未必招人喜愛的固執,一點一點往下寫。時間久了,回頭一看,他其實並不混沌,也不傻,他只是以己度人——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和體諒別人。他是怎樣對待自己的,他就怎樣對待作品中的人物。你可以說他很自私,很自戀,其實,他的心也開放,關鍵是柔軟。他希望自己多一點快樂,少一點疼痛,就因為這個基本的願望,他成了一個有生活態度的人:希望別人多一點快樂,少一點疼痛。他講理,他希望有地方講理,實在不行,他就沉默,一個人沉思。我想說,一個作家不說話了,不是因為他被改變了,是因為他沒變。
Q
你的小說屢屢獲獎,從《哺乳期的女人》到《玉米》再到《推拿》,你的長中短篇小說分別獲得魯迅文學獎和茅盾文學獎,你經歷了怎樣的探索和寫作軌跡?
畢飛宇:我的寫作歷史沒有任何特別之處,先寫短篇,再寫中篇,然後寫長篇。這裡頭其實並沒有次序上的邏輯,一個人完全可以先寫長篇,然後再寫短篇,專門寫一種也可以。小說的短、中、長之間也不存在基礎性的關係,我們可以說的只有擅長。我有些貪婪,希望自己更全面一些,我的短篇、中篇和長篇都有拿得出手的東西,這個可以自豪一下。因為實踐的廣泛性,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短篇、中篇和長篇不是一個篇幅的問題,不是同一個氣球被吹成了不同的體量。它們是三個不同的東西,它們對同一個作家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你必須滿足不同的要求才能把這三種東西完成好。把長、中、短篇小說寫好,其中的艱難性是不同的。
Q
你的長篇小說《推拿》獲得了茅盾文學獎,這是中國文學最高也是最大的獎項,你寫了一個盲人的世界,這顯然不僅僅是一個題材的選擇,是什麽觸動你寫一本關於盲人的生活與情感的書?

畢飛宇:《推拿》其實不在我的寫作計劃裡頭,當然,所謂的寫作計劃本身就有點可疑。寫作有時候是約會,有時候是邂逅。無論如何,邂逅的強度與亢奮都是約會不可比擬的。
《推拿》裡頭有三類人,一類在地上,是農民性的,主人公王大夫就是這樣。這一類人他們有一種卑微而務實的生活理想,這往往也是盲人生活的終極理想,他們想和健全人一樣,自食其力,能這樣就是最大的成功,這樣的成功有一個標誌,那就是進入主流社會;另一類在天上,小馬就是這樣。因為生理上的困擾,他們對生活的理解大多帶有冥想的性質,他們在骨子裡更接近詩人或哲學家,他們所堅持的信念其實就是假象,他們熱衷於假象,甚至沉迷於假象;還有一類就是沙複明這樣的,說不好他們是在地上還是在天上,他們的腳踩在地上,腦袋卻在雲端裡頭。我想說的是,哪一種類型其實都不容易,即使是我們這些所謂的健全人,其實也都不容易。
我在寫《推拿》的時候非常著重一樣東西,那就是愛。愛是脆弱的,在這個問題上我承認受到了莎士比亞的啟發。莎士比亞非常重視人類的愛,但是,他悲觀。他所呈現出來的愛有兩種極為動人的形態:一種是羅密歐式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很愛,他們的愛最終被外部的力量埋葬了,具體說,就是家族的或社會的仇恨。另一種則是奧賽羅式的,奧賽羅與苔絲狄蒙娜也很愛,因為懷疑和忌妒,最終,不是外部的,而是他們內心的負面力量摧毀了自己的愛。我癡迷於悲劇,我也是那種具有悲觀傾向的寫作者。
想起在看婁燁改編《推拿》電影試映片的時候,我看到一個鏡頭:恢復了視力的小馬提著菜籃子回到他破爛不堪的住處,天很冷,他的女友小蠻正在那裡洗頭,熱氣騰騰的。小馬站在過道裡,就這樣看著自己的女人,小蠻知道他在看,卻以為他看不見,小馬則乾脆閉上了眼睛,他閉著眼睛微笑。這個畫面我的小說裡頭是沒有的,但是,這個鏡頭讓我確信了愛的存在,它破爛、困厄、錯位、沒有被精確地認知,但它就是在那兒,這個太動人了。我忍不住告訴婁燁,我希望電影用這個鏡頭做結尾——怎麽拍電影是他的事,我其實是無權干涉的。感謝婁燁聽了我的建議。這個鏡頭打動了無數的人,也為婁燁贏得了無窮多的掌聲。

Q
你認為小說最動人的力量是什麽?或者說,一個小說直指人心的東西是什麽?
畢飛宇:當然是真,真實的真,真理的真。小說的終極價值就在求真,這是文學的巨集觀要求。對一個小說家來說,表現真實就是追求真理。
Q
寫作中你有沒有那些“靈感”和“頓悟”的時刻?
畢飛宇:這是有的。我始終覺得小說人物和作者之間存在一個反哺的關係。有時候,是作者哺育了小說人物,有時候,是小說人物哺育了作者。小說人物的命運有時候會給作家帶來頓悟,作家會在這樣的過程當中修正自己,這樣的過程不會輕鬆,你會懷疑自己,尤其會懷疑自己所受到的教育。我的第一次懷疑來自《雨天的棉花糖》,這個小說的影響力並不大,但是,它給我的影響是深刻而久遠的。它讓我確立了最基本的人道主義立場。那是1992年,我還是一個28歲的年輕人,在處理小說人物也就是“紅豆”的命運。它不只是“故事的走向”那麽簡單,它不是“編故事”,它是有潛台詞的——你到底希望生活在怎樣的生命語境裡頭。這是文學,或者說嚴肅文學必須面對的題中之義。這篇小說我寫了兩遍,第一稿和第二稿的區別是巨大的。
另一個就是“玉秀”,《玉米》系列中的那個小說人物,和《雨天的棉花糖》一樣,這部小說我也是寫了兩遍,第一稿,玉秀死了,第二稿,玉秀活下來了。活下來的玉秀給了我極大的幫助,它提升了我對小說的認知——一個作家的權力究竟有多大?當作家決定小說人物死去的時候,小說人物有沒有求生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說,作者也是小說裡的人物,他參與了小說內部的社會生活,然而,他不是主宰,沒有人可以主宰生活。


Q
你是如何構建自己的小說世界的?請談談你的生活積累和寫作資源。
畢飛宇:中國的小說有現實主義的傳統,我自己也可以說是在這個基礎上構建自己的小說世界。在我們談論現實主義的時候,有一個靈魂性的東西不應當被忽視,那就是作家的現實情懷。我們必須承認,現實主義是一回事,現實情懷則是另外的一回事。所謂的現實情懷就是求真。在我看來,一個作家,最可貴的東西就是現實情懷,他選擇什麽樣的主義,換句話說,他擅長什麽樣的美學表達,反而是次要的。卡夫卡也好,加繆也好,和傳統意義上的現實主義相去甚遠,但是,他們的作品裡頭有一種最大的真實,也就是真實的人類處境,真實到何種程度?我們做讀者的都能夠身臨其境,都能夠設身處地。我想說,他們都是具備了現實情懷的作家。現實情懷的具體體現在哪裡?還是加繆說得好,那就是“緊緊盯著”,不是盯著看的意思,他說的是緊盯現實。
我敬仰有現實情懷的作家,同樣要求和希望自己是一個具備了現實情懷的人,有沒有做到呢?我不做結論,但是,我注重自己的現實情懷,這個是真的。

為什麽要強調這個呢?還是和小說的功能有關。小說的功能無非就是兩個,第一,美學呈現,第二,認知價值。就認知價值而言,你辛辛苦苦寫了一大堆的作品,後來的讀者得到的只是一大串的謊言,這樣的東西寫它幹什麽?謊言和真實高度相似,這是謊言最為蠱惑人心的地方,但是,謊言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它扛不過時間,時間一到,它會暴斃。為了作品能夠活下去,一個作家應當重視現實情懷。
我本人的生活經歷基本是從校園到校園,沒有太多的涉世經驗,我可以說是書齋裡的人,是在虛擬世界裡成長起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寫作促進了我的生長和成熟。
Q
哪些作家或作品對你產生過很大的影響?並使你找到了自己的小說風格?
畢飛宇:我是在上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我在思想上主要繼承的還是啟蒙主義的那一路。在呈現啟蒙主義思想方面,我認為做得最好、最為完整的,反而是浪漫主義時代的雨果。在小說的表現手段方面,學得比較多的是馬爾克斯和博爾赫斯,當然,我也在提醒自己,不要過分陷入其中。
到了90年代後期,也就是35歲左右,我有了很大的變化,我說的是表現形式方面。我不虛榮了,不虛榮就不會趕時髦,這個“向後轉走”是決定性的,福樓拜和托爾斯泰的價值在我的身上體現出來了,在當時,這屬於“落伍”的行為,甚至有點不可思議。還有一件事是想不到的,我突然愛上了《紅樓夢》。回過頭來看,是“向後轉走”挽救了我,也成就了我。讀者開始關注我,就是在這個時候。
Q
你寫作中的華彩時刻是什麽樣的?
畢飛宇:個人覺得比較精彩的故事發生在我寫《玉秀》的日子。我有一個習慣,每當來到書房的電腦面前,會把上衣脫下來,掛在椅子的靠背上。剛開始寫的那幾天,我清楚地記得掛的是夾克,突然有一天,發現掛上去的是羽絨服,我嚇了一跳,手裡的夾克怎麽變成了羽絨服呢?一想,原來好幾個月過去了,我竟然一點都不知道。我站在椅子後面,幸福了很久,也傷感了很久,用今天的話來說,時間都去哪兒了?所幸的是小說完成了。
另一件事情就是寫《平原》,寫了三年七個月,終於,我把稿子發出去了,高興得不得了,整個人都輕了,都飄了起來。幾天之後,完全出於本能,我又來到了電腦前,打開電腦打算接著寫,可突然想起來了,稿子已經寄出去了,《平原》已經和我徹底無關了,我的眼淚一下子就衝了出來,心裡難受極了。我沒有女兒,但那個瞬間我體會到了父親嫁女兒的心情。
Q
寫作改變了你什麽?
畢飛宇:要說有什麽改變,似乎也沒有,沒有覺得我和過去有什麽顯著的變化。不過變化肯定也是有的,是我自己體會出來的一些東西。比方說,耐心。寫作需要耐心,寫作也培養耐心,因為寫作的緣故,我現在非常有耐心。另一個就是提升了語言的辨別能力,每一個字落下來都要求自己做到精準。
Q
你在你的《小說課》中說:“好作品的價值在激勵想象,在激勵認知。僅僅從這個意義上說,傑出的文本是大於作家的。”你怎麽想起要寫一本分析和講解小說的書?

畢飛宇:說起《小說課》,我首先要說丁帆教授,他是我們南京大學的前輩了。他一直有一個巨集大的計劃,就是出一套書系,有關閱讀的各個領域。
我的《小說課》隻講了一講,丁帆教授就給我打來了電話,他讓我把最終的講稿交給他,後來就有了人文社的《大家讀大家》這個系列。我認為《小說課》的價值在於,它填補了我們的一個空白,那就是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縫隙。做理論的人往往自己不實踐,做實踐的往往不重視理論。因為命運的安排,我在一把年紀的時候走到了這個縫隙的中間,就在這個縫隙裡頭吐了一點絲——《小說課》就是一個寫作多年的人具備了一點理論素養,在實踐和理論之間結了一個蜘蛛網,這是一個比較符合實際的說法。
Q
你現在的身份除了是作家還是南京大學文學院的教授,寫作之外你是否承擔教學工作?你還承擔哪些社會工作?
畢飛宇:我在南京大學沒有教學任務,所做的事情切口很小,就是帶領年輕的大學生讀小說,閱讀小說可以提升一個人對世界的認知。
以前我一心寫作幾乎不參加社會活動,但是,這幾年做得比較多一些。這是有緣故的,我的故鄉興化給我建了一個工作室,很大的一個院子,我的兩位高中同學找到我,商量在那裡建“小說沙龍”和圖書館——就成了現在的“廣場書屋”。
“小說沙龍”一個季度做一次討論,和南京的《雨花》雜誌合作,我也參加。“廣場書屋”每個周末都對外開放。興化的中小學老師來做義工,在這裡熱起來的不只是文學,還有各個門類的義工。
對我來說文學就是一個夢,所以我對學生說,不要帶著目的去做夢,而是要懷著熱愛和情懷去投身文學。
本文轉載自《瞭望》,若您讀後有所收獲,歡迎關注雅理讀書!
編輯 | 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