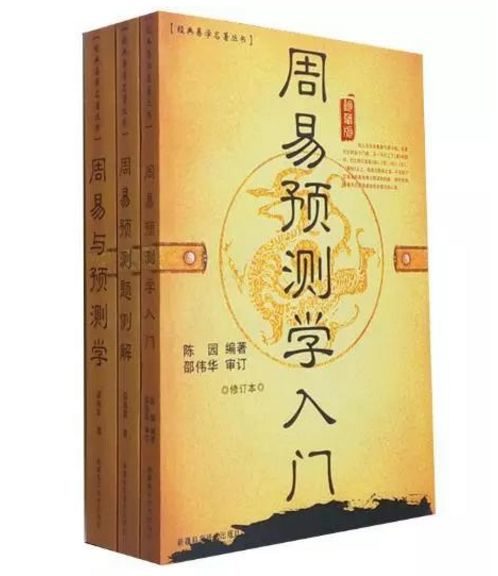(本文首發於2019年5月16日《南方周末》)
“四大奇書”其實是比照“四書”來命名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四大正書”,《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則是“四大奇書”,“正書”代表的是大傳統,“奇書”代表的是小傳統。
考察中國文化的歷史進程可以有多種角度,比如,從國家體制的演變著眼,可以將西周至1911年間的中國文化劃分為封建時代的文化、帝製時代的文化;從文化的載體著眼,又可以分為以簡帛為書寫工具的時代(東漢以前)、以紙為書寫工具的時代(東漢末至北宋)、活字印刷時代(南宋至清中葉)、機器印刷時代(清末以降);從社會經濟形態和國家管理形態著眼,還可以分為上古文化、中古文化、近古文化、近代文化;從“哲學的突破”著眼,則特別關注中國思想史上幾個重大的變動時代,如春秋戰國之際、漢晉之際、唐宋之際、明清之際;這幾種不同的角度之間,有重合之處,也有歧異之處,各有其闡釋優勢,又各有其闡釋盲點,因而可以互補而不能相互取代。
一、從五經到四書
從世代更替的角度選擇中國文化經典,其首選無疑是“五經”“四書”和“四大名著”,而“四大奇書”則是“四大名著”的雛形。
自西漢至盛唐,經典的數目雖然不斷增加,有“七經”“九經”“十二經”之稱,但延續的仍是以“五經”為核心的經典體系。這一體系從中唐起才逐漸被以“四書”為主的經典體系所取代。這並不是說“五經”就不重要了,而是說“四書”在思想文化上的影響力更大,“四書”取代“五經”成為意識形態的重中之重。西漢大儒董仲舒教人以五經六藝為本,隋代大儒王通著《續六經》授徒講學,唐太宗命孔穎達修《五經正義》,所看重的首先是“五經”。而中唐韓愈等人已注意到《孟子》《中庸》《大學》的重要性,發宋代理學之端,至宋代大儒如二程、張載、朱熹、陸九淵等人,雖然學術主張不盡相同,但在論為學次第和內容時都有相似的見解,那就是對“四書”特別重視。誠如呂思勉所言:“唐中葉以後新開之文化,固與宋當畫為一期者也。”
“四書”取代“五經”在很大程度上與佛學衝擊、挑戰儒學影響力相關。相較儒學,佛學的優長在於其心性之學。自魏晉南北朝時代,佛學由波若本體論向涅槃心性論轉化,佛學逐漸找到其特色議題,涅槃佛性成為佛學主流話語。對心性之學的縱深開拓,使得佛學漸脫玄學苑囿,至隋唐以降而大張其道,士庶上下的思想疆域多為佛學所佔據。
為了和佛學抗衡,複興儒家的文化傳統,必須對過去的儒家經典重新加以詮釋,即回溯儒學原典中的心性之說,重建儒學心性話語。韓愈重視《孟子》《中庸》,發揚孟子的“性善”理論而分性之品次,李翱也標舉《大學》《中庸》,在《複性書》中分辨情性。這一體系在宋代得到完善,依托“四書”構建起一套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程朱的貢獻尤其重要。二程“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這個體系在宋學集大成者朱熹那裡得到了完成。他構築起以“理一分殊”為核心的本體論體系,“理”是貫穿其中的具有本體色彩的概念,它是宇宙萬物生成之源,又蘊含在一切事物之中。朱子通過重新詮釋儒家經典,構築起以“四書”為核心的經典體系。
“五經”經典地位的確立,標誌著百家爭鳴的時代落幕,文化史上的中古時代正式開始。中國歷史上的帝製時代始於秦始皇登基,帝製時代的前期常常被稱為“中古時代”,其主體部分為秦漢至唐末。但就文化性質而言,漢武帝時期至盛唐才是典型的中古時代,其特徵是,以“五經”為核心的儒學在帝國的政治秩序、文化秩序中居於主導地位。
“四書”經典地位的確立,標誌著中古時代的落幕,文化史上的近古時代正式開始。帝製時代的後期常常被稱為“近古時代”,其主體部分是宋元明清。但就文化性質而言,唐中葉至明中葉才是典型的近古時代,其特徵是,以“四書”為核心的理學在帝國的政治秩序、文化秩序中佔據主導地位。

二、四大奇書的崛起
“四大奇書”的崛起是中國傳統文化開始向現代轉型的標誌,而“四大名著”經典地位的確立則標誌著一個新的文化傳統已日漸清晰地呈現在世人之前,這個新的文化傳統是西學與中學相互衝突和融匯的產物。
“四大奇書”是明代四部長篇章回小說《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的合稱。明末天啟、崇禎年間,這四部書就常被論小說者並列,至清初,李漁更明確提出了“四大奇書”的概念。他在為兩衡堂刊本《三國志演義》所作的序中說:“嘗聞吳郡馮子猶賞稱宇內四大奇書,曰:《三國》《水滸》《西遊記》及《金瓶梅》四種。余亦喜其賞稱為近似。”自李漁之後,“四大奇書”成為論小說者的常用術語。明末清初“四大奇書”概念的出現,蘊含著特定的文化深意——因為,“四大奇書”其實是比照“四書”來命名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四大正書”,《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則是“四大奇書”,“正書”代表的是大傳統,“奇書”代表的是小傳統。
“四大奇書”興起的晚明,正是以“四書”為核心的理學權威遭遇危機的時期。明代文化發展的一大歷史轉折是明中後期程朱理學走向衰頹而心學大盛。自陳白沙開啟明代心學,其後分為湛若水、王守仁兩派,尤其是王守仁所開創的陽明心學,為其弟子所發揚光大。泰州學派認為由於理存在於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堯舜”,即使是不讀書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為聖人。陽明心學以講會的形式傳播到民間,影響廣泛,盛極一時。清人評論說:“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複幾人矣。”一方面,士人對程朱理學和四書的公開批評時有所見,由袁宏道論“宋時講理學者多腐”,馮夢龍詆理學宗師程頤為“迂腐”,到李贄譏“《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可見一斑。另一方面,儒家經典的莊嚴性及其所倡導的道德觀念的嚴肅性也面臨危機,一個例子就是遊戲八股文的興起。八股文本是“代聖賢立言”的文體,卻被寫成了“代才子佳人立言”的戲謔文章,《西廂》製藝等是其代表。
大傳統中的“經典”在人們心目中的實際權威遭遇危機,小說戲曲等的文化影響則迅速擴大。大體說來,明代文壇在中葉之前以雅文學為主體,台閣體居於雅文學的核心位置。明中葉以降,雅、俗文學開始進入並駕齊驅的狀態,一邊是前後七子和唐宋派的興盛,另一邊則是《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的刊行和傳奇
劇演出的蓬勃景象,至萬歷年間,俗文學的發展進入鼎盛狀態。文化人不僅是這些作品閱讀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對小說經典地位的生成起到關鍵作用。除了參與對作品的修改、潤飾以提升其文學品質,小說戲曲評點的勃興也是此時值得注意的文學現象。李贄、袁宏道、湯顯祖、金聖歎等一批文人先後參與其中。李贄聲言漢以來“宇宙間有五大部文章”,分別是漢代的《史記》、唐代杜甫集、宋代蘇軾集、元施耐庵《水滸傳》、明李夢陽集。袁宏道在《觴政》中視《西廂》《琵琶》《水滸傳》《金瓶梅》為“逸典”。他表示,區分酒肉俗士與文人雅士的標準就在於是否熟讀“逸典”。金聖歎編選“六才子書”,突破文體藩籬與雅俗觀念,將《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西廂》並列稱賞。
“四大奇書”之“奇”,是與“四書”之“正”相對而言的。屠隆論及晚明的文化氛圍時,說當時的一般讀書人“聞一道德方正之事,則以為無味而置之不道;聞以淫縱破義之事,則投袂而起,喜談傳誦而不已。”“四書”所代表的主流文化,其內容重心是關乎國家政教的“宏大敘事”,其精神向度是歸於“中庸”之正。“四書”中不僅包括傳統儒家的社會政治思想,諸如《論語》中的德治、《孟子》中的仁政、民本思想等等,也包含大量的關於儒家道德倫理的教訓。而“四大奇書”關注的顯然是有關世俗情感、道德經驗的民間生活,其追求的是與眾不同的“奇”氣,“把一本書列入奇書的範疇,就意味著它跟原來的文化格局不一樣,創造了一種奇峰突起、奇氣盎然的景觀”。
清初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二說: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氣決裂潰敗也。
劉獻廷的議論透露出三個重要信息:一是主張要在小傳統的基礎上創造新的文化經典,二是確認小說戲曲才能代表他所處的時代的文化,三是強調新的文化經典的確立要“原本人情”。“原本人情”是一個重要的提法,也是對四大奇書文化特徵的鮮明揭示。在中國文化史上,“原本人情”的指嚮往往是質疑一部分失去了活力的傳統,以建立新的更富朝氣的傳統。阮籍說“禮豈為我輩設”,嵇康自稱“不喜俗人”“情意傲散”“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劉諧呼孔子為“仲尼兄”,李贄為之喝彩,凡此種種,都是不滿於既有經典格局的表示。中國人的生活在不斷變化,中國文化在不斷變化,確立新的文化經典勢在必行。
三、四大名著經典地位的確立
真正將四大章回小說置於現代學術研究的範圍並確立其文學史經典地位的,是胡適、魯迅等人。胡適在《白話文學史》的“引子”中談到,白話文學的“種子”在三四百年前的《水滸》《三國》《西遊》《金瓶梅》,一百四五十年前的《儒林外史》《紅樓夢》那裡就埋下了……《水滸》《紅樓夢》……已經在社會上養成了白話文學的信用了”,對幾部白話小說的文學史貢獻和地位點名表彰,這對於四大章回小說被納入文學史經典序列自然意義非凡。胡適的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不僅廓清了四大章回小說的一些疑難,諸如情節演進、作者生平及版本情況等,更由此開創了一種具有典範意義的研究方法。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則開國人著小說史之先河。魯迅以其小說家兼學者的敏銳藝術感受力和學術洞察力,對明清章回小說進行了流派、類型的劃分與研究,不僅是對一段歷史時期小說藝術的總結,而且揭示了不同小說創作所獨具的藝術品質與文化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學術界仍然是在文學範圍內談論四大名著的經典地位,而在1949年後的當代中國,“四大名著”的表述逐漸取代了“四大小說名著”。“小說”這一定語的消失是個意味深長的象徵,它表明了這樣的事實:在當代中國的文化語境中,這四部小說的經典意義早已超越了文學的範疇,而具有了融合政治、思想、學術等多元要素、影響全社會的文化意義。這種經典地位的確立,當然離不開當代的出版環境、政治氣候以及國民教育的影響,而更深刻的原因在於,它在建設現代中國文化的歷程中具有無可替代的功能。
說到“無可替代”,這絕對不是誇張的形容。如夏志清在《中國古典小說史論》中所說,“的確,從過去四十年間學術界在這幾本書上所下的驚人功夫來看,似乎就是它們構成了中國小說的傳統。現在,不僅中國學者,就連西方的漢學家,對有關它們的作者以及版本方面的最細微的問題,也都以極為嚴肅的態度來探討”。這些事實本身構成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文化現象——在現代中國社會,即使人生理念不同,人們仍然一致重視四大名著的經典地位,這說明四大名著在現代中國文化建設中的功能和作用確實得到了普遍認可,而並非某種特殊的政治原因使然。
正如西方民族國家意識的萌生,伴隨的是各國民族文學的興起,意大利有但丁、英國有喬叟,中國也要在西學東漸時代重建民族文學與文化。四大名著之所以成為新文化建設的重要資源,就因為其本身包含著與現代文化相契合的思想因子,承載著人類社會關於公平正義的理想。新文化人敏銳地意識到這一點,將現代價值觀念如平等、自由等新思想融入到對四大名著的闡釋中,將《水滸》《紅樓》等視為“社會小說”,乃至“政治小說”“哲學小說”“道德小說”,在《水滸傳》中讀出梁山好漢的“人人平等”,在《紅樓夢》中讀出“專製君主之威”“男女婚姻之不自由”甚至“中國社會數千年來退化之跡”。經由這種闡釋,新文化人成功地將四大名著建構為蘊含現代文化的“傳統”經典。由此可見,我們對“傳統”的塑造和重構,乃是源於認識和建設“現代”的需要,我們對經典的選擇和確認,乃是因為它適應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需要。
博爾赫斯說,“經典是一個民族或幾個民族長期以來決定閱讀的書籍,是世世代代的人出於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熱情和神秘的忠誠閱讀的書”。“經典”總是在不同文化語境中被建構,是重新發掘傳統文化意義與價值的文本載體。現代中國社會對四大名著經典地位的建構,是在20世紀中國社會向現代轉型的背景中進行的,對四大名著的闡釋,是以建設中國社會文化的“現代性”為價值訴求的,而這種“現代性”在很長時間內又是以西方近代以來的若乾理念為準的,比如以科學、理性為核心精神,以自由、民主為政治理念、以進化論和線性史觀為發展觀的一套關於“現代性”的敘事。這對於發掘四大名著的現代價值是有意義的,但也不可否認,因為過於切近今人的理論命題,有可能導致對古人用心缺少“了解之同情”,以致對其所蘊含的文化傳統失去親切之感,以致流於對經典的“誤讀”。在全球化時代多元文化價值得到重視的今天,我們對四大名著的闡釋,有必要借鑒漢人的五經闡釋和宋人的四書闡釋,以期建立一個涵容西方文化精粹而又以中國人文理想為基點的新的經典體系。
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陳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