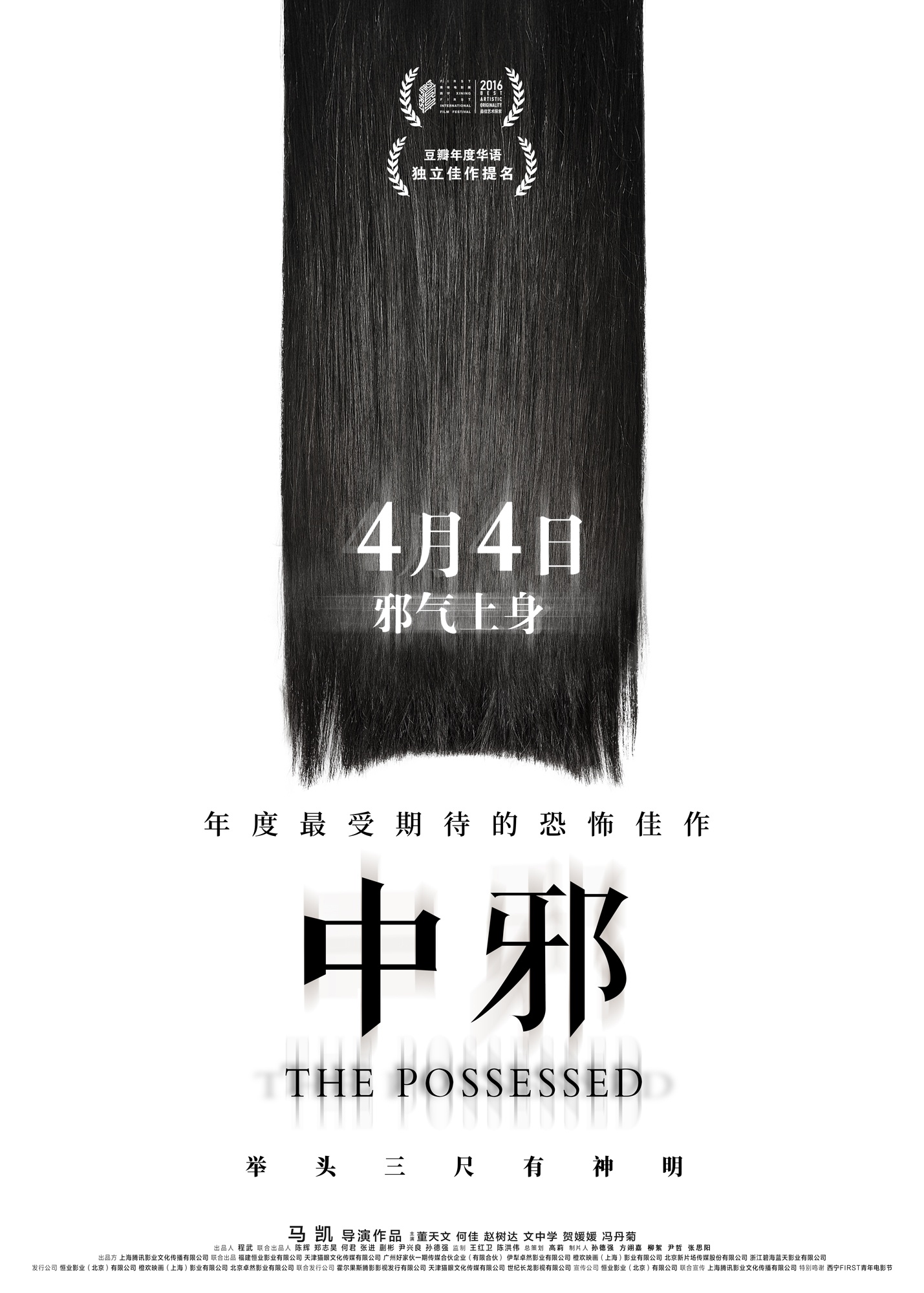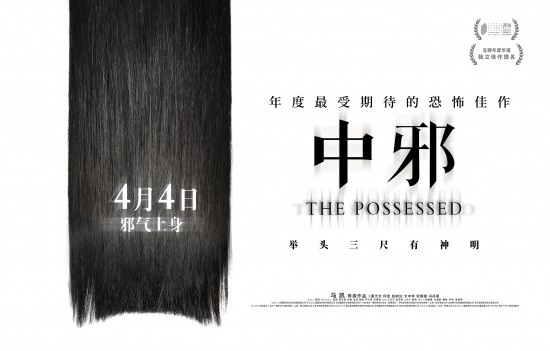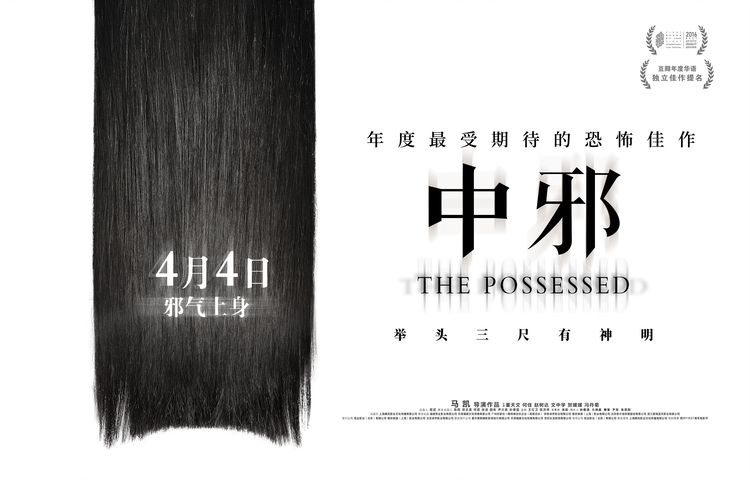2019年,周軼君導演帶著紀錄片作品《他鄉的童年》來到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他鄉的童年》中,她走訪日本、芬蘭、以色列和英國,最後回到中國,用影像記錄了一趟關於教育哲學的思考之旅,帶領觀眾從不同角度感受不同的教育方式。開播至今近一年,《他鄉的童年》在豆瓣仍保持著9.0的高分,引發著大家對教育和社會的熱烈討論。
周軼君不僅是一名導演,她也曾是新華社駐巴以地區的戰地風雲記者和鳳凰衛視的資深國際記者,長年奔波在國際熱點地區,經歷了尼泊爾改製,朝韓危機,戰後阿富汗、伊拉克重建等一系列變革。隨筆《在埃及數駱駝》被編進了九年義務教育六年級第二學期課本,在國內,她還是《圓桌派》的常駐嘉賓。
今天,周軼君作為GZDOC2020金紅棉初評選片人,和我們聊了聊她的近況以及她對初評影片的看法。

周軼君
“所以然工作室”創辦人。資深國際記者、作家、紀錄片導演、主持人。紀錄片作品《他鄉的童年》入圍2019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金紅棉終評,並獲得優秀新媒體紀錄片提名榮譽。
Q
A
GZDOC
中國(廣州)
國際紀錄片節
周軼君
GZDOC2020
金紅棉初評選片人
“ journalism只是在不同的載體中流動”
GZDOC:2020年因為疫情,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您是否有帶來什麽影響?
周軼君:今年一方面我跟大家一樣,有相當多的時間被困在家裡。另外一方面我還在拍片,疫情期間拍片是相當困難的,現在去哪裡都不方便。其他一些事情可能因為個人的才華和靈感,坐在家裡就能做,但紀錄片是不可能的。我到現在為止已經隔離過三次了,可能接下來還要去隔離。
疫情這個消息傳來以後,一開始確實會有一種很不真實的感覺。每天一醒來,就會在想這件事是真的嗎?怎麽這世界就變成這個樣子了,太突然了。我覺得我們都被徹底地改變了。
《他鄉的童年》預告片
GZDOC:繼第一部紀錄片作品《他鄉的童年》後,您現在也在拍攝新的紀錄片。您其實也是非常出色的主持人和記者,為什麽會選擇轉型做紀錄片導演?
周軼君:我最早做國際報導、新聞,整個Journalism(新聞業)在今天的世界已經引起了非常大的變化。那麽媒體人的表達方式以及跟社交媒體的競爭,可能都會面臨跟我當初做記者時完全不同的狀況,遭遇從來沒有過的挑戰。
雖然說媒體的形式,比如傳統的報紙電視可能在衰落和被改變。但是journalism的核心,調查、分析和揭露被人忽視的事實,實際上並沒有改變。只是可能轉移到了紀錄片,甚至電影,像很多電影也標注“based on true stories(基於真實故事改編)”。所以如果把 journalism當做一種媒體形式,那它是在變化,但是當做一種手藝來講,它其實並沒有很大的變化,只是在不同的載體裡面流動。
儘管我自己仍然是很迷戀文字,但另外一方面我發現自己也很喜歡畫面和故事的表述,而不僅僅是一種理性的概括,所以對我來說好像是很自然被吸引到另外一條路上去了,而不是自己很明確地在主觀改變。
“拍紀錄片是一件我想到就會高興的事”
GZDOC:您在這麽多身份之間轉變,未來還可能會嘗試其他領域嗎?
周軼君:我其實覺得不是我選擇了轉變,是轉變選擇了我。我朋友就開玩笑說你現在叫“斜杠中年”。我也希望能夠在某一個領域裡安定下來,我很羨慕那些在一個領域乾一輩子,深入把這件事情做到最精最好的人。我也有想過自己為什麽不能定下來,這可能是我的弱點。將來是否會嘗試新領域我自己也不清楚,但目前拍紀錄片是一件我想到就會高興的事,無論中間經歷了多少苦難和非常崩潰的時刻,但最終看到影像連貫成一個故事的時候,還是會覺得很欣慰。所以我會繼續做,但做不做得好,能做到什麽程度,會不會一直做我也不知道。
GZDOC:《他鄉的童年》拍完後您最大的收獲是什麽?
周軼君:我感受到了紀錄片的影響力和它能夠持續跟人們交流的程度。像我過去做報導,關心的是政治性比較強的國際話題,相對來說比較硬。那麽《他鄉的童年》雖然也講了很多外國的事情,但是引起中國家長的共鳴,肯定是遠遠超過我之前的任何報導。而且片子播出至今,我還在不斷地收到很多的反饋,是讓我覺得挺幸福的事。我做的事情可以在國內引起大家的共鳴,甚至可能促成一些改變,跟過去的國際報導隔岸觀火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我也一直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僅僅當作一部教育片來看,它其實包括我們每一個人的成長。教育這個話題實際上並不僅是養娃,它更多的是關於我們希望將來生活在一個什麽樣的社會裡,我希望能夠在這個方面引發大家更多的思考。
可能有人覺得外國的教育不符合中國國情,可是從人性的角度來說,很多東西是差不多的。一個人的成長和他的教育經歷、社會文化都分不開,這件事情幾乎每個社會中都一樣。所以我覺得還是有一些基本的東西是可以去尋找。
在我看來質疑是一件好事。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看到,過去的東西作用在每個人自己身上都是不一樣的。每個人看待另外一個社會的眼光都是不同的,我想用這部影片為大家提供一面鏡子或者說一個窗口。
“疫情下,教育發生大變化”
GZDOC:經歷過疫情之後,您對於教育有什麽新想法嗎?
周軼君:我現在想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將來如果沒有學校了,都上網課怎麽辦?如果疫苗的研發和有效推行需要很多年的時間,網課教育下的娃長大了,是否會變得跟我們很不一樣?我去年在拍《他鄉的童年》時也在考慮這個問題,將來的社會跟現在不一樣,下一代他們所面臨的職業需求和社會環境也都不一樣,但沒想到這個變化來得這麽快,今年可能就要考慮這個問題了,疫情實在讓人太措手不及。
GZDOC:《他鄉的童年》是和優酷合作的,廣受關注,豆瓣還有9.0以上的評分,取得了非常好的反響。但是也有很多的紀錄片、好的作品,他們不一定能被觀眾們看到。
周軼君:我今年作為廣州紀錄片節的初評選片人,看的片子裡不乏優秀的作品,但我也注意到,有些作品即使對準不同的國家和社會,但關注的題材和議題是比較相近的。比如說一個環保的大題目下面會有千千萬萬的故事,那觀眾可能會覺得自己看過類似題材的作品了,真正傳達到閱聽人那的衝擊力就會小很多。雖然說這些領域的故事都很重要,一方面我認為需要講,但另外一方面確實是我們有沒有更新的東西來講。
我也在想,很多時候紀錄片都是走影展,那麽對於普通觀眾來說,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搶到票,或者像現在疫情的關係,想看到這些片子其實是挺困難的。現在很多片也在不同的流媒體平台上投放資源,但資源分散,每個平台都需要交費。我希望紀錄片將來能被觀眾看到的渠道更廣泛一些,讓大家把紀錄片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紀錄片是能夠讓我們感受到生活的層次和事物多樣性的。
GZDOC:那您跟優酷合作的經驗,有什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的呢?
周軼君:我拍攝《他鄉的童年》第一季的時候,國際拍攝是一個困難,另外一個就是資金。我覺得蠻幸運的就是優酷從一開始就跟我合作,大家一起分擔這樣一個風險。不是每個平台,在一開始沒有看到結果的時候都願意像這樣去冒險的,所以我很感謝優酷。
我們本來今年要談第二季的,但疫情以來,跨國拍攝幾乎成了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們也在等待時機,如果情況適合,我們還是會繼續做。第二季的話我相信會很不同,因為我們在新的疫情背景下,談論的教育會變得非常不一樣。
“紀錄片本身就是去看見被忽視的”
GZDOC:那您這次以選片人的身份參與金紅棉的初評環節,在您所看到的作品裡,最喜歡哪幾部,為什麽呢?
周軼君:到目前為止,我最喜歡的一部是烏克蘭的《The Earth Is Blue As an Orange》,它這個名字很好玩,就是《地球是藍色的就像個橙子》,這個片非常吸引人。第一個我印象最深刻的點是他對於戰爭的描繪特別節製。他拍攝一個處於頓巴斯的家庭。俄羅斯佔領克裡米亞以後,在烏克蘭老工業區那邊經常會發生一些軍事衝突。我自己那時候去過,所以我對那個地方印象很深刻。

《地球是藍色的就像個橙子》海報
但我去過的這件事情並不影響我看這個紀錄片。這部片中戰爭衝突對他來說只是個背景,影片絕大部分時間都沒有直接的戰爭場面,處在一種非常平靜的氛圍中。影片裡的人也在拍一部電影,直到最後他們自己的片放映的時候,你才看到炮彈掉下來,他們在奔跑,房子在晃動,所以是到最後才讓觀眾意識到,原來他們經歷了這些。
《地球是藍色的就像個橙子》預告片
導演這麽處理真的很節製,表現力和衝擊力不但絲毫沒有減少,反而讓人覺得驚歎。而且我相信在當時的條件下拍攝,應該不會有特別好的硬體設備,但所有畫面表達都很到位。再加上裡面的音樂都是這一家人自己玩的樂器,當地人就是這麽多才多藝的。我覺得整個畫面非常自然,非常溫馨,非常有衝擊力。
初評還有一部《This is not a movie》講中東的,拍Robert Fisk,好像傳記一樣。說實話看前半段的時候,我有點失望,導演前半段非常肯定Robert Fisk,Robert Fisk自身也很肯定自己做的事。但就像我們提過Journalism這個領域的變化很多,為什麽導演和被攝者傳達出來的都是絕無困惑?
《這不是一部電影》預告片
但到了後半段,導演跟隨這位記者去做了一些調查式報導。在這個過程中,我逐漸理解到Robert Fisk想要傳遞的信息:我們現處一個電子傳媒、社交媒體的時代,大家會覺得第一手資料的獲取是特別昂貴的,需要一個非常有經驗的記者一直住在那裡花時間花精力,但大部分媒體現在都不做這個事了,所以這個世界的真相實際上在慢慢流失掉,慢慢不被人看到。最後他提出來的問號是非常值得警醒的。我覺得紀錄片本身就是應該去提出一些被人所忽視的問題。
《口罩獵人》海報
掃描二維碼觀看全集
其實我初評看的10部片子都不錯,《口罩獵人》也是一部非常好的紀錄片。花總跟林棟是不期而遇的,但他一開始就很敏感地意識到要抓住這個人,這個時候攝影機就是花總的一個武器,他讓我們看到了紀錄片的一個魅力,就像是一種應激的反應。影片中的很多對話,也可以讓觀眾感受到拍攝者非常努力在一個所謂的熱點事件背後挖掘人性。

《Acasa,my home》海報
也有一些片子把光亮照向那些我們平時不太容易看到的人群,比如《Acasa,my home》,一個大城市邊緣,在熱帶雨林裡面生活的一些人,我覺得紀錄片拍攝者都是在想怎麽關心那些,比較容易被我們去忽視的人和事。
“房間裡的大象”
GZDOC:對您來說,您覺得什麽樣的紀錄片是一個好的作品?
周軼君:對於我自己而言,我會希望能拍出像房間裡的大象一樣的東西,就是說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它存在於我們身邊很大,但是我們很少去談論它,那樣的東西對我來講就會是一個非常新鮮的刺激。
GZDOC:在這一次您看的金紅棉初評作品裡,您覺得他們有在做這樣的事嗎?
周軼君:我覺得《This is not a movie》拋出的問題確實就是這個房子裡的大象,我們每天都在使用社交網絡,慢慢我們的觀點,我們對事實、對真相的認知是在被改造的,但我們可能沒有很清醒地意識到這件事情。《Coded bias》也是,我們理所當然地覺得滿大街的攝影頭帶來了社會安全感,但我們其實並不知道這些監控在幹什麽,AI這個東西本身就是有偏見、有取捨的。我們可能知道什麽被改變了,也知道我們變成了什麽樣子,但我們可能不知道是哪些東西在這個過程當中消逝了。

《Coded bias》海報
GZDOC:全球疫情蔓延,節展都受到波及,國內外都在摸索和嘗試,是困境也是挑戰,同時也是機遇,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今年雖受到影響,但還是持續在尋找方式,年底以更好的面貌和觀眾見面。可以說一下您去年對我們節展的感受以及今年的期待嗎?
周軼君:對,今年是挺困難的,原本上海電影節有一個紀錄片環節讓我去主持,但是我在香港,因為疫情不能過去,雲主持太難實現就最終無法安排。我就想將來無論是電影節或者其他的活動,人和人之間的交流有沒有更好更有效的辦法?我們可能真的要想一個比較長久的模式,將來這幾年哪怕有疫苗,疫情可能還是一個此起彼伏的情況,所以需要Plan B,如果做不成那如何應對。
去年我來廣州國際紀錄片節是很開心的,有一場分享好像很快票就都發完了,現場人也很多,對我來說是蠻感動的,而且也剛好有機會碰到業內的很多人。其實我覺得你們已經做得很好了,我就是希望你們能順利召開,今年不要受疫情的影響。
採訪最後,周軼君向我們推薦了一部紀錄片與一本書。

《Bébés》海報
周軼君:《Bébés》這支紀錄片選了四個不同國家的孩子出生的第一年,非洲的、蒙古的、日本的、法國的孩子。它沒有預設的感動,所有的表現都是直接莽撞的,比如說非洲的孩子永遠是在髒水裡給他一放,他就自己去游泳了,或者是孩子大便拿著石頭在屁股上刮一刮,然後轉到日本的孩子可能還不到一歲就要去上幼兒班,在很精致很貴的那種環境下學習非洲鼓,另一面你看到非洲孩子就在泥地裡面玩,它不斷用這種非常真實的反差,其實是非常幽默的東西,但你看了會感到心酸。

想田和弘《這世上的偶然:我為什麽拍紀錄片》
我最近還看了一本挺感動的書《這世上的偶然:我為什麽拍紀錄片》,日本的想田和弘寫的。其實他經常就是一個人的隊伍,自己做了很多事情,當然我不主張所有人都這麽乾,因為你技術上肯定還會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他這種製作的方式,他的理念等等,他找到了他的語言,我還蠻欣賞那種語言的。所以我覺得紀錄片拍攝到最後,實際上不管你用的是什麽樣的題材,什麽製作方式,最後都是找到你自己的語言。
採訪:超然
編輯:張汩、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