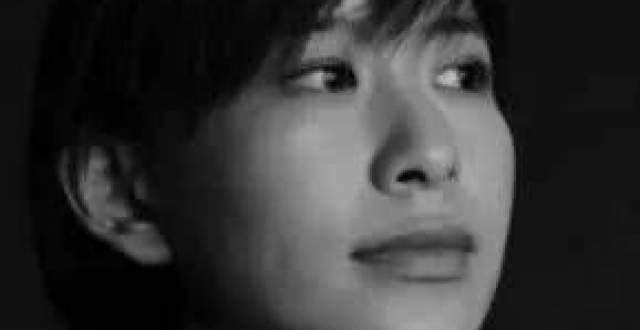作家如何在文化的精變中找到自己?
“不是靠聰明,寫點子,現在文學的弊端都是太聰明所至。支撐中國文學地圖的都是死心塌地、悶聲不響在那兒寫作的。”
蔣子龍:文學不是聰明人的遊戲
——中國作協2019年“文學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講堂在津舉行
文 | 王楊
今年,距離蔣子龍的代表作《喬廠長上任記》發表已過去整整40年。當年,他敏銳地關注到社會現實的需要和變化,寫出了反映新時期經濟改革的經典作品;如今,已經78歲的蔣子龍仍然直面社會現實,並保持著文學的敏銳性。7月12日,在中國作協2019年“文學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講堂上,蔣子龍以“文化的精變”為題,和家鄉的同行分享了他對當下文化現狀以及在自己在寫作中遇到的困境的思考。本次活動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天津市作家協會、中共天津市西青區委宣傳部、共青團天津市青年聯合會承辦。天津市作家協會黨組書記李彬主持活動。
(點擊觀看)蔣子龍在中國作協2019年”文學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講堂作演講
1
“精變”:一個重要文化現象
“文化的精變”是蔣子龍獨創的概念。所謂“精變”就是“成精”,人人都想成為“精英”,渴望成功。在蔣子龍看來,掌握社會話語權、引導社會潮流的,是各種各樣的精英,這已經成為了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在當今社會流行文化中,對寫作衝擊最大的也是這種精英文化。

文化的“精變”為寫作者帶來了什麽樣的影響?蔣子龍認為有三個:一是有話不好好說,雷人雷語多。“我也看網絡小說,也有微信,也接觸時髦用語,但當我寫作的時候,我把這些東西全部丟掉,隻留下一種印象和信息,最怕寫作時冒出一句網絡用語或雷人的話。”蔣子龍說,作家要防備和拋棄這種語言。網絡語言聽第一遍很新鮮,第二遍就會索然無味。“精變”現象給當代語言帶來的劇烈改變,它同時也改變了年輕人的表達和閱讀習慣。“作家寫作品,還要顧及到年輕人的習慣和審美,但不能丟掉文字和語言的本質。”
從語言,蔣子龍說到文化的“精變”帶來的第二個問題:文學創作變成了一種“聰明人的遊戲”,寫作變成寫點子。而與之相關的第三個問題就是故事的缺乏。蔣子龍觀察到,地鐵裡所有年輕人幾乎都在看手機,他們在看什麽?看故事。“人們在尋找故事,但是大部分是‘事故’”。“事故”在發生的一瞬間,生命力就結束了;而故事的生命力是永恆的。蔣子龍由此引出問題:面對“精變”,寫作者怎麽辦?當今寫作如何找到故事?
蔣子龍並非不認可文化的精變這一事實,求強求勝在本質上是沒有對錯、無可厚非的,但“成為精英要有資本”——蔣子龍所說的“資本”指向種種現象背後實在的本質;而他所反對的,是“聰明人的遊戲”,那些“太輕飄”。

文學愛好者們認真聆聽講座
2
故事是魔咒
柏拉圖說:誰會講故事,誰就擁有世界。整個講座中,蔣子龍給聽眾講了很多故事,他講這些故事的重點就是說明故事的重要性。
有一年蔣子龍去好萊塢,發現他們寫劇本的不叫文學編輯部,而叫故事部。每年,他們都從社會上搜羅三萬多個故事,這些故事裡包括我們所謂的細節,一個有意義的細節也被認為是故事,最後不斷淘汰,留下三百個左右。好萊塢對故事的訴求是高於一切的。美國作家、編劇羅伯特·麥基說過,在一部完成作品所體現的全部創作勞動中,作家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勞動都是用在設計故事上。
“人類為什麽迷戀故事?因為人的誕生就是故事,故事創造了人類。死亡是人類不可改變的結局,但故事讓死亡的意義改變了,有些人不死,是因為那個人有故事。”
因此蔣子龍認為,故事是一種力量,不光對一個人,對社會也是。故事的力量對於作家的意義更非同一般,小說家的價值就是提供和奉獻故事。“能講故事,說明你有力量;全世界的人都能聽你的故事,這就厲害了。”
故事是魔咒。“我們小時候都有過著魔的時候,直到現在讀到好故事還會著魔。”小說不能提供好故事,很難形成社會記憶。多年前,蔣子龍曾到劍橋講學。讓他感觸很深的是,下午三點喝下午茶時,教授們會談論起同一本書。“過去,我們也有這種現象。但現在很難了,幾個作家湊到一起也很難找到共同閱讀,人們甚至很難唱同一首歌。”
在蔣子龍眼中,故事是社會最敏感的神經。寫故事不光要有時間背景,還要有社會背景。“我寫小說時,編輯告訴我,身後永遠要站著讀者;我寫戲的時候,導演教給我,要面對觀眾。”他不無幽默地舉例說,美國作家辛克萊的長篇小說《屠宰場》中寫到,有時候會有死貓死老鼠掉進做香腸的容器,頃刻之間會和鍋裡的肉混在一起,被做成香腸。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習慣邊吃早餐邊看書,正好吃到香腸……羅斯福總統從此開始吃素,而美國的食品衛生法也從此開始一步步完善。故事的力量能夠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改變一個國家的社會面貌。“大家都憑聰明,寫點子,發行量和點擊量都很高,很熱鬧,但是與社會與現實有多少關係呢?而我們的現實又能從文學中吸收到什麽營養?”蔣子龍說,人的性格、民族精神,有時候是要靠文學作品來營養的。缺少支撐或者營養品格、精神的作品,“文學現在被邊緣化,一點兒都不虧”。

聽講座的文學愛好者在認真記錄
03
用笨辦法留下自己的故事
為什麽要強調故事的重要性?蔣子龍希望到場的寫作者都能夠找到自己的故事,寫出自己的故事,留下自己的故事。文壇很熱鬧,但蔣子龍認識到文學藝術創作一個非常殘酷的規律:一聲不響的大規模淘汰。“這就太殘酷了。”為了避免作品被快速淘汰,作家就要找到自己的故事,也就是找到最好的自己。
作家如何在文化的精變中找到自己?“不是靠聰明,寫點子,現在文學的弊端都是太聰明所至。支撐中國文學地圖的都是死心塌地、悶聲不響在那兒寫作的。”蔣子龍說,中國古人還有一種觀點,就是“笨”。他認為,“笨”也是一種天賦,現在的問題主要是缺少笨人。在精變的時代,大部分都是精英在講故事,機場和車站的書店擺在明面的都是勵志的致富的,“但這些故事中有好故事嗎”?
蔣子龍覺得,寫不出好故事的另一個原因就是爆炸性新聞太多。生活被爆炸性新聞淹沒了,作家的想象力被“事故”、被生活剝奪了,想象無法超越現實。“首先一定要承認,社會生活永遠大於文學創作;但同樣,社會現實無論怎樣豐富,也不能代替文學創作,不能代替精神。”蔣子龍告訴在場聽眾,不要被急功近利的故事限制自己的想象力。
蔣子龍講到,在泰國街頭有一尊水泥佛像,表面已經開裂了,很破爛。一個和尚善念一閃,拉著這尊佛像上路要好好安置它,走到半路,和尚發現水泥裂開,現出裡面的一座金佛。蔣子龍認為,文學創作也要找到平凡生活內藏的“故事金身”,“現在的弊端是被聰明掩蓋的平庸——平庸的靈魂,平庸的故事。好的故事一定是從靈魂開出的花兒,非常好看的花朵,枝葉繁茂。”
怎樣才能寫出有靈氣的作品,在靈魂開出好看的花?蔣子龍說自己是個笨人,有一些笨辦法。中國古代要培養一個人才,第一步是養地,把家裡的地養好,地會長人。人有了,就要養氣,養浩然之氣,就是培養精神。“我們現在的地是什麽?是現實,是生活。”很多大作家都會從自身找故事,蔣子龍並不反對,但他提醒聽眾,作家也要注重行走。行走是中國的文學傳統,古代文學大家都是在行走中寫出了流芳千古的作品;美國作家愛默生也曾經說過,誰能走遍世界,世界就是誰的。蔣子龍說,如果靈魂安定下來,從魂兒上就高枕無憂,很安逸,不可能有好故事,作家的靈魂應該永遠處於行走的狀態。
演講尾聲,蔣子龍說:“好的故事有深刻的東西在其中,是有靈魂的。而有的故事沒有靈魂,它就不能生長,沒有生命力。在這樣一個複雜的文化時代,怎麽找到自己的好故事?在同質化的時代,大家都被格式化,但你不要讓自己的靈感被格式化。找到自己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那不同的經歷就是財富。”

播音專家何佳朗誦《農民帝國》片段

詩人張秋鏵朗誦自己創作的長詩《濤聲回響六百年》片段

學生代表朗誦蔣子龍散文片段
講座結束後,現場還舉行了優秀作品誦讀會。天津市朗誦協會會長、播音專家何佳朗誦了蔣子龍長篇小說《農民帝國》部分片段;作家張秋鏵和學生代表分別朗誦了自己創作的長詩片段和蔣子龍的散文片段。天津市作協會員、文學院簽約作家、網絡文學作家、評論家代表以及天津市青聯委員代表、西青區宣傳部宣傳乾事和市司法局公證處的文學愛好者等150餘人參加了活動。
編輯 | 王雅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