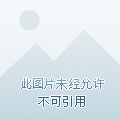看!世界真遼闊
《淮南子》中有記載:“昔者倉頡造書,而天雨栗,鬼夜哭”。西漢末年的《春秋元命苞》中的記載則更進一步,稱倉頡造字,“天為雨栗,鬼為夜哭,龍為潛藏。” 在中國的神話中,唯獨倉頡造字這個故事特別有想象力,它給人帶來了巨大的力量。歷史學中常常說“有史以來”這四個字就與文字的關係甚大。在文字出現之後,歷史就漸漸擺脫了記憶和口述,“有史以來”似乎也可以替換為“有字為憑”。但我們也必須要意識到,在能看懂的文字或是迄今為止還看不懂的文字出現之前,人的歷史還走了相當漫長的一段時間。況且,在還沒有足夠多的文字用來表達的情況下,人的歷史也依然是豐富和表現多樣的。之所以會提及倉頡造字的故事,還是想將《古代狂想曲》這本書多說一些。哪怕不對,都是自己的理解。
《古代狂想曲》中敘述的提及的“訪古”旅程中,那些激發了池澤夏樹不斷追尋的文物中,提及文字的只有一處,那就是土耳其篇中的“账本和碑文之間”。池澤夏樹的感慨是:“文字可真是不可思議的東西,如果寫字者和閱讀者不能共享同一種知識的話,文字就不能發揮作用。” 文字是要選擇對象的。從圖畫演化為記號,從記號進化為符號,符號再與發音相適應,這或許是文字被創造出來的一個路徑吧!人和文字已經共存了幾千年了,在人發明文字之時,大概根本就沒有預料到文字給人帶來的災禍就是文字的報復。顯然,池澤夏樹謹慎了選擇那些能促使他想看多一眼的文物,除去文字之後,雕像、建築、圖畫、圖騰柱這一類物件更能將不同的人聯繫起來,這些在往昔生活中可以直觀去看的存在可以直接跨越語言的藩籬,來自不同地域、不同歷史中的人都可以獲得最直接的觀感。雕像、建築、圖畫這一類可以“共通”的物件,在人的想象力中可以任意發揮。如果池澤夏樹選擇在不同於文字記載的歷史遺跡中穿行和想象的話,他一定會找那些不不需要過多言說就能感受到的共通之處。或許這才是《古代狂想曲》的書名中“狂想”一詞所依賴的基礎吧!暫不論面對歷史遺跡該如何施展想象,但至少這種想象力是可被理解的。
在閱讀《古代狂想曲》時,請一定不要忽略池澤夏樹漫不經心的觀察,比如當地當地的氣象、地形、道路。數千年前在春天下的雨水,在數千年後的春天依然會準時的落在同一個地方。從這個層面看的話,人的歷史---尤其是“有史以來”的歷史其實短的不值一提。“人出生,成長,長大成人,與人相戀,成家生子,再將下一代撫育成人。在此過程中,種種故事、事故和幸運,各種悲歡離合,組成了一段段人生。而五千年之久遠,相當於這樣的人生重複了兩百五十遍。”
在面對古代時所展開的想象也罷,狂想也罷!想到的會是什麽呢?站在今天,借助這些凝固了的時間遺跡,看到與想到的是否會保持一致呢?池澤夏樹在《古代狂想曲》中沒有回答這個問題。現在我們能看到的這些留存到數千年後的物品多數都憑運氣。歷史遺跡告訴我們的另外一個事實是,在歷史中更好的人類作品基本都是命運不濟的。對好東西的佔有和爭奪不是你我才有的本性。現在我們能看到的歷史遺跡都是僥幸存之。而且它們也不會流傳千古,“塵歸塵、土歸土”的命運不單在人身上應驗,也同時在歷史的遺跡上應驗。人在土地上營造的一切,都會回到土地裡去。現在可以看到的這些歷史遺跡我們常常會驚為天人之作,但實際上是打了折扣的。即便如那些經過精心挑選過的圖騰柱,在抵達時間點之後也會化為一堆腐土,再也看不出原來的模樣。在《古代狂想曲》中挑選出來的器物是“形”與“意”的結合,而不是將“形”作為主角。由此產生的遐想就是,那些最初的稚嫩中是如何產生力量的。就像伊瑞克提翁神廟中支撐屋頂少女像柱以及眾多女神雕像,散發著生存的喜悅,似乎仍有溫暖,柔軟、光滑的軀體無不是對生的讚美,那是怎樣一個時代呢,優美的身姿,強健的軀體,洋溢著以肉身存在於世間的歡愉,而如今,我們的時代,在匆匆的腳步聲悄然前行,不知能留下些什麽?面對不同方向上的追尋,池澤夏樹所挖掘的不是懷念,而是關照當下的警惕。

該如何眺望過去呢?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這樣說:“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實際上,王羲之在永和九年暮春之初的蘭亭修禊時,眼中所見應該是一幅歡暢之境,“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這樣的場景實在看不出一絲絲可以用來“悲”的因素來。王羲之似乎也是將自己抽離出來,站在一旁看著這一群享受春日閑暇時光的人,如果不是《蘭亭集序》這篇文章的話,那一刻歡愉的時光過去了就過去了,人散去之後,崇山峻嶺和茂林修竹不會因人而不同。王羲之站在人群中,不但看到蘭亭之前曾經發生過的歡愉,也想到了在遙遠的未來或許也會有人與他一樣想象此地正在發生的歡愉!只是這種歡愉,怎麽看都像是沒有存在過。
過了幾百年之後,讓王羲之“悲”的感概在另外一人的手中改頭換面了一下,不過實質仍在。杜牧在《阿旁宮賦》中說到:“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複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杜牧所生出的哀歎要比王羲之更為幽遠一些。相比王羲之,杜牧在《阿旁宮賦》中的哀之鑒之一大半還沉浸在“安史之亂”的陰影中。而且,杜牧要比王羲之的痛感更深切一些。從“悲”字遞進到“哀”字之間的變化,除非是自己深有體會。
將王羲之和杜牧寫下的文字拿出來牽強附會一下,就是看到他們所提到的“今之視昔”的現實和“後之視今“的想象。這一點與池澤夏樹在《古代狂想曲》中展現的氣質如出一轍。只不過池澤夏樹從來不悲傷,畢竟走了那麽遠的路,還依然能見到歷史遺跡的出生地,那心裡的”小確幸“啊!可不是一點點!
“出發吧!把它們都看個遍,看著石雕少女美麗的臀部,男人暗自下了決心。”寫下這樣的文字,是個性情中人。
=====================================================
每一次閱讀都會邁向遼闊!《短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