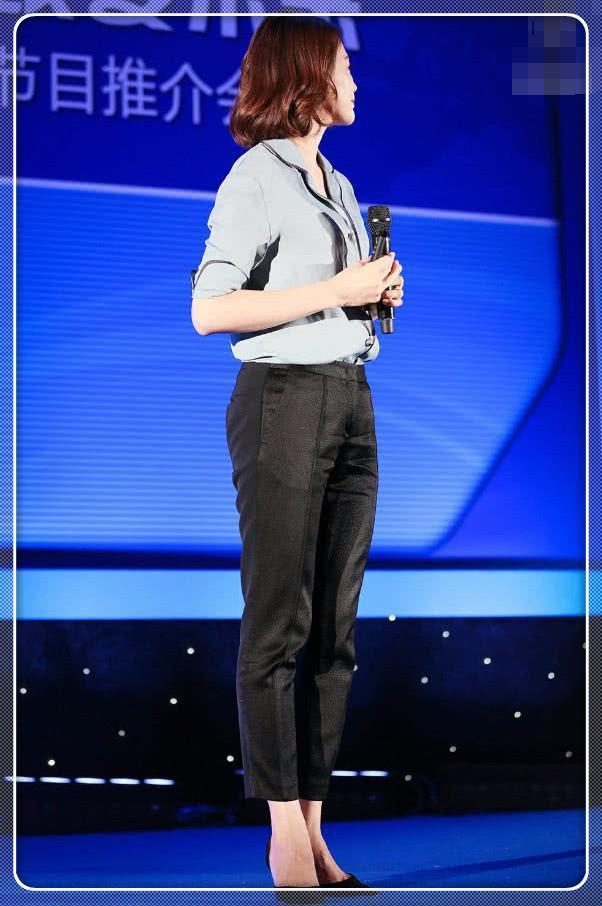清乾隆時期的文學普遍具有向日常生活貼近的傾向。相對這個時期而言,古代文學作品常常具有一種詩性品格,是人的精神自由舒卷之地,亦是對現實逃避的家園,因此常常處於與日常生活形成對照的文化系統之中。《儒林外史》以還原的方式對古代作品中出現過的浪漫的富於想象的藝術形象進行消解,在文化上便具有了一種對傳統的顛覆意味,這便形成了《儒林外史》的解構主義特徵。

一、古典典型形態和情節模式的詩性傳統
《儒林外史》以前的中國古典小說,其人物類型化的趨向非常明顯。性格的某一主要特徵即“類”的共性佔主導地位,而人物的個性往往沒能得到應有的重視,或者因“類”的共性過於顯目而在一定程度上淹沒了性格的複雜性和豐富性。前者如《三國演義》中劉備是“仁”的化身,關羽是“義”的體現;後者如《金瓶梅》雖然出現了宋惠蓮、西門慶等圓型人物,但主要人物之一的潘金蓮仍然只是“淫”這一惡德的代表。與古典典型形態的類型化相似,小說情節往往有模式化的特徵,例如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說。這是與崇尚眾美皆備或眾惡皆歸以及追求脫俗的古典美學相適應的,也因此使古代文學作品具備了詩性品格。
這種詩性品格,是經過作者理想“裝飾”(詹姆遜語)的“烏托邦”。它與世俗人生和日常生活形成對照,展現的是詩意人生和詩化生活。對於這一點,我們不妨結合古典小說(以及戲曲)常見的愛情題材和俠義題材來加以分析。
先看愛情題材。“中國男女之間,除了歌台舞榭之外,不能公開社交。挾妓尋歡,是男子的特權之一。”(注:蔡正華:《中國文藝思潮》,見《中國文學八論》, 中國書店1985年6月版)因此,愛情題材中相當一部分是反映文士與妓女的交往,其常見的模式便是才子佳人型。唐代的傳奇小說或許是最早描寫文士與妓女戀愛的文體。(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五《詩話》談到唐人傳奇時說:“大抵情鍾男女,不外離合悲歡,紅拂辭楊,繡襦報鄭,韓李緣通落葉,崔張情導琴心,以及明珠生還,小玉死報。凡如此類,或附會疑似,或竟托子虛,雖情態萬殊,而大致略似。”沈既濟《任氏傳》、元稹《鶯鶯傳》、李朝威《柳毅傳》等均是有聲有色的名篇。元代戲曲中也出現過大量“富家小姐窮秀才”型的愛情故事。雖然女主角不一定是妓女,但與唐傳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浪漫的理想色彩掩蓋了生活的真實面貌。本來,文士與妓女的交往既有兩情相依互相傾慕的一面,也有森然可怖和充滿銅臭的陰暗一面。據孫棨《北裡志》記載,“大中以前, 北裡頗為不測之地”,不時發生鴇母與妓女合謀殺死嫖客的事,《李娃傳》也寫到“資財仆馬蕩然”的鄭生被逐出妓院的事(雖然作者委過於鴇母)。元代儒生仕途坎坷,生活潦倒,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出現《破窖記》等戲中描寫的“才子落魄遭白眼,貴家小姐偏愛憐”的美好姻緣。然而,作家們不願破壞浪漫國土上的浪漫情調,他們一廂情願地編織統滿詩意的美夢。究其原因,一是唐代文人的性格偏於詩,受這種性格的引導或推動,唐人傳奇寫文士與妓女的戀愛,不免虛飾或美化。二是據章學誠解釋,作家在此采取的態度近於古代樂府詩人寫豔詩,目的是為了“寄懷”,其中別有寄托。正如元代知識分子生活痛苦,而希望有朝一日有人能識英雄於草莽一樣。他們編織的美夢實際上是對痛苦心靈的撫慰。
才子佳人作品的詩性品格,還有一個突出的表現,即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常以一種放誕不羈的方式對待愛情和生活,我們可以稱之為“才子的優越感”。舊文人有兩種,一為儒生,一為才子。儒生必須循規蹈矩,做社會的表率;才子卻可以風流倜儻,扮演“佳話”中的浪漫角色。實際生活中,儒生佔大多數;而在文學作品中,唱主角的更多的是才子。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才子的行徑,有敗壞社會風氣之嫌,故現實生活中不能容納太多才子,必須由儒生來構成和維護一定的禮法秩序;而文學作品,作為知識分子的情感依托,淡化對倫理禮法的責任感而著力渲染才子的優越感便在情理之中了。同時,現實生活中的少數才子,諸如唐寅等吳中名士,一旦進入文學作品,還可以起到點綴升平的作用。正如(清)趙翼《廿二史劄記》所指出:“世運升平,物力豐裕,故文人學士得以跌宕於詞場酒海間,亦一時盛事也。”這也可以看成是“才子的優越感”這一詩性傳統得以鞏固和發展的一個推動因素。
再看俠義題材。中國古代,俠客活動格外有聲有色的時期是春秋戰國時代,唐睢、豫讓、聶政、荊軻等都是聲名顯赫的俠客。相應的在文學上則有《左傳》《國語》《戰國策》的片斷記載,而《史記·遊俠列傳》則是相當成熟的描寫武俠的作品。這種情形是與西周封建制解體後自由武士、自由文士階層興起這一時代特徵相適應的。而秦漢以後,大一統的專製國家建立,俠客失去了其依托的社會背景。為俠者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是佔山為王,成為《水滸傳》世界的好漢;二是為“清官”效命;三是橫行一方,實即土豪。俠這一社會階層,實際上已不存在。但俠的精神,卻作為一種人生境界進入文學作品中。無論是唐詩中的《俠客行》、《結客少年場行》,還是唐人傳奇中的吳保安、昆侖奴、馮燕,亦或是《水滸傳》中的魯達、李逵、阮氏三雄,以及唐傳奇中的女俠形象,諸如紅線、紅拂、聶隱娘,我們或可以感受到“救人於厄,賑人不贍”(司馬遷語)的道德力量的感召,或可以體味到人類生命力的勃發,更加激發起對無拘無束的自由境界的嚮往。儘管這些豪俠形象都已不是生活的真實寫照,而僅僅是一種精神和氣概的表達,是一種浪漫情懷和詩意人生的呈現,但在日益世俗化的時代裡,人們無疑需要豪俠精神的激勵。這正是其價值所在。

二、《儒林外史》對詩性傳統的顛覆
《儒林外史》以寫實的手法打破了源遠流長的詩性傳統,將浪漫的詩意人生還原到日常生活狀態,並從道德倫理的角度對部分日常生活作出判斷,對曾經受到推崇、讚美的古典典型形態和情節模式進行消解,構成小說的解構主義特徵。
解構主義興盛於本世紀70年代,作為一種新懷疑主義的文學批評方法,它認為從來沒有絕對存在的意義,只存在瞬間生成的意義。解構主義代表人物之一德裡達指出:“中心不應該被認為是以一種此在的形式存在,中心從來就沒有自然的所在,它不是一個固定的所在,而只是一種功能,一種非所在,這裡雲集了無數的替換符號,在不斷進行著相互置換。”(注:德裡達:《結構、符號和人文科學話語中的嬉戲》,見《最新西方文論選》,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頁) 另一個代表人物希利斯·米勒也指出:“解構主義文學批評尋求的目標是……找到能 使整座大廈解體的松動磚石。解構主義就是指出文本早已在無論是否知道的情況下消解了它的基礎,以此使文本賴以屹立的基礎化為消解狀態。”(注:轉引自《文藝新學科新方法手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515頁)
由此看出,解構主義實質上是一種對“中心”的放逐和瓦解,從而消解文本賴以屹立的基礎。在這裡,我們試圖以此為突破口,探討一下《儒林外史》中才子佳人(名士妓女)故事和俠義故事的解構主義特徵。
全書被作者直呼為“呆名士”的只有測字的丁言志一人。說他呆,不僅因為他“跳起來通共念熟了幾首趙雪齋的詩,鑿鑿的就伸出嘴來講名士”(作者借陳思阮之口說出)這種以名士自居的派頭,更主要的是因為他不識時務,沉浸自失於“才子佳人兩相歡”的藝術世界,以至於在現實世界中鬧出笑話。
丁言志聽說來賓樓的聘娘愛詩,嘖嘖稱讚道:“青樓中的人也曉得愛才,這就雅極了!”次日他就帶了一卷詩,換了幾件半新不舊的衣服,戴一頂方巾來到來賓樓,要和聘娘談詩,暢快地“雅”它一番。結果呢?聘娘開口便要他“拿出花錢來”。看到丁言志的花錢只是二十個銅錢,不禁滿懷鄙夷地大笑道:“你這個錢,只好送給儀征豐家巷的撈毛的,不要玷汙了我的桌子。快些收了回去買燒餅吃罷!”丁言志羞得臉上一紅二白,低著頭,卷了詩,揣在懷裡,悄悄地下樓回家去了。
在這裡,丁言志所幻想的名士與妓女互相傾慕,共論詩歌以至心心相印的浪漫世界已經蕩然無存,才情與才情交流之雅為花錢與看詩交換之俗所代替,容貌與風度互相賞玩之風流由付不起錢被逐出妓院之尷尬所代替。“才子佳人兩相歡”這一充滿詩意和理想色彩的“絕對意義”早已化為消解狀態,唯一存在的是“瞬間生成的意義”,即日常生活的本來面目。如果將“才子”和“佳人”兩者分開獨立地分析,則“呆名士妓館獻詩”的故事對“佳人”這一中心意義的消解要甚於對“才子”意義的消解。
丁言志在妓院碰壁的主要原因還是囊中羞澀。假若他是陳木南那樣的富貴之人,聘娘是不會拒之門外的。因此,儘管丁言志作為名士的資格要大打折扣,但聘娘對“佳人”這一慕才情而不羨富貴的傳統詩性形象的顛覆尤甚。聘娘與陳木南的交往和聘娘對丁言志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照,從而共同構成消解“佳人”這一“意義大廈”的“松動磚石”。聘娘最終剃頭出家則可視為這一立論的補充闡釋。
《儒林外史》對“才子的優越感”的顛覆是通過杜慎卿、季葦蕭等才子形象與杜少卿、虞博士等賢人形象的對照來實現的。與景蘭江等假名士不同,杜慎卿頗有才氣和見識,這從他成功地舉辦莫愁湖大會定梨園榜可見一斑。他評說政史、詩文,也足以使蕭金鉉那號名士“透身冰冷”。季葦蕭聰明伶俐,不當八股奴才,不相與天下權貴,也還算是一個有才情的名士。在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說和戲曲中,是“杜慎卿”、“季葦蕭”們而不是“杜少卿”、“虞博士”們扮演了被佳人簇擁、受世人膜拜的角色,他們作為才子的優越感得到了充分表現和肯定。吳敬梓的態度如何呢?作者對他們的才華是認可的,有時還借杜慎卿之口表述一下作者本人的見解。但是,一旦與杜少卿、虞博士等真儒賢人相比,“才子的優越感”所具有的中心意義就自然地分崩瓦解,為“道德責任感”所“替換”。請看下面兩種對照:
其一,季葦蕭和杜慎卿都是娶過妾的。季葦蕭自稱:“我們風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會合,一房兩房,何足為奇?”杜慎卿口頭說“為嗣續大計”,骨子裡仍是“才子佳人,正宜及時行樂”的念頭。而杜少卿則不同。當季葦蕭勸他娶一個既標致又有才情的如君時,杜少卿當即表示反對。他答道:“葦兄,豈不聞晏子雲:‘今雖老而醜,我固及見其姣且好也’。況且娶妾的事,小弟覺得最傷天理。天下不過是這些人,一個人佔了幾個婦人,天下必有幾個無妻之客。小弟為朝廷立法:人生須四十無子,方許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別嫁。是這等樣,天下無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幾個。”杜少卿的意思也就是吳敬梓的意思,作者對才子的優越感持否定態度。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麽吳敬梓借杜少卿之口把描寫男女戀愛的《溱洧》曲解為“夫婦同遊”。
其二:杜慎卿平生最轟轟烈烈的舉動是定梨園榜,“名震江南”,而在杜少卿、虞博士的人生履歷上值得大書一筆的莫過於祭泰伯祠。二者的區別在於前者顯示才情“趣”“韻”,後者重在倫理價值。前者是才子以“玩”、“樂”的態度對待生活,體現了他們的優越感;後者是賢人以拯救世風的“終極關懷”精神對待生活,體現了他們的責任感。吳敬梓雖不鄙薄前者,但很明顯,他更推崇的是後者。
通過這兩處對照,我們可以看出,對“才子的優越感”這一詩性傳統的顛覆,是基於吳敬梓心中的道德標準。對這一點,我們將在後面作具體分析。
《儒林外史》共寫了三位俠客:蕭雲仙、張鐵臂和鳳四老爹。他們的形象對於古代文學中的豪俠這一典型形態的詩性傳統來說,具有不同角度的解構意味。而另一位具有俠風俠骨的女性沈瓊枝的形象,既消解了傳統閨房女子的柔綿詩意,也顛覆了由唐傳奇開端的女俠形象。
張鐵臂之為假俠客,主要問題不在於他的武技不甚高——他來時“房上瓦一片聲的響”,“滿身血咒之城”,去時又是“一片瓦響”——而在於他打著俠義的幌子乾著違反俠義精神的勾當。他標榜“義氣”,卻以“恩仇必報”為借口騙得婁家公子五百兩銀子,走到了“義氣”的反面。蕭雲仙先是行俠,後聽從郭孝子的指教,投軍“報效朝廷”。他以遊俠的氣概建立了赫赫功勳,最終卻被當權者加上“任意浮開”的罪名,落得個削職破產,滿懷悲憤。鳳四老爹可謂真俠矣。他功夫超凡,其為人自有一股俠氣,但他行為的效果如何呢?懲罰一下船上的暗娼和欠账不還的賴帳人,還救了一位假中書,僅此而已,並無多大意義;“俠女”沈瓊枝與欲娶她為妾的鹽商沈為富鬥狠,竟然輸了。後逃到南京城,靠賣詩文過日子。由於她隻身一人,獨來獨往,引起過不少誤會。但沈瓊枝“不帶淫氣”、“不帶賤氣”,“雖是個女流,倒有許多豪俠的光景”。她沉浸在對自我的俠女感覺中,一味與世俗的庸眾“鬥狠”,而實際上正如天目山樵所評:“瓊枝行徑正與鳳四老爹相同,觀其所為似乎動聽,而實無謂。”
張鐵臂以騙人行徑消解了“豪俠”這一語義所積澱的道德力量,以拙劣的技藝消解了“豪俠”所具有的勃發的生命力;鳳四老爹和沈瓊枝動機一樣,都是為挑戰而行俠,有點像大鬧天宮時的孫猴子,又有點像唐·吉訶德;蕭雲仙和鳳四老爹結局一樣,都是夢的破滅。動機和效果的變異使傳統豪俠“救人於厄,賑人不贍”的社會責任感及其對社會所起的感召作用在這裡化為消解狀態,古代文學作品中豪俠們無拘無束的自由境界也因此不複存在。另外,沈瓊枝的“俠行”也顛覆了養在深閨足不出戶的女性這一古典形態。(推廣開去,視張鐵臂為座上賓的婁三、婁四公子不也是對禮賢下士者如孟嘗君之輩的形象的消解嗎?)

三、對詩性傳統的顛覆實質上是文化悲劇意識的體現
吳敬梓用還原和對照的方式對古代文學中出現的浪漫的富於想象的形象進行了重新處理,其依據有兩點,一是作家在日常生活中的切身感受,一是作家心中的道德準則。而越向日常生活貼近,作家對日常生活就看得越透;作家執著於挽回世俗頹風的道德感越強烈,世風日下的社會現實也就越顯眼。因而,對傳統藝術形象的否定與顛覆就越激烈,文化的悲劇意識也就越深沉厚重。
根據張法的解釋,悲劇意識是悲劇性現實的反映,也是對悲劇性現實的把握。它由相反相成的兩極所組成:(一)悲劇意識把人類文化的困境暴露出來。這種文化困境的暴露,本身就意味著一種挑戰。(二)同時,悲劇意識又把人類文化的困境從形式上和情感上彌合起來。這種彌合也意味著對挑戰的應戰(浪: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頁)。
我們依然從《儒林外史》寫到的才子佳人故事和俠義故事來進行分析。
呆名士丁言志因囊中羞澀被名妓聘娘趕出妓院這一事實表明:日常生活中的所謂名士常常並不才華橫溢、風流倜儻,而往往是不識時務、迂腐可笑;所謂名妓也並非都把感情的交流和心靈的默契放在首位,她們往往更看重嫖客的身份地位和擁有的財富。當然,丁言志並非對詩一竅不通,他還是懂幾首詩的,但聘娘卻一開口就提“花錢”。由此看來,聘娘的所為更能體現這一“才子佳人”故事所暴露的文化困境:曾經被無數的人們所讚美和嚮往的心靈之約這一內在的東西已經被身份財富這一外在的東西消蝕得一乾二淨,“心靈”在“外物”面前極度地柔弱無力。而且,這裡的“外物”是由於主觀原因而非客觀原因才顯得很強大。具體地說,舊的禮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些限制和壓抑青年男女感情交流的“外物”之所以強大,與青年男女任何一方的主觀意志都是無關的;但丁言志與聘娘之間卻是因一方主觀上愛慕榮華富貴而阻止了雙方感情的交流。從文化含義上看,它表明了偏於內心偏於情感的文化精神遭到破壞,而對這一文化困境的暴露正體現了悲劇意識。
吳敬梓對“才子的優越感”的不滿,源於他對才子風流可能導致的消極後果的憂慮。世俗社會理想主義的失落與作家心中崇高的道德準則和強烈的社會歷史責任的巨大反差,使《儒林外史》充滿著悲劇意識。杜慎卿、季葦蕭等人也不失才俊,但他們的社會歷史責任感極其淡薄,他們沉溺於才子風流,以名士自許,以享受人生為目的。他們雖不令人厭惡,但他們缺乏理想主義的精神和可以為世楷模的正氣。與虞博士、杜少卿等人相比,他們實際上是生活於空虛、無聊之中。(清)章學誠曾對小說戲曲提出嚴厲的批評,指責它們在描寫男女的事情時,男的必然輕佻儇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風流;女的一定冶蕩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絕世。這些作品對讀者的危害很大,那些有小慧而無學識的男子,以及通文墨卻不明禮法的女子,往往將小說戲曲中的才子佳人視為古代的真實人物,愚蠢地加以仿效。另有一些心術邪惡的人,更自命風流,無所忌憚地以才子佳人故事來迷惑人。這種情形,令嚴肅正直的讀書人非常擔心。吳敬梓與章學誠的想法是一致的,他表彰虞博士等真正信奉儒家精義的真儒,就是為了樹立矯正偽妄世界的道德楷模,為了建立批判偽妄世界的價值尺度。作家這種執著於挽回世俗頹風的精神不正是一種悲劇意識的體現嗎?
吳敬梓對豪俠形象的還原,其依據是日常生活的真實狀態:要麽是張鐵臂那樣的假俠客,要麽是有俠義風骨但實際上卻無所作為的鳳四老爹和沈瓊枝,要麽是行俠和入仕都無法實現人生價值的蕭雲仙。古代文學作品中光彩奪目的俠客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司馬遷曾熱情謳歌俠士“不愛其軀,赴世之厄困”的精神,並深為“匹夫之俠,淹滅不見”而“甚恨之”。他不無嚮往地說,秦漢以前“為俠者甚眾”。吳敬梓秉承著和太史公一樣的情懷,不但痛恨文士日益庸俗化,也恨真的俠士和真儒一樣日稀了。因此,寫假俠客張鐵臂是和寫婁府的那些假名士相呼應的;而寫真俠鳳四老爹,而且安排在虞博士等真儒消磨盡了之後出場,則具有更深層次的含義:不但許多真儒大賢無用武之地,連真俠也不可能有所作為。因此,寫真俠是為了強化真儒的悲劇意識。真儒對自己理想的人生道路素來有著執著的追求精神,然而在這個日益世俗化的社會裡,理想不可能實現,因此便產生了悲劇意識。理想失落了,而失落者對理想又有著永恆的懷念和執著,同樣也產生了悲劇意識。至於沈瓊枝和蕭雲仙,他們或行為方式或行為結果都與鳳四老爹有些相似,因而都可以看作是鳳四老爹形象的補充。
前面說過,悲劇意識不但包含暴露文化困境這一層面,還包括彌補困境的層面。《儒林外史》顛覆了古代文學作品的詩性傳統,還原到日常生活的狀態,暴露出文化的諸多困境。對於彌補困境,吳敬梓沒有可能從實際措施方面作太多努力。但在情感上,全書所蘊含的隱逸思想不妨看作對文化困境的一種抗爭方式。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布!
出處:《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年第02期 第80-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