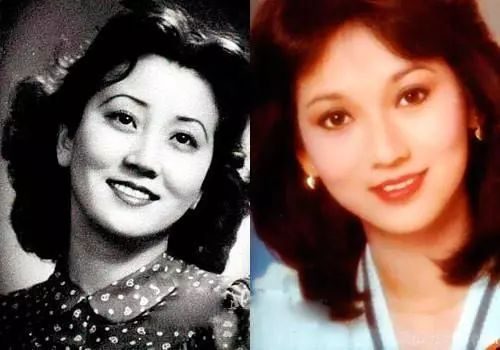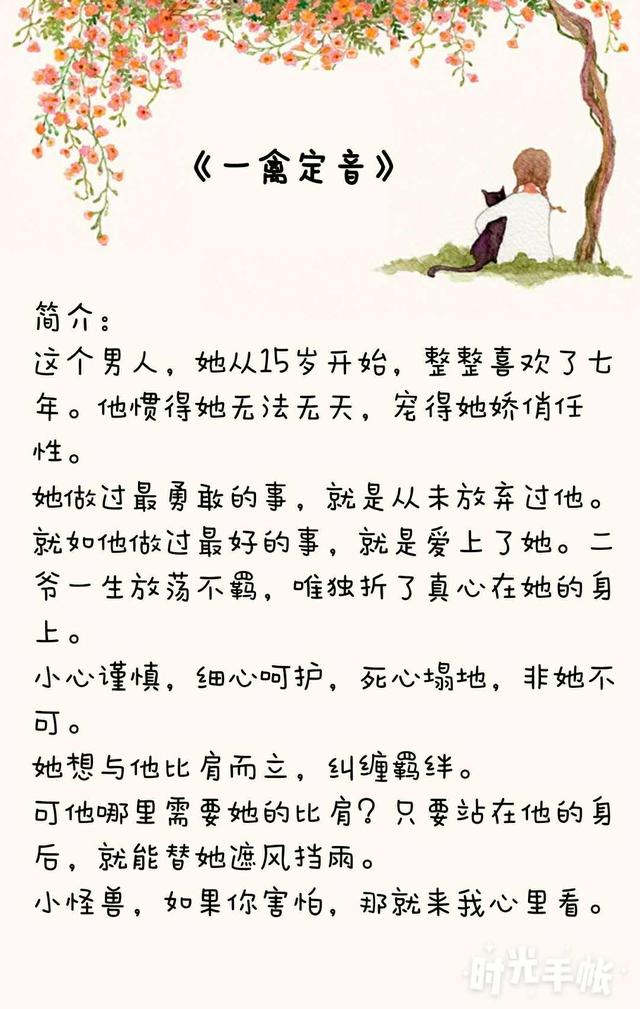余華,《愛情故事》
文 | 李浩
……一直存在兩類作家(當然這一區劃並不是那麽地嚴格,但界限卻是恆在的),一類是影響大眾閱讀的作家,另一類則是影響作家的作家。
卡夫卡是影響作家的作家,但因為名聲的顯赫他同樣會被大眾有限度地接受,無論這一限度是否遠比閱讀者以為的更根深蒂固;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和古老的《一千零一夜》都具有通俗性,然而它們同樣會不同程度地影響著作家。不過我想我們也必須承認,在大眾閱讀和作家閱讀之間,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趣味分野,大眾更願意通俗和易懂,誇張與離奇,在閱讀中盡可能不耗費什麽力氣,而作家們則更看重“對未有的補充”和啟發性,影響作家的作家往往會對後來的作家們提供“喚醒”,讓他突然意識到小說還可以這樣寫,進而讓他“急迫地試圖”完成自己的創作。影響作家的作家,其寫作一定包含著諸多的可能和極為精細的設計,它讓後來的作家們歎服,在品啜中獲得無窮的滋味;而大眾閱讀則更多地願意曉暢、迅速,“險象環生”,“好看”——這兩類作家在寫作上的訴求是不同的,朝向也是不同的,但方式方法上卻可互通有無。
在我看來余華屬於那種影響作家的作家,他的影響力的彰顯更多地是對作家們的影響而得以完成,中國七零後的作家和部分的八零後作家多數曾從余華的寫作中領受惠澤,他的寫作具有強烈的啟示性,完成度極高,可以從多個層面去學習和得到。他也是少數短篇、中篇、長篇都有絕佳表現的中國作家之一。
在余華的短篇中,往往會呈現那種精致之美,充盈的詩意之中包裹的又往往是生存的殘酷以及被擊碎的哀歎,張力強勁。是的,余華的文字(尤其是前期作品)時常有種冷峻氣息,但說他“血管裡流淌的是冰凌”雖然漂亮但並不確切。榮格在談及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時說過,“喬伊斯頭腦的這種奇異的特徵表明,他的作品是屬於冷血動物的,更具體地說,是屬於蠕蟲家族的”——嚴格地說,它其實並不適用於對余華的評判,對余華這類寫作的評判。余華不屬於那個蠕蟲家族,他的冷和酷是認知需要而非情感性的,他有意直面那種殘酷性甚至部分地誇張化,均是因由小說內在力量的需要,這種文字間的克制冷靜恰恰在閱讀中強化的是情感投入,這種方式更有益於對閱讀者的情感喚醒。在這點上,他更接近於卡夫卡在《變形記》和《在流放地》的表現而不是《尤利西斯》。
一、互文和延展

無論余華有心還是無意(我個人更傾向於有心),我想我們都會拿他的這篇《愛情故事》與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進行比對,它們都是短篇幅,它們的敘述核心都是一男一女,墮胎手術或孕情檢查,同樣地,男女各有心事,他和她的心事的向度是不同的……當然它們也有近乎同樣的大面積“留白”,那種獨特的“經驗省略”——當然所謂“經驗省略”並不是把實體經驗省略掉,海明威和余華在他們的小說中省略的其實是我們憑經驗可以填充、想象的部分,他們依賴讀者的經驗。因此這種省略技巧其實是最大限度地調動讀者的經驗參與,使讀者覺得作家很信任自己的理解能力和經驗能力——我甚至傾向於這種比對恰是余華的下懷,他就是要我們進行這樣的比對,他的《愛情故事》就是以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為支點和源頭而完成的互文式寫作,他故意地留下了“蹤跡”。
留下蹤跡,其一是致敬,當然這一致敬的過程中暗含“較量”的雄心;其二是充分地利用“互文”的關聯性,讓另一篇小說中的講述和意蘊也能補充到這篇小說中,構成另外一層深厚,它類似中國古典詩歌中的“用典”;第三,應當是“較量”雄心的彰顯,它願意重新講述一遍類似的故事,但在舊故事之外它有別樣的發展、發現和豐富。所有的互文性“重新講述”都更為看重這一點,就是它的新提供,新認知,新經驗,這才是互文寫作的動力和動機所在。
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這個故事真的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一個美國男人同一個姑娘在一個西班牙的小站等火車,男人設法說服姑娘去做一個小手術。它幾乎只有一個場景,批評家吳曉東說,海明威就像一個攝影師,碰巧路過西班牙小站,偷拍下來一個男人和姑娘的對話,然後兩個人上火車走了,故事也就結束了,他們從哪裡來,他們是誰,又到哪裡去,為何來到這個小站,海明威可能並不知道,當然我們也就無從知曉。整部小說運用的是典型的純粹的限制性客觀敘述視角,敘事者既不干涉也不進入,就像一架機位固定的攝影機,它拍到了什麽,讀者就看到了什麽——在《愛情故事》中,開頭的敘述也極為“類似”,“一九七七年的秋天和兩個少年有關,在那個天空明亮的日子裡,他們乘坐一輛嘎吱作響的公共汽車,去四十裡以外的某個地方”,它所書寫的也是一場“各懷心事”的旅程,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和《白象似的群山》中那對男女所面對的問題也是相似的:女孩因“意外”而懷孕,這是男人和男孩所無力承擔的,他們有著極為顯見的“擺脫”之心,而懷有“意外”的女孩則擁有著另一種心態……在小說的開始部分,余華甚至有意同構,讓相似性更多些,他願意將冒險強化,讓我們誤以為它會一直籠罩在舊故事的陰影下。這是一個有“我”存在的故事,它是由“我”來講述的關於“我和我的愛情”的故事,但小說在開始的部分和回憶的部分卻是以第三人稱來敘述的:它有意和“我”拉開距離,有意保持和《白象似的群山》中的敘述相類似的“純粹的限制性客觀敘述視角”,敘事者既不干涉也不進入,在這一敘述中“我”抽離了情感的介入,而讓它客觀呈現——在這點上,余華和海明威保持著一致,同時保持了一致的還有大量的對話運用,以及每句話都盡可能多的“言外之意”。
恰如哈羅德·布魯姆所指出的那樣,沒有任何一個寫作者願意跟在別人的寫作之後成為“渺小的後來者”,余華在刻意保持著“模仿性”的同時隨時準備著驟然的蛻殼飛升,他就像一個飛速朝水面急墜的雜技高手,就在你以為他必然地會落入水下的驚呼中突然騰起,那種“幾乎落入窠臼”的刺激感正是他的欲求,他要在你以為他仿寫一遍海明威的舊故事的時候他才做出改變,做出延展。
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幾乎只有一個場景,然而余華《愛情故事》中的場景卻是兩個,一個是講述的“現在”,另一個則屬於回憶的“過去”,它的另外一個場景的存在並不是故事的順接而是撐開的,有更複雜的向度;在《白象似的群山》中,敘事的方式只有一種鏡頭式的客觀,而在《愛情故事》中余華有意識地讓和海明威小說構成互文關係的那部分文字同樣地保持鏡頭式客觀,而另一個場景、另一個時段的敘述則是有“我”在場的、是第一人稱的敘事。《白象似的群山》在時間跨度上僅有二三十分鐘,而余華的《愛情故事》則有意跨出了十多年,“這個女孩在十多年後接近三十歲的時候,就坐在我的對面。”《白象似的群山》在批評家貝茨看來是一則道德故事,裡麵包含著對“那個美國男人”的暗暗譴責,“這個短篇是海明威或者其他任何人曾經寫出的最可怕的故事之一。”《愛情故事》同樣屬於一則“道德故事”,只是它有了更為複雜的、深厚的向度,它不僅僅簡單指向最初時段“意外懷孕”的那種“失魂落魄”,而且還指向經歷了當初的愛情之後太熟悉的“青梅竹馬的可怕”。在我看來余華所發明的這一漂亮的短語“青梅竹馬的可怕”真是精妙而可怕,它是這個《愛情故事》最為重要的意蘊延展,是整個故事的重心所在。如果沒有這一“發現”,余華或許不會寫作這樣一篇小說。
《白象似的群山》始終回避的是“墮胎”,小說中用“小手術”替代了它,它被遮掩在敘述的後面;而在余華的《愛情故事》中,“愛情”這個詞也沒有一次在小說的文本部分出現,它同樣屬於被遮掩的部分:在《白象似的群山》中的遮掩是因為點破的恐懼,男人不願意正視它,而在《愛情故事》之中,“愛情”似乎是籠罩性的但它在經歷了十幾年的共同生活後,變得稀薄,幾乎已經無跡可循。
以一個舊故事、舊傳說或者舊情節為支點,再繁衍出一個新的、不同的故事,這在西方的經典文本中並不少見,許多的作家都願意如此嘗試,譬如詹姆士·喬伊斯以古希臘神話為對照創造性地寫出了《尤利西斯》,讓-保爾·薩特的戲劇《蒼蠅》則是以古希臘神話中俄瑞斯忒斯的故事為基礎創造的另一新故事,唐納德·巴塞爾姆的《白雪公主》與格林童話中的《白雪公主》構成奇妙的互文……但在中國的小說寫作中,這樣脫胎於另一經典小說的“互文寫作”卻是少而又少,它容易被人認為是在影響下的寫作,時常會遭受“創造力匱乏”的詬病,這一詬病通常來說也不無道理。再一就是,中國作家普遍在思考力上有所欠缺,我們更擅長生活描述而並不擅長提出追問,而基於舊文本尤其是經典性文本的互文再造恰是對思考的多樣性和深刻度提要求的,它的難度因此更為巨大。
我看重余華的《愛情故事》,更多的是它對難度的呼應,看重的是它在《白象似的群山》這一舊有文本的參照之下做出的延展和豐富。它的意旨包含了《白象似的群山》的全部意旨,它在《白象似的群山》之後又發展了另一層更有意味和思考的空間,讓“我”和我們一起不得不面對。
二、故事講述
“一九七七年的秋天和兩個少年有關,在那個天空明亮的日子裡,他們乘坐一輛嘎吱作響的公共汽車,去四十裡以外的某個地方”——時間,地點,以及一片和男主人公相抵牾的明亮天空,這個反差當然是有意的設計。“嘎吱作響”既是實寫也包含著男主人公的心態反襯,這一路他不會平靜,因此上這輛公共汽車也不會平靜。“車票是男孩買的,女孩一直躲在車站外的一根水泥電線杆後”:這句話很有意味,但余華點到為止,同樣很有意味的還有接下來的那一句:“女孩此刻的心情像一頁課文一樣單調”。
接下來敘述的追光打向了男孩,他的表現和女孩形成著反差,小說中在極短的文字中用在他身上的詞就有“憔悴”、“緊張”、“心神不安”、“驚惶失措”、“膽戰心驚”等等。作為一個“做了錯事”的孩子他無法鎮定。在小說中(尤其是在對一九七七年的秋天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個男孩是主導性的,有一種強勢,他安排和設計著而女孩多是順從和有顧及的遷就,然而女孩始終平靜,在她身上的某種理性似乎未被情緒所左右(他的表現與《白象似的群山》中的男人的表現不同,那個男人為了說服女孩做那個“小手術”而明顯有討好和遷就,不夠穩定但又不得不適可而止的是女孩)……
回到故事。關於一九七七年秋天“那個天空明亮的日子”,小說隻給了一個“準備坐車去某個地方”的情景描述之後便戛然中止,場景以一種“硬轉場”的方式完成了切換,時間也換到了十多年之後,這時敘述也從第三人稱換成了第一人稱,“我們一起坐在一間黃昏的屋子裡,那是我們的寓所……”在這裡,十幾年的時間交給了空白。小說裡還有一句一閃而過的埋伏,“她的第一次懷孕也是在那時候”。這句話裡其實有種特殊的寒光。自始至終,小說沒有提及這次懷孕後嬰兒的處理,也沒有提及他們生有孩子——我覺得這句有寒光閃過的話背後之意其實是種提醒:她不止一次地懷孕過,可能經歷了一次次的墮胎,最終他們也沒有孩子。
小說接下來點到作家洪峰的信,以及“洪峰的美妙經歷”,它是接下來“我”提出終結這種“舊報紙似的生活”的由頭。洪峰,當代作家,先鋒文學代表作家,1959年生於吉林,現居雲南,其人生頗為傳奇——余華在這裡“塞”入他的信件,一是欲蓋彌彰地增強虛構故事的真實性,二是借用洪峰的傳奇性映照此時“我”的生活的平淡,三是強化遊戲的意味,四是讓“我”試圖脫離舊有生活尋到合適的借口,讓故事發生轉圜……
這時,余華借用小說中“我”之口,從不同的角度來闡釋“青梅竹馬的可怕”。是的,“我”的話語裡有強詞奪理和不斷誇張的性質,不那麽道德的性質,但我想我們也應看到它的確是一種現實存在(因為這一節側重於故事講述的方法問題,我們不糾纏其它,這個話題放在後面)。
接下來是回憶,關於第一次的性生活和她懷孕之後的面對,在這裡這段屬於“一九七七年秋天”前後發生的故事沒有交給第三人稱,而是採用第一人稱“我”的角度來完成的。我們似乎可以讀出,這段回憶性的文字多少是“事件之後的回憶”,有一定的時間清洗和慢慢加入的主觀性。這當然是作家的設計,有意而為。面對可能的後果,“我”給出的答案是“自殺”,而她認為“懲罰比自殺好”。男孩給出的答案是回避形的,“自殺”其實是用一種極端的方式逃脫,而女孩的答案則是接受形的,發生的則需要負責,無論它的結果有多麽的重量。
回憶在繼續,這時余華用第一人稱的方式“重述”了之前第三人稱的講述,並讓敘事略略地向前發展了一點兒,就是他和她坐在了車上,一起感受著汽車的震顫——小說中有個細節意味深長,“在汽車一次劇烈的震顫後,她突然哧哧笑了起來,接著湊近我偷偷說:‘腹內的小孩震出來了。’她的玩笑只能加劇我的氣憤,因此我湊近她咬牙切齒地低聲說:‘閉上你的嘴。’”
在這一細節過後,有一段貌似客觀而平靜的描述:海邊的輪船,幾隻灰色的鳥等等。這一方法是現代小說中較為常用的方法,是一種節奏上的調和,同時又延展了音韻,並且可以成為情節之間的轉場銜接。是的,在這之後余華的敘述進行了轉場,平靜而不解釋地轉入到“一九七七年的秋天”,由第一人稱轉入第三人稱:“汽車在駛入車站大約幾分鐘後,兩個少年從車站出口處走了出來”。
場景,情境。畫面。鏡頭感。兩個孩子面對同一境遇不同情緒和態度的張力。在男孩看到女孩從商店裡走出之後,兩人有一段對話,它其實可以和《白象似的群山》中兩人的對話相比較。在《白象似的群山》,女孩是主導性的,那個男人是個小心翼翼的“話多的男人”,話語也是柔和的,而在《愛情故事》中,男孩是主導性的,其話語有一種冰冷感,至少是冷峻。在《白象似的群山》,女孩對“白象似的群山”的比喻是有意的、化解性的偏題,她在回避對那個手術的面對,而在《愛情故事》中女孩提議“去商店看看吧”和“我很喜歡這條裙子”卻不代表她對問題的回避,而是其它:譬如她願意為這個心愛的男孩接受後果,譬如她大約試圖用這種方式為男孩舒解,譬如她……《白象似的群山》中女孩面對自己的處境是有怨懟的,而在《愛情故事》中則不包含這一成分。這些,當然是從他們的對話中滲透出來的。
“女孩的嗓音在十六歲時已經固定下來。在此後的十多年裡,她的聲音幾乎每日都要在我的耳邊盤旋。”用這句漂亮的、富有詩性的句子再次轉場,再次,從一九七七年的秋天脫身回到“我”和三十歲的她一起坐著的那間屋子裡,那個黃昏。
“我”繼續闡述平常平靜所帶來的乏味。
“她停止了織毛衣的動作,她開始認真地望著我”。這話其實也有深意所在。之所以前面她沒有停止動作,沒有認真地望著“我”,大約是:“我”的這類抱怨之前有過,但最終複歸平靜;她不覺得“我”是認真的,所以也沒認真對待。但這一停止,其嚴峻性也就真得來了。
又是一段對話,男人的回避,“我沒有否認,而是說,‘這話多難聽’”。“我”在意的是話語的難聽,而不是其實質——余華在書寫中的冷再次呈現出來,在這篇小說中,這種冷其實是時時在場的,儘管他書寫的是“愛情故事”。
小說結尾。“我”依舊固執地回憶著一九七七年的秋天,“我”說那個時候“我可真是失魂落魄”,已經成為三十歲女人的女孩糾正“我”,你沒有。我說我確實是失魂落魄了,她繼續說不是,你只有一次失魂落魄。“什麽時候?”“現在。”這是小說的高潮,它形成著渦流,在這裡,余華及時而有力的收住,余音卻在悠長地回響。
整個故事中,一九七七年的那個秋天居於核心,我們可以分明地看見那個男孩(或者說,“我”)的表現有失魂落魄的成分,而她卻並不認為那時的他是失魂落魄的,男孩(“我”)真正的失魂落魄只有一次,就是向她闡述了“青梅竹馬的可怕”並提出分手的“現在”。為什麽如此?真的是如此麽?她的看法中,包含了什麽?小說沒有給出答案,它留給了閱讀者和大片大片的空白。
……《愛情故事》設置了兩個場景,兩個“現在”,我是說故事講述的“現在”——它在以監視者視角講述一九七七年秋天的故事時所呈現的是發生的“現在”,而轉以“我”的視角與她對話的時候所呈現的也是“現在”狀態,雖然這兩個“現在”相隔十多年——它們相互交纏,在講述中又互有滲透。
是的我承認《愛情故事》的講述完全可以不這樣“複雜”,最為簡潔的方法是:將故事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講述男孩和女孩去四十裡以外的某個地方做檢查的故事,在那個時間裡充分展開;第二部分,則集中講述十幾年後,男孩和女孩組成了家庭,他們現在的感受,“青梅竹馬的可怕”和試圖分開的故事。內容上不做半點兒的減損,而故事卻可以更順暢簡潔,容易進入。這當然是可以的,能夠完成的,有一些小說就是采取類似的方式——為什麽余華不採用?為什麽,他要採用複雜的、甚至會阻擋一部分閱讀者的這種方式?
我認為,余華要考慮的一點兒是交融性,他需要兩個故事始終是交融的、粘接的,而不是分散的——何況,如果兩個故事霍然地分開,那前面的部分就盡是《白象似的群山》的呼應性改寫,會極大地消耗掉小說的意味。我們還看到他在兩個視角相互交插的過程中,以“我”的視角重述了記憶裡的故事並將它前推,這一做法就使二者的關聯性、整體性進一步強化,它類似於中國建築的“榫鉚式結構”,是互搭的,共同受力。
敘述的陌生化也是余華採用這種結構方式的動力之一,他需要在敘事中完成冒險和創新,即使在技藝的使用上也沒有誰希望自己是跟在別人之後的渺小後來者。他和他們試圖向難度和更難度挑戰,我們如果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有一個統一性考量的話,我們會發現向難度、向陌生、向新穎和變化發起挑戰是一種普遍和流行。有人說十九世紀以來世界上所有的風格樣式,所有的嘗試都在中國的“八十年代文學”中對應性地嘗試了一遍,大約不謬。也就是在那一個時期,中國的文學趨向於複雜和多樣。我猜度,余華將兩個場景交融到一起還有一層考慮,那就是“青梅竹馬的可怕”也是延綿的,它是一個整體的愛情故事但也是一個整體的,愛情不斷麻木和消損的故事。
《愛情故事》較為充分地展示了余華在故事講述上的能力。他對節奏的把握和控制,場景的描繪中的鏡頭把握和那種有意外的“身臨其境”感,言外之意的精心設置,對話中人物心態和性格的展示……
我想我們大約還可注意到,余華在人物對話的設計上的用心:短語,基本上能看出剪裁感,既讓它完成人物個性和心態的展示又讓它“統攝於”整個敘述語調中——在人物對話上,余華一直將統攝的控制權牢牢掌握於自己手中,他筆下的人物大約永遠不會說出“千不好萬不好也是爹啊,俺心煩意亂,睡不著。越睡不著心越煩,越煩越睡不著。俺聽到那些菜狗在欄裡哼哼,那些肥豬在圈裡汪汪。豬叫成了狗聲,狗吠出了豬調;死到臨頭了,它們還在學戲。狗哼哼還是狗,豬汪汪還是豬,爹不親還是爹。哼哼哼。汪汪汪。吵死了,煩死了(莫言,《檀香刑》)”這類的話——余華不會讓他們這樣說話,即使在他筆下的那個人物類似於莫言筆下的這個。余華筆下的人物對話具有某種的“統一性”,就像莎士比亞筆下、馬爾克斯筆下、胡安·魯爾福筆下的人物也具有類似的統一性一樣。他要他們說出的話符合敘事所要求的統一性美感和統一性腔調,所以無論什麽樣的人物來至余華或者莎士比亞、馬爾克斯筆下,他們的話語都會進行“適應性”剪裁並可能添加裝飾性羽毛,而在莫言那裡則又是一種不同。兩者各有優劣,我們也許不能完全地偏袒任何一方。

三、“青梅竹馬的可怕”
《白象似的群山》是一個道德故事,一個男人,美國男人,用種種的手段說服了西班牙姑娘,並“陪同”她去墮胎。《愛情故事》本質上也是一個道德故事,只是它在舊文本的基礎上更有演進。在《白象似的群山》中,作為愛情的部分已經發生著搖晃,男人的話語裡滲透了某種自私,狡猾,虛偽,他試圖用墮胎的方式化解掉屬於自己的危局的意圖是掩飾不住的(儘管米蘭·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曾為這個美國男人百般辯解)。故事以一個片斷的方式結束於他們在小酒館前的等待,但我們似乎可以想到之後的可能結果:女孩墮胎。她以服從的方式試圖挽留住這個男人,但是……
而在余華的《愛情故事》中,他按住了那樣的發生:女孩墮胎,男孩依然在她身側,並且和她進入到婚姻中:從青梅竹馬到花好月圓,中間的波折似乎可以看作是微瀾,這個男孩在一九七七年秋天和女孩去檢查時同樣滲透出的倨傲暴躁,自私和怯懦都可有所忽略,它並未深入地影響到所謂的“結果”。然而。
然而危機還是來了。它甚至更有“本質性”。
小說中,余華讓“我”一遍遍地這樣提及:
“難道你不覺得我太熟悉了嗎?”
“你對我來說,早已如一張貼在牆上的白紙一樣一覽無余。而我對於你,不也同樣如此?”
“我們唯一可做的事只剩下回憶過去。可是過多的回憶,使我們的過去像每日的早餐那樣,總在預料之中。”
“在你沒說話的時候,我就知道你要說什麽;在每天中午十一點半和傍晚五點的時候,我知道你要回家了。我可以在一百個女人的腳步聲裡,聽出你的聲音。而我對你來說,不也是同樣如此?”
“因此上我們互相都不可能使對方感到驚喜。我們最多只能給對方一點高興,而這種高興在大街上到處都有。”
……
重新提到余華的那個漂亮的短語,“青梅竹馬的可怕”。男人的這些話的確含有“強詞奪理”的片面性,我們暫時略過被他的話語引發的道德評判,而轉向對這些話語的認真審度:它會不會是一個人的真實想法和看法?它是否是一種真切存在?
沒錯。它存在。或多或少,或淡或濃。否則我們也不會創造“熟視無睹”這樣的成語。即使童話裡的王子和公主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也需要新鮮和調劑才有恆久的保持,而我們常見的卻是消損,不斷的消損。消損可以說是一個常態,這完全可以在心理學中找到合理的解釋,不過處在消損中的男人和女人出於種種的規約、計算和考慮,有時會裝作它並不存在,有時會忽略它回避它,而已。在日常中,在生活中,大約每個人都有一個“沉默的幽暗區域”,有時它完全像深淵一樣寬泓,但多數人采取的是回避策略,不看它,不知它,不問它。久而久之,我們也會“遺忘”掉它的存在。
但作家們不同。作家們往往注意的、或者更注意的就是這個沉默的幽暗區域,他一次次向深淵處窺探,並通過小說的或詩歌的方式把我們引向這個深淵,讓我們和他一起面對。卡夫卡的《變形記》,他采取的方式即是如此,通過格裡高爾·薩姆沙的變形,讓我們和他一起窺見在父母之愛、兄弟之愛這一珍珠上的暗影,讓我們和他一起窺見,在愛的掩藏之下那些屬於個人人性中的被忽視的微點,讓它放置於顯微鏡下:於是這些私和偽,第一次被他“放大”到那個驚人的樣子,它顯示了它的吞噬力和它的可怕。余華的《愛情故事》同樣如此,他把我們引領到“青梅竹馬”這個詞的面前,然後把一個顯微鏡遞到我們手上。
我們於是窺見。
原來,在這個美妙的詞的後面,卻是一道不被注意的深淵。
對於這個男人來說,熟悉已經消磨掉了他大致原本就稀薄的愛情(在“我”描述兩個人之間的第一次時,裡面的愛的成分就是相當薄弱的,隻提到了“欲望的一往無前”),甚至已經消磨掉了他的欲望,在經歷了一九七七年秋天的懷孕事件和後面的婚姻之後,這十年的時間裡他過的只是平淡而平庸的“日子”,它沒有驚喜,一覽無余,總在預料之中,每天都是舊的。
“‘我們從五歲的時候就認識了,二十年後我們居然還在一起。我們誰還能指望對方來改變自己呢?’她總是在這個時候表現出一些慌亂。”——小說中如是說。它意在標明,他和她都已無可改變,沒有改變的指望,驚喜不會在改變中出現,一覽無余是生活的必然。“她總是”,小說也在提示我們這個男人大約不止一次地這樣報怨過,他的怨懟也是積攢起的。被生活和日常磨掉的缺損由他的怨懟來填補著。
在小說中那個女孩(後來的“她”)一直“後知後覺”,“我”所說的這種磨損、消耗和驚喜的匱乏在她那裡似乎並不存在,她安於這樣的生活,安於那種平靜和平淡——《愛情故事》中男孩(“我”)和女孩(“她”)對待事物、事件的態度上的不同也是非常值得品味的點,如果說“青梅竹馬”有AB兩面,她就處在與這個男孩(“我”)不同的那一面。我們看到她被動於安排,但她總能以一貫之地接受,更多地表現出的是略有木然的安於。在她那裡,也許愛是一種更為堅固和未曾消損的東西,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可能:她覺得生活只能如此,最好如此,並不存在更好的選擇性。無論怎樣說她都能喚起我們的悲憫,她,在這樣的生活中。她和男孩(“我”)之間形成著一種不同頻的力量。
“你沒有失魂落魄。”她說。
“你不用安慰我,我確實失魂落魄了。”
“不,你沒有失魂落魄。”她再次這樣說,“我從認識你到現在,你只有一次失魂落魄。”
我問:“什麽時候?”
“現在。”她回答。
小說至高潮處戛然而止,它反覆出現和被強調的是“失魂落魄”這個詞。無疑,男孩在一九七七年秋天的行為確可認為是“失魂落魄”的,但在她的眼裡卻並不是,真正的失魂落魄出現於“現在”,也就是他強硬地提示了青梅竹馬的可怕並提出分開的“現在”。
何出此言?
這是個問題。
小說最大的爆發力集中於“失魂落魄”這個詞上,它那麽集中地在篇尾出現而前面卻沒有呼應性地埋伏,這是余華有意安排的險棋,他要用突然性來強化效果。問題是,如何理解“失魂落魄”這個詞,如何理解他在一九七七年秋天的表現不能算失魂落魄而現在才是?
這個難以用另外的詞來完整解釋的詞,這個可以吸納你的經驗、思考而總感覺仍有未明的、未被完全說清的詞,恰是小說最為晦暗的妙筆。
四、藝術的,道德的
余華的小說尤其是短篇小說多給人以精致的美感,結構講究,敘事精到,語言中有著充盈的詩性——閱讀余華的小說往往是一場充滿著趣味和起伏感的美妙旅程,它時有險峻,時有平靜,時有絲緞展開時的滑暢,時有極具吸納力的渦流……余華的語言有一種硬朗的潤澤,是的,它兼有硬朗感同時又兼有潤澤感,有著小小的鏗鏘又有著讓人愉悅的流淌性……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他把中國小說的敘事語言推向了一個高度,我以為。在余華那裡,尤其是在他的短篇小說那裡,他的精心和才華同時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一向耐心而謹慎,我一向認為小說是設計出來的,那種完整性、那種了無痕跡的自如恰是耐心和謹慎的表現。
余華擅用比喻,那些奇妙的而又極有準確性的比喻是余華小說中最讓人驚豔的魅力之一,它讓余華的小說總有不斷閃爍而起的光,這光構成了通道。余華擅用比喻,說他擅用其實還包含了他在排布比喻時安插上的精心,他不會讓比喻連接比喻讓它們過於繁華而又在相互的爭奪中失色,也不會讓某一段敘述過於平淡找不到語言亮點的所在。是的,比喻的使用其實可以看出他的精心布局,更不用說情節和細節的使用了。
小說開頭的第一段,從平常的敘述開始,是介紹性的,但它裡面有意地設置了起伏感,不是簡單的事件描述。公共汽車,男孩和女孩,當敘述之光打在女孩身上時,余華使用的比喻是:“女孩此刻的心情像一頁課文一樣單調”。後來,他又說“我覺得自己沒有理由將這種舊報紙似的生活繼續下去”,又說“你對我來說,早已如一張貼在牆上的白紙一樣一覽無余”,“他們的說話聲在夜空裡像匕首一樣鋒利”,“我感覺自己像是被裝在瓶子裡,然後被人不停地搖晃”……這些比喻有著良好的新穎度,它讓我們的漢語甚至生出了些許的陌生;而它們落在小說的那個情境裡又讓你感覺太貼切、太美妙、太精確了,以至任何一種描述包括使用貌似更準確的客觀敘述都遠達不到它所提供的精確。
除了語言的詩性美妙,我覺得余華的語言還有另一微妙,就是他充分地發揮著語言的、故事的“計白當黑”的能力,更多地讓語言生出多重和歧意。他應當熟諳海明威的“冰山理論”——海明威把自己的寫作比喻成在海上漂浮的冰山,用文字表達出來的東西只是海面上的八分之一,而八分之七都在海面以下,它屬於省略或有意的掩藏。它必須是有意的掩藏,也就是說,海面下的八分之七,作家知道,懂得,對它的省略是種故意,而不是非要依借闡釋甚至是過度闡釋來完成的:余華的《愛情故事》也是如此。在解析它的“故事講述”的時候我已經提到,譬如“她的第一次懷孕也是在那時候”,譬如“她總是在這個時候表現出一些慌亂”,譬如“她”回答說“我”真正的失魂落魄的“現在”……它們有豐富的言外之意,它們有著暗暗的提醒,它們,有時會自己形成渦流。
……其它的妙,應在閱讀中(包括反覆的閱讀中)體會。
我想我需要承認余華的《愛情故事》是一則“道德故事”,它的裡面有著潛在的道德追問,雖然余華並非站在“我”的一方也未站在“她”的一方,雖然這一道德追問更多地是喚起作為閱讀者的我們並由我們發出的。和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一樣,我們看不到任何一句具有價值判斷的話,也沒有標明作家情感和好惡的形容詞,沒有,它有的只是貌似的客觀,讓小說中的“我”按自己的理由來說話,哪怕有些話我或我們並不那麽認可。
呈現,讓我們信心為真,並從另外的角度審視小說中的他和他說的,發現它的合理也發現它的問題所在……真正優秀的作家會在他的故事中“藏身”,他不會前呈地介入對其中的人物指手劃腳,哪怕他對其中的人物有著特別的愛恨。從這點上,我極為認同米蘭·昆德拉所說的“懸置”,小說的智慧產生於道德懸置的地方,它不是說我們對人物、事件和情感沒有判斷,不是,它說的是我們在寫作的過程中不應對處在故事中的人物思想、行為有指向性、道德性干涉,那樣會導致故事的“失真”,也會影響故事的說服力,我們需要知道假設我們設定了一種真實那就必須要接受它的“必然後果”。
小說裡的“我”就是這樣想的,他覺得一覽無余的生活實在匱乏得難以忍受,他認定青梅竹馬有著它的可怕,作為作家的余華絕不應對他的認知有半點兒的“校正”,不能,他需要保證他預設的真實和後果的必然;至於“她”,作為作家的余華理解也好,同情也好,厭倦也好,可憐也好,在完成文本的過程中並不重要,他沒有權利把“她”從“她的生活和她的想法”中拉出,他要做的只能是接受後果,並將它藝術地呈現出來。
“人類渴望一個善與惡能夠被清楚地區分的世界,因為他有一個天生的、不可扼製的願望,就是要在他理解之前做出判斷……他們只能這樣來對付小說,那就是把小說的相對和模糊的語言翻譯成他們自己絕對肯定的、教條的話語……這種‘是與不是’囊括了一種無能,無能容忍人類事物最基本的相對性,無能正視上帝的不存在。”在《貶值了的塞萬提斯的遺產》一文中,米蘭·昆德拉的這段話實有振聾發聵之感,我們的批評太多時候做的就是這樣的事,他們無視小說的藝術倫理和獨特的呈現訴求,他們希望確定,希望善惡在出場的時候就帶著臉譜。
作家的寫作當然存在它的道德性,那就是在習焉不察中、在繁複混亂的生活表面做出自己的“發現”,他要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東西,並用小說的方式來呈現它、確認它、強化它。認知和思考交給聰明的閱讀者吧,他們會通過作家呈現的世界來追問:生活如此嗎?非如此不可嗎?有沒有更好的可能?
如是,等等。
“真正的作品不需要指控,作品的邏輯足以表達道德的要求,得出結論是讀者的事”。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曾如此說到。
五、“在西方文學的影響下寫作”
在西方文學影響下的寫作……八十年代中國先鋒文學被認定是一種“混血生長”,它們的文字中包含有“狼奶”的氣息,受西方文學的影響巨大——這一點不可否認。但一個大約被忽略的事實是,中國的先鋒文學中詩歌更多地是受歐洲和美國詩歌的影響,而小說則更多地取自於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文學爆炸”更顯勁和直接地影響到中國的先鋒小說,而所謂(以歐洲為核心的)“西方”對中國小說的寫作影響有某種間接性:歐洲小說影響拉美,拉美小說影響中國。在這裡我並不是諱言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歐洲文學以更為的強勁的風勢進入到我的國度,我要說的是,中國的先鋒作家們更多地從拉丁美洲的文學中而不是從歐洲的小說中“看到了借鑒的可能”。
歐洲的小說重思辨,更強調哲思和社會學認知,它對知識、智識的要求相對苛刻,但同時它也略有沉悶和堅硬之嫌,在閱讀和理解上有一定難度。中國作家普遍在哲學思辨和社會學認知上有欠缺,邏輯思維的訓練不夠,這樣的欠缺是難的速成的渠道,它更多地是緩慢積累而且需要一個普遍的提升才能達至,更不用說智識上的求新和抗衡了。
我們當然可以說中國的或東方的智慧如何如何高卓,伏爾泰、卡夫卡、尤瑟納爾等人無不從東方的尤其是中國的智慧中汲取滋養——這自然是事實,但可汲取與是另一株枝繁葉茂的樹是兩個概念。寫作《西方哲學史》的弗蘭克·梯利不無誠懇地說過,“哲學通史應包括所有民族的哲學。但是並不是所有民族都產生了真正的思想體系,只有很少民族的思辨具有歷史。”“許多民族並沒有超越神話階段。即使是東方民族的理論,印度、埃及和中國的理論也主要是由神話和倫理學說構成,他們的理論並不是完整的思想體系,而是滲透在詩歌和信仰中”——這是我們不得不正視的限度。
我不是說中國的小說家們不重視或者不希望從西方文學(歐洲文學)中汲取,絕對不是,我的意思是另外一重:中國小說家們思考的是如何在汲取西方文學滋養的同時形成獨特性,形成對西方尤其是歐洲文學的“反哺”——這時,拉丁美洲的文學進入到中國,它讓中國作家們看到了另外一種“反哺”的可能,這就是拉美作家們的做法。一是強化地域的陌生感,它本身就具備獨特標識,那種生活和對生活的認知是西方文學所沒有的,它具有經驗上的獨特性。當然僅有經驗上的獨特性是不夠的,它還需要以一種現代的眼光來審視和改造,甚至可以容納小有的誇張,這一點,屬於中國的獨特經驗完全可以完成,我們是有和拉美作家們相抗衡的資源的;第二,是在故事的講述上下功夫,變換出更多的花樣兒來:在內容的深刻度上如果我們無法形成對西方(尤其歐洲)的反哺,那我們就在技藝形式上做出新提供,當然這一新提供的前提是思考性並不太弱……出於種種的原因和作家們的審度,諸多的先鋒作家更多地調整,向拉美作家學習,更多地學習了技藝經驗,他們在一段時期裡至少豐富了中國故事的講述樣貌,為中國的文學提供著豐富性的新質和可能。
向拉美的反哺經驗學習,從拉美小說中汲取,眾多的中國作家轉借、拿來,逐步完成了自己的講述樣式與個人風格。說實話這也是相對容易學到的部分,更便於拿來並完成改造的部分。所以在一個時期內中國作家首先提升的是故事的講述能力,在技巧上的臻熟幾可與任何經典性文本相媲美。莫言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於斯德哥爾摩的演講題目即是《講故事的人》,其實在那個時期裡多數先鋒作家都是“講故事的人”,他們從拉美、從歐洲的技藝經驗中獲得很多,並已完成了個人的消化。
在余華的寫作中我們當然可以看到馬爾克斯、胡安·魯爾福的影響,他的故事設計、語言方式甚至人物行為的某些“誇張”都依然帶有“拿來”未褪盡的尾巴。在今天,我們必須承認沒有任何一種寫作、任何一種藝術還可以憑空產生,來自於人類的任何藝術經驗都可以借鑒並讓它成為我和我們的,“影響的焦慮”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學習和借鑒激發屬於我們的創造性。在這裡,我願意把余華的《愛情故事》看作是這一話題的隱喻:它大約脫始於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然而那只是支點,我們看到余華的《愛情故事》是一個很中國化的、有中國經驗納入的故事,它同時有了另外一層的延展和開拓。這延展和開拓,使它成為了另一篇有深意和新意的小說。
【作者李浩授權分享】
作家李浩

李浩,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著有小說集、評論集、詩集共計20余部。
曾獲魯迅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蒲松齡文學獎、林斤瀾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