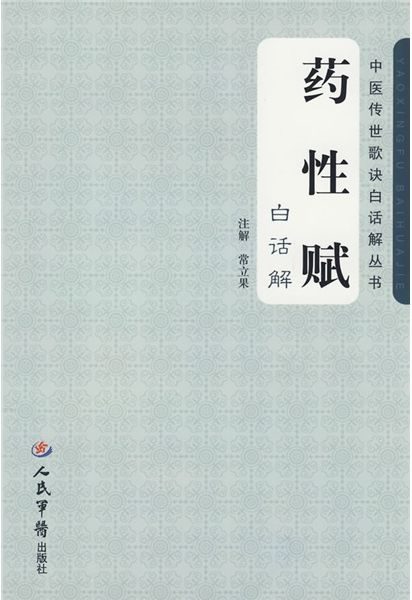張煒,1956年生於山東龍口市,原籍山東棲霞。其80年代前期所創作的長篇鄉土小說《古船》是一部具有史詩品格的長篇力作,成為20世紀80年代文學創作潮流裡長篇小說中的佼佼者之一。
2011年,張煒憑借耗時20余年所創作的七百萬餘字大河小說《你在高原》榮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背誦和朗讀
“這個時代是朗讀的荒野。”
現在是一個網絡時代,資訊像潮水一樣湧來,我們難得像過去一樣耐心地閱讀。這是一個迅速的、並且是一再提速度的時代。許多東西正在泡沫化,像泡沫那樣飛揚,轉瞬即逝。在這個時代裡,一個人要記住什麽,比如牢牢記住有意義的東西,將是十分困難的。
所以,一些很優秀的人就走在相反的路線上:回到一些古老的閱讀與記憶的方法上來。比如讀書,不光是看,還要朗讀。古文,好的小說,詩,應該朗讀。這是個美好的過程,這個過程會引起進一步的感動、聯想和回憶。對理想的追求,對境界的領會,都在同一時間裡得到加強。字裡行間有一種鼓舞的力量,需要聲音去傳遞和強化。
再就是抄寫了。好的文章要一筆一筆抄下來,以體味從字到文的過程,感受文字的意義。古文要抄下來,詩要抄下來。這些辦法好像太笨太慢,但有以一當十之功。時代強加給我們的精神疾患,比如浮躁、恍惚,不求甚解,被我們用抄寫——這個古老而簡單的方法給遏製了。時代越快,我們就越慢。當我們進入了一個緩慢的系統之後,時代的流行病毒對我們也就無可奈何了。
回想一下,現在人們朗讀的興趣和欲望是大大降低了。記得在二三十年前,那時候的人是很願意朗讀的。古今中外,我們身邊,都有一些朗讀的好例子。你會記得中學時代,那時候寫出一篇東西來會有怎樣的衝動——遠方總是有一個朋友,總是有一個知音,總是有一個文學的耳朵;而你總是恨不能立刻把一切呈現到他的面前——不是從視覺上,而是從聽覺上,越快越好。
我們是否擁有這樣的記憶:天正下雨,你把剛剛寫好的東西用塑料布包好,走幾十裡路,只為了去找一個人——為了說不清的熱愛,為了贏回那一小會兒的驕傲和陶醉。如果我們發現了一本好書,也會帶上它走很遠的路,翻山過河——只因為山的那一邊有一個人,只為了讓他與自己一起感動。
可見,誰發現了一本好書,這本書首先感動了誰,都會成為一樁可資記憶的快事。
傳遞好書可能是人的一種義務。那些真正優秀的人,往往一生都保持了這種對藝術和思想奔走相告的勁頭。
現在我們偶爾還能遇到這種人:他們時刻準備著去朗讀,以分享幸福——可是當這個人正處於激動不已的時刻,山那邊還會有一個傾聽者嗎?
山那邊的人正轉向了其他的興趣,在看電視連續劇,在酒吧裡,在網上。人們變得口味粗疏。結果這個人再也找不到一個喜歡傾聽朗讀的人。
你可以找到一本好書,由於它好得不得了,忍不住就要找人共享——四下裡遙望,到處都沒有你所要找的人。於是你就像站在了漠漠荒野裡一樣。
這個時代是朗讀的荒野。
有人寫了一個得意的片斷,很想像當年那樣用塑料紙包好,冒著雨雪翻山越嶺、過河,去讀給一個人聽。很可惜,山與河俱在,聽他朗讀的人卻沒有了。雖然這個時代的文學人士比過去翻了幾倍,可是他們都不願朗讀了,也不願聽別人朗讀。
那個尋找朗讀的人可能心懷了一種古老的情緒。情緒也可以古老,這在我們年輕的時候是無論如何也沒有聽說的。但這是真的。
朗讀,這不僅是一種對待文字和語言的形式,不僅是一種狀態,而是孕含了一種生命的品質。
有人仍然具有當年的那種熱情,但是大大降低了。一個人成熟了,老練了世故了,就懂得隱蔽自己:什麽都隱蔽,從情感到激動。有人連友誼也要隱蔽起來。所以說這是一種遮遮掩掩的生命,是生活品質的降低。
記得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有兩個天資非常好的文學少年,當年一個十七一個十九,天各一方,誰也不知道誰。其中的一個由於偶然的機會看到了另一個的作品,感動不已,馬上遠遠趕來。他們的相見對於彼此都是一件大事。後來幾十年過去了,一個仍然在寫,另一個卻轉而經商,並成了大老闆——他對文學的信念完全喪失了。偶爾大老闆還是要想起少年時代,想起與那個夥伴在一起的場景:他們那時急急相約,就為了心中那團火。那時他們一夜一夜不睡,激動得奔走不停,吸煙,一個聽另一個滔滔不絕地朗讀。就是這樣的一種氣氛和感覺,他們本來可以如此一生——可是時代把他們分開了,分得越來越遠。大老闆有一天又想起了往昔的夥伴,心裡一熱,就從很遠的南方趕到了北方。
他們在深夜兩點見面。一個見了另一個,竟然馬上想到的是為對方讀新寫的作品。
大老闆在聽,一直聽到了黎明。他一聲不吭,迎著曙色吸煙。後來他回過頭,讓人發現了滿眼的淚水;半晌,他小聲說了一句:“原來文學在默默前進……”
大老闆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十幾歲時可以一口氣背兩個小時的唐詩。他一直著迷於朗讀,願意背誦。
回頭再說那個大老闆的朋友——深夜朗讀的人。這個人在十七歲的時候,由於各種原因,背著寫下的一大包東西和喜歡的幾本書,到南邊大山裡流浪去了。他一邊打工做活,一邊到處尋找喜歡朗讀和寫作的那種人。七八年的時間裡他隻找到了兩三個:有兩個像他一樣既能寫又能讀;有一個女的,她喜歡寫,一邊寫一邊哭,但她不太喜歡聽別人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