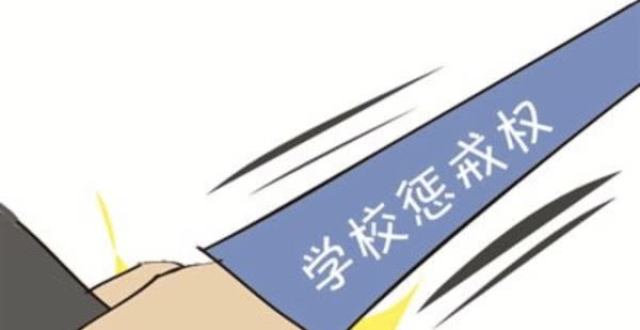原載於《上海文學》2018年第6期
倒立行走
蔣軍輝
1
好吧,現在,讓我給你們講講我的老師馬玉寶。
馬玉寶老師是我初中時的班主任,我剛讀初一時,他還是個民辦教師,有點胖,像個地主。他站在講台前,兩隻手一抖一抖的樣子,常常讓我聯想到一條直立的狗。每天早上校鈴一響,他準會騎著那輛破自行車衝進校門。兩分鐘後,走廊上便傳來“吧唧吧唧”的腳步聲,像是什麽東西在有節奏地拍打著地面。那聲音是由被他當拖鞋穿的解放牌膠鞋製造的。老師的肚子每次比腳先進教室,偶爾幾次比肚子先進教室的是殘留在他鞋子上的泥巴,伴隨著橡膠鞋的拍打,“吧唧”一聲被甩在了門上或水泥地上。老師的臉一進教室門,我們的班長便響亮地喊一聲:起立。這是老師的得意創舉,全校唯有我們班是老師到教室門口,全體學生起立,致敬,吼一聲:老師好。這個規矩剛開始實施時,任課老師們都站在門口不知所措。我們的英語老師進入教室時可能正陷入沉思,班長響亮的一聲“起立”把她給嚇了一跳,不斷誇張地拍她那脆弱的胸口。
老師褲腿挽得一隻高一隻低地走進教室,身上漫散著一股大糞和莊稼的氣息,他歷聲叫道:坐下!上節課講到哪了?老師是學校唯一一個頑強地堅持用國語上課的民辦教師,他的國語不土不洋,如同一堆夾雜著亂碼的文字,一段連貫的話變成了一小截一小截的碎片,連蒙帶猜我們也只能理解個稀裡糊塗。我們曾一致要求老師用土話上課,老師斷然拒絕了我們的無理要求,老師說:你們都要走南闖北的,國語是唯一能讓全國人民都能聽懂的話,我要教你們講國語。
初一第二學期老師轉正了,變成了公辦教師。老師早就擁有了轉正的資格,但前幾次他沒請客送禮,名額就一直輪不到他。他老婆罵他是個飯桶,除了一肚子屎外,什麽本事也沒有。老師糾正他老婆的錯誤,說那應該叫糞桶,不叫飯桶。氣得他老婆真的要到糞缸裡舀糞給他吃。老師說:真乃不可理喻也。老師說的是國語,他老婆聽不懂,說:你罵誰?你罵誰?邊說邊伸出手掌要打他嘴巴。老師只好用土話對剛才的話作出解釋:我說我真是個軟蛋。後來老師在他老婆的押送下給主管評審的幾個長官送了禮,才順順當當地轉了正。
那時候我們班成績在年段倒數第一,老師心急如焚,他苦口婆心地教育我們:讀書要有一種老牛啃石板的精神,我教了這麽多年書,什麽課都教過,這些課我自己也不懂,怎麽辦?就是憑著老牛啃石板的精神,先自己啃下來,再教你們。不過老師的老牛啃石板經常有啃不下來的時候。他教我們數學,在講題的時候,常常講著講著便愣住了,講不下去了。這時他把我當救星。這道題該怎麽解呢?老師想請你們開動腦筋,看誰最聰明。老師說。然後他環顧一下教室,把我叫到黑板前,等我做完了,他便說:有沒有做對?對了,你真聰明,大家要向他學習。那時候我便會露出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臉。有一次下課時我回想自己剛才在黑板上做的題目,發現解錯了,而老師依然判我是對的。我連忙去找老師。老師看著那道題目,皺著眉頭聽我講解了半天,最後說:你真的認為現在的解法是對的?
是的。我說。
其實上課時那種解法也是對的,是嗎?他狡黠地眨著小眼說,邊說邊從抽屜裡摸出兩粒大白兔奶糖塞在我手裡。
初二下學期,老師被剝奪了教數學的權力,改行教美術。學校找到了一個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的小青年來教我們數學。老師對此憤憤不平。
一個連大學都考不進的人,會教什麽數學?他說。
他的不平並沒有持續多久,他的精力很快被繪畫所吸引,每次路過他的辦公室,我們都能看見他光著膀子在白紙上畫個不停,畫得滿頭是汗。
馬玉寶,你是在畫畫還是種地?出這麽大力!旁邊的老師對他說。
老師見了我們,衝我們招招手,我們走進辦公室,只見老師的辦公室裡攤著各種畫冊。
這就是藝術!老師指著這些畫感歎道,這就是大師!接著,他拿出一張他畫的水彩畫讓我們欣賞。畫紙上,有一團綠色和一灘褐色,讓人情不自禁地想到一隻惡作劇的貓,掉進了顏料缸裡,然後在上面滾了一下。
老師,你畫的大白菜真好。我奉承道。
他瞪著我,接著臉一紅,囁嚅著,我,我畫的是一棵松樹。
老師希望我們在學好數理化的同時,能和他一起在藝術世界裡走一遭。有一次,上美術課,老師提著一塊小黑板走進教室。今天我們來畫素描。他說。他看看我們,不知在猶豫什麽。然後,我們看見我們的老師把小黑板轉了過來,掛在了黑板上面的釘子上,小黑板上用圖釘釘著一張圖片,圖片上是一個裸體男人的雕像!雕像上那個也許不應該出現的部件赫然在目!
男同學指著那個地方嘻嘻哈哈地鬧,女同學全部趴在了桌子上不敢抬頭。
這是藝術!藝術!老師說。他顯然有些不知所措。
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個裸體男人叫大衛。
在學生們勉強安靜下來之後,我們的老師開始給我們示範畫法,他不是教我們素描,而是線描,當畫到那個部位的時候,我們的老師顯然猶豫了一下,但他還是決定畫下去,因為這是藝術!然後,我們看到,我們的老師,把那個地方畫成了——一個葫蘆!
男同學哄堂大笑,有的還拍起了桌子。女同學們都不敢抬頭看。
第二天,有三個女學生的家長跑到了學校,揪著老師就要打。
他在課堂上耍流氓,讓學生畫雞巴。他們很憤怒,這個流氓,你們說該不該打?
這是一個雕像,一件藝術品,美術學院還有真人的裸體讓人畫呢。老師辯解道。
什麽?你還想光屁股讓她們畫?一個家長衝著老師的臉就是一拳。
校長及時趕到,了解了情況後,當著家長的面把老師狠狠罵了一頓。於是,老師被剝奪了上美術課的資格,改行教音樂。
我們的老師居然會彈風琴。那時候我們沒有音樂教材,老師就自己刻印歌曲。老師刻印的都是當時流行的一些影視歌曲,我們都愛唱。他又黑又粗的手指有力地敲打著風琴的鍵盤,粗啞的喉嚨裡發出勞動號子般有力的聲音:身雖女兒身,心是壯士心……(香港電視連續劇《十三妹》主題歌),唱的還是粵語,直唱得額頭上青筋繃起。老師沉浸在他的音樂裡,常常聽不到下課鈴響,直到我的同班同學,他的兒子紅著臉站起來對他喊:下課了!你耳朵聾啦!他才回過神來,問一聲:下課啦?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後,他便擺擺手,說:下課吧。
2
我讀初二那年的秋天,老師突然失蹤了。一個大屁股的粗俗女人怒氣衝衝地趕到學校,有人告訴我,這個人就是馬玉寶的老婆。女人搜遍了學校的每一個角落,甚至無所顧忌地進入了男廁所。她在學校裡蹲守了一個星期後,老師鼻青臉腫地再次出現在了我們面前。
馬老師落在那個女人的魔爪裡了。同學們嬉笑著說。
那時候老師還在給我們上數學課,那節課上的是全等三角形,講著講著,老師忽然憤怒了,他的臉部表情有些扭曲,一轉身,揮動著粉筆,在黑板上寫下了一首打油詩:
遠看一堆肉
近看一堆肉
上看一堆肉
下看還是肉
其實就是一堆肉
知道這是什麽嗎?老師怒氣衝衝地問。我們都驚訝地望著他,等著他的答案。他瞪著眼望著我們,過了一會兒,他泄氣了,說,不說了吧。
事後,一位和老師同村的同學告訴我,老師寫的是他的老婆,他給自己老婆起了個綽號就叫“一堆肉”。
老師熱衷於在課堂上講述他的家庭生活,我到現在都搞不清楚,他的思維是怎樣從平行全等一下子跳到他家庭生活的雞毛蒜皮的。老師向我們呈現的記憶內容使我們對老師家裡角角落落的事情了如指掌,包括令他追悔莫及的換老婆的劣跡。
老師年輕的時候意氣風發,一表人才,當了幾年義務兵後複員,在公社中學當代課老師。那時候他已經結婚,老婆是和他同一大隊的,又黑又粗,很能乾活。按他自己的說法,他的婚姻是他父親的意願。那時候這樣的姑娘在農村很受長輩們歡迎,實惠,能掙工分。但老師卻不喜歡這種類型的女人。他認為自己既然要和一個女人生活一輩子,這個女人至少應該讓他感到賞心悅目,顯然,他老婆與賞心悅目有很大的距離。
後來,公社中學食堂新來了一位燒飯的姑娘,那姑娘比較白淨、苗條,估計是讓老師賞心悅目了,他們是誰先勾引誰,怎麽勾搭到一塊兒的,老師沒跟我們講,總之老師是神魂顛倒了,不顧一切地向結發妻子提出離婚,一意孤行,死不回頭。他的結發妻子哭哭啼啼地回了娘家,老師離婚的同時也拋棄了六歲的兒子。那時候老師臭名昭著,要不是學校缺教師,他早就被開除了。
愛情是美好的,一個人追求美好的愛情有錯嗎?老師曾在課堂上向我們,一群情竇初開的初中生這麽說,他的語氣相當憤憤不平。
這個食堂裡燒飯的姑娘就是我的現任師娘,也就是為轉正的事要舀糞給老師吃的那個女人,老師在娶這個女人時顯然屬色迷心竅缺乏長遠眼光,幾年內食堂女人一口氣給他生了三個兒子兩個女兒。跟老母豬似的,老師歎口氣道。更要命的是,她的體型也如同發酵的麵包一般迅速發脹,變得肥碩無比。就像一隻大水缸一樣,老師曾在課堂上哀歎道。還不如買一刀豬肉挖個洞呢。他憤憤地說。
初二第二學期,學校組織初三學生和全體老師去紹興遊玩,那時候老師儘管被貶為音樂老師,但還擔任著我們的班主任。他向長官提出想帶自己班的班幹部一起去,長官怪他多事,但最終同意了。於是我們十來個班幹部混跡在初三學生的隊伍裡遊了大禹陵、百草園、三味書屋等。遊完計劃的景點,還早,老師帶著我們在紹興街頭東遊西蕩。這時,一陣悠揚的音樂飄飄渺渺地傳來,我們沿著聲音走去,看見了河邊的一排房子,房子的頂上,有一塊牌,上面寫著:愛情島咖啡館。
這是小提琴在演奏,老師說,這樂曲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你們有沒有聽出來,樂曲裡有天鵝飛起來的聲音?
我們豎起耳朵聽,我們什麽也沒聽出來,我們只是覺得好聽。
多年以後,我在大學裡聽了許許多多的古典音樂,當我再次和這位老朋友相遇時,我才發現,她的名字叫《魔鬼的顫音》,作者意大利小提琴大師塔爾蒂尼。
你們喝過咖啡麽?老師問。
我們搖搖頭。
我也沒喝過,去喝一杯?他說,這玩意兒以前是上流社會的人,那些資本家、藝術家們喝的。
貴不貴?我們沒那麽多錢。我說。
不就一杯水裡加了點東西麽?我請客。老師顯然很想進去,但他和我們一樣,有些膽怯,他需要我們替他壯膽。
喝杯咖啡,聽會兒小提琴。老師鼓動我們說。
我和五個膽大的同學表示願意追隨老師赴湯蹈火。於是我們跟在老師屁股後頭進入了咖啡館。
走走走,這裡沒廁所!裡面的服務生見了我們就驅趕。
我們想喝一杯咖啡。老師說。
這個人想喝咖啡。那個人衝裡面一聲喊,話語裡有揶揄的味道,七杯?
對。
七杯!
我們圍著一張桌子坐下,一個穿長裙的姑娘,正站在屋子中央,目中無人地拉著小提琴。屋子裡還坐著些人,他們用怪異的眼光看著我們這些闖入者,顯然,我們這些人與這裡的氣氛和環境格格不入。
咖啡端上來了,我喝了一口就全吐出來了,苦的。其他同學也一樣。我們都看著老師,只見他皺著眉頭,滿臉痛苦,一口氣把那杯難以下咽的咖啡喝了下去,然後咧著嘴,吸一口氣。
老師對小提琴曲的喜愛顯然是葉公好龍,他的注意力不在姑娘的演奏上,他東張西望,好奇地打量著裡面的陳設,他的目光在一尊裸女的塑像上駐足了很久,他發現我們都在關注他,就把頭抬高一些,目光在屋頂掃視一番,又拿餘光去瞄那尊塑像。然後,他坐不住了,他注意到了屋子裡還有其他一些人在關注他,讓他覺得自己現在正在被觀賞,他很不自在。裡面的一切顯然與他想像的有差距,他感到索然無味。
給錢。他喊。
服務生捂著嘴,笑著向他走來,向他出示了账單,他的目光在账單上停留了很久。看來,账單上顯示的價格遠遠超出了他的想像力。
怎麽這麽貴?他紅著臉問。
不貴,別的咖啡店比我們貴多了。
我,我沒帶夠錢,我把我的學生壓在這兒,我去借錢。老師狼狽不堪,滿臉通紅。
老師跑了出去。十幾分鐘後,他滿頭大汗地跑了回來,把抓在手裡的錢數了兩遍,然後遞給了服務生,把我們贖了出來。
掏錢的時候,我的手是發抖的。後來在課堂上說起這事,老師痛苦地說,要知道我們在裡面待了三分鐘都不到,卻花掉了我將近一個月的工資。
我們注意到老師的左臉上有一塊烏青,右臉上有好幾道抓痕。我們感到很愧疚。
3
老師出事是在我初中畢業好多年之後,確切地說,應該是1994年,那年秋天的某個早晨,我的老師馬玉寶一腳踹進了人生的谷底,成了一個臭名昭著的人。在此之前,他擁有一個還算過得去的名聲,儘管他在學校裡的工作更像是一個雜役,管電教儀器、給活動拉橫幅、拍照等,只要與教書無關的場合,都能看見他健碩的身影,和那一碗亮閃閃的光頭。
事情肇始於物理老師的一次大膽冒險。那天,住在三樓教師宿捨的物理老師在吃完早飯後打算回寢室,他發現掛在腰間的鑰匙不知去向,在經過了仔細的搜查和痛苦的追憶後,物理老師斷定鑰匙應該是被忘在寢室裡了。他走到樓的後面進行了一番觀察,然後決定采取一次冒險行動:他打算沿一根下水管爬上去,因為這根下水管離他寢室的後窗比較接近,屆時他可以輕而易舉地騰出一隻手來攀住窗沿,順利翻入寢室。
物理老師寢室的下面是馬玉寶老師的辦公室兼暗房,我的這位老師負責保管學校唯一的一隻相機,並因此擁有了一間簡易的暗房。馬老師的辦公室窗戶開著,物理老師在實施冒險行動的過程中順便向馬老師的辦公室望了望。他吃驚地發現馬老師辦公室的後半間別有洞天,只見一根根的細鐵絲橫七豎八地斜拉著,鐵絲上掛著一張張顯然洗出沒多久的照片,但照片上的圖象已清晰可見。物理老師看見一個個光屁股的女人在風中飄來蕩去,他頭昏目眩,差點失手摔了下來。
我們的物理老師當時正積極要求上進,預謀著能接管學校的團支部工作,以便今後節節上升,所以,他把這件事向有意提拔他的校長做了匯報。1994年秋天那個涼爽而晴朗的早晨,我的老師馬玉寶一路打著哈欠,嘩啦嘩啦地騎著他的那輛破舊的永久牌自行車進入校門。他在車棚裡支好自行車,一抬頭,看見了校長陰沉沉的臉。
照片上的女人是哪個學生?在校長辦公室,校長把一疊照片摔在了馬老師的面前,然後嚴厲地直指問題的核心。照片上的裸體女人無論是站著、坐著、躺著,都沒有露出她的臉。她身材細長,臀部窄小,給人還沒發育透的印象。十幾分鐘前,總務主任打開了馬老師的辦公室門,和校長一道對辦公室進行了地毯式搜查,繳獲了所有罪證,沒收了作案工具——那架照相機。
老師拿過照片一看,臉上堆著的笑容頓時如同海浪坍塌一般退下,接著像被潑了一碗醬油,紅得深一塊淺一塊,他咧開嘴,吸一口涼氣,露出哭不像哭笑不像笑的表情。他痛苦地回憶了昨晚洗完照片後的情況,他記得自己應該是關了辦公室門的,只是臨走時順手打開了窗戶,以便照片可以乾得快些。他不明白校長怎麽就發現了這些照片。
這是人體藝術。老師說。
說,這些裸體照上的女人是哪個學生。校長盯著他的眼睛問。
這不是裸體照,這是人體藝術。老師說。
說,裸體照上是哪個學生。
我老婆。馬老師說,對,我老婆。是我老婆,沒錯。
你老婆?你老婆屁股比七石缸還大,腰比搗臼還粗,你騙誰?
不要貶低我老婆。
說,是不是學生?馬玉寶,你居然敢打初中生的主意,你還是人嗎?
確實是我老婆,要不,我把我老婆叫來,讓她脫光了,你看看是不是和照片上的女人吻合?
滾!
那一天,老師的名聲像夏天裡保存不善的豬肉一樣迅速變質發臭,老師開始接受調查。他這才知道,事情鬧大了。
校長向當時的鎮教辦長官做了匯報後,由鎮教辦長官牽頭,下屬各學校派一位長官參加的調查組便進駐了老師所在的學校。我也被安排進了調查組。那時候我從師范大學畢業才一年,在另一所學校教書,作為學校唯一的正規師范大學畢業生,校長對我很看重,才教了一年書,就把我提拔成了一個小頭目。
我現在的身份和老師的處境讓我和老師都倍感尷尬。
調查組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找老師談話。老師的身體越來越精瘦了,他的頭髮也掉光了,據說是讓吃發蟲給吃光的,整個腦袋油光光的像粒燦爛的花生米。在嚴厲的調查組面前,老師已沒有了當初課堂上的滔滔不絕信口開河。他語無倫次,頭上直冒熱汗,像個做了錯事的好學生。老師的辯解概括起來是兩點:第一,這些照片是人體攝影,人體攝影是藝術;第二,他一再強調,照片上的女人是他老婆。
校長把老師所謂的人體攝影遞給我們看。老實說那些照片稱它們為人體藝術有些名不副實,叫它們裸體照也許更恰當些。更可疑的是老師拍攝的角度,無論拍的是正面還是背面,截取的都是從腰部到膝蓋這一部分,也就是說,老師拍了一堆屁股和大腿。
根據老師的交代,照片上的女人應該是我的師娘。從年齡分析,師娘應該有五十多歲了。五十多歲的女人,早該屁股松垮,肌肉鬆弛,身體走形了。照片上的女人明顯不具備這些特徵。但老師仍一口咬定照片上的女人就是他老婆。調查組也拿不出什麽證據來否定,畢竟我們不能把他老婆叫來,讓她脫光了供我們核對。
我們調查的核心是這照片上的女人到底是什麽人?如果真是他老婆,那是他們的私生活問題;如果是社會上什麽女人,那是他的生活作風問題;如果是個女學生,那性質就嚴重了。調查組組長,教辦主任向我們指明了調查的方向。問題是,我們依據什麽去判斷這個女人的身份,無論是在大街上,還是在校園那些成熟的女學生中間,這樣的腰身比比皆是,就跟農村裡放養的鴨子一樣稀松平常,毫無特徵。
調查無從著手,教辦主任決定先進行外部調查,了解老師的生活作風及與女學生的交往情況。調查結果顯示,老師的人生很灰暗,在他老婆的強力管束之下,他與女性的交往基本處於點個頭打個招呼的層次。至於女學生,自打我初中畢業以後,老師便不再從事學科教學,也不再當班主任,這就基本剝奪了他與女學生進行親密接觸的機會。
不過我們的調查有一個意外的收獲。這個收獲讓我們投鼠忌器。老師和原配離婚時,拋棄了他當時六歲的兒子,這個兒子,現在身處高位,是我們這個縣級市的某局局長。
你們能確定李局長和馬玉寶是父子關係?教辦主任問。
村裡人都這麽說的,好像他的前妻後來改嫁了,李局長是隨了繼父的姓,他繼父是個窯廠拉車的,李局長小時候吃過很多苦。有人說。
他去窯廠幫繼父乾活,窯門塌了,他繼父把他推了出來,自己壓死在裡面了。我說。
馬玉寶說照片上的女人是他老婆。教辦主任拿起那些照片,若有所思。我看不是不可能。他說。
我們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表態。
他想認這個兒子,可人家壓根不認他。有人說。教辦主任看了那個人一眼,那人連忙低下頭。
老師確實去認過這個兒子,他這麽做是被另外幾個兒女逼的。當他的這些子女知道自己還有這麽個同父異母的兄長時,都很振奮,他們去拜訪了這個兄長,但他們的兄長對他們很冷淡,連見一面的機會都沒給他們,就讓秘書把他們打發了。他們很氣憤,罵他們的兄長勢利眼,不近人情。然後,他們就逼著自己的父親去找那個兒子。
哪有當兒子的不認爹的。他們說。
他不認你,你就去紀委告他沒有盡到贍養責任。他們說。
連他的老婆也一反常態,唆使他去認兒子。老師自知無顏見前妻和兒子,但他被逼得沒辦法,只好去了。那天正好是市政府舉辦群眾接待日,市長、各局辦一把手親自接待群眾來訪。老師找到了他兒子所在局的接待處。他猶猶豫豫縮頭縮腦地坐在兒子面前。
大叔,你有什麽事要反映嗎?他兒子愣了一下,然後盯了他一會兒,問。這回輪到他發愣了,兒子離開他時六歲,應該記得他的樣子,後來父子倆也見過幾面。
我想見你。他支支吾吾地說。他不知自己該說些什麽。
你想見我,有什麽事要反映嗎?
我,我想見你。
兒子看了他一眼,對旁邊的人說,這位大叔你接待一下,我上趟廁所。又對他說,大叔,我有事出去一下,你有什麽問題跟劉副局長反映吧。說著起身走了。老師站起身,愣在那裡了。
4
我決定去拜訪一下老師。為了躲避學生和同事們異樣的目光,老師已請假一個禮拜,除了隨時聽候調查組的召喚,他基本上把自己關在家裡,這樣他就無法逃避師娘對他憤怒的謾罵。我到老師家裡時,老師在沙發上正襟危坐,師娘一手叉腰,一手指著老師的鼻子在叫罵,那樣子如同一隻茶壺。師娘罵人就像當年老師給我們講課那樣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你這個吃屎的東西,這麽大年紀了還要去勾引女人,你把臉去糞缸沿磨磨……見我進屋,師娘頓時閉了嘴,轉換出一張笑臉,又是讓座又是倒茶,然後極不好意思地說:讓你們看笑話了,這個死鬼,一定要讓我給他當什麽模特兒,我這麽大年紀了拍這個東西,還讓人發現了,丟不丟人?我活了五十多歲了,身子隻給這個死鬼看過,現在讓這麽多人看了……以後我怎麽做人。師娘邊說邊抹起了眼淚。
我看了看師娘的體型,不管她穿得多麽緊身,她這麽大號的身材絕對與相片上的女人對不上號。
我衝著老師笑了笑。
這幾天沒上班?我沒話找話以便打破尷尬的氣氛。
沒臉見人咯,老師說,他亮閃閃的腦袋低垂著。請了一個禮拜假了,請一天假要扣十塊錢的全勤獎,年終考核時又要扣幾百多塊,損失大了。老師心疼地說。
家裡還好吧。
哎,老師歎了口氣,說,就那樣了。三個兒子,一個成天鬧離婚,把女兒扔在我這兒不管,還有兩個不去找個正經工作,整天打牌賭錢,只有他們餓的時候我才能見到他們,至於你師娘,你剛才也看到了。
相片上的那個女人真的是師娘?我突然發問。他一愣,繼而滿臉通紅,張張嘴想說什麽,但接著他眼裡閃過一絲警惕,說,當然是你師娘,不然會是誰?
他忽然站了起來,走進屋,不一會兒捧出一大堆東西,說,我還是市裡的攝影家協會會員呢,你看,這是會員證。接著他又把一些他的攝影作品介紹給我看,講一些作品的來歷,拍攝地點,拍攝趣聞,仿佛又沉浸在他的攝影世界裡了。
我在家裡待不住,只好跑到外面去,跑出去總得乾點什麽,正好手頭有學校的照相機,就攝上影了。
在我看來,老師的攝影作品更像是私人家常的拍照,但老師卻試圖用他的作品來向我證明,他搞的是藝術,那些裸體照是人體攝影。
你是我唯一的高材生,老師說,讓你看老師的笑話了。
老師的這句話讓我心頭湧起了一陣感動。我記得初三的時候,老師因工作負責,仍當我們的班主任,那天,他在鄰村喝完喜酒路過我家,那時候已是半夜三更,他酒氣衝天地敲開了我家的門進行家訪。他滔滔不絕地向我的父母講述我的優異表現,那種喜悅之情,就像是父親在誇自己的兒子一般。後來我考上了重點高中,又是他親自將錄取通知書送到我的手中。那天正在下暴雨,老師的自行車鏈條斷了,他是推著車走了十多裡路趕到我家的,他渾身被雨淋得像落湯雞一般,身上濺滿泥漿,一隻皮鞋已不知去向。他的臉上還留著血跡,顯然他跌了一跤。當他顫抖著手把錄取通知書從口袋取出時,我發現通知書居然一點都沒濕,它被小心地折疊著,散發著淡淡的體溫。
就在調查組打算以老師的口供為依據,草草結束調查時,物理老師向調查組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老師似乎對初三的一位女生比較關心,而且可能還去過這位女生家幾次。這位女生的父親早死了,母親又生了一種慢性病,不能乾重力活,靠織手套維持生計。
顯然,該女生具備被金錢利誘的客觀條件。
教辦主任先是眼睛一亮,接著沉下了臉,物理老師現在的行為很不合時宜。既然有人舉報,那就得給舉報者一個交代,調查只好繼續下去。
當那個女學生被叫到辦公室迎接我們核對的目光時,我們依然沒有理由認定她就是相片上那個女人,儘管我們認為有相似性。
在精心設計的隨便聊天后,教辦主任水到渠成地把話題引向了調查內容。主任漫不經心地迂回側擊:你覺得馬老師這人怎麽樣?主任這麽做完全是出於對真相的好奇。
挺好。女孩子說。
噢,具體點,好在哪?主任問。
反正我覺得他挺好。女孩子說。
他對你們學生好嗎?比如對你。
挺好啊。女孩子說。
主任沉默了會兒,忽然發問:他給過你錢嗎?
主任這一問猝不及防。女孩子一愣。主任把女孩子的神情看在了眼裡。
給過。女孩子說。這回主任一愣,他可能沒料到女孩這麽爽直。
他為什麽要給你錢?
有一回我沒錢交學費,在校園牆角哭,恰好他看見了,知道了我家的情況,就給了我一些錢。
給了你幾次?每次多少?
每學期開學時他就給,每次三四十。
他去過你家嗎?
去過幾次,給了我媽一些錢。
他沒對你和你媽提出過什麽要求?
沒有。
你不用怕,大膽說,我們會替你保密。
沒有。女孩子哭了。這個調查組的性質以及剛才的問話已經讓女孩子明白她現在是被懷疑對象。
我們只是隨便問問,並不是說你跟那些照片有什麽關係,我們是想了解一下馬老師的情況。主任安慰她說。
接下來的問題是,全校的學生和老師都看見了女孩子從調查組辦公室出來,校園內馬上便流傳女孩子是裸體照上的那個女人的消息。這個消息又通過全校一千多張嘴迅速傳遍了全鎮。我那沒頭腦的師娘在如釋重負地掀掉了那個她極不情願背的黑鍋後變得耀武揚威,她把老師揪到大庭廣眾之下臭罵一頓以替自己沉冤昭雪,之後她又趕到女孩家,拍手跳腳地把女孩子和她母親痛快淋漓地罵了一頓。
第二天我到學校的時候,傳來了女孩子自殺未遂的消息。事情的發展出乎教辦主任的預料,這件事已經完全失去了控制。
就在我們不知所措的時候,馬老師匆匆趕來了,他兩眼通紅,一進門便對教辦主任說,主任,我坦白,我交待,我坦白交待。
主任沒料到馬老師會找上門來,他早已經和我們打好招呼,不管女學生說什麽,都按馬玉寶老師的口供處理這件事。一愣之後,主任支支吾吾地說:好,好,坦白也好,坦白了還是個好同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是政府的一貫政策。不過,你已經交代過了,就不必再交代一遍了。
那……那……那個女人是我……從街上找來的一個野雞。老師說話變得非常吃力。
野雞?我們吃了一驚。
你是怎麽找到這個野……這個女人的。主任問。
怎麽找?我怎麽知……停頓了一會兒,老師說,在路上恰巧碰上的。這時的老師反而變得平靜了,有一種死豬不怕開水燙的豪邁。
你怎麽知道她是個妓女?主任又問。他的眼裡透著一絲精明。
這還不簡單?坦胸露背,搔首弄姿,而且她還主動勾引我,對,是她勾引我,我才知道她是隻雞的,然後我給了她三十塊錢,請她給我當模特兒。
這麽說你還是個嫖客?
嫖客?我連個妓女都沒見……沒碰過,怎麽算嫖客?隻拍照,沒嫖。當然我也沒證據證明自己沒嫖,你們要認定我是個嫖客我也沒辦法。
你敢對你說的話負責?
我負責。老師說。
那好吧。教辦主任無可奈何地說。
你們趕快公布調查結果和對我的處理意見,越快越好。老師臨出門時說。
我一回頭,看見老師的背有些駝了。
5
一個月後,我接到了派出所打來的電話,電話那頭先確認了一下我的姓名,然後說,你認識馬玉寶嗎?
認識。
他嫖娼,我們要通知家屬,他說可以找你。你來一趟派出所吧。
在派出所,我見到了我的老師,他已經在裡面蹲了一天,顯得很憔悴。他希望我能把他保釋出去。
怎麽嫖起娼來了?我問。那件事的處理結果還沒下來,又出了這件事,他徹底把自己毀了。
其實我是想找個女模特,拍幾張人體攝影,去參加一個攝影比賽,獲個獎的話就可以證明我拍的不是裸體照,是人體攝影,是藝術。
這很重要嗎?
我一輩子被人瞧不起,這是我人生的價值。
照相機不是被沒收了嗎?
借的。
看你折騰的。
過了一會兒,我終於好奇地問出了我一直想問,卻不好意思問的問題:你,嫖了嗎?
他看了我一眼,臉紅得像個打過秋霜的南瓜。
人體是藝術,誰能抗拒美的誘惑呢。他說。
唉!
(文內圖片若未標明均來自互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