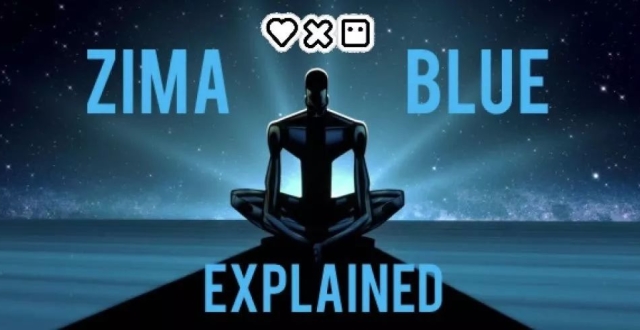《波洛克傳》
[美]史蒂芬·奈菲、
格雷高裡·懷特·史密斯著
沈語冰等譯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8年7月出版
883頁,158.00元
━━━━
文︱孫一洲
“哦,這從未年輕過的新世界啊”,當西奧多·羅斯福這位東海岸的貴胄子弟撰寫《贏得西部》的時候,腦海中的畫面應該是馬刺、左輪手槍和奔馳在赤色土地上的牛群。這裡無垠的荒原、豐富的礦藏和粗野的開拓者有美國的兵源、票倉和質樸剛健的民族形象。但以牛仔自詡的羅斯福可能沒想到,不到半個世紀,這個新世界就急不可耐地要向東部輸送一位敏感的藝術大師和他熱烈而狂躁的作品。
“去他媽的這玩意你來畫”
傑克森·波洛克的雙親都是二代邊民,生活在西部並不是他們拓殖精神發作的選擇,而純粹是東海岸沒有容納自耕農的生存空間。西進運動並不像買農場過家家的羅斯福想得那麽浪漫,從舊大陸到新大陸,從東海岸到西海岸,這些家庭至少從十七世紀開始就過著世代遷徙的生活。至少從這一點看,散落在落基山脈以西惡劣的自然環境並不比舊世界的宗教敵意更惡劣。遷徙-定居-破產,只有少數幸運兒才能在某個水土豐茂的河畔扎下根,而他們繼承不到財產的小兒子也終將踏上他們未竟的路線。波洛克的家庭一直在搬遷,沒有穩定的朋友和職業。安土重遷的地產廣告篤信者和讀了德勒茲的知識分子可能會一廂情願地相信,非定居是屬於昨天甚或先民的生活,然而對這個世界上大部分流動人口而言,這依然是正在發生的歷史。
老波洛克是一位老實巴交的自耕農,有著野草般的生命力,卻也像野草一樣飽受市場大潮的來回摧殘。毫無生意頭腦的他無法將自己的勤勞變現。可即使在家庭和經營雙重破產只得外出務工後,他也沒有懈怠過作為一家之主的責任,默默供養著五個虎頭虎腦的兒子。儘管父子關係從未融洽過,但父親對波洛克童年的羞澀和年輕時的胡鬧還是非常縱容,或者說無能為力。如果有人想用弗洛伊德的理論把波洛克情緒上的缺陷歸咎於父親,那麽在父親的壓抑這一部分需要有編造材料的勇氣。
父親在情感生活中的缺位讓幼子在心理認同上偏向母親,這位中西部婦女雖然心靈手巧卻不事產業,熱衷精致的生活。一旦遭遇挫折,就會驅趕著全家搬到另一個地方,只是單純出於相信未來會更好。波洛克從母親混亂的階級認同中繼承來了不善交際的童年,又從不善交際的童年中收獲了敏感、怯弱和優柔寡斷的性格。他過家家就喜歡扮演母親,直到十六歲他長成一位孔武有力的壯漢,還因厭惡體育而不惜被學校開除。青年波洛克更像是一個遊手好閑的社會閑散人員,很容易就被神秘主義或激進政治所俘獲。

作為五兄弟的幼子,傑克一直生活在母親的溺愛和兄長的陰影下。這位抽象表現主義大師的童年實在是乏善可陳,因為小波洛克實在是平平無奇。這不是古天樂式的平平無奇,而是徹頭徹尾的平庸。二十歲之前,他既沒有求知欲也沒有好奇心,在任何場合都沉默而敷衍,除了幾位怪誕的師友,基本上沒有人認同乃至注意到他。他有兩位兄長早在高中就展現出了藝術天賦,他的藝術路線不過是對哥哥的亦趨亦步,而且如其父親所見,也有出於叛逆和好逸惡勞的成分。
作為盡職的史家,本書作者詳盡地描繪了傳主的童年,採訪了無數他童年的鄰居和朋友,考慮到他母親舉家遷徙的癖好,更顯得不容易。誠如譯者所言,這是以政治人物的標準為藝術家作傳。但這並沒有影響這些童年瑣事不過是每個家庭都會發生的杯中風暴,而波洛克似乎與其他不成器的小兒子也沒什麽區別。對美國地方主義的旗手托馬斯·本頓生平精煉的概述充分佐證了作者也許有能力在一章內把波洛克的童年寫完。儘管家境優渥得多,本頓也有著和波洛克近似的童年——撕裂的家庭、虛榮寵溺的母親和缺乏藝術訓練。最重要的是,本頓和波洛克一樣,病態地渴求自己童年所缺失的男子氣概。弗洛伊德的理論大概要略作修改,他們恰恰是因為佔據了過多母愛,才在成年後更渴望成為父親,甚至不惜尋釁滋事。本頓舉止粗俗,露骨地吹捧大男子主義,波洛克則杜撰自己沒有甚至沒有見過的牛仔過去,這種長時間的虛張聲勢構成兩人間隱秘的情感紐帶。
得益於長兄查爾斯及其導師本頓的收留,高中輟學無所事事的波洛克得以到紐約接受藝術家聯盟的培訓。這是當時最時興的藝術從業訓練,辦學理念先進且組織靈活,既有一時興起的票友也有繼續深造的名門。波洛克本應在世界之都接受各地藝術家的八面來風,但狷介而脆弱的性格讓他始終困在本頓的小圈子中。他並不靈活的雙手在那些老練的同學面前相形見絀,波洛克開始敵視幾乎所有人,包括他們的才華和身份地位。學業受挫和他的自卑構成了惡性循環,酒精才是他的解藥。年輕的波洛克在這一時期開始酗酒本不奇怪,可酒精輕易就能稀釋了他那紙糊一般的城府。從那時起,波洛克的朋友們就開始注意到,酒精就像麵粉廠裡的火星,只要一滴就能把面善的傑克變成狂暴凶惡的波洛克。
讀到這裡,本書已經接近了一半,可讀者似乎根本沒有接觸到任何天才的火花,反而像是在讀一個巨嬰的病史。他一直渴望認同,只要片刻得不到關注,波洛克就會沉入自我毀滅的深淵。他的幼子身份是他猶疑性格的主要來源,可他的兄長們從未放棄過他。波洛克一家已經習慣了為照顧傑克而做出自我犧牲,哥哥們輪番成為他的情感依靠和生活中的拐棍。成名之後,他的朋友們也先後加入 “把醉漢波洛克弄回家”的輪值公益活動。可他的哥哥最終對蹲號子的弟弟也無計可施了,只有尋求更專業的幫助。
波洛克在成年之後歇斯底裡的性格來自他和父母的病理性關係,在他的生命中一直有一些長輩陸陸續續地出現,扮演他家人的替補。首先是托馬斯·本頓,助長了他自我毀滅的囂張氣焰。榮格的弟子約瑟夫·亨德森醫生在波洛克身上嘗試了新銳的精神分析理論,並幫他逃過了兵役。墨西哥牆畫家西克羅斯,教給他動態顏料的使用和一整套原始意象教。這些人或多或少緩和了他一段時間內的焦慮,對他後來的藝術天賦也不無貢獻,但絲毫談不上根治他那要命的酒癮,或從沉淪中勾回波洛克的魂魄。

早在與老師度假時,波洛克就發現本頓夫婦之間名為夫妻,實為母子,他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相同的軌道。對於同樣渴求男性氣質的他,而最終的救世主仍然是一位女性——李·克拉斯納。波洛克夫人後來將他們的相遇編造成藝術天才之間金風玉露一相逢,但事實上她剛剛結束了與圈內風流浪子多年的姘居,正為有一天人老珠黃而發愁。但沒有人會苛責這位女性,畢竟她選擇與情緒不穩定的酒鬼同居,充當他的情人、經紀人和保姆,並年複一年地忍受著波洛克間歇性發作的神經質。這對夫妻的關係絕對稱不上和睦,但對波洛克的藝術成就功不可沒。她滿足了波洛克一直以來渴求的單一性關係,讓他真正能在他人關注中心無旁騖地創作,以至於後來波洛克寧可一窮二白也不讓妻子外出工作。來自另一個藝術團體的李也曾留有余地地指點波洛克的創作,隻換來一句“去他媽的這玩意你來畫”。至少從那時起,在拚貼藝術上有不俗造詣的李就不再染指波洛克的創作,甘心做他的綠葉。
蒙德裡安點點頭
回顧波洛克的藝術學徒生涯,失敗似乎都不足以形容他在天賦上的魯鈍。油畫、素描、雕塑,他嘗試過一切,卻無一例外地發現這些工具非但沒有我筆寫我心的輕便,反而處處和他作對。在徹底放棄掙扎之後,他開始反求諸己,從他半虛幻的記憶中尋覓可供發揮的素材。“那些強大的意象所產生的共鳴,足以為一幅畫提供能量,同時也富有危險。無論是具有毀滅力量的女性、進攻中的公牛還是模糊的性向,就是傑克森最需要壓抑的意象。終其一生,他經歷中情緒上的大起大落也是他創作出最鮮明意象的時期。夢魘般的怪異女人和瘦骨如柴的醜陋嬰兒縈繞在他的腦海中。所有最為黑暗而可怖的真相幾乎不受任何約束地在其意識世界中徘徊,並出沒在他的藝術世界中——它們披上了焦慮的外衣,只有酒精能夠平息。在李的支持下,他已經控制住這些魔鬼,甚至學會在《速記形體》和《男人和女人》這樣的作品中直面它們。然而恐懼仍然存在,就像抽象畫的需求和其所遮蔽的東西一樣一直存在。”
波洛克生活在二十世紀最波瀾壯闊的幾十年裡,但大蕭條卻只是他神話的一個注腳。在這幫“達則領賞花錢買醉,貧則集會抗議資本主義”的紐約畫派中,波洛克一點也不特殊。他一無所有,不會像他苦心經營的父親一樣落得雞飛蛋打;接濟、零工和新政的斷斷續續,讓他從未斷過炊。“羅斯福新政”的資助讓這些藝術家在戰時依然過著戰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在一個內心波瀾不定的年輕人眼裡,即使再平靜的世界也是動蕩的海洋,外界的離亂更是助長了他的判斷。

長年的苦熬讓他從這些作品中逐漸積累了一些聲譽,逐漸靠近了紐約藝術的中心。波洛克在事業上的轉機首先得益於霍華德·普策爾不遺余力地向佩吉·古根海姆推銷波洛克的作品。在不情不願地將波洛克的作品納入她的國際拚貼藝術大展後,古根海姆依然不願放下身段。當被她千方百計請來的評委蒙德裡安駐足於波洛克的《速記形體》時,這位在藝術品位上極其歐洲中心主義十足的名媛立刻跑來,老練地對來自荷蘭的藝術大師苦笑致歉:
“相當糟糕,不是嗎?這都不是一幅畫。”
蒙德裡安沉默不語,凝視了幾分鐘。
“完全沒有訓練可言,這個年輕人問題嚴重……我認為不應該把他的作品收入進來。”古根海姆的聲音已經明顯不安。
“我不太確定”,蒙德裡安摸了摸下巴,“我試著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麽。這是目前為止我在美國見過最有趣的作品。”
後來,這個時刻被藝術史賦予了神話般的傳承意義。年逾古稀的抽象藝術泰鬥跨越意識形態的鴻溝,向美國年輕的表現主義藝術家張開雙臂。不過,這次吹捧實際上只是蒙德裡安前來為自己的讚助人和門徒(對藝術家而言,兩者經常是一回事)霍茲曼助拳的一個副產品。他只是節製地敲打佩吉要學會欣賞不合自己口味(即霍茲曼)的作品,但這卻被後者解讀為對波洛克藝術潛力的莫大認可,並開始作為經紀人不遺余力地推銷他的作品。得到佩吉的幫助,波洛克得以在短短幾年內口碑爆棚。
然而,這次無心插柳之後實際上潛藏著愛國主義的潛流。隨著局勢的動蕩,一波波的歐洲知識分子漂洋過海,把這個已經獨立了一個世紀的年輕共和國再次變成自己的文化殖民地。與哲學圈形形色色的德裔不同,紐約的藝術圈一直是左岸咖啡館的飛地。佩吉·古根海姆本人就是布勒東門徒團體的信眾,在超現實主義式微後產生了由愛生恨的情愫,這次大展事實上正是這種感情的外溢。美國的知識圈同樣早已受不了這些故土淪喪的歐洲人跑來顯擺陰柔而晦澀的法語詞,渴望著自己的大師。
不過從二戰結束到波洛克就位還有幾個春秋的輪回,主要的拉鋸發生在波洛克的生理和心理上。任何生活的風吹草動都可能拆去他的心理支柱,讓他重歸乙醇的懷抱。在他糟糕的酒品成功得罪了紐約的每一位酒保後,他離開了紐約,來到小鎮斯普林斯居住。家人的關懷很早就被證明作用有限,最終波洛克不得不求助於鎮定劑。他從未真正擺脫過對酒精的依賴,不過只要能在與酒精的搏鬥中稍稍佔得上風,創作的高峰和現實的成功就會如約而至。

“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姿勢。他一隻手拿著一罐黏稠度被稀釋到和蜂蜜一樣的油畫顏料。另一隻手握著一根棍子——可能就是他用來將顏料和松脂的混合在一起的棍子。跪在一小幅畫布旁,將木棍在顏料桶裡醮一下,然後揮舞著木棍將顏料灑在畫布上。木棍朝下,一股顏料擰成的細流從一端滴落到畫布上。顏料在畫布上匯成涓涓溪流。木棍上的顏料流光時,細流變窄, 然後變成時斷時續的液滴。”
對滴畫法的首創藝術界一直莫衷一是,無數藝術家將自己之前的工作視為波洛克的先聲。波洛克使用堅硬的樹枝塗抹合成樹脂材料,連大部分同代人都完全無法理解。這樣事實上改變了畫布直立的作畫範式,並引導畫家而非觀眾也從不同角度觀看繪畫。相比同樣揮灑顏料的前任們,他更不追求滴畫在畫面上的效果,只是在意揮灑的動作。這種“行動繪畫”在多重意義上釋放了藝術家的創造力。不知不覺間,波洛克已經奔馳在駛向“最偉大藝術家”的快車道上。
在藝術批評的陰影下
《生活》雜誌的宣傳把波洛克徹底推到了聚光燈下。這篇廣告頁一般的簡介被冠以聳人聽聞的標題——“他是美國最偉大的畫家嗎?”內容對波洛克的師承、風格或作品隻字未提,卻端出了最適合想象的反傳統藝術家形象。《生活》雜誌的報導並非完全處於善意,卻意外引起了圈外的爆炸效應。波洛克,一位西部土生土長的木訥糙漢,絲毫不懂歐洲舶來的藝術理論,自然也和喋喋不休的法國人劃清了界限。他後來在採訪中對歐洲藝術先賢的無知只是出於他的文盲和坦率,卻不出意料地被大眾媒體視為美國藝術的璞玉。
波洛克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媒介。除了藝術媒介和新聞媒介,一位名叫漢斯·納穆斯的年輕攝影師也借助媒介,把藝術家本人也變成了藝術品。他對波洛克形象的興趣大大高於對其藝術的興趣,跟拍波洛克作畫的狀態,把波洛克作畫時恍惚的舞蹈姿態定格為一位桀驁不馴、靈感爆棚的非凡畫家。在他的慫恿下,跟拍很快成了擺拍,攝影也變成了錄影。波洛克很享受這種自我推廣的過程,不惜在凜冽的寒風中做出各種故作瀟灑的狂放姿態。這樣迎合觀眾浪漫主義式的想象的手法,正是秋元康打造AKB48時所使用的偶像文化——藝術品變成了藝術家人設的周邊手辦,而畫展則演變成了簽名握手會。波洛克的形象和他的作品就這樣一起被寫入了藝術史。

藝術圈總離不開知識分子來推波助瀾的闡釋或者造勢。紐約的藝術批評圈繼承了巴黎文化中那種近身搏鬥的習氣,批評經常只是一個小圈子的月旦。批評家和藝術家之間過多的交集讓人很難區分真誠討論和黨同伐異之間的界限,而藝術批評就是藝術家之間的軍火庫。波洛克的命運也和藝術批評中“三座大山”(格林伯格、羅森伯格、斯坦伯格,伯格即德語的山)的時代緊緊捆綁在一起。然而對於不善於人情世故的波洛克而言,是憂是喜猶未可知。
在現代藝術史的神龕裡,沒有比格林伯格和波洛克更好地互相成就。波洛克對批評敏感而多疑,經常被媒體上的隻言片語所刺激。他需要理論和理論家的庇護(兩者對波洛克區別不大)。而克萊門特·格林伯格,這位文藝批評界的失敗者在波洛克身上嘗試了諸多新銳而玄奧的理論,不僅完善了藝術批評並為抽象畫家正名,還在身後把波洛克和自己一道推到了殿堂級的高度。波洛克雖然絲毫不理解格林伯格高深的理論術語,但早在榮格派的心理治療體驗中,就深信自己的繪畫暗合宇宙的玄奧——“我就是大自然”,傑克森·波洛克如是說。木訥而又教育程度低的波洛克需要這樣精致的畫論包裝,才能和歐洲的藝術哲學相抗衡。兩個人在藝術上攜手走過了四十年代。
但格林伯格毫不節製的推崇也逐漸為波洛克樹敵。另一位伯格則充當了波洛克神話的掘墓人——哈羅德·羅森伯格。他的夫人正是波洛克夫婦的證婚人,而他在掀翻格林伯格的統治中,將格林伯格的寵兒波洛克一道變成了過去式。他以另一位畫家威廉·德·庫寧為例影射波洛克在創作上的枯竭。這最終演變成了一場抽象表現主義中曠日持久的內戰,兩位畫家被擺在藝術批評的拳擊場上赤膊相見。經過格林伯格的闡釋,“行動繪畫”的光環從波洛克的頭頂褪下,被整個紐約畫派所分享。波洛克夫婦睚眥必報,卻突然意識到他們早已孤立無援。

事實上,成名後的波洛克很快適應了他的新角色,以“全世界最偉大的畫家”自居。他紙醉金迷,直到債台高築也未接濟過家族,任由為自己發愁的兄弟們捉襟見肘。他毆打妻子,更加粗暴無禮地闖入不歡迎的派對吹噓打罵。他嗜酒縱欲,帶著藝術圈的外圍女子回家同居。最讓人痛心的是,他在藝術上開始駐步不前。早在四十年代末,格林伯格就提醒他“正在自我重複”。但此時他已經已經嘗到了名利雙收的甜頭,學會了拖延到畫展前一個月作畫,並把自己的低迷歸咎於“月亮太圓”之類的理由。只有在販賣作品的時候,他會強打精神清醒一會,推諉、托詞並自我吹捧。有增無減的名氣讓他獲得不明所以的觀眾的喜愛,卻把家人朋友和同行都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他還是那個被寵壞的孩子。
波洛克又一次故態複萌,醉心於自我毀滅,世界曾一度感動於他那些突出自發性、心理能量和無意識的意象,縱容了本書中第無數次自暴自棄的情節。一般情況下,這些情節都會終結於他的朋友們在紐約的某條陰溝中撈出了不省人事的波洛克。他太習慣於命運的寵溺,又一次酒後駕車在高速公路上狂奔。可這一次,命運之神打了個瞌睡,這場與他的才華捉迷藏的遊戲終於無以為繼。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