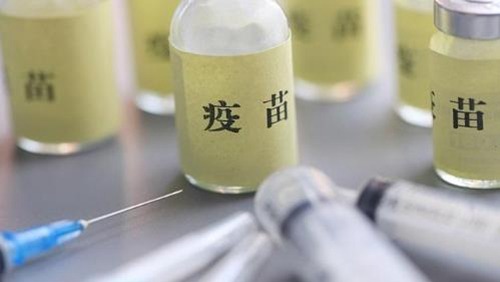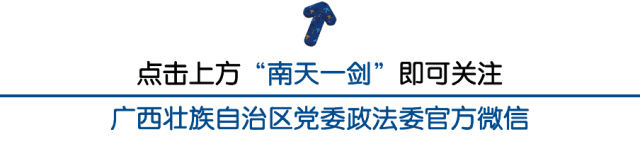我是記者郭靜。
如果說武漢是這場疫情的中心,那麽中心的中心,就是金銀潭醫院。作為武漢市傳染病專科醫院,這裡是最早打響這場全民抗“疫”之戰的地方。在與死神較量的正面搏擊中,身為一院之長的張定宇,他拖著身患“漸凍症”的病體,還要默默承受妻子也感染新冠肺炎的巨大打擊。來武漢這麽多天,我一直在想,一定要採訪張定宇。但可以想見,這段日子他有多忙、多累。
採訪約在了疫情稍微平穩一些的時候。原定的採訪本是前一天,距離採訪前一小時,他突然出現了房顫,我聽後非常擔心,他真的是太累了。沒想到,他把採訪又約在了第二天下午,而且一談,就談了兩個多小時。
他記憶力超好。他對事件的還原,足以記入這段歷史。
1
12月27號,同濟醫院說要轉來一個病人
我叫張定宇,今年56歲,我是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的院長。
我是2014年1月2號來的金銀潭醫院,在這工作已經超過6年了,我想,剩下的時間我也會在這裡待下去。
我們醫院以前有三個名字:武漢市醫療救治中心、武漢市傳染病醫院,還有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後來把第一個名字給去掉了,武漢市金銀潭醫院、武漢市傳染病醫院,這兩個名字保留使用。
說起這次疫情,最初大約是2020年1月3號前後,媒體對武漢的關注度就比較高了。但其實更早一點,2019年12月27號晚上6點半左右,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武漢天黑得很早。那天,我,還有黃朝林院長,都在辦公室。黃院長接到同濟醫院一位教授打來的電話,說要向金銀潭轉診一個病人。我們問是什麽病?對方說是冠狀病毒感染的一個病人,沒說肺炎。
這是什麽病?我當時並不了解,包括我們醫院這些人當中也沒有誰接觸過冠狀病毒是怎麽回事。於是我們馬上就打電話給北京地壇醫院的專家,問“這個病人我們應不應該收?能不能收?”地壇醫院的專家馬上就回復說,“你們應該收,金銀潭是傳染病醫院,這個病人你們要關注。”於是我們馬上就又打電話給同濟醫院,讓他們把病人轉過來。
但是,這個病人本來是從武漢市二醫院轉診到同濟的,讓他再轉到我們這麽一家機構,他不願意。一邊同濟給病人做工作,同時我們也開始做準備,要了解冠狀病毒是怎麽回事。
作為醫生,實際上心裡是比較敏感的。我們想的是,首先得把病毒的基因序列拿到,所以打電話到第三方檢測公司。實際上這個公司也是很謹慎,他們第一次給的報告上面並沒有指出是“冠狀病毒”,隻說“RNA病毒未檢測”,但他們在電話裡和同濟的大夫說了。我們就告訴第三方公司,你既然做了測序,這個序列必須給我們,因為這個病人到時候要轉診到我們金銀潭來。
這樣,我們把基因序列拿了過來,找到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當天晚上病毒所就比對出來了。當時是27號晚上大概10點多。比對出來最像什麽?叫做“蝙蝠來源的SARS樣冠狀病毒”,吻合度非常高。當時病毒所也是在電話裡跟我們這樣說了,沒有出報告。
第二天28號,我們就追問同濟病人轉診的事情,那邊說病人家屬不樂意,不願意轉。我們也就不能強迫。
29號是星期天。下午稍晚的時候,黃朝林副院長打電話報告我,說要帶一個醫生去新華醫院(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會診,討論的是群體性感染的7個病人。他去的時候省疾控中心的專家也在,討論的結果就是:往金銀潭轉診。
根據之前了解到的信息,我們已經有了警惕性。所以29號去新華醫院轉診的時候就已經全套防護了。但在心理上還覺得,這是一個孤立事件。當時馬上就元旦了,春節也快到了,我們希望趕快把它解決掉,乾完就完了。
就跟2017年的禽流感一樣,當年禽流感也是在這個季節,大概到3月份就結束了。那次禽流感全省總共二十來個病人,絕大部分都轉診到金銀潭來了。所以當時我也是這種心態:集中精力把這幾個轉診來的病人救治好。
但是,前面說是7個病人,實際上後來轉診來了9個病人。為什麽是9個?有兩個一起來的家屬說自己也有症狀,不肯走,也要住院。所以第一次是9個病人,當天晚上就住院了。
2
12月30號,做了最正確的一件事情
12月30號是周一。上午科室醫生在病房裡討論完病人情況,我也去問了一下。他們告訴我,病人都做過了咽拭子檢測,但檢測出來結果全部是陰性。當時也有一個試劑盒,裡面可以檢測到32種病毒,涵蓋了SARS冠狀病毒。
別人基因測序說有,我們為什麽沒檢測到呢?沒檢測到,那就有問題嘛。我就跟黃朝林副院長說:“不行,我們得把所有的病人做肺泡灌洗,先進行支氣管內鏡檢查,之後再做肺泡灌洗。”
下午2點鍾,內鏡科主任帶著護士進去了,大家也是防護得非常好,用上了正壓頭套。
這是個有創的檢查,轉來的9個病人裡有兩個人拒絕簽知情同意。
到下午4點,7個人的肺泡灌洗全部做完以後,我們把樣本分成四份,一份交給武漢市疾控中心,一份交給中科院武漢病毒所,另外我們自己留兩份,考慮到以後可能會用得著。
大概4點多鍾的時候,樣本已經全部準備好了。武漢市衛健委的一位分管領導帶著疾控中心的人也到了金銀潭,這時候疾控中心的人告訴我,他們做過了32種病毒群檢測,這32種病原體什麽也沒有。
我告訴疾控中心,我們的7份樣本全部在這了,請疾控中心盡快把它檢測出來。
同樣我們和病毒所也說了。很快,他們連夜就做了檢測,兩個和SARS冠狀病毒相關,測出來是陽性。因為它和SARS冠狀病毒同源性很高,所以會呈陽性反應。這就更加讓我相信,肺泡灌洗這個措施應該來說非常及時。
我的一個判斷是,病人是下呼吸道先感染,直接感染到肺泡,逐漸發展到把肺泡佔滿了,然後從肺泡漫出來,之後咽拭子才能夠檢測得到。這是我自己的觀點。
到31號下午的時候,國家隊的專家還有省內的一些專家就過來了,坐滿了我們的大會議室。當時已經不是9個病人了,30號接著在收病人,31號也在收病人,大概已經有20多個病人了。大家把所有病人全部過了一遍。說完以後得出結論:首先,這些病人畫像畫完都是一個樣子,所以肯定是同一種病;第二個結論:他們說這可能是病毒感染,不是其他感染。
當天晚上,就開了一個跨年的工作會議。到1月1號凌晨兩三點鍾的時候,武漢市領導決定:關閉華南海鮮市場。
我現在並不知道國家衛健委為什麽派專家來,可能是30號晚上我們這兩個陽性結果已經報到國家去了,也可能是網絡上的輿情引起了國家CDC的警惕。
但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給病人做肺泡灌洗是早期我們做得最對的一件事情。我做醫生、做醫院的管理者,至少這個關口我沒松掉。萬一松掉了,那我就是罪人。所以,我們這家醫院具備這個能力,你就必須把這些做掉。核心就是你要守土有責,每一件事情都要守土有責。
第三方檢測公司當然也是可信賴的公司,但是你作為一家醫療機構請到了CDC和病毒所來檢測,得出這個結論印證第三方公司的檢測結果,這個證據鏈就是很強的。
3
元旦過後,金銀潭成了風暴之眼
接下來病人逐漸開始增多,1月2號、3號不停地有病人來。
境外的媒體也在關注。有同事發圖片說CNN、《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都報導了,並且把我們醫院的照片作為背景放在報導裡。
媒體的關注也讓我提高了警覺。那個時候我就跟大家說,我們現在是在“風暴之眼”,是世界媒體關注的地方。當時我本人也感覺到,這個事情還可能會比較重大。一個是病人增加的速度比較快,到了2號、3號的時候,已經有四、五十個人。病人越來越多,政府關注也越來越高,每天都有匯報、報告。也有很多專家過來,包括疾控方面的專家、病毒所的專家,還有醫療的專家,比如李興旺教授和曹彬教授,大家聚在一起討論,希望可以集中力量打個殲滅戰。
三十、五十,然後八十、九十、一百……病人逐漸就漲到這個數字了。當時就聽到專家們說,外面哪個醫院哪個醫院現在也有很多病人。實際上當時我們在醫院裡消息還是很閉塞的,因為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醫療救治,忙不過來,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麽事情。在醫院裡面清楚的是什麽?是我這裡病人很多,病人很重,我們要不停地準備,把病人接納下來,讓病人能夠得到安置。
可能每次我們的動作都比事件發展稍微快了半拍,一拍都沒有,只能快半拍。怎麽快半拍的?病人突然要增加的時候,我們已經清空了一個樓層,準備接病人來了。樓層不是清完了就可以住病人的,清完了以後還要做徹底的消殺,地面、物表、牆面、空氣,統統要做消殺。消殺完以後,要把所有的單元,床、床頭櫃、凳子等等準備好。
反正先準備吧!因為已經感覺到外面病人在增加。當你準備好了以後,“嘩”一下!這個樓面又滿了。還沒住滿的時候我們就又馬上準備下一個樓面,一個樓面一個樓面地展開。
剛開始的時候不是開的ICU,是普通的隔離病房。包括我們6樓、5樓、4樓,當時都是普通隔離病房。後來大概是十幾號以後,重症病人增加得非常快,而且省衛健委組織了同濟、協和、省人民醫院的 ICU團隊來支援我們,要求他們一人對應一個樓層的ICU病房。這個時候,我們就把南6樓、南5樓改造成了ICU病房。
大概也就是1月3號到5號的時候,我們就開始緊急採購呼吸機、監護儀、點滴泵、體外的除顫設備還有心肺復甦設備等等。每個樓面大致按照25台呼吸機、25個點滴泵這樣來準備。其實準備好以後也還是有點顧慮:是不是開口開太大了?準備這麽多,萬一沒用呢?萬一買多了平時又用不了,這50台呼吸機怎麽辦呢?
實際上到了十幾號以後,所有的呼吸機都用上去了,該上ECMO的也上了。
當時倒也沒有感覺是在作戰,隻覺得事情很緊迫。當時我也跟我們的同事反覆強調:要保衛我們這個城市,保衛武漢的人民,我們不希望把武漢人民困在這裡,如果我們很快地把疫情控制住,大家春節該幹啥幹啥。
因為思想動員做得比較充分,所以每個樓面開展起來還是比較順利。我們醫生護士沒有一個人抵觸,有時經常是晚上突然通知他們樓面要清空,要轉運其他的病人,他們就得把在院的病人轉到另一個樓面,然後把樓層清空做消殺做處理,第二天早晨再收其他的病人。這套流程我們做了很多次,雖然很忙,但還是比較有序。
當時病人每天逐漸在增加,我們整個三幢樓,南樓、北樓包括綜合樓已經全部清空了。當時我們還有一個GCP(藥物臨床試驗)病房,它佔了一層樓。本來我們過完年後還有臨床試驗要進行的,到了臘月二十七的時候我已經下決心要關閉了。GCP是我最後關的一塊,目的就是讓我們的同事全身心地投入醫療工作。
所以為什麽我說每次都要快半拍,是因為我自己首先心理上做好了準備,我們同事也做好了心理準備,而不是等到局勢逼我,要我們做這個決斷。
封城是幾號我不知道,說實在的沒有太多的印象。只是覺得每天都很緊張,每天都有大量病人要收進來,每天有那麽多重症病人要搶救,要氣管插管,有的病人要上膜肺,還有一些病人在死亡……
因為不停地有病人進來,就必須有病人出去才行。有的病人一待二十多天,怎麽得了?那醫院就堵成“堰塞湖”了。當時的出院標準一是持續10天不發燒;二是症狀消失,症狀改善;第三是肺部的影像吸收,因為當時沒有別的檢測方法。1月1號到1月31號,我們將近有三百多個病人出院。
這樣,醫生臨床的工作量就會非常大。我們整體的醫務人員有限,而且他們又是在穿防護服的狀態下來做這些工作,所以做起來就非常吃力。到了春節前夕,確實有點吃不消了。
當時也已經有媒體過來了,我們也沒太關注,完全沒有心思跟媒體打招呼。一直到大年三十的時候,有人說央視春晚上面有你們醫院的鏡頭,我當時也覺得很意外。
4
1月9號之前,已經把病人的餐飲全部承擔起來
最早我們病人是收費的,兩千、三千,有些搶救的病人交一萬、兩萬都有。媒體在報導中提到治療費用後,政府很快給了指示:不要病人交那麽多錢,交個門檻費就行了。
所以大概是1月5號的時候,我們就隻收醫保的起付線。
大約9號之前,我們就已經就把病人的餐飲全部承擔起來了。為什麽呢?因為3號、4號我去病房查房的時候,看到了很多病人自己定的便當,中午吃的晚上吃的,都沒收拾完,堆積了很多。因為是他自己掏錢買的,我們也不好處理,他說他還要吃你怎麽辦?發現了這個現象,我就下決心了,每天吃飯的費用暫時不要由病人付,我們先承擔下來再說。
當時給病人的餐飲是按一天90塊錢準備的。到了1月9號的時候,市委市政府明確說了,病人費用一分錢不要收,已經收費的統統退還。既然政府已經說到這個份上,我還是比較敏感的,那就病人和醫務人員應當同一個餐標,統統按120塊錢準備。
這時候病人飲食也得到改善了。雖然知道便當難吃,但病人也會體諒我們:這份餐食是由醫院代表政府提供給大家的,而且標準又和醫務人員一樣,他們吃什麽我們吃什麽,這樣做下來以後,整個病房氣氛就比較平靜,不會再為吃飯的事情發生爭執。
春節前我們還啟動了一項工作,就是克立芝的藥物臨床試驗。
最早也就是1月5、6號的時候,中日友好醫院的曹彬教授跟我們提到了克立芝,他把文獻給我們看,說在2003年SARS末期的時候,香港的袁國勇院士用這個藥治療了一部分SARS病人,通過和歷史數據對比,可以看得這個藥能夠抑製SARS冠狀病毒。
既然有證據,而且這兩個病毒又比較靠近,我們為什麽不用?而且我們有一個先天的優勢,因為克立芝是抗艾滋藥,我們醫院是管艾滋病的,全省的艾滋病藥全部在我們這。
當時想著一個病人按14天來算,大概是需要56顆藥,一瓶藥120粒,可以給兩個病人吃。按照這個算法我們大概有1000人份的藥。所以我們很快在臨床展開了,鼓勵一些科室主任,如果有重病人的話,趕快給這個藥,說不定有用。
用了大概五、六天的時候,有個主任打電話給我,很興奮,他說,“張院長,那個藥好像真的有效!”
我說怎麽有效呢?他說他把吃了藥的幾個病人的片子拿起來對比了一下,好像確實肺的吸收要快一些,病人的病灶區全部在往吸收方面好轉,這給了我一個很強的信念。
再往後,我們就嚴格按照臨床試驗開展了。2月2號,整個臨床試驗入組完成。現在來看,臨床試驗效果是好的,不能說是特效藥,但是是有效藥。 “我們既要在疫情這塊要打勝仗,科研這塊也要打勝仗。”這兩塊現在已經顯現出來了。
曹彬教授作為第一批來的醫療專家,他為前期的病情診斷和病人救治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印象最深的還是,他每次看病人不僅僅是聽匯報,他要穿上防護服到病人跟前去一個病人一個病人地看,看完了以後他會給一些醫囑,或者基本的判斷,比如呼吸機該怎麽調整等等。
有一次我跟他進病房,當時有個女病人,也就三十五六歲吧,情緒非常不穩定。她一直在ICU裡面哭,吵著說我要回家。其實她當時已經缺氧很厲害了,用的高流量給氧裝置,但還是在不停的哭鬧。曹教授來了以後,我就跟她介紹說,這是北京來的中日友好醫院的曹彬教授,他是國家醫療隊的專家,特意來看你。曹彬教授非常體貼地跟病人溝通,告訴她現在得安安心心在這治療,有這麽多人在關注她、幫助她,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把病要治好,病人逐漸也就安靜下來了。
5
春節前,衛生員和保安突然辭職了
前面說到元旦前我們開了一個連夜的跨年會議,我和我們院王先廣書記是凌晨三點多會議結束後回到醫院的,當時想在對面的酒店找個床睡一下,但是沒床,王書記只好睡在躺椅上,我睡隔壁一個沙發,睡了幾個小時。早上六七點鍾,我們就讓院辦通知所有職能部門以及科主任、護士長全部到崗。當時覺得也就是要取消一個元旦假期,後面可能還有一個周末,並沒有覺得全部假期要砍掉,後來是一個一個取消的。再往後一點,就沒有考慮過春節休假了。
所有護士的正常休息也取消了,甚至下夜班的休息都不能保證他們了,這是最痛苦的時候。因為我們的人手已經到了極限,每個病區的人手根本就拉不開。我們一個病區也就是十五六個護士,而管理的病人是三四十個。穿防護服進去一乾就是4個小時,4個小時換一下,再進去幹4個小時,每天8個小時在裡面。
大概是1月12號到15號之間,有一天突然走了50多個衛生員。他們看到病人來得那麽多,醫護人員防護這麽緊密,很害怕。雖然我們對衛生員也是要求全部做三級防護,就像對自己的員工一樣,因為他們汙染了也會汙染我們的同事嘛,但有些人還是很害怕。我們總共一百多個衛生員,走了一半。還有當時臨時聘用的18個保安,有一天突然全部不來了。
唉呦,可把我們搞慘了!
我們所有的行政後勤幹部職工都要上病房去,送餐。你不會看病人,但是送個餐食應該是可以的,是吧?衛生員走了以後,我們的行政人員也要進去。所以衛生員的工作基本就是護士還有行政人員在承擔。大家也沒有什麽怨言,還是把這事情做下來了。這也是當時碰到很棘手的狀況,你平時覺得一個衛生員怎麽會是個事情?在這個狀況下就是個事情。
本來ICU護士還是配得比較充足,後來實在沒辦法了,臨床其他科室護士不夠,只能削減ICU的隊伍去滿足其他的隊伍。因為普通樓面的病房裡面也有很多重症病人,普通病房的工作狀況可能不比 ICU要好。所以當時那些護士在裡面的工作時間非常長,做得很苦。
到了大年三十,解放軍的醫療隊、上海的醫療隊進來以後接管了我們四個樓層,極大地緩解我們的壓力。你就覺得這個事情有希望了。而且你會感覺到我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後來解放軍醫療隊走了,福建的醫療隊過來了,這也是特別能戰鬥的一支醫療隊,他們管理的兩個樓層收治病人和出院病人都非常多。他們在的兩三個星期,收治病人是一百九十多,出院病人一百三十多。
當然從一開始我們也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一直有湖北省和武漢市的醫療機構抽人在這裡支援。
6
1月14號,我愛人也出現了症狀
我愛人是1月14號前後開始有症狀的。她以前是武漢市第四醫院的護士,後來在醫保辦公室工作。他們醫保辦在門診大廳有個服務台,她要在那兒回答病人的一些問題。
14號的時候她就有點發燒,在家有點低熱。那段時間我偶爾還能回家,大概是18號晚上回家的時候,已經十一點多、十二點了。她給我準備了吃的,我就跟她說說工作上的事情,我說醫院的病人很多都有氣短、胸悶、喘氣的症狀。
她說,“我也有點喘氣”,當時我實際上不太高興,因為我每天工作忙得不得了,現在我說病人病情的時候,你跟我說你也喘氣?你為什麽先不跟我說?多多少少有點責備她吧。但心裡又放心不下,我說明天一定去做一個CT掃描。結果第二天上午一掃CT,她的兩個肺體就是很典型的改變。我說做完CT還不行,趕快再做個血常規,一查,很明顯的淋巴細胞降低。
她19號上午做的這些檢查,中午我就抽空回去一下,給她采個痰,同時給我自己也采一個,因為我還要工作,如果我感染了我也得隔離。采兩份痰,兩份肛拭子,送到醫院來做檢測,當天下午就得到結果:她的兩個都是陽性,我兩個都是陰性。沒得說了,她得去住院,當時是住在四醫院,她的工作部門。
我有壓力,因為我知道這個病是怎麽回事。她反而沒有太大的壓力,她說身邊包括他們同事也有人在生病。
大概20號還是21號晚上,也是很晚了,我自己一個人開車回家,那時候我已經看到了很多死亡,而且不知道那些重症是怎麽發生的,不知道怎麽就朝著那個方向走了,我就感到很恐懼,開著車,眼淚就奪眶而出,很害怕,因為你不知道你的親人會發展到什麽程度。
幸運的是,她很快就轉歸,大概一兩周就康復了。出院回家也是她自己回的,我沒時間去接她。
實際上我幾乎就沒怎麽照顧她,住院期間我就去過一次,陪她在床邊坐了一會兒,聊會天,拉拉手,給她一些鼓勵。
我一直覺得對她有愧疚,在她最艱難的時候沒有照顧她。我們兩個人感情比較好,她也說她對我有愧疚,在我工作最忙的時候沒給我幫上忙。
後來,因為我可能在媒體上有一些影響,就跟她聊了一下血漿捐獻的事。她說,正好他們有幾個同學,包括一些同事也願意參加血漿捐獻。她是主動的,其實不應該說是我動員的。我說,“等我們采漿點準備好了,你就到我們這邊來獻漿算了。我在媒體上說過了,你也支持一下。”她說,“不是要支持你,我本身就應該做這件事。”我妻子還是蠻勇敢的。
一開始我的防護也做得不是特別好。幸運的是,可能我們院感控制做得比較好,辦公區域一直都是清潔的,所以反而沒出太多事情。
7
我們全院感染21個人,現在都出院了
總共我們全院感染是21個人,有8個是行政人員,另外大概有9個護士。8個行政人員有一個很明確是在華南海鮮市場感染的,完了以後又感染了我們另外三位同事。真正在病房裡面感染的,就一個醫生。另外有一個醫生是在檢驗科,因為要給病人做血常規、生化常規,開蓋的時候可能會有小的氣溶膠“嘭”一下懸浮在外面,檢驗科的同志可能是這麽感染的。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黃院長,可能跟他經常在病房、在門診,跟病人接觸比較多有關係。
現在,我們所有的醫務人員都出院了。恢復得都不錯,有的已經來工作了。
而那些罹難的醫生,無論是中心醫院的、漢口醫院的,還是武昌醫院的劉智明院長,我們大家都是非常好的朋友,聽到這個消息還是很傷心。他們是自己的同事、同行,感情上確實也受不了。我們每天都在救別人,你對自己的同行同事卻完全手足無策,幫不了他們。你會覺得很沮喪,很沮喪。
災難醫學這一塊,它是需要擴充的,我們要做好這種物質上的準備和思想上的準備。思想上有準備,事件來了,你就能夠很正常地應對它,不會很慌亂,不是這個事情“嘩”一下砸到你頭上。你平時沒有積累,這次我們肯定會垮掉。你個人很浮躁,就會帶動你的團隊也很浮躁。雖然我脾氣很急,但實際上我是一個偏安靜的人,我願意一個人或者兩三個人這樣坐著聊聊天,說點事情。首先第一個是你要安靜,他會給你蓄積這些能量;第二個,平時也要很敏銳,要觀察事情,你知道外面發生什麽事情。
這次的災難,我想給我們國家、給我們醫療專業的同事包括衛生管理部門,也會提供一些其他的啟示。
我們國家發展到今天,為什麽醫患矛盾這麽尖銳?為什麽現在(疫情期間)就沒有這個矛盾?醫生護士和大家一起共對災難是一方面,那如果我們要收費呢?現在是國家很強大,把這個全部包住了。但是我自己的一個感受,如果以後我們的醫療能夠保證那些最低端的邊緣化的人群,能讓他們享受一些免費的醫療,就能讓我們整個社會心理得到安定。如果你需要更好的醫療,你就要努力地工作;如果你實在是條件很差,現在還有一個最基本的醫療在這。應該有個性化的、高端的服務,也應該有方艙醫院這樣平民化的東西,讓平民百姓能夠得到一些免費的醫療,基本的救助。因為資源永遠是有限的,你不可能把資源配置到無限的狀態。
要說這次疫情最大的感受,還是祖國的進步、國家的強大。1999年我在阿爾及利亞曾經看到為應對一場疫情,他們一個醫院可以一下子拿出六七十台呼吸機,當時很震驚,因為那會兒整個武漢市,包括同濟、協和,也沒有一家醫院可以同時拿出那麽多台呼吸機。現在我們要申請呼吸機,國家很快組織恢復生產,其他的救助設施,像ECMO、CRRT,包括救治人員調動,也是一樣。
我還是覺得,這次這麽大一個災難,中國人民和武漢人民做出了自己的犧牲和奉獻。封城,雖然是很痛苦,但是也是非常英明的一個決定。包括我們後來的方艙醫院,多大的設想?所以除了佩服,還是佩服,佩服我們的國家,佩服我們的人民。
8
坦然接受了漸凍症的事實
“漸凍症”這個名字翻譯得真是好,就真的像凍住了一樣,你走不開。當你走開了以後反而稍微好一點。你走不開的時候,就只能就一點一點地磨嘰。特別是天冷的時候,晚上我想去病房,又不願意同事看到我這種慘狀,我就趁沒人的時候,自己慢慢過去,看一看。
其實2017年7月份的時候,我就覺得自己要麽膝關節要麽髖關節有什麽問題,走路有些緊繃。最後確診,應該是2018年的10月份。四個節段都有問題,頸段、胸段、腰段、骶尾段全部有問題。我沒怎麽告訴同事,主要是跟我們的黨委書記王書記說了。因為身體疾病也是一項很重要的個人情況,你需要跟黨委報備一下。共產黨的基層領導幹部,基本素質還是應該有的。
我不能因為我自己生病了,然後賣慘。這次這個事情是我主動說的,因為來了這麽多媒體,基本的尊重應該有,你不能人家走,你在這裡坐著。但起身對我來說,這個動作啟動比較困難,我真走開了以後沒什麽事,但啟動是比較困難。第二個是送專家,你總是比別人晚一點,別人會說你,“這是哪裡來的一個院長,這麽大個架子?最基本的禮貌都沒有嗎?”
別人不會怪你,但是你自己覺得還是過意不去。而且來的很多都是我很敬仰的一些專家或者領導,你這基本的禮貌要有。所以後來我想,這個事情還是我主動說好,說了以後別人也不會怪我。
幸運的是,我的身體情況沒有影響到我的工作。同事們也給了我很多的幫助,我現在下樓的時候他們只要看見了,都會過來給我搭把手,稍微讓我扶一下。所以也非常感謝我們同事。
這個疾病晚上它會抽筋,突然一下。這段時間,晚上抽筋又有增加,特別是大肌肉抽搐,要站起來才可能把它壓製住。幾乎每個晚上都要抽筋,一個晚上抽幾次,非常痛苦。倒不是這個疾病走路跛行讓我痛苦,是晚上睡覺睡不了,抽筋可以讓你抽醒。比如這隻手指頭這麽抽筋,上肢有時候也會,我就悄悄地趕快立一下。這段時間也可能是跟勞累有關係。
還有一個就是房顫,昨天搞了一天的房顫,好難受。我愛人都說晚上你說什麽夢話,下回你再說夢話給你錄音錄下來。我昨天就感覺自己說夢話會把自己說醒,關鍵是心裡總有事情。這段時間我就趕快吃抗房顫的藥,今天就好一些。所以昨天為什麽後來我不能接待你,跟這有關係。
昨天下午完全不行,今天還挺好的,今天心裡就不一樣,嘣,嘣……我能感覺非常明顯的。昨天搞了一天了,難受,我晚上睡一覺,就過來了,那挺好的。
對我來說,(患漸凍症)這個事情已成現實,我也就很坦然地接受了這個現實,不覺得有多恐懼。以前我還每天騎自行車,後來專家就建議,不要騎自行車了,容易摔跤,要是摔骨折,那完了!因為本身骨折以後肌肉容易萎縮,你再加重它怎麽行?反正你就不要騎自行車了。
我最長的騎行距離是70公里,在武漢環一整圈,我蠻喜歡一個人背著水騎行,感覺很青春!有時候上班也騎自行車過來,就蠻舒服的,沿路上有很多風景。我還徒步走到過醫院,從家過來15公里,三個小時,包括生病確診以後也走過。
武漢確實還很美的,特別是我們現在做了綠化步道,很漂亮,看著蠻舒服。我現在也還能走,但是上台階下台階害怕,我就像老頭老太太那樣舉個拐杖上下。登山杖我已經用了很多副了,最近他們說國博要征集文物,我還開玩笑說,乾脆就把我的舊登山杖給他們算了。
口述時間:2020年3月12日
“我們經歷著生活中突然降臨的一切,毫無防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用來形容這些天,是那樣的貼切。
在突然被按下暫停鍵的危城武漢,既有個人的茫然無助,也有凡人的挺身而出。恐慌,痛苦,感傷,感動……災難之下,再剛硬的人也變得柔軟。
我們想通過十個人的講述,記錄這段歷史,記錄2020年這個春天的武漢。
策劃:高岩、任捷
採訪:郭靜、凌姝
編輯:章成霞
製作:單丹丹
新媒體:孫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