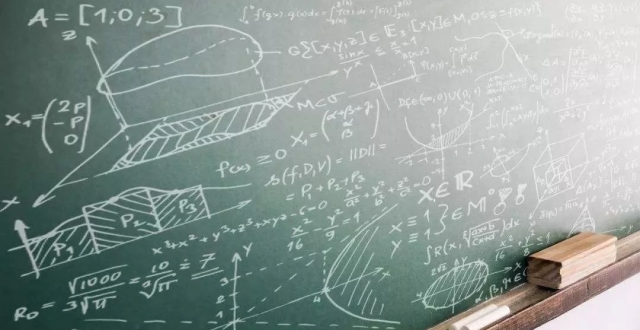1881年,清光緒年間,一個叫查理·宋的中國年輕人進入了杜克大學的前身三一學院。
當時他十八歲,在絲茶店做過學徒,在緝私船上學過劍術。緝私船船長瓊斯和教會牧師的培養和推薦幫助他叩開了杜克的大門,成為杜克歷史上第一位國際學生。
畢業後,他做過傳教士、洋行買辦,乾過新民主主義革命,還養育出了赫赫有名的宋氏三姐妹——他就是宋耀如。
這位不遠萬裡奔赴杜克求學的少年,比第一批庚款留學生赴美還要早二十八年;當時他並不知道未來自己及子女將如何影響中國近代史。

1934年,一個叫理查德的年輕人,拿著全額獎學金赴杜克大學法學院報到。
就讀期間,他加入了學校的《法律和當代問題》編輯部,還被選為校律師公會的主席,不斷為反對種族歧視發聲。1937年,他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績畢業。
那時的他一定想不到多年之後自己會成為美國第三十七任總統,並因開創美國總統訪華的先例以及簽署一份《中美聯合公報》而讓“尼克松”這個名字家喻戶曉。

2013年,杜克大學走出美國北卡州,跨越近兩萬公里來到中國,和武漢大學、昆山市政府共同創辦了昆山杜克大學。
譚好是這所年輕大學的第一屆大學生。
夜晚,時針走過十一,她還在讀第二天上課要討論的一百多頁閱讀材料;讀完書,她又開始學西班牙語,“drrrrr”和“trrrrr”在她的單人宿舍裡回響。
接下來的四年中,她和她的同學們將有機會到杜克的北卡校園學習,並在畢業時被授予杜克大學的本科學士學位,和昆山杜克大學的本科學士學位,開啟下一段人生旅程。

從開始籌建這所大學,到2014年迎來首批碩士研究生,再到2018年秋天來自全球各地的首屆大學生入學,約莫十年過去了。
首屆 259 名大學生來自 27 個國家——這樣的全球化密度,或許尋遍世界也難以得見。
國際學生將近一半來自美國,此外還有來自英國,法國、韓國、紐西蘭、巴西、摩納哥和塞爾維亞等國的學生,不遠萬裡來到這個位於上海與蘇州之間的秀麗水鄉求學。
同樣,教授也來自於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挪威、韓國和印度等世界各地。
一所年輕的大學,一場從零開始的建造。
昆山杜克大學相鄰的陽澄湖以大閘蟹聞名。作為第一批吃“大閘蟹“的人,究竟是什麽吸引了學生和教授們來到昆山杜克?

你們是“知道”勾股定理,
還是“相信”它是對的?
早七點半,天蒙蒙亮,剛開門的食堂裡已坐下了早起的學生。幾個學生為了省時間,用一杯涼開水兌進才出鍋的粥裡,早早吃完便把自己埋進圖書館。
經歷了嚴苛的高考,家長們終於為孩子們松了一口氣。沒想到,這批考生和他們來自全球各地的同學一起,很快迎來了和中國高考同樣嚴苛的美式本科教育。
四川男孩熊一安的媽媽很心疼兒子。
“兒子每天都會抽空在微信群裡和我們‘匯報’狀態。他經常忙得連剪指甲、倒垃圾這種事都要寫備忘才記得住;11 點過了還在說,‘今天還有 97 頁書要讀’,一讀就往凌晨兩三點跑……我們看著心疼,忍不住問兒子,‘你現在比高三還忙還累,有沒有後悔?’他卻說,‘沒有,忙得舒服,心安’。”
心疼之餘,熊一安的媽媽說,“作為家長,其實我們心裡又暗暗高興”。

同樣高興的還有這所學校的校長馮友梅教授。
馮友梅校長去年卸任武漢大學常務副校長、和首屆大學生幾乎同時“加入”昆山杜克大學。
作為中國恢復高考後考進大學的第一批大學生,馮友梅比這些新生上大學整整早了四十年。
在這些新生的身上,她看到了當年的自己和同學們在醫學院苦讀的影子。
“學生們熱愛學習,教授們熱愛教學,整個學校以學生和教授為中心、以教學和科研為中心,這就是大學該有的樣子。”馮校長對此不無驕傲。
來自湖北的王燁宸中學時就在信息學奧賽上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上完第一堂數據科學課後,他覺得自己開始像個學者。
“我們小組的結課課題是《道德經》。《道德經》怎麽做數據分析?它有一百多種英文譯本,但是每種譯本的翻譯都不一樣。比如‘道’這個字,有的譯者翻譯為 ‘Tao’,有的譯者翻譯成 ‘Way’。
我們將每種譯本提取出來,根據不同作者的翻譯習慣將這些譯本進行分類,然後比較同一個類別的譯本,找到他們的作者是否有一些相同或是不同之處。
他們是否來自於同一個國家?翻譯習慣是否受時代和作者年齡影響?是否存在一個統一的翻譯流派?這些都需要從數據中找到答案。”
“在最後一周,我們精心製作了項目海報並做項目展示。每一個同學都為了讓別人理解其獨具特色的課題,絞盡腦汁地去解釋說明。這讓我感到自己不僅僅是一個學生,更是一個學者。
學生大多是被動地接受知識,而學者則是主動去發現知識。我們需要每晚熬夜到凌晨查找資料,編寫算法。從毫無編程基礎,到精通 Python 語言,甚至能自創算法,做一些有意義的項目,這一切隻用了短短七周。”

在昆山杜克,學生們挑戰的絕不只是自己的體力和智力極限。
在全球化中國研究課,放棄了哈佛錄取的薩爾瓦多男孩阿爾貝托·納亞羅(Alberto Najarro)和他來自全球各地的同學們剛剛討論了二戰中中國的角色。
阿爾貝托說,“我們國家的歷史書在講到二戰時很少提及中國,許多人覺得中國並未進行積極的抗爭,也沒遭受太大的傷害。
這堂課讓我看到了中國的抗爭歷程,我也從中習得了和不同背景的同學談論各自國家時的正確態度:不要著急下定義,不要讓偏見演變為無知”。
譚好理想的大學是雅典學院式的。學生可以依喜好選擇天文,物理,文學,數學,哲學等各類學科;課堂不大,師者或引導,或詰問,從不干涉學生表達意見的自由。
昆山杜克的課堂契合了她的想象。

歐文·弗拉納根(Owen Flanagan)教授的哲學課是令譚好印象最深的幾門課之一。“教授鬍子花白,看起來就是位智者。”
她清楚記得第一堂哲學課的情景:
教授問:世界有幾個大洲?
學生們答:7個。
教授:如何定義“大洲”?
學生:被海洋包圍的一塊陸地。
教授:那歐洲和亞洲之間有海洋嗎?南美和北美之間以前連河都沒有,那裡有海洋嗎?
……
教授:誰知道勾股定理?a^2+b^2=c^2
大家紛紛舉手。
教授:誰能現在立刻證明?
只剩寥寥幾個人。
教授反問其他人:你們究竟是“知道”勾股定理,還是“相信”它是對的?

弗拉納根教授對“知道”和“相信”的提問,顯然觸動了同上這門課的美國男孩科林·亨利·史蒂文斯(Colin Henry Stevens)。
一次早餐亨利遇見了弗拉納根教授。餐桌上,他不帶拐彎地詢問,“我們為什麽要相信你?”教授點頭,“這是個好問題”,隨後帶進教室拋給其他學生:“你們為什麽相信我?因為我的博士學歷?我的幾十年教學經驗?或許我們的教育體系本身就是錯的?”
大家隨後就“教育”與“權威”進行了一場討論。
譚好說來到昆杜後困惑變多了。“越學,越覺得自己無知,越無知,越要學,越要追問。“
不只是冒險的,同時也是有趣的。
“你最愛昆山杜克的什麽地方?”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提到了“教授”。
昆山杜克的師生比約為1 : 11。得益於這一近乎奢侈的師生比,學生們可以在課堂內外和教授們都有非常深入的互動。
昆山杜克的特色之一,是在本科階段就為學生提供和教授一起做自主研究的機會。
四川男孩周子昂就加入了由電子工程教授李昕、化學教授高嵩和數學教授劉哲共同領導的一項用大數據方法研究空氣汙染的項目。
周子昂沒想到大一就能跟著教授做研究,“我以為至少要到大三”。
“我們從各地的歷史汙染指數數據庫中挖掘出有用數據並搭建模型,通過數據可視化繪製不同城市的汙染物變化趨勢,通過機器學習對未來的空氣質量進行預測,以便更有效地展開預防和預警,降低人們的健康風險。

團隊連我一共 6 個同學,有同學負責閱讀環境科學相關的文獻,有同學負責製圖,我負責編程。
項目預計進行 14 周,我們每周開組會,交流手頭工作進度,教授們則會給出意見和指導。
教授的期待是,項目完成後我們能在學術刊物上發表一篇有分量的論文。”
同樣,對於李昕教授來說,在昆山杜克工作,也讓他在合適的時刻遇上了合適的學生。
李昕教授是國際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會士,在卡內基梅隆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多年的他,放棄了卡內基梅隆的教職加入昆山杜克。
這裡的首屆大學生讓李昕教授印象深刻:“他們是特別有開拓精神和創造力的群體,他們對世界充滿好奇心,懷著執著的探索精神,願意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付出。
對於我們每一位教授,這樣的學生是求之不得、千載難逢的。”

跨學科的高度融合是昆山杜克的另一特色。
學生可以在一門課上學到幾個專業的知識;這也同樣意味著,教授們要和別的教授一起合作,共同來開發和講授同一門課程,並且要付出比單獨開發和教授一門課程多得多的時間和努力。
彼得·皮克爾(Peter Pickl)教授自2010年起就在曾培養了 31 位諾貝爾得主的慕尼黑大學任教,如今來到昆山杜克的他十分看好這所年輕的國際化大學。
“昆山杜克的課程設計遵循了最前沿的理念。這些教學理念包括將不同學科融合到一門課程。例如生物、化學和物理由三位不同學科的教授聯合授課。
這類融合課程在西方大學非常普遍:我之前所在高校慕尼黑大學,它的碩士項目也有此類課程,比如數學和物理聯合授課,生物和計算機科學聯合授課。而昆山杜克大學在本科階段就融入了這一理念。”
公共基礎課之一的全球化中國研究(China in the World)由兩位歷史學教授傅知行(Zach Fredman)和朱倩,人類學和考古學教授斯科特·馬塞切恩(Scott MacEachern)以及人文學和宗教學教授詹姆士·米勒(James Miller)共同執教。

四位定期碰面,討論如何讓學生了解更多維的中國。
傅知行教授形容他們就像一家小型的矽谷創業公司,“我們的課程大綱是動態的,如果學生對絲綢之路的討論異常活躍,或是提議了解更多中非關係的知識,我們就會相應增加這部分的教學”。
除了杜克水準的教學質量,學生從教授身上學到的還有更多。
“平等”是學生們對與教授交往最深的印象。
本科課程事務與教師發展院長彭諾亞博士(Noah Pickus)和他的女兒米拉每周都會舉辦一次晚餐聚會,邀請學生到家中做客。
他們一起嘗試做煎餅、香辣秋葵和炸蔬菜等各種菜式,許多從來沒有做過飯的同學把大廚初體驗獻給了教師公寓的開放廚房。

美國數學學會會士劉建國教授為學生買早飯的故事也已傳為美談。
據來自江蘇的王瀟楠媽媽回憶,“瀟楠和三個同學周五有一個實地考察旅行,與當天的考試衝突。劉教授得知後決定在周五早上六點半為他們四個人專門提前考一場。
考慮到孩子們考完就要趕去上海,沒時間吃早飯,劉教授還特地為他們買好了三明治和果汁”。
除了師生間的互動,學生和教授們都很享受的還有“創建者“和“設計師”的角色。
因為沒有現成的學生社團可加入,學生們便從起草章程開始,自發組建了編程、哲學、模聯、戲劇、辯論、創業創新和跆拳道等 40 多個社團。
社團的招新會上,象棋社的攤位前黑白棋廝殺不停,籃球社同學搬來籃球架玩起了現場投籃大賽,擊劍社的同學則全副武裝地來了場劍術表演。每周五晚,足球社的同學都會一身短袖球衣出現在操場。
足球在綠茵場上來回穿梭,霧氣在他們紅熱的臉上升騰。

和學生們一樣,進入這樣一所全新的大學任教,於教授而言也是一次特別的體驗。
“只有少數教授能享有在一所新的大學加入開創型教師團隊的經歷,這樣的時刻千載難逢。”皮克爾教授說。
繁重的教學任務之餘,皮克爾教授偶爾會在學校附近的餐廳樂隊客串一把,那時的他不再是嚴謹的德國科學家,而只是一位 study hard, play hard 的歌手。
和皮克爾一樣熱愛音樂的瑪西婭·弗朗斯博士(Marcia France)除了是化學家,也曾是岩石橋交響樂團樂團的首席長笛演奏家。
她從大洋彼岸的美國選擇加入昆山杜克大學,任職大學生院院長。此前,畢業於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學院的她,在美國頂尖文理學院華盛頓與李大學工作了24年。
談到為什麽放棄這所,由美國國父華盛頓和南方著名將領李將軍參與建設的大學、來到中國,弗朗斯博士答道:“長久以來,我都喜歡各種國際化的事物,比如旅行和了解不同的國家和文化。
我被昆山杜克大學的國際化辦學理念吸引,很開心有機會來到中國工作生活。同時,我也非常熱愛從事大學生博雅教育的工作。在與來自全球各地不同背景的同事和學生交往中,我們重新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文化,享受共同建造新事物的樂趣。”

在昆山杜克這樣一所年輕的大學,弗朗斯博士認識到給予教員和學生充分的反饋和討論空間至關重要。
“我們開放了多種反饋機制,比如教學評估團隊會定期對課程教學進行評估,以便教員適時地調整教學策略;我們定期開設教員工作坊,討論課堂學習中存在的普遍問題以及如何提升教學效果;
我們有非正式座談,邀請不同國籍不同背景的學生組成‘焦點小組’一起交流學習生活;我們有專門的線上反饋渠道,學生們可以留言並提出建議;
除了每周五的辦公室時間,我還辦了一個 “院長下午茶”(Tea with Dean),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三學生可以和我預約面談,周三下午則開放自由拜訪。”
“這樣的溝通讓我們能第一時間發現並解決問題。比如許多學生反映閱讀任務太重。

的確,這裡 7 周的密集課程要求學生具備更好的學習和時間管理策略。
於是,教授們就適當地減少閱讀量,同時教導學生如何做有的放矢的策略閱讀,放棄逐字逐句,而是把握文章的總體結構,再挑重點細讀。
很多教授會通過引入導讀或研究問題的方式,來幫助學生更好地關注重點內容。
經過這樣的訓練,同學們學會了‘抓大放小’,其實這不僅是好的閱讀技巧,也是有效的管理時間和人生的策略。”
教授和學生間的直率溝通是否僅是首屆的特權?弗朗斯博士搖搖頭,“昆山杜克將一直保持這一傳統”。
此外,她還希望開創另一個傳統,“我想在這裡和大家建設一個交響樂團。大學不應該只是學習,還應該包括享受學習以外的很多時光”。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英文寫作課講師溫侯廷(Austin Woerner)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形容來到這裡是一場 “Adventure”。
“Adventure 翻譯過來是‘冒險’,但‘冒險’不能完全反映這個詞的全部含義:它是有風險的,同時也是有趣的。”他在接受學生採訪時說道。
寫作課之外,他還創辦了一個“昆杜跨文化讀書會”。
“我們會挑選一些帶有感情的書目分享給同學和同事,告訴大家這本書對我們有怎樣的影響,在文化中如何塑造我們。”
溫侯廷表示這是“人生中第一次與這麽多‘探險家’聚在一起”,“特別有收獲,特別有趣”。

修繕世界
課堂之外,他們還在做更多。
常務副校長丹尼斯·西蒙博士(Denis Simon)說,“希伯來語有句古話,‘修繕世界’(Tikkun Olam),指的是我們有責任為這個世界貢獻力量,使其比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之初時更美好一點”。
2016年11月末,馮小桐向學術事務副校長高海燕博士發去了一封郵件,標題是:“老師,我想捐贈”。
馮小桐是昆山杜克第二校園國際化學習項目(GLS)15年春季班畢業生,現上海交通大學研究生在讀。他戲稱自己曾是“學渣”,在偶然選修了高海燕教授的物理課後重又煥發了對學術的熱情。
心懷感激的他決定將“人生第一桶獎學金”——一萬五千元人民幣全部捐給學校。
馮小桐不是個例。有位同學每年生日當天都會捐贈一筆和自己的生日數字相當的款項。而自2014年秋季起,各個項目的畢業班級更是全都參與了 “Class Gift”(畢業班級捐贈)活動。

作為比首屆大學生更早的先驅者,昆山杜克第二校園項目和碩士項目的校友們當初甚至需要更加堅定的“這就是我的選擇”的信念。
昆山杜克沒有令他們失望。那段校園時光給予了他們堅定走向下一段人生的鎧甲,他們感恩,繼而回饋,鑄就了昆杜精神最初的力量。
對數據科學感興趣的周子昂與幾個同學一起利用聖誕假期去到斯裡蘭卡,參與了一個保護海龜的項目。
“起初我們主要做了一些基礎工作,比如為小海龜的水池加水,測量水的溫度,鹽度,酸鹼度。後來我們開始小心地踩在沙子上,測量海龜蛋的環境溫度。
此外我們還發現,漁民捕魚時經常會撈到海龜,漁網會割破海龜的皮膚,甚至勒斷它們的手腳。海龜皮膚再硬,也硬不過粗麻繩,傷口不斷往外湧出血的樣子特別觸目驚心。
我們很不忍,於是主動提出幫漁民捕魚,把不小心撈上來的海龜搬回保護中心治療,觀察健康狀況,確認沒問題後再放生。”

“當地的海龜保護主要依靠人力,海龜數量一多,工作人員很難每隻都照顧到。”周子昂一邊做志願者,一邊思考如何利用所學解決這個問題。大數據研究中心的空氣汙染項目給了他靈感。
“我想以後可以建立一個海龜數據庫,為保護中心的每隻海龜編號,錄入它們的健康狀況,保護地點等信息,以便追蹤並針對不同狀況的海龜進行相應的保護措施;未來數據足夠多之後,還可以通過機器學習對海龜的相關數據和指標進行預測,更高效地調配保護資源。”
當然一個想法還不足以解決問題,這個瘦高的男孩靦腆地笑了,“我現在的水準還不夠,還需要更努力地學習編程和數據科學。”
和周子昂一樣,許多同學都利用周末和寒暑假時間做義工,用自己的所學去幫助他人。
有的去動物救助站為流浪犬清理毛髮、號召領養代替購買,有的去西南山地參與大熊貓生態保護研究,有的深入緬甸農村調研貧困真相,有的在肯亞研究自然、健康與貧民窟……
杜克大學的宗旨是“知識服務社會”,武漢大學的校訓則是“自強,弘毅,求是 ,拓新”。
在昆山杜克,中美兩所大學的光榮與夢想在這裡扎根、融合;一粒粒用所學知識強大自身、繼而回饋世界的種子在同學們心中種下。

在譚好看來,挑戰自己體力、智力還有思維的邊界,享受美妙的大學時光,參與創建這所大學,並有機會回報社會,正是她心目中大學的樣子。
加入全球健康研究中心做實習研究員的阿爾貝托則說, “昆山杜克能給我親手畫出理想大學模樣的參與感、讓我‘愚蠢’的理想主義有繼續生根的泥土,這是任何其它大學都無法給予的”。
這所大學所在之處,自古便是誕生賢人與新知的靈秀之地。
昆山人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呼號猶言在耳;嘉靖三大家之一的歸有光在此出生、求學,寫就名篇《項脊軒志》;曾任昆山地方官的祖衝之將圓周率推算至 3.1415926 和 3.1415927 之間,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將圓周率精算到小數第七位的科學家……
在這片鍾靈毓秀之地,昆山杜克的學子們又會創造出什麽呢?
是像他們的校友尼克松和宋耀如那樣開創一段歷史,還是像先賢祖衝之和顧炎武那樣發現一些新知,抑或,是從建立一個保護小海龜的數據中心開始?

除了他們自己,沒有人能夠定義他們的未來。
畢竟,他們當中,有的小小年紀就決意要過“經過了審視”的人生,有的放棄了哈佛來到這裡,有的求學路漫漫、單是轉機就要一兩天。
他們是一所大學歷史上的首屆大學生啊,他們是如此勇敢而堅定的少年。
來源:昆山杜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