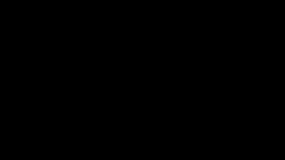我和《繁花》的緣分很深。
去年《繁花》舞台劇第一輪演出的時候,“山河小歲月”組織了粉絲觀摩團,我也做過一輪關於《繁花》原著的講解,甚至還做了一次讀者《繁花》討論會。
我喜歡向朋友們推廣舞台劇《繁花》,因為這是屬於上海的“海上繁華錄”。
我記得之前和《繁花》的作者金宇澄老師聊過一次上海菜市場,他說起報紙刊出1940年一個上海阿姨的專欄,天天開菜單,一禮拜不重樣,非常細,上海人確實講究“翻花樣”“實惠”,講究怎麽“過日腳”,這是市民階級的特徵,即使經過無數次的革命,上海市民仍然“談吃談穿”,非常執著。
特別印象就是,比如一個舊弄堂的上海男人會端坐家門,面對一隻光鴨,戴眼鏡專心拔細毛——也只有上海弄堂男人會這樣做,這麽精雕細刻,耗費一上午時間準備中午菜,屬於上海市民男人的一種享受。
《繁花》給我的另一個感受,是裡面的飯局很多,大大小小,至真園、夜東京,常熟蘇州,長長短短,細細密密,有時候甚至有點厭倦了。但細細一想,人生,不就是一場又一場的飯局嗎?不一樣的組合,不一樣的場合,飯局裡的故事就不相同。
在這個夏天,舞台劇《繁花》第一季推出了複刻版。從原著還原的角度來說,是帶著一種老實而虔誠的態度的。如果你是一個小說《繁花》的粉絲,你會在那裡看到許多忠實的細節。我一開始擔心北京觀眾對於上海話的陌生感,後來發現擔心多餘,身邊一對情侶,男生似乎來自南方,女生則是北地女孩,看的過程中一直問:“這是什麽意思?”“這代表什麽?”小毛罵大妹妹是“小娘皮”,女生問“啥叫小娘皮?”男生戳一戳額頭,說,“鬧,你就是小娘皮。”
我忽然意識到,這也是“鴛鴦蝴蝶夢”。
今天的文章,來自小歲月觀察團。2019年夏天,《繁花》舞台劇再出發,在上海與北京兩地上演。讓我們一起,做一個繁花似錦的仲夏夜之夢。
——阿舒
了解一個陌生城市最好的方式是什麽?
有人是通過食物,乾絲雪白,蘿卜嫣紅,讓人嗅到了揚州的煙花三月;有人是通過風景,石塔印月,湖心映雪,瞬間定格了杭州的如水蟾光。更有人是通過參觀走走停停,琉璃瓦丹朱牆的紫禁城,橫平豎直卻又錯綜複雜的胡同,勾勒出了小歲月現在生活的城市北京。
看完舞台劇《繁花》第一季複刻版,我意識到,了解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可以通過舞台劇。“舞台劇就像一把鑰匙,打開了你與這座城市之間永遠打破不了的那堵水晶玻璃門。你打開了,就和這座城市融合在一起了。”導演馬俊豐如是說。
看懂了《繁花》,就是看懂了上海這座城。
《繁花》的舞台劇化,是為了讓更多非本土人士了解上海這座城。
相比小說,舞台劇《繁花》表演是立體的,它把小說變成舞台上的現實;儘管演繹的只是片段化的日常和世相的邊角,但那些流動的舞台、克制的燈光、優雅的用詞,以及摩登大膽的多媒體和電子樂演繹,都帶給觀眾強烈的視聽覺衝擊和情感體驗,不知不覺,一個嘈嘈切切、堆疊人情世故的上海就浮現於你的眼前。

《繁花》舞台劇的中心是一個大圓盤,劇中人在上面行走最終回到原點,這其中有一種命運輪回的味道。
眾生癡相,舞台劇《繁花》延續了小說的龐雜與格局,男男女女,浮華一生,莫過一個癡字。

人世間,百般癡態,匯聚譜寫了《繁花》。也正是因為種種癡相的存在,舞台上的那些人物才如此鮮活。他們從來不是劇中人,而是你身邊的某個朋友,而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就像是發生在我們自己身邊的事一樣。
如同小說卷首語所說的那樣——“上帝不響,像一切全由我定。”舞台劇《繁花》有這樣的魅力,觀眾們不由自主地脫離上帝視角,將自己的心,放到舞台情境中,跟著劇中人一起哭一起笑,哭笑他們的癡。

《繁花》舞台劇的高潮落淚一幕,姝華讀信。
個性淳樸耿直的小毛,在吃到生日蛋糕時高興地要表示要與眾人義結金蘭,在偷聽到銀鳳向大家提及自己要結婚的消息時感到羞辱憤怒,一氣之下發狠與大家斷了聯繫,這是癡;看似鑽石王老五的阿寶,身邊追求者不斷,心中卻始終放不下兒時那個彈鋼琴化作金魚的小妹妹,這也是癡;少年時期有點激進喜歡明哲保身的滬生,長大之後化身佛系男子,卻始終逃不出陰鬱和暗淡,他過去最純真的追尋和理想,早已隨著諸事灰飛煙滅,徒剩寂寥與淡然,這也是一種癡……
除了演繹各種人的執念與癡態,小歲月觀察團還有三個理由,向你隆重推薦舞台劇《繁花》,都來自我們第一手觀劇體驗。台詞、敘事、勾連時代,無一不繁花,幕起待君來。
滬語,是最上海,也是最上海人的演頒布詞。

語言,可以說是一種極為高級的藝術形式。
就像德裡達所說的那樣,語言總是保持了差別,並且充滿了多重意義與曖昧性。它隱藏著各種文化信息,和地域以及那裡的人密切相關,具有強烈的代表性,又是流動的、多變的,可以完整地體現一個城市的風貌。
即使你不懂當地方言,也能從中猜測出當地人性格一二:東北話爽朗直接,天津話幽默利索,重慶話快起來像機關槍打連珠炮,上海話則是軟軟的、糯糯的,像嚼花生糖。即使不是本地人,但聽多了,也同樣能感受到其中暗含的嗲嗲的性感。

就像電影要看原版一樣,上海人的故事就是要講上海話。言如其人,正是這樣的上海話將書裡的平面世界變成了舞台上的“口述歷史”,支撐起了整個舞台劇的脈絡與靈魂。
舞台劇《繁花》此前在北京市場的成功,一票難求,也正說明了滬語台詞,是塑造人物的必要手段,滬語源自每個人物的靈魂深處,一張嘴就是阿寶和滬生,自然地一幕幕之間生長,指向人心。

我頂頂喜歡的一幕,是囂揚跋扈的汪小姐,向兩個外地閨蜜得意洋洋的描述在徐州遇到的“上海老派男人”如何妥帖周到的那一段:
下午醒過來,模模糊糊,躺在一張雕花帳子床裡,懶懶起身,老派男人端茶過來,放了唱片,備了洗澡水妥帖周到。最後,兩人坐在窗前,邊上是雅致茶几,古薰裡飄來了上好檀香。老派男人換了幾張唱片,留聲機慢慢轉,有一首唱的是,我等著你回來/我想著你回來/等你回來讓我開懷/你為什麽不回來/我要等你回來/還不回來春光不再。
這段話用咿咿呀呀的上海話念出來,自帶一種繞梁不絕的慵懶余韻,連著那“蟾光如水浸花牆,香霧凝雲籠幽篁”的蘇州評彈,也不由自主地籠上一層小資情調的輕紗。你會忽然意識到,這才是屬於那個時代人的高級浪漫呀!

當然,《繁花》注定是要開出上海的,滬語不會成為舞台表演的藩籬,考慮到非滬籍觀眾的觀劇便利,演出是有字幕器的。
平淡的,瑣碎的舞台敘事,就像綿密的織錦,絮絮叨叨也是一種娓娓道來。

如果你曾經對《繁花》小說略知一二,大概能夠猜測出這部小說改編成舞台劇的困難性。
所有人物,愛恨情仇交織在一起,就像劇中人物李李所說的那樣“潮潮翻翻”,重合、疊加、混雜、反覆,很難理出個真正的頭緒。舞台劇抽絲剝繭,3個小時,以阿寶、滬生、小毛三兄弟的情誼及感情生活為經線,再逐漸異塵餘生到別的人物故事去,用平實細密的針腳,扎實地勾勒這幅海派浮世繪。舞台呈現上,也刻意減少單調的旁白敘述,讓觀眾與角色一起融入到整個劇情,身臨其境地感受上海這座城市的變遷和浮光掠影。

多線程的敘事方式乍看之下信息量極大讓人難以接受,但這種繁雜細密也恰恰是《繁花》的魅力所在——
觀眾不用再被情節牽著走,每個人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場景產生屬於自己的獨特審美經驗:你可能在上一秒還在鄙夷汪小姐的輕浮與愛慕虛榮,下一秒就可憐起她“只想生個小囡”的單純與悲涼;前一分鐘還在感歎徐總作為老油條的冷漠無情,下一刻就對他即使落入窘境也不忘托阿寶帶信封而唏噓……儘管沒有強烈的波瀾起伏和情感衝擊,但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都像是飛花撲蝶、草蛇灰線,看似東拉西扯、沒頭沒腦,事實上一個個小小波瀾衝撞起來可以激起千層漣漪,戲劇化的矛盾衝突就藏在日常化當中,最終,匯成一條壯麗大河。

舞台劇勾連了60年代與90年代兩個大時代,時代起起伏伏,人生花開花落,繁花上演。
60、90,時代跳脫,交叉。年代看似遙遠,又相得益彰。舞台劇把交叉性的時代敘事,延續,放大:60年代的純真;90年代的迷醉,平靜與喧囂,在黃浦江之畔,互文上演,正如同人生的起伏跌宕。這,才是上海這座城市真正的模樣。

兩個時代,為演員的表演留出了足以大量發揮的斷層和空白。這種體驗就像是在看八大山人的水墨畫,明明畫中背景空曠,分不清水波還是霧靄,卻依舊能夠激發觀眾的想象,顯出魚遊海裡、鳥飛雲端。正是這種中國水墨畫式的空間留白給了舞台劇更多元的發揮和填補的可能性。
能夠看出來,導演和演員們在不少場景中加入了自己的理解,比如少年時期的滬生和姝華情竇初開,兩人的親密並不是牽手或者擁抱,取而代之的是極為純真的“頭碰頭”,正是這樣的肢體語言,與時代是非常相宜的。觀眾心領神會,這是“真正在演60年代的故事”。
再比如,最後謝幕前,有一個所有回憶一掠而過的場景,配樂融入了導演的私心,叫做《太空重逢》,這段帶有未來色彩的電子樂不僅和整部話劇融合得天衣無縫,還帶有一絲絲庫布裡克拍攝《2001太空漫遊》式的哲思,以及宿命的意味。交叉時代敘事的強大留白,可以對跨時代的東西兼容並包。

對於當下的人們,如果你去問,上海是什麽?
有人會說是個撲朔迷離的魔都,也有人會說是個瞬息萬變的網紅城市,但撥開表面去看更深處,你會發現那些早已逝去的鹹菜大湯黃魚味道、那些略帶慵懶的燈紅酒綠鶯聲燕語,才是上海這座城市的底色。
這一次,舞台劇《繁花》第一季複刻版的使命,就是帶著全新的蛻變,向更多沒有在上海生活過的人們還原這樣的底色。就像導演馬俊豐告訴我們的那樣,“它讓我們知道了我們當下生活的城市是什麽顏色,又有什麽樣的顏色疊加了上去。也讓我們知道現在的我們帶來了哪些東西,又有哪些東西在歷史的長河中被衝刷掉,被留下來。”

劇照攝影:尹雪峰
《繁花》上海場即將開演
6月27日至30日
美琪大戲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