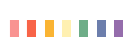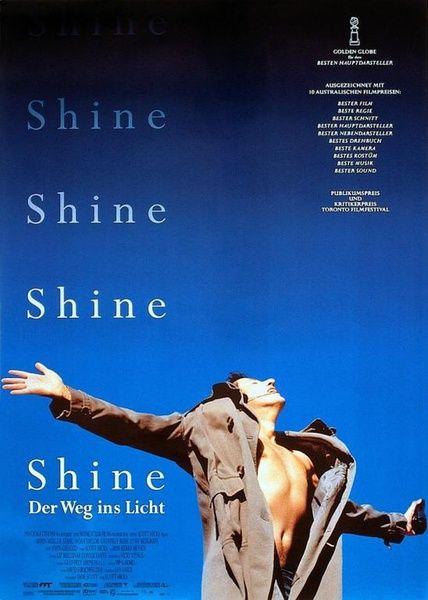2018-5《收獲》

專欄:行走的年代
叩開聖殿之門
——八十年代的上界聲音之覓
文 | 朱偉
音樂是上界的語言是黎青主的說法。青主當年在柏林大學,學的是法學專業,作曲乃內心的追求。1993年籌備創辦《愛樂》雜誌時,我去朔風蕭瑟的風廬,邀宗璞先生賜稿。先生跟我說起陳夢家與趙蘿蕤,說起資中筠,賜了《風廬樂憶》。在《風廬樂憶》裡,宗璞先生就說到,能接近“上界的語言”的人是有福的。此後每想到這句話,我確實就有一種莫名的感恩。尤其是在夜深人靜,聽著那些似乎帶著很遙遠印跡的無伴奏合唱,身臨其境。
有一個奇怪現象:似乎愛樂者的家人都難覓知音。我還記得,倪萍跟王文瀾在一起的時候,倪萍多次跟我說起,經常是,她回到家裡,沒有燈,音樂在黑暗中。打開燈,王文瀾淚流滿面。我太能理解這樣無助的眼淚了。音樂能輕易就撥動我們脆弱的心弦。遺憾的是,我們的親人,卻往往無法理解、不知所措於我們的熱淚。因為他們聽不到上界的聲音。
我知道交響曲,始於“文革”中。
那時候,我家有一台算昂貴的紅燈牌收音機。我有五個姐姐,萍姐是唯一的大學生。她後悔當年報考了體育學院,是家裡最時髦的。紅燈牌收音機是她極力說服父母買的,她回家,就霸佔了這收音機。就在這收音機裡,我知道了交響樂。但聽過什麽?卻完全沒有印象。現在問萍姐,她是一臉茫然。

我被音樂感動,始於俞麗拿的《梁祝》,則是極清晰的。七十年代上半期,我下鄉回家,我家鄰居李家大豐邀我到他家裡。他家“文革”前就有唱盤,母親說,抄家時候,他家一大摞唱片都給砸碎了。這是他家重置的唱盤,在他家木樓上,我當時真被琴聲給鎮住了——母親是越劇迷,越劇《梁祝》十八相送的唱段,我本是熟悉的。但那旋律,由小提琴拉出來,就帶出那麽纏繞、綿暖的情感,它開啟了我的心智——原來世上還有這麽好聽的音樂。我還記得那不是黑膠,是紅色的塑料唱片,還記得大豐當時得意地看我的眼神,他比我大三歲。李家當時給我音樂啟蒙的,不僅是這首《梁祝》,還有大豐的哥哥,我們叫他胖胖哥哥(其實他瘦高,喉結突出,一點都不胖),在夏夜隔著粉牆樹影,傳來的幽衷簫聲。那是多麽誘人的夏夜!可惜時過境遷,大豐現在是天天酗酒,胖胖哥哥則已經過世,那粉牆木樓,當然早就夷為平地,蓋上了醜陋的馬賽克瓷磚樓。
故鄉已經不在,那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故事。
與音樂,大約是需要眾裡尋他的緣分的吧。
我的八十年代真正的愛樂之路,始於俞大使,一位曾派駐日內瓦的老大使,我太太閨蜜的公公。七十年代末,我們去他家裡,俞大使有我眼紅的一大抽屜國外帶回來的進口磁帶,老人吝惜地一次就借我兩三盒。我清楚記得,他第一次借我的,有一盒是奧地利指揮家卡爾·伯姆指揮的莫扎特小夜曲,那盒磁帶上除了那首耳熟能詳的K525《弦樂小夜曲》,應該還有K320的《郵號小夜曲》。憑我直覺,更喜歡有長笛、雙簧管、巴松、圓號等的K320。相對K525整齊欣悅的弦樂重奏,那每一件各種音色的管樂器似乎都能從黑暗中跳出來,彼此對話,其中的慢樂章尤其令我迷醉。另有一盒是匈牙利指揮家喬治·索爾蒂指揮的理查·斯特勞斯交響詩,其中有《唐璜》《蒂爾的惡作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理查·斯特勞斯是浪漫主義晚期的德國作曲家,一個將管弦樂配器發展到複雜無比的大師。《唐璜》與《蒂爾的惡作劇》是他最通俗的兩首交響詩。《唐璜》表現他在心儀的女人之間翩翩起舞,表現他的沉醉,在一次次獵豔的歡愉過後,是空虛寂寞。《蒂爾的惡作劇》則用豐富的樂器,表現一個用各種各樣惡作劇尋找樂趣的小人物,樂器傳達的,其實是一種幽默的溫暖。最後,這個小人物被判絞刑,他戰戰兢兢走上絞刑台,溫暖的惡作劇便也就結束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用音樂表達尼采的思想,則是理查·斯特勞斯交響詩的巔峰。它以查拉圖斯特拉下山面對那個噴薄而出的朝陽輝煌地開頭,然後回溯他在山中,通過憧憬煎熬自己,完成自身與自然關係的思考,表達一個超人誕生的過程。這首交響詩裡表達超人脫胎,尤其是弦樂表現的部分非常之美,這當然都是我後來才慢慢聽出來的。聽音樂,是作曲家的樂思在你面前慢慢清晰呈現的過程。剛開始聽的時候,它們是混沌一片的。我覺得,音樂開啟的過程,就像“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在光與暗之間,慢慢才有了越來越清晰的輪廓,然後才有慢慢清晰的結構與細節。理查·斯特勞斯,我那時當然是不可能理解的,俞大使一開始借我這兩盤磁帶,可能是有目的的:從莫扎特古典主義的小夜曲到理查·斯特勞斯的交響詩,跨越了一百多年音樂史,他讓我聽到兩極。
俞大使那裡,聽完再去借,也好像隻借過兩三次。遺憾的是,他沒有讓我一開始就聽莫扎特的鋼琴協奏曲或者小提琴協奏曲。他借我的,記得有奧地利鋼琴演奏家布倫德爾演奏的貝多芬鋼琴奏鳴曲,不僅有《悲愴》《月光》《熱情》,還有《月光》前的第十三號,這是我尤其喜歡的布倫德爾彈的一首。大約考慮到我的接受程度,俞大使沒借我貝多芬的晚期奏鳴曲。他所借我的磁帶中,印象深刻的,還有一盤吉東·克雷默演奏的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它讓我知道了克雷默這個出生於現屬拉脫維亞的演奏家,他的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是磁帶時代我百聽不厭的曲目。因為這首協奏曲,我聽到了貝多芬濃厚細膩的情感。現在回想,俞大使的音樂修養是相當好的,他沒向我普及卡拉揚。記憶中,奇怪的是,他好像沒借給我過肖邦的磁帶。
那時我家只有一個國產落地單卡錄音機,是七十年代向往有一個落地音箱情結的結果。單卡不能翻錄磁帶,翻錄還須求我太太的閨蜜。
第二位引我進愛樂天地的,就是傅惟慈先生了。認識傅先生,是因為鍾愛他翻譯的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八十年代,好像沒有輩分與階層的隔閡,因為這譯作,我打聽到傅先生四根柏胡同的地址,就可以直接登門找去。好在傅先生家也是隨便可以登門的,記憶中要在胡同裡曲裡拐彎幾次,反覆打聽才豁然找到。傅先生好客,喜歡年輕人去他的小院。據說,北島他們也是當年他家常客,我卻一次都沒遇到過北島。我是在傅先生家裡認識的譚甫成。傅先生那時幫我翻錄過十盒九十分鐘的TDK磁帶(好像我買的是鉻帶),那是八十年代初我最早的磁帶收藏。記憶中,傅先生自己的原版磁帶好像不多,他說,他的磁帶,也都是兒子從國外幫他轉錄回來的。他給我錄的磁帶沒有版本,只有曲目。這十盒磁帶,很重要的是,給了我弦樂四重奏這種室內樂最高表達形式的啟蒙。十盒裡有三盒弦樂四重奏:貝多芬的兩盒晚期四重奏:第十二與第十四號、第十五與第十六號,還有一盒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我的生活》與德沃夏克的《美國四重奏》。從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中,我聽到那種在感人沉思中超脫自身的境界,聽到悠揚的舞曲節奏中對灑滿陽光生活的眺望,聽到在寧靜中飽滿的感恩與幻想。
相比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就像還在青春期。我那時也特別喜歡斯美塔那《我的生活》裡那種掙脫命運糾纏的感覺,撕裂中搖曳般的歌唱特別有力量,柔板樂章的依戀也特別有質感。這是斯美塔那失去聽覺後所作,四個樂章分別表達他人生的三個階段。與《我的生活》比,德沃夏克的《美國四重奏》則像是一首思鄉頌,包裹了甜甜的多愁善感。現在回頭看,傅惟慈先生給我錄的這十盒磁帶,最重要是樹立了我聽覺上的貝多芬晚期四重奏音樂境界的標準。
這十盒磁帶,有些曲目記不住了。記得有肖邦的兩首鋼琴協奏曲,當時卻並未產生聽到三盒弦樂四重奏那樣的激動。倒是那盒西貝柳斯的交響詩,也成了我日後常聽的選擇。也應該感謝傅先生能讓我那麽早就認識西貝柳斯。在《芬蘭頌》中,我聽到一種雄渾低徊的力量,聽到一種冷峻中的莊嚴。然後,《卡累利亞組曲》裡那種充滿情感的厚重敘述很令我感動。這十盒磁帶中,當時最難有感覺的,竟是勃拉姆斯的第一和第四交響曲。對初聽者而言,也許是勃拉姆斯的和聲太深奧了,較難產生感情共鳴的緣故?
最早帶我踏上聖殿台階的俞大使與傅先生,都已經先後去世了。
那時候,買進口磁帶在王府井的外文書店。一盤進口磁帶要十幾元,我的工資是三十多元,可謂昂貴。還記得我買的第一盒磁帶是柴科夫斯基的《1812序曲》與《意大利隨想曲》。為什麽要買《1812序曲》?就想聽聽那能震撼的炮聲。我選的是EMI公司,應該是芬蘭指揮家帕沃·貝爾格倫德指揮伯恩茅斯交響樂團的版本。當時這個曲目其實有好幾個選擇,現在看,這是個特色不夠的版本,之所以選它,完全是因為封面的油畫。那是風雪中一支衣衫襤褸的隊伍的形象。八十年代初,我與上海《萌芽》的谷白交往多。他來北京買了磁帶,會先給我聽。清楚記得,他說買了盒柴科夫斯基的《四季》,到我家播放出來是小提琴而不是鋼琴,他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還有一個維瓦爾第的《四季》。那時,我們家已經有了可翻錄的雙卡錄音機。
八十年代,我沒有黑膠唱盤,就錯過了一個購買黑膠的黃金時代,我買的都是磁帶。
真正成為發燒友,磁帶量幾十盤幾十盤地擴展,是八十年代中期,我跟著王蒙回《人民文學》,與詩人楊煉交往密切的那段日子。我從進《中國青年》雜誌就認識楊煉了,那時他在中央廣播文工團寫歌詞,《中國青年》創刊不久就發表了他的詩,很激情洋溢。後來,他加入《今天》,又與甘陽、劉小楓等當時前衛的思想家交往,越來越前衛。那時他住在頤和園後的國際關係學院,似乎是他姐姐的一間房子。我住在白家莊,坐遙遠的公共汽車,幾乎要一周跑到他那裡去兩三次,聽音樂,借磁帶。他父親是天津的一個教授,他回一趟天津,就從老爺子那裡帶回一些翻錄的磁帶,我就再借這些磁帶回去轉錄。我還記得我們在他的小屋裡聽肖邦的夜曲,楊煉形容,那月亮上真像有水滴,一滴一滴地落下來。楊煉父親是專業老燒,翻錄回來的磁帶都注明版本。肖邦的十九首夜曲是魯賓斯坦的,其他則都是阿詩肯納濟。我在楊煉那裡第一次聽到了西班牙大提琴演奏家巴保羅·卡薩爾斯的巴赫無伴奏組曲,當時對卡薩爾斯能把大提琴拉成像鋸木(這完全是現代主義的解讀),震撼到五體投地。我在楊煉那裡,也第一次聽到了蘇聯鋼琴演奏家斯維亞托斯拉夫·裡赫特演奏的巴赫《平均律》,對那種似水波一波波推動的層次迷戀至極。在楊煉那裡,我聽懂了巴赫,明白了對位、複調的魅力。我後來說,聽音樂可以選擇各種各樣的捷徑,可以從柴科夫斯基,可以從肖邦,也可以從巴赫。老實說,我是從裡赫特彈的巴赫《平均律》始,好像才真正打開了走進上界的那扇神秘之門的。裡赫特的《平均律》因此也是CD時代我最早索求的巴赫。最早買到的,是Melodia公司的CD。
因此,楊煉父親也是在俞大使、傅先生後,第三位對我愛樂產生過影響的老人。我主編《愛樂》雜誌後,曾托楊煉向他父親約稿,他父親叫楊清華,還真寫了一篇《一張失去的唱片》,刊登在第二期《愛樂》雜誌上。文中說到,他五十年代在瑞士購買的一批珍貴的密紋唱片,一直保留到“文革”中,進乾校後寄存在一位工人家裡,回來發現遺失了幾張,其中有一張卡薩爾斯與波蘭鋼琴演奏家米奇斯瓦夫·霍爾紹夫斯基、匈牙利小提琴演奏家山多·韋格合作的舒伯特《降E大調鋼琴三重奏》,他當時是苦覓這張唱片不到。現在尋找這個版本當然已經非常簡單,但在九十年代初,卡薩爾斯最早引進的Sony套裝與東芝EMI的套裝裡,似乎都找不到這個版本。
與楊煉一起買磁帶、錄磁帶的那段時間,楊煉對我很大的影響是,他對當代音樂的狂熱追求。剛開始是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還有波蘭作曲家彭德雷斯基。老實說,對巴托克的樂隊作品,我當時並不太理解其魅力。很奇怪,我是從巴托克的弦樂四重奏與他的《小宇宙》開始喜歡他的。《小宇宙》就是從楊煉那兒錄的,似乎是匈牙利鋼琴演奏家喬治·桑多演奏版,六首弦樂四重奏是我自己買的匈牙利塔卡斯四重奏組的版本。波蘭作曲家彭德雷斯基的《晨禱》(Utrenya)不知楊煉是從哪個朋友那裡翻錄到的,他在他那個小屋裡放給我聽,一開始那種低沉強大的禱告聲鋪天蓋地,其中聲部又那麽豐富,真有被震撼、打擊感。這情結使我後來一直尋找這個曲目。1991年第一次去美國,在芝加哥的唱片店裡,我找到了彭德雷斯基的《波蘭安魂曲》,卻找不到《晨禱》裡那種感覺。後來,我是見到了Wergo唱片公司的老闆,他說一定幫我搞到,過了段時間果真把這張CD寄給了我。這張CD確實不好找,是美國Muza公司1973年在華沙的錄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