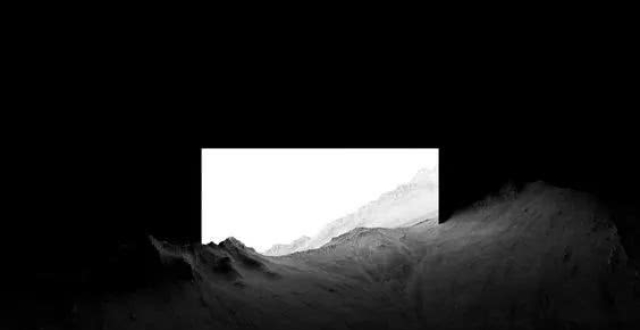孟京輝選擇《活著》作為自己轉型正統題材的作品,無疑是一步險棋。余華的原著早已深入人心,比起話劇講了什麽內容,人們更好奇一向熱鬧乖張的孟氏風格該如何演繹這個苦悶內斂的故事。余華對此放話道:“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麽誰對誰錯,人們常因為對一個東西太熟悉而把陌生的定義為錯的,所以孟京輝願意怎麽改編就怎麽改編,只有笨蛋才會忠於原著。”
誠然,導演可以有自己的風格或標誌,因為改編畢竟也是一種創造,不該要求藝術改編必須“忠於原著”,但孟氏風格是否適合這部小說,又是另一個問題。很難定義話劇《活著》對原著是依賴還是顛覆,也許說二者並存更恰當——孟京輝選擇了這樣的表現方式:一方面忠實地還原了故事,甚至讓演員黃渤原封不動說出書中的大段獨白;另一方面,在表現風格上卻大相徑庭,極盡張揚、乖戾之能事。這種天馬行空的舞台風格是否合適,便是本文想討論的重點。

話劇《活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當屬先鋒戲劇標誌性的舞台形式感,用荒誕魔幻的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手法闡述現實主義的內核。其舞台風格主要見於三個方面:
演員動作設計
開場時用眾人突然跳起迪斯科來表現大少爺福貴花天酒地的敗家景象。群演戴面具燙爆炸頭,黃渤身著皮靴牛仔褲,群魔亂舞仿佛現代蹦迪。兒子有慶為難產大出血的縣長夫人輸血至死,福貴在舞台上連續猛砸礦泉水瓶,用“血”花四濺表現憤怒,寓意生命的白白流逝,這段設計張揚有余,但有冗長、炫耀之感。鳳霞二喜婚禮中,二人舉著紅皮書宣誓瞬間切換到文革,紅皮書成了眾人黨同伐異的毛主席語錄。還有鳳霞難產而死,舞台後部高低行走的群演充當心電圖最終趨於直線……演員不僅表演角色本身,也可以是蒙太奇手段、道具甚至背景。
舞美燈光設計
溝壑縱橫的平台設定讓人驚喜,演員蹲下就能消失,站立又能上場,時而變成田埂時而變成戰壕,具有很強的功能性和延伸感。再如拉起白布用人影和電音表現福貴吃喝嫖賭的荒淫;春生與福貴談話時兩人一左一右站立,幕布上投出巨大倒影;賈珍獨白時側方的鏡面和煙霧效果等等。
借助多媒體影像
如有慶死後抽象的西方卡通片、政治波普短片。有慶死後的動畫或許是想把大家從福貴的喪子之痛裡帶出來,又或是童聲歡快欲與絕望氛圍形成對比,從筆者個人體驗來看,並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反而突兀出戲。

群舞、電音、多媒體影像、政治波普……這些都是先鋒戲劇用了再用的手法,導演試圖通過這種技巧的拚貼來呼應原著的情緒高潮,生怕觀眾不覺得“苦”,只是用力過猛顯得誠意不足,情緒宣泄或許能短暫地震撼視聽,卻無法帶來更深的思考,表面張牙舞爪,內裡缺乏張力,不夠貼合故事走向與人物心理。
除了舞台形式,情節與台詞細節的幽默化處理也具有類似的問題。在小說原著中,主人公福貴走過坎坷的一生,還是唱著“皇帝招我做女婿,路遠迢迢我不去”與老牛相依為命,自言自語。在我們看來,福貴經歷了戰爭、大躍進、饑荒、文革,至親在困苦中一個個死去,還有比他更苦的人嗎?可對於福貴來說,這就是活著。這是含淚的笑。小說用看似平鋪直敘、不動聲色的語言,講述了主人公殘酷悲涼的命運,這種表裡的矛盾使作品極具內在張力。再看話劇裡反覆出現福貴騙吃胖子的薄餅,鳳霞和二喜相親時對殘疾的調侃,這些都是孟京輝式的插科打諢,觀眾笑得很開心,但這笑無關主題,甚至不利於觀眾理解人物。話劇把深刻的主題淺層次化了——舞台形式將痛苦表面化,情節台詞將幽默膚淺化,兩者均沒有抓住精髓,反而衝淡了內在的痛苦感與荒誕感。

孟氏風格在表現某一類劇本時可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我認為不適合《活著》這樣的作品。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先鋒元素的舞台設計確實令觀眾應接不暇,耳目一新,卻也衝淡了悲憫沉重的主題,為了形式而形式,為了逗樂而逗樂。孟京輝說:之前自己的戲都希望給觀眾衝擊,是那種鋒利的刀子,但這個戲卻希望是個錘子,拿著麻袋套在你頭上狠揍一頓,那種悶悶的力量。我認為他沒有做到,話劇《活著》仍然是把刀子,如果說有悶悶的力量,那更多是由於對原著情節的保留。
小說《活著》的時間跨度大,人物情節飽滿且背景複雜,留給改編的余地不大。小說可以平鋪直敘,不動聲色,可是舞台上相對要集中濃烈,甚至比電影動作性更強一些,這個特點不能否定。比較張藝謀電影與孟京輝話劇,會發現兩者對原著進行了截然不同的處理,體現在人物、情節、敘事手法上,各有長短。在情節線和台詞上,話劇完全貼合原著,電影中徐有慶的死是被縣長開車撞塌的牆砸死的,話劇中仍保留小說情節,是為縣長的女人輸血輸死的。話劇《活著》極大程度上回歸了小說原著,甚至添加了小說第一人稱“敘述者”這個角色,由黃渤在舞台左前側的椅子上扮演。電影《活著》截取部分情節,重點講述大政治歷史背景下的個人命運;電視劇版本則拉長了小說的情節,增添眾多支線和生活細節。話劇則幾乎還原了整個故事,福貴人生中的重要節點無一刪改,小說原文近十四萬字,一口氣讀下來差不多正是話劇的時長三小時,這是最好的處理方式嗎?我覺得不是。福貴、有慶在台上大段大段地說出書中的獨白時,我心中疑惑,何不辦一個劇本朗讀會?

《活著》故事的動人之處,正如作者余華在自序中提到的,“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裡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叫喊,也不是來自於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孟京輝說,“《活著》對於我,依賴與顛覆共生;我有一種無能為力與挑戰並存的感覺”。觀眾期望在先鋒的形式下體悟原著強大而深刻的現實意義,從個人感受來說,我是失望的。我認為導演作出的風格創新並未勝過原著的深度,主題反而被形式弱化了。話劇《活著》在情節上十分依賴小說,但顛覆了原著深沉而平實的氣質,導演的荒誕風格與故事不夠貼合,導致話劇的形式感喧賓奪主,使觀眾不斷地入戲又出戲。看來,在忠於原著與突破原著之間如何均衡取捨,確實是一個值得思考和努力的命題。(作者系上海戲劇學院在讀學生;指導老師:丁羅男)
(注:本文所用圖片皆取自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