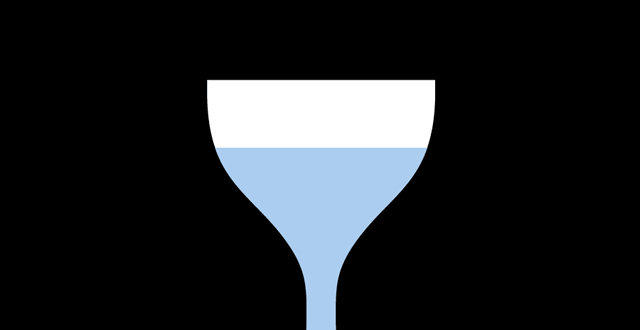“
蔣藝出生不久,舅爺舅奶一合計,決定把蔣藝送給舅奶鎮上的表妹家做女兒,夫妻倆好好調養,為攻克第三胎做準備。

全民故事計劃的第280個故事
一
七舅奶已經第三次來我家了,喊門、換鞋、兩手一擺坐在沙發上,嘴巴張開喊道一句:“我的命怎麽這麽苦啊!”
就開始哭哭啼啼起來,整套動作一氣呵成。
“丫頭,你和蔣藝關係好,再去她那裡勸勸,自己的親弟弟躺在病床上,等她的腎救命呢!”七舅奶見眼淚快供應不出來,猛吸一下鼻子,可憐兮兮地看向我。
我有點猶豫,心裡雖不快,卻不能在臉上發作。
舅奶伸手去抽紙,白色的紙張在空中劃出一條弧度,狠狠地吸弄一下鼻子,眉眼往上一撇,“丫頭,他也是你表哥啊,你可不能像蔣藝那個白眼狼,忘恩負義!”
“可是我……”
“哎呀好啦,你就聽你舅奶的話再去一趟,”我本還想推辭,就被心軟的母親搶先接了話,“畢竟是人命關天的大事。”
舅奶見狀連忙應和:“對啊對啊,你就去一趟吧,蔣藝現在都不願意見我們,”她的聲音完全沒了哭腔,“要不然,我也不會總是來麻煩你們啊。”
我厭煩地擺擺手,無意再糾纏下去,敷衍著回答:“那我就去吧,但是別抱太大希望,要怪,就只能怪你和七舅爺當初太狠心了。”
“你這孩子,怎麽對舅奶說話的,”母親用胳膊肘使勁頂了我一下,“當年不是窮嘛,給你慣的,都不知道什麽是苦日子了。”
舅奶見我臉色變了,生怕我因為和母親吵架而撒潑不去了,連忙走過來緊握住我的雙手,有些低聲下氣地說道:“丫頭,你哥的命交給你了啊。”
我盯著那雙蒼老的手,手指的老繭磨得我心裡直癢癢,想想長輩們也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心一軟,便不再爭辯什麽。
二
蔣藝是我的小姨娘,舅奶家的二女兒。在她之前,舅奶已經有一個兩歲的大女兒,當年一大家子都在催著舅奶早點懷二胎,按農村的土話來說就是,“十八談人,二十嫁,二一女,二二男,二五之前老母豬”,意思就是二十五歲之前的女性身體健康生育能力強,生孩子就像母豬般一胎一胎往外擠。
這二胎終究是懷上了,可誰知道有沒有“帶把”?
我們那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當產婆接生完後,對屋外回應“抱雞來”就是生的女孩,“抱鴨來”就是生的男孩。當年七舅奶生二胎的時候,家裡老太太早早就把鴨子圈起來等著產婆一喊就抱進去。一圈人等待著裡屋一陣急促的哭聲傳出來。
“是男娃不?”
老太太透過著門縫朝裡面喊,懷裡的大白鴨不停地折騰,拚命掙脫束縛。
“雞呢,快抱雞進來啊!孕婦流太多血,快不行了,快抱雞進來!”
老太太一聽到“雞”,把懷裡的鴨子摔在地上,大白鴨一落地,開心地“嘎嘎”就溜了。事不關己地走開了。七舅爺連忙去雞籠裡逮雞,看見一隻肥母雞,擰膀子就提起來,進了屋子裡。
這個一出生就被嫌棄的女娃娃就是蔣藝,七舅奶生她時幾乎是鬼門關前走一遭,個把月才恢復。坐月子期間,不斷遭受公公婆婆等家族親人的冷嘲熱諷。她大氣不敢出,隻恨自己不爭氣。
在她心裡,蔣藝就是一個“討命鬼”,是她抬不起頭的“罪證”。
除去精神上的厭惡,物質上完全跟不上供給,七舅奶產不出奶,蔣藝天天餓得哇哇大哭,吵得一大家子人不得安寧,大的小的都要伺候,田裡的農活都落下了。生孩子這一原本稱得上喜事,卻攪得所有人眉頭髮皺,本就不寬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蔣藝出生不久,舅爺舅奶一合計,決定把蔣藝送給舅奶鎮上的表妹家做女兒,夫妻倆好好調養,為攻克第三胎做準備。
舅奶的表妹與我母親也是親戚關係,我們兩家人是左右鄰居,就在小姨娘蔣藝來鎮上的第二年,我也出生了。在共同成長的漫不經心的歲月裡,蔣藝和我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蔣藝搬離農村的那年,七舅奶成功生了個男孩,老太太如願以償地抱著鴨子進去,再抱著大孫子出來,老王家一片熱鬧景象。當時蔣藝因高燒病倒,久治不愈,雖是住在鎮上的養父母家,但也禁不起醫藥費折騰,他們向七舅奶求助,請求救救自己的親骨肉,卻被一口回絕。
“都抱給你家跟你姓了,生死不都是你們的?”
養父母無奈,只能請鄉下的醫生,一通醫治雖是退了燒,卻因為亂打針留下了雙眼視力0.1的後遺症。
活下來已是萬幸了。
三
視力的問題在蔣藝念三年級才慢慢被發覺。她先我入學,卻因視力問題導致成績跟不上,留了一級和我成了同屆。在我們等待小升初的時候,我激動地告訴她,我要去面試一家私立中學。只有去私立中學,才能走出去。
“咱們鎮上的公立中學出不了大學生的!”
她被我說得心癢癢,回家後婉轉地向養父母透露了這個心思。
養父母聽完,面露難色,他們後來也生了自己的兒子,再加上面臨養父的失業的危機,囊中羞澀的他們,實在承擔不起私立學校的學費、生活費。
在養父母這裡碰壁之後,我勸蔣藝去找舅奶,看能不能幫忙讚助學費。七舅爺自從喜得兒子後乾勁大增,他每天起早貪黑,販菜去市內,不出幾年竟壟斷了附近幾個村與市菜場的蔬菜供應,賺得盆滿缽滿後,舉家落戶市中心。
“你別那麽倔,這可關乎你的未來,”我架著她強行來到舅奶家,整個做客過程中,蔣藝顯得很疏遠,結結巴巴開口提了私立中學的事後,舅奶便停下了往表弟碗裡夾雞腿的手。
“蔣藝啊,姨在市內的開銷可不小哎,沒你想的那麽風光,每個月還得還房貸,再看看你表弟,每周學鋼琴,每學年交借讀費,我還不能上班,得全職陪著他,家裡就你姨父一個人工作,日子也是緊巴巴的,幫不上你什麽啊!”
舅奶熟練地說出這段“哭窮話”,一看就是嘴上經常溜的措辭。
私立中學徹底對蔣藝關上了大門。九月,她送走載著我的汽車,騎上養父傳給她的老舊自行車,拚命地踩著踏板,向那所臭名昭著的混混中學駛去。
中學時期並不太平,雙墩中學就像是是一個妖魔鬼怪聚集的洞穴,蔣藝自動選擇與他們劃清界限,一心學習,兩耳不聞窗外事,但清水難隱於染缸中,她的自我奮鬥令周圍墮落的少男少女們眼紅,無故的仇視與憎恨相繼而來。
某個平常的課間,班裡的小痞子們像往常一樣聚集在一起靠在欄杆邊上,蔣藝恰好從廁所回教室經過那裡,痞子頭石磊突然上前猛地用手將她的衣服向下一拽,T恤被扯到了左手手肘處,少女的左胸也被窺探地一清二楚,痞子們眯起眼睛哄堂大笑對著她落荒而逃的背影補上幾句髒話。
自那以後,蔣藝就減少喝水的量,憋著不去上廁所,放學後就立馬衝出教室跑去停車處,騎上自行車就匆匆趕回家。
在學校受了欺負,她也只能偶爾在跟我說。只是她假期的時間都很忙,每逢寒暑假,她都要和養母一起去栽樹。鄰縣新修的一條馬路需要建綠化帶,大巴車每天早上五點在鎮上接栽樹組的人送去那裡,四點就得起床趕過去集合點,那年夏天安徽的氣溫又出奇的高,汗水壓得蔣藝頭暈腦脹。
有一天工作間隙,她摘下熒光橙的帽子就近在路牙邊上坐著歇息。
“喲,這不是咱們班學霸嗎?怎麽穿成這個樣子坐在這啊?”
蔣藝眯起眼,抬頭去尋找聲音的來源,是班裡大姐大的跟班,她嘟囔了一句“假期沒事乾而已”便埋下頭。
開學後,班裡傳遍了蔣藝是個為了掙錢連命都不要的“種樹女”,流言愈傳愈烈,最後演變成蔣藝白天種樹賺小錢,晚上育人賺大錢。這個流言跟著她六年,一直到高中畢業,她也沒有跟任何人有過辯解。
“我當時就在心裡發誓,就算是在那種垃圾學校,我也要考上大學,高三那年,我每天就睡四個小時,下晚自習是十點半,回去後再自學到一點,早上五點半又得起床去背書,中午困得不行,寫不下去試卷,就拿一桶冷水,一邊泡腳一邊刷題,不蒸饅頭爭口氣。”
她常常在電話裡和我訴說她的生活,語氣平靜,像是在講別人的事情。
四
臘月的氣象,格外清冷,我去她上班的地方找她,不知是氣象的原因,還是心裡發慌,一路上我都在忍不住地打哆嗦。
她見我來了,遞給我一杯奶茶,看著她一如既往倔強的臉,我不禁一陣心疼。
蔣藝當年成了混混中學唯一一個單憑文化課成績考上大學的學生。
上了大學後,她從大一就開始打工賺錢,做家教、發傳單、當服務生,只要有空,只要能賺錢,她都接。她要自己承擔自己的學費,不想再花養父母一分錢。
這次寒假,蔣藝回家不久,就在奶茶店找了兼職。我在等她下班的間隙,糾結著如何開口,便先跟她閑聊,“馬上都過年了,也不休息一下?”
“過年是最能賺到錢的時機,我晚上還得去電影院檢票,三倍工資呢!”她毫不在意地說道。
“你真是個鋼筋做成的女子,”我打趣她,“這次來還是那件事,舅奶讓我再過來勸你給浩然捐腎。”
“不捐,這些年他們一家怎麽對我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上大學時,我爸媽求她借點學費都不願意,現在還好意思割走我一個腎?再說,我那個所謂的親弟弟跟我像陌生人似的,他喊過我姐姐嗎?”蔣藝緊蹙著眉頭不滿地說。
上大學這件事舅奶表現的也是十分小氣,自己留下的大姐和小寶都是初中輟學,抱出去的二姐卻爭氣地成了大學生,心裡十分不痛快,當初蔣藝一家去借學費錢的時候,舅母撒潑似地把他們羞辱了一頓。
“上大學有什麽用?還是要出來嫁人的,耽誤了生孩子最好的年齡,錢也撈不到。”
我攪著吸管,連連歎氣,“唉,我也不知道該幫誰,要不你和舅奶見一面,心平氣和地談談這件事?”
蔣藝“啪”一拍桌子,“談?還有得談嗎?她上次在我家又鬧又哭,當我爸媽面罵我不懂事沒良心,還大言不慚地要花錢買我的腎,我一開始真是瞎了眼答應她去做配對檢測!他們一家人現在是死是活和我都沒任何關係!”
我只好作罷,不再勸她。自覺這件事不再有希望。只好對蔣藝說,“你自己照顧好身子,不要太拚。”她朝我點頭,見我要走,又塞了一杯熱奶茶到我手裡,“天冷,熱一下身子。我的事,我自己會妥善解決的。”
五
後來,我在甘肅支教,母親和我影片說到這件事的後續。
舅奶豪氣地拿出三十萬,要求養父母二人先斬後奏,告訴蔣藝,說已經收下並把其中二十萬給彩禮錢給出去了,剩下十萬是她的營養費。
“你弟媳婦那邊不給彩禮不結婚,我們也是沒辦法啊,養了你這麽多年,是時候該為這個家考慮考慮了。”養父母犯難的樣子讓蔣藝沒法拒絕,養母幫別人栽樹臉曬得黢黑,養父在小區門口當個保安掙不了幾個錢。
“你不是想出國留學嘛?你姨說了,只要你捐腎給浩然,出國留學的學費他們承包了,只要你答應,先把人救活了,一切都好說,”養母見她態度有些動搖,再次拋出舅奶的糖衣炮彈。
我追問母親蔣藝最終有沒有答應捐腎。
“捐肯定捐了,蔣藝也不是個冷血的孩子,她還是心善的……”
聽母親喜形於色地說完,我不自覺地感到後背發冷,不知道自己去勸說蔣藝捐腎,是對還是錯。
作者從嘉,大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