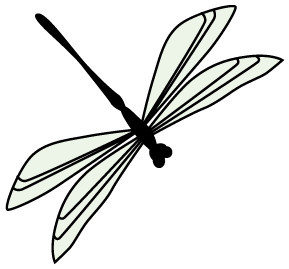
2017年3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推出白先勇新作《白先勇細說紅樓夢》,在海內外引起關注。今年3月,白先勇又在上海發表《紅樓夢與我們的文藝複興》主題演講,並與劉夢溪、寧宗一等就“百年紅樓”展開學術對話。本文是陳志明對白先勇的獨家專訪,談了《紅樓夢》、昆曲之美、文學心路、神話與文學的關係等話題。
◆ ◆ ◆ ◆
紅樓一覺夢中人
文|白先勇、陳志明
◆ ◆ ◆ ◆
陳志明:您的《白先勇細說紅樓夢》2017年在大陸首發,迅速引起關注。請問您是從什麽時候開始接觸中國古典文學、閱讀《紅樓夢》的?
白先勇:我第一次接觸到《紅樓夢》的人物是六七歲時。在重慶有一種“美麗牌”香煙,每包都有一張公仔圖,有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我的堂姐喜歡收集這些《紅樓夢》人物,並且講《紅樓夢》故事給我聽。
直到我十一二歲才真正看到《紅樓夢》這本書,是母親收藏的一套繡像《紅樓夢》。我似懂非懂地翻閱了一遍,沒想到從此跟《紅樓夢》結上一輩子的緣。這本書我也教了大半輩子。雖然我在大學主修西洋文學,但對中國古典文學一向是愛好的。
陳志明:您的父親白崇禧是軍人,您卻喜歡和熱愛文學。請談談您的文學心路。
白先勇:我父親是軍人,但他的古文根底不錯。他特別注重我們的教育,尤其是中文,一定要我們打好根基,暑假還請老師來教我們《古文觀止》裡面的文章,而且還要背書。我個人從小就愛文學。因為小時生病,患了4年多的肺病,抗戰時,肺病是致命的傳染病,因此被隔離。我離群獨居了4年, 等於失去了童年,因而在孤獨中變得十分敏感,時常愛幻想,聽家人講古、閱讀小說便引導我走上了文學之路。
陳志明:您曾經說過,要借助寫作,“把人類心靈中無言的痛楚轉化為文字”。您自己也有著一份“無言的痛楚”嗎?您怎麽看這份“無言的痛楚”?
白先勇:我曾經回答過“為什麽寫作?”這樣的問題,答案是:“我寫作因為我希望把人類心靈中無言的痛楚轉化為文字”。我寫的是“人類”心靈中無言的痛楚,而不是我一己之痛,那太狹窄了。但我跟我創造的人物的內心痛楚一定是有同感的,要不然我寫不出來。
陳志明:您熟讀《紅樓夢》,認為它是“天下第一書”,這裡面除了《紅樓夢》本身的文學魅力外,還有沒有其他“情結”(比如您的自況等)?
白先勇:我青少年時經過抗戰、內戰,經過家國社會的大流離、大顛倒。我出身大家族,也經歷了家族的起伏支離,對於《紅樓夢》描寫賈府的興衰,人世的枯榮無常,自然感觸特別深。尤其對賈寶玉這個人物的意義,的確有我個人的看法。

白先勇
陳志明:您認為後四十回仍系曹雪芹所作,但很多人並不這麽認為。請談談您眼中的《紅樓夢》後四十回。
白先勇:《紅樓夢》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之爭是百年來紅學界永遠得不到定論的議題。主要因為現在我們還找不到曹雪芹的原稿,所以大家的理論都是一種臆測,等到哪天曹雪芹的原稿真的出現了,這個謎才能揭開。我對後四十回的看法有兩方面:
第一,我相信後四十回還是曹雪芹的原稿,而非高鶚的續作,高鶚只是個修補者。理由如下:
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程偉元、高鶚的序以及次年程乙本程、高二人的引言說得清楚明白,後四十回原稿是程偉元從收藏家獲得二十多卷,其餘十多卷是從鼓擔上尋得,重金購買。因原稿“漶漫殆不可收拾”,程偉元乃邀高鶚“細加厘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對於原文特別申明“未敢臆改”。到現在也未有鐵證斷定程偉元、高鶚二人說謊,後四十回是高鶚偽托。何況程高本問世離曹雪芹死去並不久,當時紅迷甚多,如果高鶚敢偽托,早已群起攻之了。鐵證未出現以前,我們還是姑且相信程偉元、高鶚二人說的是真話吧。其實不少紅學家如林語堂、高陽等人早已認為後四十回不是高鶚續作,根本就是曹雪芹原稿。
世界上好像還沒有一本經典小說是由兩位或兩位以上的作者合寫而成的。何況《紅樓夢》前八十回早已千頭萬緒,漫天撒網,後四十回如果換了一個作者,如何能將前面長長短短的線索銜接起來而不露裂痕,尤其人物語調口氣的統一就是一個大難題,前八十回的賈母與後四十回的賈母絕對是同一個人。後四十回是寫賈府的衰敗,最後被抄家,可以感受得到,作者對於賈府以及其中人物的命運充滿悲憫哀憐,《紅樓夢》是曹雪芹自傳性的小說,高鶚跟曹雪芹的身世有天壤之別, 很難有個人真摯的情感注入其中。
《紅樓夢》第五回的判詩對人物的命運結果,後四十回大致都能符合。許多伏筆,如寶玉贈給黛玉的定情手帕、蔣玉菡與寶玉交換的紅綠汗巾,後四十回都用到了,而且用得非常有效、恰當。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是一脈相承,前後貫通的。如果後四十回真的矛盾重重,情節不通,這兩百多年來,一百二十回程高本哪可能感動世世代代的讀者?
第二,很多人對後四十回的藝術成就有微詞,張愛玲甚至說曹雪芹的紅樓夢隻寫到八十回是其終生遺憾之一,她看到第八十一回就感到“天昏地暗”。我完全不是這樣的看法,我覺得《紅樓夢》的悲劇力量全在後四十回,黛玉之死、寶玉出家是全書兩個最要緊的關鍵,是撐起紅樓夢這座大廈的梁柱,這兩段情節只要有一段寫差了,紅樓這座大廈便會應聲倒地,可是後四十回這兩段關鍵情節偏偏寫得最精彩,尤其是寶玉出家,可以說是中國抒情文學中一座無法超越的高峰, 最後“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前八十回當然寫得好,但寫得再好也是替後四十回鋪路的,沒有後四十回,《紅樓夢》不可能成為完整經典。很多人嘗試續《紅樓夢》,但沒有一個能成氣候,可見程高本的後四十回是無可取代的。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
陳志明:您曾經說過,《牡丹亭》和《紅樓夢》是影響您一生的兩本書,《白先勇細說紅樓夢》出版以後,“總算都為它們做了些事,了卻這輩子的心願了”。從今而後,您還有哪些寫作規劃?
白先勇:《牡丹亭》與《紅樓夢》是我最喜愛也是影響我最深的兩本中國古典文學,我算是替這兩本經典做了一些事,替《牡丹亭》青春還魂,替《紅樓夢》下了一個新注解。下一步我還有許多文債沒有還,我父親的傳記隻寫了兩本,它應該是三部曲。
陳志明:有人稱您推廣《紅樓夢》和昆曲是“一個人的文藝複興”,您怎麽看這個“一個人的文藝複興”?
白先勇:“一個人的文藝複興”是誇大的說法。我一直有一個願望:希望21世紀中國會發生一場歐洲式的“文藝複興”。19、20世紀中國因為國力及文化衰落,在世界文化領域中失去了發言權,都由西方強勢文化長官發言。21世紀中國強盛起來了,正是建設我們文化的好機會。我們整個民族都需要文化的救贖。“文藝複興”當然是一條漫長崎嶇的路,但如果全民族都有這個心,中國的“文藝複興”就有希望。首先當然是要從傳統文化去尋找靈感啟發,這些年我之所以拚命推動昆曲及推廣《紅樓夢》,就是因為像《牡丹亭》《紅樓夢》這樣的作品都是文化標杆,我們需要這些文化標杆來引導我們踏上“文藝複興”之路。
陳志明:在新著《白先勇細說紅樓夢》中,您一再強調《紅樓夢》的神話架構以及它的象徵性。從文學史的角度觀察,其實自魏晉志怪以降,隋唐傳奇、宋元平話、明清神魔小說等,都有向讀者傳遞豐富的“神話”資訊。現代作家、當代作家的作品中也不乏對神話的解讀與變形。您能不能從文學史的角度,講一下神話與文學的關係。
白先勇:西方心理學家榮格認為,神話是一個民族心理下意識的投射。文學裡運用神話,往往包容了整個民族性,因此視野特別闊大。《紅樓夢》一開始便用女媧煉石補天的神話,女媧煉了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石頭,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就這一塊沒有用,這塊靈石後來便變成寶玉下凡去了。其實,女媧賦予這塊靈石的使命更大,靈石(寶玉)下到凡塵孽海裡是去補情天的,《紅樓夢》又名《情僧錄》,情僧(寶玉)須用“情”來普度眾生,在中國人、中國文學的傳統來說,“情”是宇宙的原動力。靈石在青埂峰(情根峰)下生了情根,“情根一點是無生債”,從此寶玉在大觀園裡便有還不完的情債。《紅樓夢》裡的神話、寓言把小說從寫實架構提升到抽象象徵的境界。
陳志明:《白先勇細說紅樓夢》出版後,也有一些不同意見。安徽女作家閆紅發表文章《白先勇誤讀了〈紅樓夢〉,也看錯了尤三姐》,認為“相對於程乙本的黑白分明,庚辰本裡講述的尤三姐的一生,更讓人一言難盡”;並說:“《紅樓夢》是一部很容易在閱讀中融入個人體驗的書,白先勇或是別的人,也許能在程乙本裡讀出更多妙處,這個不予置評,但只是隨口下判斷,斬釘截鐵地說哪個版本更好,對於這樣一部書,似乎不相宜。”您怎麽看這些不同意見?
白先勇:《白先勇細說紅樓夢》這本書有我許多個人的看法,跟有些人對《紅樓夢》的意見有所抵觸,爭論一定是有的。文學問題有爭論是好的,何況《紅樓夢》的內容如此複雜,自然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細說》這本書是由我在台大教《紅樓夢》導讀教了三個學期100個鐘頭的講稿編輯而成。教書期間我用了兩個版本,一個是以庚辰本為底稿,另外一本是以程乙本為底稿的《紅樓夢》。我有機會把兩個版本從頭到尾、從第一回到第一百二十回都仔細對照過一次,我完全是從小說藝術、美學觀點來比較這兩個版本,我發覺以庚辰本為底的版本也隱藏了不少問題,我都一一指了出來。其中我認為最嚴重的是庚辰本把尤三姐這個人物扭曲了,把她寫成了一個水性楊花的女人,早跟姐夫賈珍有染,因此關於她的後來幾個章節就說不通了。程乙本把二尤姐妹做了一個對比,這也是曹雪芹塑造人物常用的手法,二姐柔順,三姐剛烈,賈珍雖然對她垂涎,但因三姐脾氣不好惹,所以不敢冒犯。可是庚辰本寫到第六十五回,賈璉娶尤二姐金屋藏嬌,一日賈珍也來引逗二尤姐妹,尤二姐與尤老娘故意避開,讓賈珍狎暱三姐,剛烈如三姐竟讓姐夫“百般輕薄”,“挨肩搽臉”,連小丫頭都看不過,躲了出去。此處三姐不僅順從而且逢迎,可是到了下一段,當賈璉敬酒湊合三姐與賈珍,三姐卻突然間大怒痛斥賈璉、賈珍,這是《紅樓夢》寫得最精彩的片段之一。但如果三姐如庚辰本所寫是個水性婦人早與姐夫有染,此處她便完全沒有立場呵斥賈珍、賈璉對她不敬了,這麽精彩的一段就變得不合情理了。尤三姐一心要嫁柳湘蓮,柳湘蓮懷疑三姐乃“淫奔之流”,三姐當場用鴛鴦劍自刎以示貞潔。如果三姐早已失身於賈珍,那麽柳湘蓮懷疑她並沒有錯,三姐更沒有理由自刎以示貞潔了。那麽尤三姐的愛情悲劇便不合邏輯。這是我對閆紅女士的答覆。
陳志明:您指出,《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是釋迦牟尼式的人物,為什麽會想到“釋迦牟尼”?您隻講了《紅樓夢》有著神話架構,卻沒有講《紅樓夢》為什麽要採用這種神話架構,希望您能從“神話與文學的關係”這個角度對此進行分析。
白先勇:《紅樓夢》有很強烈儒、釋、道三家哲學思想的暗流在主導小說的發展,儒家思想主要表現在寫實層面,而道家跟佛家思想則構成了《紅樓夢》神話寓言的世界。《紅樓夢》在某方面來說是一則佛教神話:頑石歷劫的故事。寶玉出家很像佛陀前傳,悉達多太子四門出遊,勘破生、老、病、死,剃發離家成佛,寶玉的一生也類似悉達多太子:享盡榮華富貴美色,最後看破紅塵,歸彼大荒。王國維評李後主詞“乃以血書者”,儼然似釋迦、基督擔負了人類的罪惡痛苦。我覺得這句評語用在賈寶玉身上更合適。寶玉穿了大紅猩猩氈鬥篷,光頭赤足,向父親賈政合十四拜,隨著一僧一道在雪地上飄然而去。我認為寶玉出家是背負了世上所有“情傷”的十字架而去。所以《紅樓夢》又叫《情僧錄》。情僧指的就是寶玉,情是他的宗教信仰。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8年5月18日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