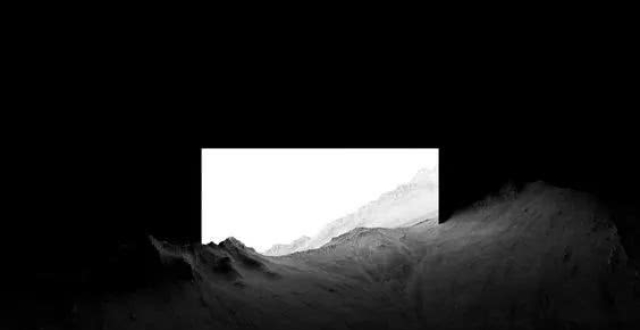文/錢江晚報 馬黎
張牙舞爪的中長髮,在舞台的光影中掄出一個辨識度很高的剪影:“誰都不許急,只有導演可以急。”
烏鎮大劇院,孟京輝從觀眾席第六排靠走廊的位子上站了起來,他的新戲《茶館》正在下半場聯排。麥有些小問題,兩位老師有些急,他站起來安撫每個人的情緒。

舞台上,沒有茶館,只有一個巨大的輪子,一圈一圈,緩緩的,逆轉,順轉,冰冷的鋼架交錯重疊,發出咯吱咯吱的重創之聲。
跟老孟合作了《戀愛的犀牛》、《活著》等30多部戲的禦用舞美設計張武,這次送來的“輪子”,是他所有作品裡單場最大的舞美作品。
老舍在《茶館》中埋葬了三個時代的齒輪,60年後,依然在滾動,和時間,和我們每一個人較著勁。


馬越 攝
小心,小心,這兒台階。張武早有預料,連續提醒了兩次,摸位子的孟京輝還是在黑影裡歪了一下,蓬松的頭髮一炸,唉喲一聲,抖抖腿。
我要是那天拄著拐杖上舞台宣布,烏鎮戲劇節-開-幕,是不是也挺牛的?他在黑影裡笑起來。
10月18日晚,第六屆烏鎮戲劇節正式開鑼,孟京輝導演的新戲《茶館》,來自老舍先生的經典之作,作為開幕大戲世界首演。
而戲劇節結束後,10月31日-11月3日,《茶館》也將來杭州,在杭州大劇院連演4場。
首演前三天,聯排結束,晚上6點10分,飯點,劇場後台的水房,還是昏暗的燈光,桌上放著各種點心,不知道吃飯睡覺為何物的孟京輝,胡亂塞了幾塊餅乾。
此時的烏鎮,是一塊桂花糕,愛浪漫的他,沒多少時間聞聞嘗嘗。10月2日到達烏鎮後,劇組幾乎每天都工作到半夜3點,他早上10點半起來,遊個泳,“一下子就沒事兒, 6個小時(睡覺)差不多了。”
任何事對老孟來說,都不是問題,沒有想象力,不好玩,才是問題。貼著他名字的工作間,桌上放著一摞書,《致後代:布萊希特詩選》放在最上頭,夾了很多白紙撕下來的標簽,他挑出了布萊希特的話:“能被好好講述的故事,都不是好故事。”適用於《茶館》,以及一切。

孟京輝
1。
1958年1月1日,《文藝報》第一版刊登了一篇《茶館》座談會的消息,這個會議非同尋常,參加的人有林默涵、陳白塵、張恨水、李健吾,每個人都有長篇發言。
1958年3月29日,《茶館》在首都劇場首演。
巴金先生主編的《收獲》也在1958年第一期,把《茶館》當作首篇發表了。
1958年發生的這些事,給中國傳遞了一個消息,中國文學界出現了一個大作品。
孟京輝沒有想那麽多。
就跟舞台上的輪子一樣,轉到哪兒,就是哪兒,時間的輪子剛好轉到了60年後的2018年。今年明明已經交出了《太陽和太陽穴》、《莎士比亞和狼》兩部夠得上觀眾給予他“先鋒”稱號的新作,可他還要折騰一次,主動選擇了看上去和“實驗”背道而馳的中國文學經典之作,教科書式的《茶館》,中國觀眾都知道的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也是北京人藝演了60年的金字招牌,深入人心。
他當然知道,深入人心,代表著冒險。
上世紀80年代,他還在北京師范大學讀中文系,第一次讀了《茶館》的劇本,看了電影、錄像,覺得挺來勁兒的。90年代,他看了北京人藝版的現場演出,“豐富,強烈,風格化,中國特別有力量的東西在裡面。”
知道要排《茶館》,很多人也覺得意外,也為孟京輝擔心。就如2012年,當人們知道他要把余華的小說《活著》搬上舞台的疑惑,那之前,孟京輝觸及歷史題材和農村題材的經驗幾乎為零,而且小說是現實主義題材,換句話說要“講故事”,再換句話說,孟京輝會把原作改得“天馬行空”嗎?

《活著》2012年 李晏 攝
排到《茶館》第三幕,小丁寶來茶館應聘女招待,和掌櫃王利發有一段戲。
停——孟京輝很敏感,小丁寶,原劇本中是這麽說的嗎?他在黑暗中拿著話筒。
工作人員一對劇本,念出老舍先生原著裡的台詞:“他媽的,我才十七,就常想著,還不如死了呢!”
有三個字換了位置。
這兩句話完全不是一個意思——孟京輝大聲提醒“小丁寶”。
“好多氣質和能量必須從原劇本裡認真地說出來,差一個字,就變了。”
孟京輝的《活著》,原作一字未改,當時余華說了一句話:孟京輝對原著的忠實程度讓我吃驚。
“對吧,我還是比較尊重原著的,對啊,余華也這麽說,活著的,死了的,都這麽說。”他笑起來。
但余華還有後半句:他的方式更讓我吃驚。
《活著》的舞台手段依然完完全全的“孟氏”,但作品中對於人和命運的關係震撼了太多的觀眾。可以這麽說,余華的《活著》、湯顯祖的《臨川四夢》,直到這次老捨的《茶館》,是孟京輝對於經典重述的三部曲,“有一點點好像是和經典的一種對話”。
孟京輝從來不忌諱“忠實”和“講故事”,但他知道該怎麽講,該怎麽對話。他看重的,是如何從原著,從傳統中汲取力量。

《臨川四夢》蔡寶豐 攝
2。
老舍先生很多沒有寫出來的話,18400個有限的字背後所藏著的是什麽?孟京輝要帶著觀眾嚴肅地想象,“可以說是完全飄向精神層面的一個《茶館》。”
《茶館》的戲劇構作塞巴斯蒂安·凱撒(Sebastian Kaiser),他和中國觀眾最近的交流,就在2年前的烏鎮,德國當代戲劇大師弗蘭克·卡斯多夫(Frank Castorf)導演的《賭徒》中國首演,同樣改編自俄羅斯文學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名小說,他也是戲劇構作,複雜的拚貼式文本,挑戰演員肢體極限的理念、爆發力,讓人印象極深。(2016年曾經採訪了塞巴斯蒂安,回顧戳:烏鎮戲劇節|卡斯多夫《賭徒》:好不好看,這個問題不重要)
這一次面對中國的文學經典《茶館》,這個德國人說:“今天我們嘗試尋找一種易於理解並接近我們自身的對《茶館》的設計。”
齊溪坐在舞台上,說著一段自己的故事,即時影像放大著她的臉部,棱角,自然,日常放鬆。這個《戀愛的犀牛》裡走出來的明明,已經三年沒有和孟京輝合作了。
“她還那樣,沒什麽變化”,他坐在台下聽著她的故事——停——他提醒——這個故事別說歪了,觀眾聽不懂。

《茶館》彩排照 合眾能量 攝影
《茶館》快建組時,塞巴斯蒂安對孟京輝說,《茶館》裡應該有一個女性。老孟用一種“嫌棄”的拖腔說,沒有(托很長),哪兒有啊(拖得更長),不是那麽回事兒。
但他知道,這是一種想法,就給齊溪發了一個微信。我在弄《茶館》,時間是巴拉巴拉,你幹嘛呢。
齊溪就把別的事兒都推了。
孟京輝繼續說,第一,你演什麽我不知道,第二,有沒有,也不知道,到最後可能就一句話兩句話。“這個女性,是從老舍小說裡自然而然走出來的形象,有好幾個層面的女性,獨白也很奇怪,作用就是豐富觀眾的想象。”
聯排結束,只有1小時休息,他在各個房間移動,坐在各種電腦前,修改,審稿,看影片。烏鎮戲劇節每屆都會出版的報紙版面,他像個總編輯,對每個版面的標題做最後的修改,“(加一句)莫斯科藝術劇院,前面哪怕加一句,標題裡說清楚是什麽,別人也就看明白了。”
工作人員說,導演有時候仔細的,“的得地”都能挑出錯,一枚好校對。
咱們那麽努力,萬一別人都不看怎麽辦?看著看著,“總編輯”突然來了這麽一句。
您怎麽會冒出這樣的想法呢?工作人員都有點不相信。
聯排最後的謝幕,19個演員站在舞台上,文章、陳明昊、韓青、齊溪、劉暢、趙紅薇、丁一滕等,孟京輝給他們安排了好幾個不同的謝幕角度。
您從哪兒出來?領銜主演文章站在中間,大聲問台下的孟京輝。
我不出來,(怕)人家打我,哈哈。老孟在黑暗中笑。

《茶館》彩排照 合眾能量 攝影
對話
馬黎(以下簡稱馬):為什麽這次是《茶館》?
孟京輝(以下簡稱孟):對,排《茶館》不容易,就有給別人一種挑戰的感覺,而且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不同的《茶館》,但也有人心中有一個固定的《茶館》。
我不是為了挑戰。其實分兩個部分,一部分,我想把《茶館》裡最精彩的部分傳承下來。另一部分,傳承之外的,《茶館》裡關於精神的東西,我可以遐想。這樣兩部分就在我身上很好的結合了。
馬:很多人第一反應,或者在等著孟京輝又要顛覆什麽了?
孟:如果愣要說顛覆的話,可能是顛覆想象。別的,我們在茶館裡聊的,不是要表現一個故事,情節所有人都知道,幹嘛還要那樣呢?我們年輕人怎麽看待歷史,我們年輕的創作者共同在一起走向一個新的太空,包括美學太空,包括個人的想象太空,包括集體的合作,集體的知識積澱的太空。
馬:跟年輕人聊《茶館》,他們的反應是什麽?
孟:實際上大家真不了解,既不了解《茶館》的文化,也不了解《茶館》的劇本,甚至很多年輕人連《茶館》的演出,其實都沒什麽印象,它只是變成了一個符號。對我來講也很為難,怎麽辦呢?後來我一想,正好有這麽一個可能性,能跟大家在一起很長的時間,在北京、上海、烏鎮,有一個磨合,很開心的,我把這個過程當做一個享受。感謝烏鎮戲劇節有這麽一個環境,大家在一起認認真真思考的環境,不是商業的,不是應景的,那這件事就能乾的來。

《茶館》彩排照
馬:這個過程,是一個重新認識《茶館》的過程嗎,還是說拉近我們和它的距離?
孟:幾種可能。一個是跳到《茶館》的深井裡。還有一種,是把《茶館》拉到你的生活和身邊,看看和它有什麽對應關係。
馬:比如有什麽關係?
孟:《茶館》說的是一個變化,不斷變化,還說到絕望,說到壓迫,說到人的自由。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加大它的想象,表現它的突發和你自己生發出來的一些意象。
馬:一些“加法”。我看到有加入演員在台上講自己的故事,比如齊溪。戲劇構作也提到:加上當代文化元素、演員們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思考,讓出乎我們意料的一些事實和哲學深思從《茶館》的角色中浮現了出來。
孟:我特別希望演員能和故事所生發的精神狀態連接起來,最後不知道怎麽就發展成這樣了。我說齊溪你得真實,說一件真事兒,我們把原來文學性的東西往底下壓了一下,把她個人生活的真實把這些東西合在一起,慢慢的帶著觀眾進入一個全新的維度,不管理解或者不理解,我想縱橫恣肆一點。
馬:能不能說,看上去離經典最遠,但是離當下最近的。
孟:其實,離當下最近,就是離經典最近(笑)。因為經典不跟當下聯繫的時候,經典就根本不存在了。只要你離當下最近,你就能找到一種精神上的依托,或者說精神上的一種互相的暗自迷戀,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經典的東西全部都活躍起來了。
我們在做這個戲的過程中,發現我們也長大了,我們在面對一些殘酷的東西,面對死亡,面對世間各種變化,我們變得好像更寬大了一點。我們的演員和創作者之間,有友誼,有爭論,有不同意見,但都有成長的感覺。
馬:最大的爭論在哪?
孟:各種各樣的,對人物形象的理解,比如唐鐵嘴、劉麻子,他們的這種形象,到底是說真話,還是把現實生活拉進去,有好多美學上,風格上的不同,必須這樣,也可以這樣,或者可以再跳躍地更遠一點,太多爭論了,但是我覺得都挺好玩的。
我們最多的就是變化——我們走路的時候,剛出發的時候,感覺到遠處有一個光亮,但我們走在一片森林裡,大家在一起相依為命往前走,有人說往這邊走,結果走到那兒發現是一個懸崖,跳不跳?還是拿繩子下去?還有人建議回來,有人覺得繞道而行,有一部分人就下去了,但是互相聯絡著在某一個地方又見面了。有各種各樣的風景不斷在我們周圍出現,我們一直往前走,就到了現在這個地方。反正還行,還可以,沒迷失——當然無數次的迷失,最後還好。
馬:看到導演闡述中,你說這次會以非常嚴肅的方式對待《茶館》,為什麽?
孟:主要是因為我們請了一個戲劇構作,我們在排練的時候,他不斷地重複茶館、茶館、茶館。因為我們玩起來很嗨,一群野孩子遇到了一片草地,有花,有陽光,有瀑布,但是他把我們再拉回來,情緒、主題,他和我們一塊兒在布局。
馬:他所理解的《茶館》,是怎麽樣的?
孟:他會更瘋狂一點兒。比如,他覺得這三個人物,王利發、秦二爺、常四爺,代表了不同的階層,是中國社會各種不同的狀態,他更願意用一些新的社會學的知識,哲學的思考,來面對這三個人物,進行一些拷問,我覺得特別有意思。但是有時候我們所處的狀況,我們經不起這種拷問的話,怎麽辦?
我們從人性的高度框定,我們又不斷地拷問,目前看起來對這三個人物的推進還是恰當的。所有的選擇都是我們必須的選擇,有的時候,有些話語,有些橋段,有些往前走的狀態,其實是刪掉和考慮了很多才成立的。反正我們在那兒走,老有一個人能來刺激我們。
馬:王利發這個中心人物,在您的理解中什麽樣的?
孟:他說的是一個理想國的夢想,但他自認為又是一個很荒唐的人。我們要說一些時事性的東西,我們好多人會有好多話要說,這些話是不是能值得說,而且比較恰切的,不能特別張揚,不能特別放肆,因為沒有意義。
怎麽恰切?我們實際上找了各種各樣的文學支持,比如好多布萊希特的詩,好多卡夫卡的意象,這些都是支持我們的潤滑劑,是推動我們齒輪的小細節的力度,我們這樣向前走,就很坦然。
你替觀眾在想象,帶著大家想象,是迷宮,也是魔術方塊,有一種不斷變形,化學作用,讓你對歷史,自身,對這麽多年來人類所承擔的苦難,我們進行一個自我梳理,但最後生發出的,是一個生活還是美好的結論。
馬:《茶館》過時嗎?很多年輕人可能會覺得這部作品和我們無關。
孟:當創作者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有可能有點點畏手畏腳的吧,因為覺得跟我們的社會生活沒關,就會覺得過時。但老舍先生在他的作品裡,在他的其他劇本裡,尤其在《茶館》裡,他對自己的關懷,對社會各個層面的把握和滲透,是挺厲害的。
馬:其實你這幾年一直在做這樣的“經典重述”,《活著》、《臨川四夢》到《茶館》,算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經典作品如何做更符合當代的表達,尋找當代意義?
孟:我覺得只有在理解了它內在的情感價值,精神價值之後,才能判斷它是不是經典。如果先不判斷它的話,那中國太多帝王將相奇奇怪怪的所謂的經典,還是中國文化的糟粕,你說不清楚,所以首先要判斷它。
老舍先生的作品,毫無疑問是非常經典的,當它經典的時候,就含有好多能量,有一個社會的傳遞性,還有一個美學的連貫性,還有,它在任何一個時代,任何的一群人群裡,在不斷地敞開窗戶,敞開門,讓你能看到裡面的風景,這就具備了經典最大的可能性。所以,當我們面對經典,當認為是經典了,我們必須把這扇門打開,把裡面所有的能量釋放出來。我們也在做這樣一個嘗試。
馬:可能會有觀眾帶著人藝版《茶館》的印象,來看,來比較。
孟:我不怕,因為很多人都沒看過《茶館》,也沒看過人藝的《茶館》。他們都沒有親自去過現場,我去現場了。他們都是在錄像電影裡知道的,但那隔著呢,我倒真不怕,我想他們進劇場後能有一種更強烈的對自身的一種俯視。
老藝術家比我們更純真,他們接觸的資訊比較直接,有他們自己深厚的東西,我們的想象力可能要更加豐富,所以不好在一起比較,也沒有必要比較。所以,我們經常說,偉大的傳統,偉大的當代,這兩種同時出現在我們的目光注視之下。
馬:2013年林兆華導演關於排《茶館》,曾經說到,“我想創新,但沒有能力去駕馭得更好。我失敗了,不等於不可以有後來者。”您怎麽理解這種創新?
孟:創新其實是個人習慣,不是藝術家必須的品質,可能是有一些藝術家他愛折騰。但是創新不創新並沒那麽重要,對個人來說。對藝術作品,傳承和藝術發展來講,挺重要的,對我來講就努力找到一個東西,有皮,有瓤,都不同,皮和瓤能結合得好一點,就像你吃西瓜,你吃裡面的瓤,把皮扔了,但其實,哎皮也挺好的。
馬:文章的表演,您怎麽評價?
孟:他是一個有能量的好演員。
關於《茶館》,你還可以看看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