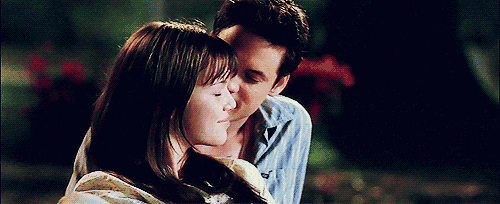你寫下的,是別人不知道悲歡喜憂
文 | 張若水
本文系“澎湃·鏡相”非虛構寫作大賽參賽作品
投稿原標題:《何日君再來》
大賽由澎湃新聞主辦,複旦大學、今日頭條聯合主辦
一
“我們離婚吧。”十六年未見的丈夫如是說。
姚暮美放下手中的筷子,看著眼前這個也老了許多的男人,欣然同意了她十六年等待的結果。她什麽也沒問,她不想知道他需要別的女人,她不想知道他對她怎樣好,至少,不想從他嘴裡知道這些。從此,暮美不再稱呼他為“我老公”,他失去了姓名,成為暮美口中的“這個男人”或“那個男人”。
姚暮美和那個男人相識於1980年的夏季。那天,她和妹妹身著同樣粉色的裙子,從和平電影院出來,碰到一個穿西服的男人問她們要不要小禮物,帶她們去前面的和平飯店拿。姚暮美想大庭廣眾之下,人家應該不會騙她們,就和妹妹跟著去了。
穿西服的男人叫她們在外面等,自己進了旋轉門,不一會,出來一個黑人,遠遠地招手叫她們倆過去。暮美和妹妹嚇得快步走開了,黑人也跟了上來,跟她們說了幾句話,她倆也沒聽懂他講些什麽,只想快點甩開他,可黑人擠到她們中間,將她和妹妹分開了。
“儂快點好勿啦!”暮美對走在他們後面的行人大喊道,那行人是她們從電影院出來一直跟著她們的兩個男孩。
兩個男孩跑上前來,與她們並肩同行,黑人識趣地離開了。一開始,他們四人一排走著,然後,變成一男一女前後兩排走著。交談中,暮美得知,與她並肩而行的男孩比她小五歲,在城隍廟當經理。她告訴他,她在服裝廠上班。男孩堅持要送她回家,她推辭不過。離家還有一條街的時候,暮美停了下來,說送到這就行了。臨別前,男孩問她能不能做一套衣服送給他。為了打發他走,暮美答應了。男孩高興壞了,說一周後下午兩點在虹口公園等她。
暮美給男孩做了一套青年裝,算是答謝他的解圍。那時的街頭,已經不時興青年裝了。她在虹口公園門口等了半個小時,沒見到前來赴約的男孩,待她要離去時,男孩大汗淋漓地向她跑來,原來,他們倆一個在正門口,一個在西門口。
緣分,真是奇妙的東西。如果她少等幾分鐘,如果他跑得慢一些,他們彼此就錯過了。在認識他之前,暮美有過一個心儀的對象,是別人介紹的。為此,她乘車去金華見相親對象。到了人家家裡,相親對象太忙,叫來自己的弟弟與她相見。回到上海後,她寫信給相親對象的父母,告訴他們,她相中了他的弟弟。這封信,石沉大海。

VCG
1975年,暮美從黑龍江農場回到上海後,她開始自學做衣服。1979年,大批上山下鄉的青年都回來了,暮美也弄回了自己的戶口。那時,工廠招人,她考進一家服裝廠。在車間做褲子的時候,因為流水作業,她是最後一個,她不願意等,常把前面的人的活拿來做。後來,車間的人也懶得做了,她就一個人做。一個禮拜後,廠長拿著記件簿過來問,哪一個是姚暮美,車間的人都指指她。廠長看著她身上的衣服,問是不是她自己做的,暮美“嗯”了一聲。那時的人都很樸素,穿得都是肥肥大大的衣服,可暮美喜歡穿緊身的,所以她就自己做衣服。暮美就這樣進了新服裝廠的技術組,每天晚上去上培訓課,學習裁剪、排版等技術。
那時,常有人給暮美介紹對象,可她不喜歡年紀比她大很多的,又嫌棄對方長相難看的,同事都說她眼光老高了。這樣一晃,晃到了30歲,遇到了這個比她小五歲的男人,長相不賴,工作也不錯,對她、對她家裡人都好。
暮美的媽媽也很喜歡他。因為他的母親是蘇州人,所以常給暮美家送來大閘蟹。一次,暮美媽媽說家裡的木盆太重了,請他幫忙弄個輕一點的木盆來。第二天,他騎著自行車,帶來大大小小的好幾個木盆。自此,暮美媽媽家裡做個晾衣架都要他來做,門口搭個涼棚也要伊來。
她每天晚上下課後,他都來接她,送她回家。談朋友的時候,每個月15號發工資,時間再晚,他都會將工資送給暮美保管,哪怕是賺的外快,也全部交給她。他給她的每一筆錢,什麽時候給的,暮美都會記在從廠裡領回來的工作手冊上。她想人家是小弟,她是大姐,她要用人家錢幹什麽,就算以後她不跟他好了,她也會如數還給她。但她也不會讓自己吃虧,他們一起出去看電影、吃飯的錢,就從他給的錢裡出,當然,每一筆開銷,她也會記账。
二
“姚暮美,有人找!”車間主任叫道。
找暮美的人,是她喜歡的第一個男孩。他們在黑龍江農場的時候,就很要好。
1966年,暮美家門口貼著大字報,因為她父親成份不好,她父親是上海紡織機械廠的工程師,他們說他欺壓工人。暮美還記得那時抱著父親寫的一堆材料,一家一家地跑,一家一家地說“我爸爸沒有欺壓工人”,請求他們簽名證明父親寫的材料屬實。
暮美的1967屆同學都快走光了,只剩下像她這樣頑固的人還留在上海。本來她想跟同學去安徽插隊落戶,父親不讓她去,說安徽太苦了。她又想跟幾個要好的女生去雲南,父親也不同意,說雲南一年兩熟,又有蛇蟲鼠蟻,老苦了。父親幫她挑到最後,實在沒有辦法,選了黑龍江農場,理由是日本佔領中國的時候,先佔領了東北三省,那裡鐵路交通發達,這是其一;其二,那裡每個月有32塊的工資;其三,那裡是一熟。
在農場裡,暮美發了她人生中唯一一次的火。一天,不知道是誰的肥皂丟了,一個個排查下來,最後人家懷疑是暮美。寢室裡與暮美關係要好的小毛告訴了她。晚上洗漱完之後,她拿著個鋤頭,站在炕上,一邊敲鋤頭,一邊說——“你們誰懷疑我,就請站出來與我對質,我會告訴你——是我還是不是我。”沒人說話。因為她剛剛在身上跳蚤咬過的地方塗完藥膏,那個樣子,著實嚇人得很。
她把小毛叫了過來,“儂講出來,是哪個?”
“我……我我沒有講儂,是……是是人家講的!”小毛嚇得講話都結巴了。
一排炕上睡16個人,暮美就一個個地問,結果沒有人說自己懷疑她,她這才罷休。
12月5號,暮美把剛領的工錢放進包裡,跟他們說她要回去了,她想家了。他們以為她瞎講,沒理她。她什麽東西都沒拿,穿好衣服,背了一個包,直奔公路上,舉著毛主席像章攔車。
到了火車站,上了去哈爾濱的小火車,車上沒人查票。到了哈爾濱,她跳上去上海的火車。沒坐幾站,有人來查票。那人將她領到列車長辦公室,列車長問她為什麽沒買票。
“我要買票的——”暮美掏出包裡的所有錢——32塊,跟他說,這是她這個月的工錢,都給他買票。列車長接過錢,從中拿出幾塊錢給她,說是給她吃飯用的,叫她回座位上坐著,到站了會叫她。
快到蘇州的時候,列車長將32塊錢都還給了她。他說,火車有兩個門,讓她不要從月台門下去,他會幫她開另外一扇門,從那裡出去走到火車站前面,買一張到上海的火車票,很便宜。然後,她花了一塊兩毛買了一張車票,到了上海。
摸索著到了家,她敲門,大喊:“爸爸媽媽,我回來了!”
那時,暮美家的燈還亮著,她姐姐正在窗台邊給她寫信,她打開門一看到暮美,激動得不得了。接著,哥哥妹妹們都跑出來了,說:“儂哪能跑回來了,阿拉以為一輩子看不到儂了!”
暮美從農場逃回來沒幾日,有著高血壓的父親,突發腦溢血走了。父親一走,家裡的經濟來源也斷了。本以為可以一直待在上海的暮美,因為父親的離世,不得不再次回到黑龍江農場,那是1970年五一過後。每個月發工錢,她都會往家裡寄10塊錢,因為媽媽正等著她的錢養家。
再次回到農場的暮美,有了第一次的春心萌動。在農場的五年,因為有他,顯得單純而快樂。
1977年恢復高考,他考上了哈爾濱的大學。暮美回到上海不久,接到了他的電話,說他要回來參加葬禮,他的妹妹自殺了。暮美趕過去的時候,他正在寫挽聯。見暮美來了,他拿起旁邊一個很大的花圈,說要把她的名字也寫上去。暮美不肯,她也不知道當時自己為什麽不願意把自己的名字寫上去。進進出出的親戚見他們為此爭執,都過來勸她。一氣之下,暮美走了。那一刻,綁在他們腿上的那根紅線散掉了。後來想起他,暮美也覺得惋惜,她覺得自家老怪了,人家還送了她一塊手錶呢。
這一次,他來找她,是為了戶口的事。他大學畢業之後,留在了哈爾濱。那個時候,在農場的人的戶口可以調回來,在市裡的人就不行了。但是,他們未婚妻的戶口在上海的話,他們的戶口就可以調回來。暮美也很想幫他,但是她和那個男人都快談婚論嫁了。
三
暮美34歲那年,因為妊娠高血壓,住在醫院裡,預產期過了,孩子一點動靜也沒有。一天半夜的時候,羊水破了。她趕緊叫護士,護士說不急,等醫生來,醫生來了後,說摸不到孩子的頭髮和頭,要馬上安排剖腹產,問家屬在哪,需要家屬簽手術同意書。
“家屬還沒來呢,簽字我自己簽。”暮美說。
“不行,趕緊打電話!”
護士幫忙給那個男人打電話,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暮美掃了一眼手術同意書,就簽了。
趕來醫院的那個男人,正在手術室外跟護士吵吵嚷嚷。
“這同意書上寫的什麽‘大人小孩都不保’?!”
“是你老婆自己簽了字進去的。”
護士的話氣得他甩了護士一耳光。這時,手術室的門推開了,只聽見一句“你老婆生好了,是個兒子,七斤六兩。”他趕緊給護士賠禮道歉。
兒子出生的時候,剛好是冬天,她怕冷得很,不想給他喂奶。買奶粉需要報戶口,暮美的妹妹幫她兒子去上戶口,可她還沒想好名字,就叫妹妹報一個“高王兒”。派出所的人一聽,說“哎呦不得了,下次還要弄個公主配配呢”,不給報這個名字。暮美躺在產婦病床上想名字,正好瞅見對面牆上一行字——“不飛則已,一飛衝天”,不如就取名“高飛飛”吧。要麽飛上天,要麽就不飛,他愛飛不飛。
暮美跟他結婚的第二年,生下了兒子高飛飛。她和他們一家人住在城隍廟的石庫門房裡。暮美的小家住一個16平方的灶間,他爸媽住一個16平方的灶間,他哥哥住在後樓,大概9個平方。
雖然住的地方小了些,但那段時間是暮美人生中最開心的時候。她廠裡的工作不錯,老公好到她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男人了。他從不讓她掃一下地,或者擦一下東西,家務活都是他做。每個星期天,她帶兒子回娘家,他都會提前叫好計程車。平常,兒子是他媽媽和姐姐幫忙照料。她每天下班回來,婆婆煮好了飯菜等她。
如果非得說對他有什麽不滿,暮美能想到的是他工作太忙應酬太多,對孩子不上心。星期天的時候,她想帶著孩子去動物園看看老虎、大象長什麽樣。有一天,她就跟他說明天去西郊公園。第二天,他早早地叫了一輛車在家門口等,他告訴她,他不去,他已經聯繫了她妹妹,由她妹妹陪他們去公園。然後,又扭過頭囑咐司機送他們到西郊公園,四點半的時候,再去公園門口接他們。付完車費,他才走。
有時候,暮美也會因為他對孩子不上心的事鬧脾氣,抱著孩子就回娘家。她母親從不讓她在娘家過夜,叫她趕緊回去,說他待會就來了。這剛把孩子放在床上,窗外就響起車喇叭聲。
四
1988年4月16號——是暮美永遠也不會忘記的日子,她記得那天氣象很好,有很多朋友去送他,包括他之前做財務的同事。從去機場的路上一直到候機大廳,她抱著兒子眼淚不止,兒子也不停地用小手給她擦淚,他一聲不響。他跟每一個朋友家人告別,卻不跟她說一聲“再會”,就走進了安檢的隊伍裡。突然之間,暮美抱著兒子朝隊伍奔去,如果她不叫住他,過了這道門,她可能再也見不到他了。
“你不要走——”她拽住他的胳膊,大聲哭喊著,“你不要走——”。他推開她的手,什麽也沒說,暮美大哭。他姐姐跑過來抱走了她懷裡的孩子,將她從隊伍裡拖了出來,她全然顧不不得圍觀的人群,只是放聲大哭,淚眼朦朧中是他頭也不回地走進了那道門。她想,他在日本賺夠錢就會回來的。
有人形容80年代末的上海,彌漫著這樣一種空氣——認為只要去了日本,就能賺到錢。他聽他從日本打工回來的嫂嫂的弟弟說,那裡的鈔票賺起來容易。因此,他也一心要去外面賺錢。他跟暮美說,他要讓她和兒子生活得更好一點,給他們換一套大房子住。他告訴4歲的兒子,他出去賺錢給他買摩托車。他要出去暮美也攔不住,就像她想做什麽事,他也攔不住她一樣,所以她同意了。暮美將國債券換成現金,拿出家裡所有的積蓄,一共兩萬塊不到,他用這筆錢去了日本。
他走了之後,暮美每天下班回到家,覺得家裡全都變了,她看不到他了。她翻出他所有的照片,貼在茶几上、櫃門上、台子下面,貼了滿滿一屋子。每天晚上,望著睡著的兒子,她流淚到天亮。暮美覺得自己一生的眼淚,都是在這個時候哭幹了。

VCG
不久後,她受不了家裡到處都是他的照片,看不到他的人,看這些照片有什麽用。她將所有的照片,還有牆上的結婚照,一一取下,包起來,藏在床底下。再後來,她把他的東西也打包了起來。
每次公共電話處的人喊暮美接電話,她都是滿心歡喜地拿起聽筒,不一會,又失落地放下聽筒。他問的無非是——“你好嗎”,“兒子好嗎”,“吃了嗎”,“你自個注意休息”。有時,她也讓兒子聽電話,可兒子不聽,她就拚命地將聽筒塞在他耳邊。
又過了一段時間,暮美收到了他的幾封信。按理說,這幾封信不應該全部都送到她廠裡來,但送信的人叫她幫忙轉交其他幾封信。一封信是給他姐姐的,有幾封信是給他朋友的,還有一封是給她的。她先拆開了自己那封信,沒有什麽內容,是一些 “我在日本很好,不用擔心”,“把兒子養養好”之類的平常話。她有些不甘心,想看看他給他姐姐寫的信。她拆看一看,差點氣暈過去。他在信裡說,如果暮美要走,就放她走,讓她把孩子留下來,請姐姐幫忙撫養孩子。看樣子,他是覺得他離開了,她就守不住了。好,她就等他回來,看他怎麽辦。
但是,她不能任由自己沉浸在過去的回憶裡,她要重新開始,她不能再住在都是他影子的灶間了,她決定搬回虹口區的老窩,那裡正好空著沒人住。很快,他寄來一大筆裝修房子的費用。她拿著他寄過來的日元去銀行換錢。一個在銀行旁邊走來走去的人,叫住她,說跟他兌換的話,匯率比銀行的高。暮美覺得那挺不錯的,那人說有一張不靈的,給她換一張。她拿著親眼看對方數對的數目,去了華僑商店,買了兩件羊絨衫,一件送給兒子的老師,一件自己穿。一件羊絨衫180塊,付錢的時候,暮美才發現錢的數目不對。被騙之後,再要換錢,她都直接去銀行了。後來,他不直接寄錢給她了,而是寄到他姐姐那裡,再由他姐姐轉交給她人民幣。他每年給她寄一萬二,一個月一千塊錢。後來,她才明白,那是他給她養活兒子的錢。
五
搬到虹口區之後,暮美與他家裡的人來往得少了,但每個星期還是會帶孩子去看他奶奶。她覺得應該體諒奶奶,畢竟人家兒子在國外,人家要看孫子總不能不讓她看啊。
一天,弄堂口管公用電話的阿姨喊暮美接電話,一開始她以為是他的越洋電話,可電話那頭傳來的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她問儂是啥人。女人先說了這個男人的名字,然後說,她廠裡有個女人天天說我男人在日本哪能哪能。女人給了她廠裡的地址,叫暮美中午過來一趟,因為那女人今天剛好上中班。暮美告訴對方她沒空,掛了電話。
她不知道打她電話的女人是誰,也不知道她是怎麽找到她虹口區的電話的,對於她口中的那個女人更是無從得知了。暮美想起他還沒去日本時,有人跟她說,他和城隍廟的財務關係很要好。那時,她覺得他是經理,跟同事關係好是正常的。這個財務,逢年過節時還給她兒子送皮鞋送衣服,偶爾還上她家裡坐坐。她那時,不信閑話的。
這一天,她又接到了一個電話,是兒子的老師打來的。老師在電話裡說,高飛飛昨天沒把便當帶回家,今天午飯用沒洗過的便當盛飯。
下午去學校接兒子的時候,暮美帶了兩件廠裡做的女式襯衫。
“老師,以後你幫我們洗便當。”她把襯衫送給老師。從那以後,兒子的便當就是老師幫忙洗了。因為老師常跟她告狀,她沒少給老師送禮物。
有一次放學,暮美去學校接兒子。老師問她是不是從來不打她兒子的,她說是的。老師又問她是不是從來不罵她兒子的,她說是的。
“你今天回去一定要打打你的兒子,他上課一直搞小動作。”
“好的。”
暮美將兒子放在自行車後座,跟他說,她今天一定要打伊的,兒子說好的呀。
回家之後,她囑咐兒子去房間,脫了褲子,趴在床上,等她來打他。兒子進屋後,她開始生爐子準備晚飯。
“媽媽,我準備好了,儂好進來打了呀!”
“儂不要急,等媽媽生好爐子,再進來打儂!”
忙著忙著,她就把這事給忘了。進屋一看,兒子的小屁股趴在那裡,他把裡面的棉毛褲都脫了下來,這樣是要生病的,她叫兒子趕緊穿好。
吃完飯,給兒子輔導完功課,她跟他說,如果以後老是這樣皮,媽媽就不要他了。她讓他整理完書包,就進屋睡覺,她去幫他鋪床,一個轉身的功夫,兒子不見了。她在門口喊了兩聲,無人應答。
暮美騎上自行車,大街小巷到處躥,她大聲喊——“飛飛,儂回來呀”。騎了好幾條馬路,終於在一家水果攤邊上看到兒子小小的背影。昏暗的燈光照在兒子的身上,她的心,在那一刻軟了下來。她將自行車停在遠處,不敢喊他,怕他又跑了。她慢慢走過去,說:“飛飛,阿拉回去好吧。”
兒子回過頭,一下子抱住她,“媽媽,媽媽。”
她問他為什麽跑出來。
“儂講不要我囉,爸爸也不要我囉,儂再不要我囉……”
六
兒子這天背著書包準備去上學,暮美告訴他,待會她有個中學同學來看她。兒子馬上停下腳步,問是男的還是女的,她回答說是男同學。兒子放下書包,說他今天不去上學了,“儂不是有男同學到我家來嘛。”
暮美叫兒子放心去學校,她會打電話給阿姨,叫她來陪她。
“真的,儂要叫阿姨噢。”
她說她不會騙他的,兒子這才拿起書包去學校了。那次,她真的把阿姨叫來陪她了。暮美沒想到兒子這麽小,會這麽敏感。
一次暮美在家洗衣服,一群小朋友湧了過來,兒子的手包著一塊床單,還有血往下滴。原來是他打球的時候,不小心擦到玻璃了。
她騎著自行車,把兒子帶到醫院。醫生給他的傷口縫了七八針。從醫院回來,她去找兒子扯下來包扎傷口的床單是誰家晾曬的,找到了,賠給人家。拆線的時間到了,她沒時間帶兒子去醫院,就給他拆了兩針。第二天老師打電話來,說高飛飛上課的時候拆線。她一開始還納悶,經老師解釋,方才想起。等她去學校接他,兒子告訴她,一點都不痛,一下子就拆掉了。“儂老勇敢了”,她表揚他。

VCG
一個平常的周日,暮美加完班回到家,在老虎窗口收衣服。一個警察在樓下叫她,說她兒子在派出所。暮美一聽,手裡的衣服全都掉了,趕緊奔到派出所。原來,每個星期天,孩子們都會翻牆進一所中學裡打球。那天,為了教訓他們,學校的人就將孩子們送到派出所了,大部分孩子都跑掉了,只有她兒子和另外一個小朋友沒跑掉。人家小朋友打電話叫爺爺奶奶給領回去了,她兒子不知道她廠裡的電話,才留到了現在。
那段時間,暮美廠裡特別忙,有時候還需要她出差。可她不在家,孩子就沒人管,她只得跟老師請假,帶著兒子一起出差。
一次去寧波出差,兒子在車間裡也是很招人嫌。快下班的時候,她沒找到他,全廠的人都幫忙找孩子,愣是沒找著。
“姚師傅,你兒子在河邊!”
她跑出去,喊他的名字,他也不理她。兒子坐在河邊的石頭上,手裡拿著根棍子,正撩撥河裡的鴨子。
還有一次去安徽出差,因為他們去的時候穿的單薄,兒子感冒發燒了。廠裡幫忙給孩子做褲子做衣服,還給他買了保暖鞋。兒子怎麽都不肯穿保暖鞋,氣得她要動手打他,這下倒好,他在車間裡跟她兜圈。
乘火車回去的時候,他們買的是軟臥上鋪。晚上睡覺時,暮美一轉身,一個男的正赤身裸體地躺在對面床鋪上,嚇得她不敢作響,馬上下來去找乘警。乘警過來查看完畢,給他們換了一個床鋪。
那個時候,那個男人除了寄錢回來,也會給兒子寄衣服回來。沒有給兒子買摩托車,給他買了一輛捷安特自行車。沒兩天,自行車就被人偷了。不過,因為那個男人給車上了保險,他們也拿到了賠償金。再後來,兒子的電腦也是他給買的。
七
暮美出去買東西,從提籃橋走回來,經過下海廟的時候,一個算命先生朝她看了一眼,問她要算命嗎,她說不算,因為她媽媽告訴過她,命是不好算的。在暮美抬腿要走時,那算命先生說:送你一句話,你是一個自由人。
一轉眼,暮美50歲了,她在2001年退休了,每個月的退休工資一千塊不到。廠長說給她每個月1300,叫她再多做幾年。當時她也想繼續留在廠裡,轉念一想,這些年她已經夠苦了,就沒去上班,過上了退休生活。
每天午飯結束,暮美將家裡收拾乾淨,將晚餐所需食材準備妥當,她會去公園跟老師學交誼舞。有時,她也去舞廳裡跳,但她不是很喜歡舞廳裡的氛圍。比方說,51歲的暮美不可能找到50歲以下的男性來跳舞的,只有比她年紀大的人來找她,可她並不想跟一個60歲的人來跳。舞廳裡每個人都有舞搭子,如果對方的舞搭子沒來,可以邀請她跳。一次,一個男的邀請她跳舞,跳到一半,就把她扔下了,原來是人家的舞搭子來了,她覺得真是怪嚇人的。還有一次,一個年紀比她大的男的想跟她跳,不想跟他以前的舞搭子跳。他跟她說,他帶她出去跳專場。她想她才學不久,出去跳專場蠻好的,正要答應人家,另外一個男的悄聲告訴她,跟那人學跳舞,要每天給他一包煙,跳好舞出來,要請他吃一頓飯。
她很是生氣,從此,就不去舞廳了,換成搓麻將了。去舞廳的人,會打扮得漂漂亮的去。而麻將室呢,是一個三教九流的地方,可以穿拖鞋、短褲去,天熱的時候,男人可以赤膊,香煙吃吃。上海有一種吃吃蕩蕩的人,他不工作,整天拿個杯子東晃西晃,站在邊上,看別人打麻將身體都不帶動的。暮美搓完一局,他也看完了,真是老挫氣了。
八
那個男人回來的那一年,是2006年。
他先去見了兒子,那時,高飛飛在鼓巷大酒店上班。聽見他爸爸在咖啡廳等他,興衝衝地去了,在他對面坐下了。這些都是高飛飛下班回來後告訴暮美的,他跟他媽說,他們沒聊什麽。暮美以為這個男人見到兒子的時候,會給他一張銀行卡,跟兒子說喜歡什麽東西自己去買。她想她是電視劇看多了,這個十三點的男人,十六年沒見兒子,卻一點表示都沒有。難怪會面之後,兒子不開心。
兩三天后,他打電話約暮美在一個小飯店見面。
菜上了一盤又一盤,他卻沒動筷子。終於,他開口了,說——“我們離婚吧。”
“嗯,我同意。”
暮美想自己一個人將他兒子從5歲養到21歲,就等來他這一句話。這16年來,他不可能一個人在外面的,她願意和他離婚。她告訴自己,她和他從戀愛到結婚的時間加起來也就8年,怎麽比得過他和那個女人在一起的16年,她放他走。暮美回來後也是這麽告訴兒子的,兒子什麽話也沒說。
接著,她去谘詢法律顧問,是通過法律途徑離婚好還是協議離婚好。法律顧問建議她協議離婚,他說:“如果你要告他,你們已經16年不在一起了。像他們這種回來的人就是無賴加流氓,他可以說他一分錢也沒有,他說自己在那裡吃人家住人家的,沒錢!就算調查他的財產,也是查不到的,他可以將財產轉移到對方的账戶裡。”
過了幾天,那個男人又來找她,他讚成他們協議離婚,說他們之間沒有財產糾葛,兒子也成年了毋需爭奪撫養權。
“兒子長大了,沒有結婚的房子,你要給他預備好,還有結婚的錢,就這兩樣。”暮美說,至於她自己,她不需要什麽精神損失費。
他說可以的,會有的,以後虹梅路的房子就是兒子的。虹梅路的房子,其實是那個女人媽媽中山公園的房子拆遷後分的房子,那個女人的媽媽死了之後,他們一回來就住進那裡了。可他當時卻騙她說住在賓館,實際上是跟那個女人一起回國的。
在民政局離完婚以後,他們去了對面的銀行。他拿出一張金卡,要給她轉錢。他說,這張卡的账戶名不是他的,是雯雯的。原來,那個女人的名字叫“雯雯”。
後來,暮美才知道那個女人有一個同她兒子一般大的女兒。同樣,兩個孩子在上學,人家的孩子早早就送去新加坡讀書了,她兒子卻不知道在什麽破學校讀書呢。
離婚一年後,他在閔行區買了一套三室兩廳的房子。他是這麽分配的,他們夫妻一間,他女兒一間,兒子一間。暮美也不是霸道的人,就叫兒子住到他們那邊去,跟他們搞好關係。兒子也聽話,下了班就去了。沒想到,兒子第二天就回來了。
飛飛說,晚上吃飯的時候,看著爸爸,還有別人的媽媽和孩子,他就在想,如果是爸爸媽媽和他在一起就好了。第二天是星期天,那個女人在飛飛起床後,叫他明天洗澡先把自己的襪子褲子洗掉。可飛飛哪裡懂得洗衣服,他從來沒洗過這種東西的。暮美後來反思,是自己太溺愛兒子了。可兒子缺失了這麽多年的父愛,她是想盡可能多地給他一些母愛,所以,才什麽家務活也不讓他做的。她覺得她做的東西都讓他看到了,船到橋頭自然直,他自然就會了。
九
暮美站在窗口,一手拿著離婚證,一手拿著醫院小結,她想跳下去,一了百了。
那是2008年年初,暮美確診為乳腺癌中晚期,肺積水,肝髒旁邊有囊腫。她想跳下去,上天對她實在是太不公平了,她真的過不下去了!她想到了兒子,還未成家的兒子,若她走了,就沒人照顧他了。她要活下去,她要把病治好!
在去新華醫院開刀之前,她叮囑兒子不要來醫院看她。
她躺在手術台上,醫生叫家屬簽字。她說沒有家屬,我自己來簽。
那個男人來醫院看她,給了她一萬塊錢,走了。兒子來看她,問她疼不疼。
“不疼的,有止痛針的,儂明天不要來看我了。”
暮美不想兒子來看她,她覺得他會受不了的。但在飯店工作的飛飛,不時地會帶些甲魚湯來給她喝。
開完刀以後,要做六個療程的化療,她的頭髮都掉光了。每次化療的時候,她找中午的時間過去,晚上在醫院住一夜,第二天早上8點開始吊針,直到晚上9點。然後,她回家,咬著牙,爬上樓梯。

VCG
暮美出門去買菜,小區裡三五群人圍著,指指點點。她知道他們在說她。她走過去,問他們:“你們想知道我嗎?”她想既然人家背後議論,還不如走到前面,讓他們了解情況,她告訴他們,她得了乳腺癌,現在正在化療,所以頭髮也沒了。後來,她還是買了一頂假發。
買完菜回家燒飯,她洗個菜要洗三回才能洗好。剛洗的時候,她覺得撐不下去了,就回房間睡一會,覺得好些了,再起來洗菜。那個時候,她只有一個意念:為了兒子,活下去。
2008年年底的時候,她又去醫院開了一刀,因為肝髒旁邊的囊腫長得有小碗那麽大了,如果再不開刀的話,就要破掉了。她告訴醫生,打開她的腹腔之後,看到什麽不好就拿什麽。
身體痊愈後,暮美仍像以前一樣,每天出門前都會打扮得清清爽爽的。
過了兩年,她參加了上海市癌症康復居委會。第一次在會上介紹的時候,她說大家都是有福的人,生病時有老公或子女倒一杯茶吃,還要問燙不燙,可她呢,喝一口水都要自己親手去燒。她希望大家要積福,愛惜自己的家人。
十
飛飛生了點小病,在醫院掛點滴。暮美跟他說了之後,他匆匆忙忙地來了,遞給她一遝錢,說是雯雯叫他給她的3000塊。暮美聽了這話,有些不舒服,但還是不客氣地接過他的錢,說了一句謝謝儂。
從醫院出來之後,飛飛看到小攤上有賣手套的,就說他想買個手套,這樣開電動車的時候就不冷了。這個男人拿出300塊錢給兒子。買好手套,飛飛順手將剩下的錢放進口袋。走到一家肯德基前面,飛飛說肚子餓了。
這個男人的腳步慢了下來,他問暮美,鈔票有沒有多帶。
暮美聽著他的話,覺得這人真是傻氣,她忙說不要緊,她來付錢。她想這300塊錢應該是那個女人叫他請他們吃飯的,誰知道半路上兒子要買手套,他以為買了手套,就好坐車回去了,誰知道兒子又說要吃肯德基。看樣子,他姐姐說得對,以前他把所有的錢交給暮美,現在他把所有的錢交給那個女人,他自家是一分錢也不要的。
吃肯德基的時候,暮美指點他,“儂呢自家要藏點鈔票。”這個十三點的男人卻說,雯雯每次給他零花錢,他都說不要給那麽多,他用不完。暮美只得告訴他,你總歸還有一個兒子。暮美實在搞不懂這個男人,他回國之後在蘇州的工地上工作,在那邊要租房子要吃飯,掙的每一分錢全交給那個女人,那個女人的朋友圈是全世界旅遊的照片。她後來實在看不過,就把那女人拉入黑名單了。
一天,暮美打開信箱,收到一封銀行的催款信件。她問兒子是不是欠人家鈔票了。
兒子說他沒錢還信用卡,因為他的工資卡在老爸那裡。暮美這才知道,之前兒子叫他給他買一個手機,他同意了。買手機的時候,那個女人也去了。手機買好以後,他要去了兒子的工資卡,說買手機的費用從他的工資裡扣。飛飛沒有了工資卡怎麽生活呢,他就辦了兩張信用卡。對錢沒有概念的飛飛,瞎吃八用,就這樣欠下了一筆卡債。
暮美叫他打電話給他爸爸——
“老爸,江湖救急。你能先幫我還一下信用卡嗎?我有了錢就會還給你的。”
“自家出了事情自家處理,儂來找我做啥?”
飛飛大概也沒料想到父親會絕情至此,沒有辦法的暮美,只得幫兒子欠的錢都給還了。好在自此以後,兒子也不用信用卡了。
這件事以後,飛飛不再跟父親說話了。沒過幾天,他跟暮美說,他不想上班了。
飛飛那天做完了自己的單子,領班看他在那閑著,就把別人的單子給他做了。心情本就不好的飛飛,實在搞不懂別人做不完的工作為什麽要派給他。然後,暮美去飛飛的物流公司,找到他經理,人家領導說,他已經很照顧飛飛了。
兒子每換一份工作,暮美都會去幫他搞好關係。之前幫他聯繫的飯店工作,做了一年,他就不想幹了。現在,他又不想去上班了,還不跟她說話,也不出門見朋友,只是待在家裡。暮美怕兒子得抑鬱症,開始帶他去看心理醫生。
心理谘詢的第一天回來之後,他還是不說話。第二天,她又帶他去了,兒子說了一句話——“浪費鈔票”。暮美只得去問心理醫生,心理醫生說她兒子不配合,兩次都沒怎麽開口說話。暮美想那豈不是白來了,她跟兒子說,以後不來了。她想兒子既然不配合,那說明兒子沒病。
十一
2017年,暮美所在小區的居委會領導來找她,希望她可以帶領舞蹈隊去參加比賽、拿獎。因為之前她身體不太好,就不太去舞蹈隊。現在承蒙領導這麽看得起她,她就答應了下來。沒兩天,舞蹈隊裡就有人開始傳閑話,說——“那個女人離婚了”。
第二天排練休息的時候,暮美問她們,是不是想知道她的故事。
她們圍坐一圈,聽她站在那裡說她的故事。期間,她看到有人揩淚。那個時候,她就想,如果她生的是一個女兒,至少她換下來的內衣和短褲,女兒會一起幫她洗掉,但是兒子是不可能的。
她看過一篇文章裡說,一個單親媽媽如此教育兒子——你是男子漢,你應該保護媽媽。可她從來不會跟兒子說這樣的話。
即使兒子與他父親的關係疏遠了,她還是試圖去修複他們的關係。畢竟,他們是父子,是永遠也改變不了的事實。
前兩天,她告訴那個男人,她生了帶狀皰疹。他二話沒說,給她轉了3000塊錢。她想,他現在終於學精一點了。
兒子每天會按時幫她塗藥。塗藥前,他先數皰疹的粒數;他說如果第二天皰疹多了,就證明她的病情惡化了。接著,他要拍一張照片,因為要做顏色的對比,如果第二天顏色暗下去了,說明病情在好轉。
她在家裡說這不舒服那不舒服,床單又不好了。兒子就會告訴她,等她好了,會重新幫她換個床單。
兒子的細心,讓暮美甚是欣慰。她不願再找一個老伴,她想她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她只想跟著兒子相依為命,如果哪天兒子結婚了,看到他幸福了,她也開心了。
那個男人現在也常與她語音通話,關心她的近況,暮美也會問問他胃癌晚期的女兒病況如何。至於兒子的房子,他說兒子什麽時候結婚,什麽時候就有房子。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