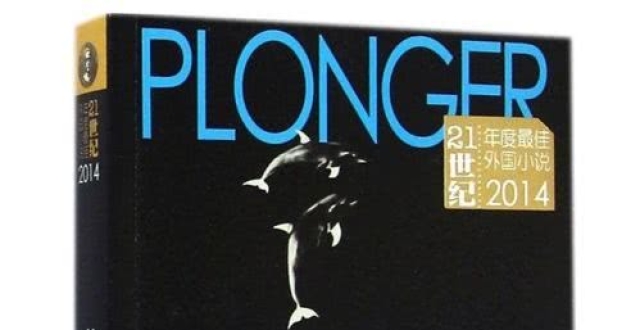∞《巴塞爾姆的40個故事》,2015
巴塞爾姆 著 陳東飆 譯
新經典|南海出版公司
《四十個故事》譯後記
一年時間,譯完了巴塞爾姆的100個故事,大概算是有了點資格說說如何翻譯巴塞爾姆了吧。(關於巴塞爾姆的背景資訊,請參閱本書前面戴夫·埃加斯的序言及其中引用的大衛·蓋茨為《六十個故事》寫的序言,以及我為《六十個故事》寫的譯後記“巴塞爾姆:留胡須的孩子”,這裡不再重複。)

巴塞爾姆1984.3.22
By Audrey Ueckert
這是我第一次“批量”地翻譯小說,就首先並且持續地遇到了意譯與直譯的問題。
所謂意譯,在我理解中,是把外國人寫的東西譯成仿佛是中國人寫的,依照中國人的習慣和語感來組織句子,以求得流暢的閱讀體驗,就是以句子(甚至段落)為部門,在保證準確遞送原文所包含的資訊(即“說什麽”)的前提下,自由發揮。
所謂直譯,是把外國人寫的東西譯成仿佛是外國人寫的,追求詞與詞的對應,盡可能地再現原文的語序,語法,句子結構(即“怎麽說”),在這裡自由的太空是極小的。
在我以往(主要是詩歌的)翻譯中,我是直譯的實踐者,因為在我看來“怎麽說”始終是“說什麽”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好的文學作品在語言和文體的方面永遠是獨一無二的。當然,意譯並非一無可取,以意譯的方式,同樣可能在語言和文體方面取得不同凡響的創新成就,在譯文所在的語言中抵達某種高度,如同原文在其語言之中所抵達的高度。
我聽說(並沒有讀過)菲次傑拉德的《魯拜集》1是意譯達至文學經典的一例,但我猜想,或許那是因為菲拉傑拉德本身是一位不遜於歐瑪爾的詩人吧,因為在好的意譯背後,必定是譯者在語言上具有與原作者同樣(至少是同等高度的,如果不是更高的)的敏感、悟性和創造力,是一位與原作者等量齊觀的文體家或詩人。他可以從他所理解的原點開始,像原作者一樣從頭創造一行詩,一個句子,一個段落,一件作品。即使我們真的以意譯獲得了一個不遜於原作,甚至超越了原作的作品,但你如何確保他所理解的原點就是真的原點?如何確保我們所讀到的一部譯文的傑作不是一部背叛的傑作?如何分辨你讀到的是菲茨傑拉德還是歐瑪爾?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David Bryce and Son,1900
讓別人去煩惱這個問題吧,我既不是一個文體家也不是一個詩人,而只是一個翻譯者,我的成功只在於盡可能地再現了原文的一詞一句,我的失敗也只在於未能做到這一點。在我曾經進行過的詩歌翻譯中,如果一首譯詩是好的,那必定是因為原文是好的,如果一首譯詩是壞的,由於原詩肯定是一首好詩,那必定是因為譯文的不準確造成的(無論是譯者的能力問題,還是兩種語言之間的鴻溝令詩意的傳遞成為不可能)。
但在小說的翻譯中,意譯似乎又扳回了劣勢,因為小說需要讀者投入到情節之中,將注意力集中到“說什麽”而不是“怎麽說”之中。小說的作者或是無所不知(所謂“上帝視角”)將一切向讀者和盤托出;或是隱於幕後,讓讀者感覺不到他的存在,以為自己從小說中獲得的一切都是由自己觀看,摸索,猜想,領悟,破解而來;或是寄生於小說中某個人物身上,讓讀者以為自己是透過這個人物的眼睛在觀看,摸索,猜想,領悟,破解一切。幾乎所有的小說都是上述三種“說什麽”的模式之中的一種,其最終目的是同一個,將小說裡的那個“故事”遞送給讀者。
意譯可以完美地滿足這一目的,因為它正是以那個“故事”為原點而進行的某種改寫,並且是相當收斂的一種。事實上,對故事的改寫,無論是否改寫成與原文同一種語言,始終是得到廣泛接受的一種形式,例如蘭姆姐弟的《莎士比亞故事集》2即可被視為一種意譯。

Tales From Shakespeare
London:Ward Lock, 1920.
但是有兩種小說是拒絕意譯的,一種是《尤利西斯》這樣,“在可能的極致程度上充注了意義”3的小說,可以說,它的每個句子都是原點,每個詞都具有不可更改的確鑿的意義,意譯(改寫)它便意味著歪曲,意味著錯譯,因此直譯是唯一可能的途徑。
另一種就是你手上的巴塞爾姆了。在我看來,它是在與《尤利西斯》恰恰相反的方向上,偏離了小說的常規模式的(而這卻讓它在某種意義上,仿佛繞了一大圈,與《尤利西斯》相遇了)。
在這裡我無法用(我所不懂的)文學批評來談論巴塞爾姆的小說,對從現代主義開始的各種主義也一概省略。在我的眼中,巴塞爾姆的小說最大的與眾不同之處,就是作者既非凌駕於小說之上,亦非隱藏在小說背後,作者本身就是與小說合而為一的一個人物,這本《四十個故事》加上《六十個故事》,合起來可以是《巴塞爾姆用一百種方法講故事》,更準確的講法是,《巴塞爾姆尋找一百種講故事的方法》。
在某一篇中,巴塞爾姆嘗試將所有的句子寫成疑問句來構成一個故事;在另一篇中,巴塞爾姆把一個故事寫成一個長而又長並且到最後仍未收尾的句子;在另一篇中,巴塞爾姆用講述一次平凡野餐的語調講述一個殘忍的私刑儀式;在另一篇中,巴塞爾姆用嚴肅的圖片,嚴肅的文字來組合成一個略微有點荒誕的博物館的描述;在另一篇中,巴塞爾姆記錄了一段不知道有幾個對話者,不知道有幾個話題,不知道對話的時空是固定還是在不斷變化的對話;在另一篇中,巴塞爾姆用採訪的形式,引誘讀者同時猜測他是在讚同,反對,暗示,諷刺,借喻某種東西,但搞不清是哪種東西……
所有的小說都在講一個故事;“巴塞爾姆在幹什麽”就是這個故事。
從整篇故事的文體到每一個句子,文字在巴塞爾姆的手中就是汽車大盜駕馭的汽車,“千萬不要讓他碰文字”4,不然準有事情發生。正如我們不能對原版的《速度與激情》中飆車的鏡頭進行任何剪輯一樣,對巴塞爾姆的文字進行意譯就是剪除它的意義,剝奪閱讀它的唯一樂趣。
例如,下面這段:
我們為公演招募傻瓜。我們有些地方需要大量的傻瓜(而在緊接第二幕出現的全體傻瓜之中,還有一些特別人員)。但傻瓜很難找。通常他們不願意承認這一點。我們將就找了呆子,二貨,笨伯。若乾幼稚兒,壽頭,豬腦,低能兒。敲定了一個憨大,連同某些二百五和白癡。一個腦殘。
——《鴿子飛離宮殿》
以上是我的直譯,我做到了在字面上盡可能的對應(但我必須承認,其中一些同義詞,如“笨伯”“豬腦”等,多少都有點隨意而可以互換,卻無法準確呈現英語中可能具有的語義差別)。如果意譯的話會是什麽樣,讀者可以自行想象。
類似的還有下面這兩段:
月球岩石是我們一生中所見過的最偉大的東西!月球岩石是紅的,綠的,藍的,黃的,黑的,和白的。它們閃爍,輝耀,點亮,迸現,明滅,和發光。它們發出轟響,雷鳴,爆炸,碰撞,飛濺,和咆哮。
——《電影》
我們支付給他們可溶性的旅行支票並企望下雨,企望大話,自誇,呼吼,吹奏,鼓樂,炫耀,喇叭齊鳴。
——《教育經驗》
將以上三段跟下面這段進行對比:
我過去一瞧……(你爸爸)咽氣了!……無常了,亡故了,不在了,沒了,沒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失敗了,失敗拔蠟了,嗝兒了,嗝兒屁了,嗝兒屁著涼了,撂了,撂挑子了,皮兒了,皮兒兩張了,土了,土典了,無常到了,萬事休了,倆六一個么,眼兒猴了——!
——《白事會》
傳統相聲和後現代主義小說並非沒有相似之處。每一個相聲都有一個話頭,每一篇小說都有自己的情節,它們講述了……反映了……揭示了……批判了……諷刺了……顛覆了……各各不同,但是依我說,歸根結底,它們的價值,也就是它們在作者死去多年之後仍被重說,被重聽,被重印,被重讀,被翻譯,被談論的原因所在,就是上面所舉例的這些無厘頭的,純粹說了開心,聽了開心,寫了開心,讀了開心的,無法被意譯的東西。
我曾經在寫給本書編輯Agnes的信中寫道:“……總感覺巴塞爾姆很多時候是在用寫詩的方式寫小說,把字放在嘴裡咀嚼,感覺,品味,看一個句子,一段文字寫下來是不是能夠讓他自己感到吃驚和好玩。”
沒有人能變成巴塞爾姆,我能做的就是將巴塞爾姆的句子直譯出來,看能否讓讀者感到吃驚和好玩。
陳東飆
2015年5月5日
譯注:
1、Rubaiyat,波斯四行詩體魯拜(Ruba'i)的詩集,其中最為著名的一部為波斯哲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詩人歐瑪爾(Omar Khayyám,1048-1131)所作,並由英國詩人,作家菲茨傑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譯成英語文學名作《歐瑪爾·哈亞姆的魯拜集》(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2、Tales from Shakespeare,英國作家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1775-1834)與瑪麗·蘭姆(Mary Ann Lamb,1764-1847)合作根據莎士比亞戲劇改寫的故事集。
3、埃茲拉·龐德語,見《閱讀ABC》(ABC of Reading)。
4、寫這句話時我聯想到的是電影《速度與激情5》(Fast Five)中的著名台詞:“千萬不要讓他們碰汽車(Never, ever, let them touch cars)”。
在我的眼中,巴塞爾姆的小說最大的與眾不同之處,就是作者既非凌駕於小說之上,亦非隱藏在小說背後,作者本身就是與小說合而為一的一個人物。
——陳東飆
—Reading and Rereading—

《巴塞爾姆的40個故事》,2015
巴塞爾姆 著 陳東飆 譯
新經典|南海出版公司

新經典
題圖:巴塞爾姆在《休斯頓郵報》期間
GIF:未知作者
關於博爾赫斯的一切
歡迎關注、投稿
搜“borges824”或“博爾赫斯”找到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