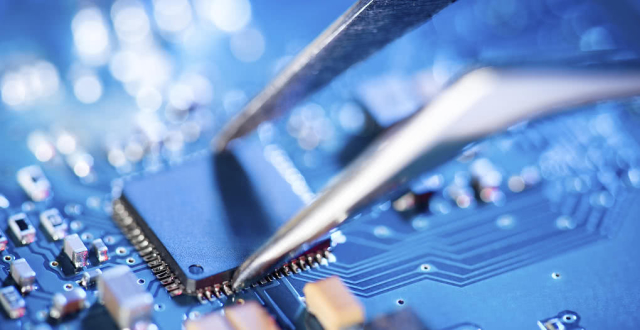作者 | 吳健偉 編輯 | 羅麗娟
“這可能是我們最後一代華為麒麟高端芯片。”
在日前舉辦的中國信息化百人會2020年峰會上,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表示,受製於實體清單,華為高端麒麟芯片可能率先宣布告急。
在經歷長達15個月、6次臨時許可延期後,華為正面臨“無芯可用”的局面。這只是過去一年多華為面對美國製裁禁令受影響的其中一面。
面對挑戰,任正非在過去一年間多次對外強調了華為正在迅速“補洞”中:大幅採購零組件、加大國內市場投入、推動鴻蒙、HMS(華為移動服務)“備胎”落地等等。
“現在大多數‘洞’已經補好了,飛機能繼續飛行;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洞’,需要兩、三年才能完全克服。”在去年年底接受採訪時,任正非向外界同步了華為的“補洞”情況。
在眾多“補洞”計劃中,華為的投資戰略變化在過去一年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
從過去以“不積極”著稱到一年出手13家產業鏈企業,從主張並購、瞄準核心技術到布局產業鏈上下遊投資。投資邏輯的轉變,能夠在動蕩中為這家科技巨頭贏取新的生機嗎?
投資“不積極”的那些年
相比起騰訊、阿里巴巴等互聯網巨頭頻繁地投資圈地,華為在投資方面一向以“不積極”著稱。而在這個標簽背後,充分體現了華為過去的投資戰略和態度。
全天候科技根據公開信息整理了2006年到2016年10年間華為對外投資清單。可以看到,在這期間,華為投資企業共20家,主要聚焦在芯片、物聯網等通信領域。

實際上,華為關於投資的戰略部署,早在《華為基本法》中就有定位。1998年,由華為領導層和中國人民大學的專家共同制定的《華為基本法》面世,這是華為最根本的規章制度。
其中第三十七條明確指出:我們中短期的投資戰略仍堅持產品投資為主,以期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迅速增強公司的技術實力、市場地位和管理能力。我們在制定重大投資決策時,不一定追逐今天的高利潤項目,同時要關注有巨大潛力的新興市場和新產品的成長機會。我們不從事任何分散公司資源和高層管理精力的非相關多元化經營。
“企業發展部”是華為負責對外投資的部門。據投中網報導,該部門在華為是二級部門,團隊規模數十人,華為所有的投資、並購均需通過該部門完成。
在華為,前期確認投資對象的環節,主要由業務部門完成。而華為各大業務體系都有相應的戰略與業務發展部,負責對投資標的進行行業分析、技術合作與甄別,與企業發展部一起與標的談判並盡職調查後,投資最終由華為常務董事會決策。
這讓華為的對外投資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目標極度明確,投資動作往往是為了得到某項技術、專利,或者是某支團隊。
對應到華為主營業務中,便是大量關於芯片、物聯網、存儲等通信領域的企業並購。
例如,在2012年和2013年,華為分別收購了英國集成光子研究中心(CIP)和Caliopa,前者主要聚焦光通信技術領域,後者主要致力於矽光子技術的光模塊研發。
2014年,華為為了擴大其在物聯網領域布局,相繼投資、並購了物聯網高性能芯片研發企業XMOS以及物聯網傳感器研發商Neul。
“華為的並購策略是收購關鍵技術,融入到華為的平台中,不會做純粹的財務投資。”2016年,華為常務董事、戰略Marketing總裁徐文偉接受媒體採訪時闡釋了華為的投資並購策略。
除了技術和專利之外,華為並購的另一個主要目標是牌照或資質資源。通信業在多數國家都有較強的監管,沒有資質就無法開展銷售運營,而申請資質需要的時間經常以年計算。因此為了快速進入某個市場,華為通常會優先選擇收購一些具備資質,但規模較小的公司。
高度聚焦和極強的目的性,使得華為在投資並購時能夠有的放矢。因此,在華為大部分並購案例中,多數標的估值都不高,集中在數千萬美元級別。
雖然華為把“永遠不進入信息服務業,永遠不去進入主行業以外的行業”寫入了《華為基本法》裡,但這並不意味著華為對於主業的定義一成不變,其中在2010年前後就有過短暫的搖擺。
這期間,華為對互聯網業務有過一段短暫的興趣,推出過包括瀏覽器、網盤在內的諸多互聯網產品。
從上述2006年到2016年華為的投資清單中也可看出,其中不少被投企業來自互聯網領域。
根據《理財周報》報導,在2008年下半年,華為成立了互聯網業務部,歸屬於華為業務和軟體產品線。由移動搜索服務商Cgogo創始人朱波空降而來擔任該部門的首席市場官,後來朱波又被任命為互聯網業務部總裁。
到了2010年初,華為將互聯網業務部並入到消費者事業群旗下,並成立了專門的互聯網與軟體投資並購小組。這個小組之後投資了昆侖萬維、暴風影音、趣遊等一批互聯網公司。
但華為關於發展互聯網業務的這段“戰略搖擺期”並沒有持續很久。
2012年,華為戰略出現了重大轉變——確定了隻做戰略投資,隻做跟自己主營相關的投資,而這裡的主業僅僅定位於通訊設備這個單一行業。
同年,朱波從華為離職。朱波後來公開表示,自己入職時華為曾有意往服務和互聯網發展,但是對於習慣了B2B業務的華為高層來說,一時間要適應互聯網的B2C模式仍存在很多與華為本身文化所衝突的地方。
在朱波離開後,華為互聯網與軟體投資並購小組也被撤銷。2016年,在昆侖萬維和暴風科技相繼上市後,華為均減持了手中的股份,淡出互聯網領域。
因此,也有分析人士認為,當時華為涉足互聯網可能更多是出於企業效益、風險規避等方面的考慮,而不是要進軍互聯網和信息服務業,“就是想養幾個效益好的企業留著過冬用。”
從許多VC/PE基金的LP名單中,也可以看到華為的身影。
在國內,華為是國家開發銀行旗下國創母基金的LP。該母基金管理平台下設PE子基金及VC子基金兩大板塊,分別為國創開元股權投資基金及國創元禾創業投資基金。
天眼查數據顯示,這兩家基金共管理著27家子基金,至少參與了23起投資事件。GP名單中不乏國內一些的知名機構,如松禾資本、金沙江創投、啟明創投、北極光創投、紀源資本、紅杉資本中國、弘毅投資、複星等。
進擊的哈勃
過去,華為在投資並購方面呈現出兩大規律,一是以並購國外企業為主,二是不投華為供應鏈企業。
通過並購國外企業進軍海外市場,符合華為一直以來的國際化路線;而不投供應鏈企業,與華為狼性文化及其長年以來的企業危機意識有關。
這一點,任正非此前曾經有過一段話解釋。
2016年,一位華為日本研究所的日籍員工向任正非當面建議,認為非常有必要對日本當地手機螢幕供應商進行投資。而任正非的回答是這樣的:
“我們原則上不對外進行投資,投資就意味著終身要購買她的東西,因為她是我的兒媳婦。我們現在就是見異思遷,今天這個好就買這個,明天那個好就買那個。當然我們也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希望你別落後了。只要你不落後,我就買你的,但你落後了,我就買別人的。我們主要關心所有的產品是世界上最好,而不是我兒媳婦生產的,我來組裝。”
然而,隨著華為旗下全資子公司哈勃投資問世,這個情況有了極大變化。
2019年4月,華為在境內新成立了一家注冊資本達7億元人民幣的子公司哈勃投資。今年1月底,注冊資本變更為17億元。
根據工商信息,哈勃投資的董事長、法人代表均為白熠。白熠自2018年4月起擔任華為企業發展部總裁一職。
成立不到半年,哈勃先是入股思瑞浦成為其第六大股東,隨後又接連出手投資了兩家半導體相關公司。
其中,半導體公司一家為從事第三代半導體材料碳化矽相關的山東天嶽先進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另一家為從事電源管理芯片設計的傑華特微電子(杭州)有限公司,均屬於半導體行業上下遊公司。
此前,華為在半導體產業的布局一直以IC設計業為主,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旗下全資子公司海思半導體。
作為中國半導體產業最重要的下遊客戶,華為的入局對整個產業而言無疑是利好的。而哈勃的多次投資,也被業內認為其意在全面布局半導體產業。
全天候科技根據公開信息統計,在過去一年,哈勃接連出手13家半導體產業鏈企業。

這或許只是哈勃投資版圖的開端。
從業務方向看,其所投企業都以自主研發高新技術為主,高度國產化生產。產品涵蓋半導體晶體、碳化矽材料、功率芯片、人工智能芯片、車載通訊芯片、石墨烯導熱膜等領域。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手機等相關業務的布局,哈勃所投企業中不乏與汽車、人工智能等身影。
過去華為主攻全球供應鏈,在國內半導體企業採購並不多,這與我國產業發展進程有關。在傳統的供應鏈領域,國內企業與國際企業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在一些新興技術領域,如半導體材料、人工智能等方面,國內企業的起點較高。
而在這些新興技術領域,華為和哈勃開始大範圍入局。
在今年年初,華為出資2206萬元拿下了慶虹電子32%的股份;而今年6月份,華為投資的縱慧芯光已進入華為旗艦手機VCSEL供應鏈,是華為Mate 30 Pro中VCSEL的主要供應商。
通過給訂單、給資金、給技術技術,甚至派駐團隊等多種方式,華為正在扶持國內半導體企業。
另一個顯著的案例,則是搭上哈勃投資快車後飛速發展的思瑞浦。
2020年4月,哈勃投資的芯片公司思瑞浦在科創板的上市申請獲得受理,這是哈勃投出的首個進入IPO階段的項目。
實際上,直到2018年,創業六年的思瑞浦仍然深陷生存危機當中。思瑞浦當年披露的財務數據顯示,2018年公司收入1.14億元,淨利潤為-882萬元。
2019年,一名神秘“客戶A”的訂單讓思瑞浦當年的收入增長167%達到3.04億元,淨利潤則達到7098萬元,彌補了創業以來的所有虧損,掃清了上市之路的障礙。

從思瑞浦招股書中可以看到,“客戶A”從2018年開始向思瑞浦採購的產品主要是信號鏈模擬芯片,這是5G基地台的關鍵部件。2019年,思瑞浦來自該客戶的營收佔比激增至57.13%
“客戶A”的具體名字雖沒有披露,但確認是思瑞浦的關聯方。而在思瑞浦的關聯企業名單,惟華為可能有如此大筆的採購。此外,思瑞浦正是華為成立哈勃投資以後出手的第一個企業。
不追求對企業的實際控制,以產業布局為主,也是哈勃投資的特點之一。
據相關統計,目前哈勃對企業主要的投資比例基本小於10%。從介入輪次與投資比例上看,大多數是早期“佔坑”,需要先幫助這些5G相關企業發展完善自己的戰略布局。
這一點,與華為過往針對目標技術、團隊進行投資並購有一定相似之處。對於產業投資而言,收益並不完全體現在投資回報率的數字上。一些隱性和綜合收益也在華為考慮的範疇內。比如對於產業鏈的補強,對於業務的拉動,對於供應鏈的穩定等等。
有分析認為,哈勃投資布局在兼顧現有供應鏈以及前瞻性技術的同時,通過投資補強短板環節,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供應上的壓力,與華為的業務形成互補和協同。
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哈勃投資可能會涉及更多的“前沿領域”,更多產業鏈上的新技術公司可能會進入哈勃投資的視線。
投資戰略轉變將助力破局?
哈勃的橫空出世,意味著華為的投資戰略再次出現重大轉變:由最初國際化擴張投資並購,轉變為圍繞半導體產業鏈進行密集投資布局。
一方面,這是由於美國禁令所造成的外部供應鏈壓力。
2019年5月,受到美國禁令影響,多家企業被禁止與華為進行業務來往,其中包括安卓手機GMS服務供應商谷歌以及眾多芯片產業鏈供應商。
為此,華為啟動了鴻蒙系統、HMS等一眾備胎計劃。最新數據顯示,華為的HMS全球月活用戶超過7億,注冊的開發者已經達到160萬,HMS生態全球排名第三,僅次於安卓和蘋果的iOS。
余承東在8月初的中國信息化百人會2020年峰會透露,搭載鴻蒙系統的華為智能手錶將於今年發布,未來華為IoT產品都有可能搭載鴻蒙系統。
如此看來,在軟體層面,華為的備胎計劃正有條不紊地進行業務過渡;而在硬體領域,半導體產業這個被卡脖子的領域始終是華為繞不過去的坑。
在美國第二輪的芯片製裁之下,華為海思的麒麟芯片無法再交由台積電代工,也無法向高通、博通這類美國公司採購高端芯片。余承東表示,華為今年秋天將會上市搭載麒麟1000芯片的Mate40,可能會是最後一代華為麒麟高端芯片。
“遺憾在半導體制造方面,華為沒有參與重資產投入型的領域、重資金密集型的產業,我們只是做了芯片的設計,沒搞芯片的製造。”余承東表示。
如今看來,哈勃投資作為華為“補洞”計劃的重要一環,正在努力彌補這份遺憾。
另一方面,華為內部業務結構的不斷變化,可能也驅使著華為在投資戰略上作出轉變。

2019年,華為消費者業務收入4673億元,佔總收入的54.4%,同比增長34%,是華為三大收入板塊中增長最快的板塊。這體現了華為從過去的B端運營商驅動型向C端驅動型轉變,而C端的重要特徵就是產品種類眾多。
儘管目前華為消費者業務旗下已經有智能手機、筆電電腦、平板電腦、智能手錶等眾多C端產品,但距離其1+8+N的全場景生態戰略依然有不少距離。
華為需要一場全產業鏈的生態升級去滿足C端業務的持續成長。
為了應對外部挑戰與內部業務發展的雙重挑戰,華為的投資戰略亟需求變。
而在華為外部成立哈勃投資公司,有別於內部機構——其受到華為基本法的約束更少,將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靈活性,在財務運營上也相對方便。
更重要的是,這是華為對外表明的一種態度,即華為願意投入資金與技術,和中國的產業鏈一起成長,從而吸引更多的企業,完善其產業鏈布局。
從目前來看,華為除了利用哈勃進行前述產業鏈投資布局外,還有更多的動作。其中一個重要信號,則是近期與深創投合作成立的紅土善利基金。
據天眼查顯示,8月12日,深圳市紅土善利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成立,經營範圍為股權投資、創業投資,注冊資本6億人民幣。
其中,華為為紅土善利的第二大股東。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認繳1.9億元人民幣,持股31.67%;華為旗下的哈勃投資認繳1000萬元人民幣,持股1.67%。國內最大本土創投機構深創投是該基金管理人。
雖尚未明確紅土善利的投資偏好,但以目前的國際形勢和華為的處境來看,紅土善利基金大概率與半導體產業戰投相關。
如今,華為的投資戰略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
相比起鴻蒙系統、HMS等一眾備胎計劃,投資周期長、成長速度慢的產業鏈布局更能代表華為在應對內外多重挑戰時真正的態度。
但面對大環境的持續動蕩和惡化,華為如何跑贏?所有人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