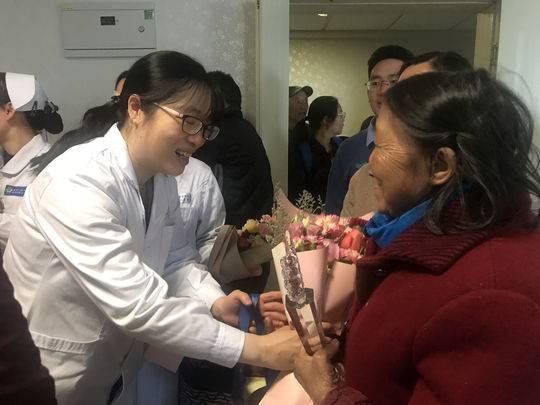今天,是武漢封城兩個月的日子。兩個月以來,武漢900萬人民經歷了人生中最難忘的日子。這些日子將留存在一座城市的記憶之中,永不磨滅。在巨大的災難之中,有一些人,他們沒有被病毒嚇到,沒有因為疫情而退縮,無論是否身在武漢,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給這座城市以關愛,給這座城市中的人們以信心。是他們,陪武漢一起走過。春天已來,解封的日子還會遠嗎?
以下為護士馮佰仟、志願者童亞聖、心理谘詢師劉洋的口述:

我是馮佰仟,今年31歲,吉林延邊人。
我是在湖北荊州上的大學,護理專業畢業後,去了武漢同濟醫院實習,一年半以後轉正,成為了這座城市的一名普通護士。
今年是我工作的第十年,工作內容主要是給腎功能不全的病人做血液透析。武漢同濟醫院血液淨化中心一共配備了2名醫生,1名護士長,7名護士。
今年1月中旬,醫院通知我們中心的一位醫生同時去發熱門診值班,在血液淨化中心和發熱門診兩頭跑。這意味著醫生緊缺,也是我第一次意識到疫情的不同尋常。
我心裡有些怕。畢竟,對自己完全沒把握的未知事物,人總會有些恐懼的情緒。
1月23日(臘月二十九),那位在發熱門診值班的醫生發燒了,人手不夠,需要我立即頂上。考慮到家裡有4歲的女兒,還有兩位老人,為了保證家人的安全,我短時間內是沒法回家了。
朋友勸我說,認識的醫護有直接不幹了、轉行的。
我是不是也該考慮一下辭職?
但我真的做不到。如果每個人都跑,人跑光了該怎麽辦?這是我的底線。
我收拾了貼身衣物和一些厚衣服去醫院了。臨走前我只和媽媽說,可能會在醫院住幾天。
1月27日(年初三)開始,同濟醫院附近的湖北省人民醫院分院被征為專門收發熱病人的醫院,這家醫院的近60名需要血液透析的病患就轉到了我們的血液淨化中心。與此同時,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的1名護士長和6名護士合並過來和我們並肩工作。
從那時開始,我所在的血液淨化中心一共有2名護士長、13名護士。隨後幾天,中心又陸續接受了其他醫院合並過來的病人,我們這個只有20台血液透析機器的小透析室,總共接納了超過160名腎功能不全的病患。

腎髒是人體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一旦沒有按時透析,很可能出現各種嚴重症狀,甚至危及生命。這些透析患者根本離不了醫院。因此,在疫情前期醫療救助團隊還沒有趕到時,就算是人手緊張,我們也只能拚了,沒有休息。
在此期間,血液淨化中心也時不時會有病人發熱。
我不記得這裡第一例發熱病人的具體日期了。隻記得那是個晚上,我們快下班的時間點,一位年過四十的病人匆匆趕來。他來了以後就說自己身體不舒服,我們猜測也許是腎功能的問題導致身體中有積水,有些心衰。
他喘。
雖然平時就有呼吸不正常的症狀,再加上有鼾症,每次血液透析他都需要吸氧才能完成。但是,護士長還是讓他去拍個X光看一下情況。
X光的結果需要等1到2個小時才能出來。我覺得自己好像很緊張,就一直守著電腦等看他的X光。
“護士長你快看,他那個肺上已經有了。”他X光上顯示有白肺。
那時血液淨化中心承擔的只是普通病患的治療,這一百多號病人原本抵抗力就很差,一旦被傳染,後果不堪設想。
另外,如果我們這裡普通患者沒有保住,都轉去新冠定點醫院。定點醫院可能都收不下,也會造成很大的麻煩。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是一場“戰爭”。
大約在1月份的最後兩天,血液淨化中心的護士長倒下了,住進醫院。
2月1日(年初八),護士長讓大家都去做新冠病毒篩查,有幾位醫護人員都中招了。
我自己反而沒有那麽驚慌了。我意識到,這就是我的工作,可能會有高風險,但我比普通人知道的總要多一些。
我還是沒能逃過。集體篩查的兩天后,我發現自己有些不對勁。
2月4日午休時,我睡在拚起來的凳子上,凳子的位置恰好在兩扇相對的通風窗之間。醒來發現,我有些冷、有些頭疼。護士長立刻讓我休息。
洗完熱水澡,我還是覺得冷。
我發燒了,38.8度。
接下來的兩天我的頭昏昏沉沉,還拉肚子。
第三天,燒退了。但我還是去醫院拍了X光、驗了血。為了避免接觸傳染,我自己給自己抽血,手都在抖。醫生問我緊張嗎,我就回頭笑:“我要說不緊張,你信嗎?”
核酸檢測陰性,但肺部和血液檢查結果都有問題,按照之後的標準來看,已經可以確診感染。當時醫療資源特別緊張,我的症狀又比較輕,就自行回到宿舍隔離休息,每天按時吃藥。
直到2月下旬,我都沒有出過宿捨的門。

隔離的日子很漫長。同事們每天都會把飯掛在我的門把手上,等他們走了,我就開門去取。
隔離一個星期後,我有時晚上會感覺胸口像壓了塊石頭,但我沒有太當回事,每天都會喝大量熱水,捏著鼻子喝下有魚腥草味道的中成藥。
慢慢地,我好起來了。
到現在為止,我還不敢告訴爸媽自己的這段患病經歷。我是獨生子女,怕他們擔心。隔離期間,每天晚上和他們視頻時,我都會裝作自己今天工作了一天,很累的樣子。有一天晚上,媽媽問我:“你怎麽和別人的臉不一樣?別的醫護人員因為戴口罩都把自己臉給勒壞了,你怎麽沒有?”
我當時被問得有些蒙,但是馬上回答說:“勒的印子一直都有啊,只是下午休息睡了一會兒就沒啦。”
面對家人的擔心,我會選擇撒個小謊。媽媽總叫我和病人少接觸,遠遠地看著就好。每天視頻都會和我說上一兩個小時。我就回答她:“你放心!我肯定沒事兒!”說這話的時候,心裡好虛。
2月底,我覺得自己完全恢復了, 就加入了拯救危重病人的一線團隊,“護腎小隊”。
這個小隊成立的目的,是用血液淨化的技術來阻斷病人體內由於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炎症風暴,除此之外,還需要收治腎功能不全患者感染病毒後轉成的危重病人。
當時武漢的疫情正值最緊張的時期,危重病人多,很缺醫護人員,在我加入之前,“護腎小隊”已經連續工作了十多天。我就決定既然已經恢復了,那就乾脆上一線吧。
從那時起,我每天早晨七點多會從光谷院區開車去中法新城院區。吃完早飯,我和同事們會戴兩層口罩、戴眼罩,戴帽子把兩隻耳朵都遮住,穿上三層防護服。防護服不透氣,讓人感覺五感缺失,行動不方便,說話聲音也嗡嗡作響,一穿上防護服我就會開始出汗,覺得又累又悶熱。

上午9點30分,我們會過五道門進入汙染區的ICU內,每一道門、每一個緩衝區對我來說似乎都有一種無形的壓力。我的工作是密切關注危重病人的生命體征,隨時記錄儀器運轉情況,關注用藥病人的體溫等。為了保證工作時間,一般到下午4點左右,我才能從ICU出來和同事交接。
雖然一開始會有些壓力,但習慣了以後,我感覺這個流程跟正常上班別無二致。只要防護到位,不暴露,也並沒有什麽問題。
我想心態上接納工作內容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成就感。

我遇到過最年輕的危重病人是44歲,病情非常驚險,但最後經過全力救治,也能化險為夷。他起初是上了ECMO(俗稱“人工肺”),後來又用CRT(心髒再同步治療)搶救,插上呼吸機。好轉後,剛剛脫機的那天,血氧飽和度又突然下降,於是又重新插上了呼吸機、上ECMO、做CRT,緊接著又做了一輪。最後好了,終於搬出了ICU區。
還記得光谷院區ICU有一位86歲的老太太,她第一次做插管和CRT治療是我去處理的。她用了很多藥、用了鎮靜劑,整個人處於昏迷狀態,還帶著呼吸機。連續做了幾次後,又輪到我的班,我發現她已經醒了,雖然身上管子很多,不能開口說話,但和她說話,能夠通過點頭、搖頭來回應。她都已經86歲了,我眼看著那些點滴泵撤下去許多,慢慢好轉的樣子,我就覺得自己沒有白乾。
3月開始,醫療救援隊都陸陸續續就位,“護腎小隊”的人員目前也已經超過30人。我們排開了班後,就有休息時間了。

在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我看到很多醫護人員在防護服上寫下自己喜歡的明星的名字,拍下照片,在微博上@他們。我們病房裡也能經常見到,覺得很解壓。本來我也想寫的,我喜歡朱一龍。但是我想讓別人幫我畫點什麽的時候,她們說:“別為難我了,我不會畫。”

下了班以後,我喜歡去光谷院區逛逛,因為院區裡有個“吉祥物”,是隻小貓咪。我喜歡和它玩一會兒,給它喂水餵食,上下班路上的花兒和貓都挺治愈。
情況慢慢在變好,但我還是會想念我的女兒,她4歲,調皮搗蛋。和她視頻的時候,我對她說,想捏捏她的臉,抱抱她。她問我:“你為什麽不回家呀?你住在哪裡呀?我也好想去住你那裡呀!”
我就回答她:“媽媽在和病毒打仗,等我們把病毒都消滅了,我就可以回家跟你一起住啦!”
我是馮佰仟,忠於職守,守護一座城,我是“武漢分之一”。

我叫童亞聖,湖北天門人,1990年生。
從上大學開始,我就一直待在武漢,乾過很多工作,後來成了一個視頻博主,記錄疫情下的武漢,以及奮戰在一線的醫護人員。
1月23日凌晨,武漢公布了上午10點即將封城的消息。中午,我準備開車去黃石,跟家人匯合後回天門過年。路上有許多警車,很多車輛排隊做體溫檢測。除此之外,還有很多人在雨中步行,都想離開武漢。這種場景特別魔幻,帶給我比較大的心理衝擊,我從沒想過這座城市會突然變得這樣陌生。
那時我才真正意識到,疫情不太妙。我害怕萬一自己攜帶了病毒回家該怎麽辦,於是,我給姐姐打了電話說,不回去了。240公里的路程,我開了一半,就決定返程。
我選擇留守武漢。
回去以後,我打開冰箱,空的。為了回家過年,臨行前,我連最後一個雞蛋都已經吃完了。只剩下幾包泡麵。幸好,我認識的一個租客是賣菜的,我就去問他買了特別多的菜。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獨自一人過大年三十。
原本我打算做兩菜一湯的,但我的粉絲在群裡說:這樣不行,兩菜一湯太簡單,要做八個菜。於是我強行做了包括水果拚盤在內的八個菜。做完以後很累,而且都不怎麽想吃了。直到看春晚時,我都還有一種特別不真實的感覺。

1月30日,我的視頻合作夥伴霍霍來找我,說有個地方需要運送醫療物資。我一秒鐘就答應下來了。
仙桃是整個湖北的醫療物資生產基地,這次的任務是去那裡把2000套防護服運到武漢,分發到四個醫院。因為對接的兩方面都給我們開具了證明和資質,在路上檢疫過關卡時比較順利。
這是封城以後我們第一次出城,也是我離家人最近的一次,湖北天門和仙桃互相挨著。家裡人發消息問我,離這麽近,要不回家來看一下?我說不行,因為現在是特殊時期。
1月31日,我們按照約定開車將物資送達武漢第四醫院。路過發熱門診時看到的那裡站著、坐著二、三十位老人,拿著病例一句話都不說。這場景我至今無法忘記。
到了辦公樓後,我們打電話給對接物資的醫生,進行防護服交接。過程中,我們看見一些穿著防護服、沒穿防護服的人在醫院來回走,垃圾桶裡全是用過的口罩。
過去聽到的疫情可能是一串數字,但是真正目睹這些真實場景的時候,心理衝擊挺大的。這讓我覺得本能地害怕,忍不住開始擔心自己。
但我沒有因為害怕就不做這件事情了。接下來和我們對接物資的醫生,讓我十分受觸動。這是位看起來50歲左右的老醫生,看到我們把物資送來後,他不停地對我們說感謝 ,說我們是好人,幫了大忙,差點兒跪下來。
當時,我們隻送了500件防護服給這個醫院,可見當時醫療物資有多麽匱乏。這樣的場景出現在我們的意料之外,我驚呆了,從沒想過自己能給別人這麽大的幫助,眼淚都有些收不住。
送完防護服後,休息了一天,緊接著我們又繼續開始運送其他的醫療物資,比如酒精。我們開著自己的車,並且聯繫了貨車,對接了江蘇南京送來武漢的12噸酒精,接到酒精後,運送至武漢江夏區疾病防控中心。運送酒精的朋友基本都是90後,當時武漢沒有賓館營業,他們只能住在車裡,我跟霍霍就一起給他們煮了點兒水餃吃。看到他們狼吞虎咽的樣子,我們內心的感激無以言表。他們頂著被隔離14天的壓力,開了800公里的車。
2月5日,我們又從仙桃載著600套防護服送往孝感。孝感當時是除了武漢之外,疫情最嚴重的地區,進入孝感後,我們檢測了十多次體溫,幾乎每五分鐘就要下車登記一次。
在孝感的醫院,我能看到的所有人幾乎都沒穿防護服、沒戴護目鏡。甚至有醫生用膠帶把白大褂的領口黏住,或者多穿兩層手術衣。

我堅持做志願者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種行為能夠影響周圍的人,一起參與到救援行動當中。
我有一個經濟條件不錯的朋友,跟我說也想做點事,可因為父親病重,沒有太多的精力。於是他從國外買了口罩、從仙桃買了酒精,又去超市買了蘋果和牛奶,共計幾十萬元的物資,自己開車送去醫院。
還有坐標在安徽的朋友對我說,他也在當地報名了志願者。
通常,我會把每次運送物資的情況記錄在vlog裡面,粉絲們會在群裡和我互動。
我的一個粉絲是護士,她有一次向我求助,讓我幫她買一雙36碼的女鞋。我問她為什麽要買鞋,她說:“我的鞋已經好幾天沒有乾過了。”
原來她是個近距離接觸重症病患的護士,需要穿著多層防護服,不允許身體的任何部分接觸重症病房的空氣。工作久了,防護服又悶又熱,整個身體就像在水裡泡過一樣。於是除了答應買鞋,我無意中對她說,要不我來記錄你們吧?

從那時起,我就決定用拍視頻的方式記錄他們的工作,一個人包攬了拍攝、採訪、剪輯、文案、配音的所有工作。
有一次拍視頻時,湖北省中醫院的汙染區和半汙染區之間連隔離的簾子都還沒有,從1樓到6樓甚至沒有標準的醫療區域劃分。更多的是在地上畫一條線,這叫心理隔離。
視頻剪輯出來後,我問過護士,這樣的記錄有意義嗎?她回答說,許多護士們看到這個視頻都會流眼淚。
我拍攝的第二個護士,是在父親病重的情況下,仍然選擇來支援一線。她的父親是個既嚴肅又慈愛的人。她念初中時,父親從很遠的地方來接她,三年如一日。
在支援武漢的日子裡,有一天,母親來電話,通知她父親快要不行了。她從醫院開了證明,原本可以回家的,但她最後還是沒有回去,因為害怕把病毒傳給家人。
也有護士會在鏡頭前和我講述一些特殊病患的情況。一名護士照顧過一位80歲的老奶奶,有三個子女。當時奶奶感染病毒時,武漢還沒有封城,她特別希望家裡人能來探望,就算是在窗戶邊打個招呼也可以。她只希望見上一面。
但所有的子女都拒絕了,還騙她說,是因為醫院禁止探視。老奶奶心情壞透了,會在住院時砸東西、拔尿管。護士說她非常理解老奶奶的心情,從來沒有帶負面情緒照顧她。
另一位拍攝對象,可能是全國年齡最小的感染病毒的護士,1997年生。有一天,她突然把自己的微信頭像換成了全黑色。我問她怎麽了,她回答說心情不太好,因為核酸檢測呈陽性。事實上,她是個特別樂觀開朗的小女孩,支援工作時也無所畏懼。
我想,小女孩都不害怕,我又怕什麽呢?做任何事都有風險的,但總有人需要站出來。
我是童亞聖,不畏風險,敢於擔當,我是“武漢分之一”。

我是劉洋,生於1981年,生活在上海。
作為一名電台主持人兼心理谘詢師,新冠疫情發生以來,我接了很多個電話,它們來自全國各地,武漢的最多。每一個電話背後的聲音都是那樣真實。聽著那些悲歡離合的故事,我內心對生命油然而生出一種更深的敬畏感。

3月11日,一個來自武漢的電話讓我震撼。
晚上11點,他打進電話,語速特別快。
這是他在家隔離的第48天。前期,他一直有症狀,多次去醫院做檢測,每次都要排7個小時以上的隊,最終確診。他說有人跑了七、八家醫院,都沒有被收治。
他爸爸是肝癌晚期患者,同時感染了新冠肺炎,早期醫院沒有床位,爸爸就在家裡,每天半夜都會起來,媽媽不眠不休、整夜地陪著爸爸 ,也不怕被感染。
他既心疼又難過。他們家是回族,人死了之後不能火葬,必須土葬,這是傳統。但是,在那種情況下,人去世了必須要火葬。他爸爸非常恐懼,他就說:“爸你放心,萬一有什麽事情,我就把你背回去。我就是死也要把你扛回去,扛進土裡去。”
好在,武漢政府下達了“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的政策,他們陸續得到了有效治療。三口人都已出院,正在家裡慢慢康復。
在自己和父母的求醫過程中,他看到“太多的悲歡離合。”那時,每天都有很多新增病例,他看不到頭,抱怨、憤怒、焦慮,各種負面情緒襲來。
他每天強迫自己消毒,甚至懷疑是否需要吃一些精神類的藥物。
他不敢跟別人傾訴,害怕別人覺得他矯情,因為畢竟他的家人都完好。而武漢有些家庭,可能幾口人都不在了。
他把心裡話一股腦說出來之後,自己平複了一下。
我一直在聽他傾訴,直到他平靜下來。我告訴他,究竟是什麽讓他們一家人過了新冠肺炎這一關?這就是背後的那份愛。他們無形當中啟動了一份偉大的力量,那是愛的力量。
我讓他重新來看待這些事,引導他在心底先跟父母把這份情連起來,把他的愛流動出來給爸爸。開始時他說不出來“爸爸我愛你”,他不習慣這樣的表達。慢慢地,他去體會和感受。然後,他說自己重新連上這份情了,原來可以通過愛的流動來抵達對方的生命。如果沒有疫情,他說自己可能永遠都不會發現有多麽愛家人。
他又擴展開來,家裡人相繼被感染後,他只知道抱怨醫生、社區工作人員,抱怨這個世道為什麽這麽不公平。現在,重新看待這一切,他知道大家都需要這樣來流動愛。他要把他的愛流動給所有的家人、醫護人員、社區工作者,所有他能夠接觸到的人。
他說,整個武漢,真的都太需要流動愛了。
六年前,我成為了一家心理關愛中心的志願者。1月30日,中心成立了一條心理支持熱線。我也是從那天開始接電話的。
我們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留下不同接線員的手機號、微信、固定電話,當求助者打電話來的時候,接線員再把求助者發給當時值班的心理谘詢師志願者。
2月2號,在心理熱線的基礎上,我們又成立了一個生命關愛特別小組。這個小組的志願者主動打電話給求助者、特別是武漢的求助者,提供心理幫助。
我本身就是一個心理谘詢師,又做了多年志願者,當這個全國乃至全球性的公共衛生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希望自己能夠為此做些什麽。雖然我不能衝到前線去,但我可以力所能及地做些有用的事,這一點責無旁貸。
我們心理支持熱線由43位心理谘詢師輪班值守24小時,每一個班是3個小時,有2到3位谘詢師。

我的值班時間一般是上午11點到下午2點,有時也有夜裡,從11點到凌晨2點。這些時間正好錯開我的上班時間。下班到家後,身體上可能會累,但是精神上一點也不疲倦,一旦進入接線狀態,整個人就精力充沛了。
我一般都是在家裡接電話。凌晨值班時,丈夫會在旁邊陪我。他不會刻意做些什麽,就在旁邊忙他自己的事,給我力量。我的女兒也會陪著我,有時候她躺在我腿上睡著了,等到值班結束,我再把她抱回床上。
大部分打來電話的人的情緒都是恐懼和焦慮的。但是每個人恐懼和焦慮的又是不一樣的東西。
一個母親,她的兒子只有3歲,得了白血病,之前經歷了7次化療,25次放療,還需要很多次這樣的治療才能慢慢好起來。但是現在,治療因為疫情原因被耽誤了。她很怕,本來已經好轉了,現在這樣,接下去怎麽辦?
我之前覺得,這個孩子應該是安靜地躺在床上。但是在電話裡,我聽見那個孩子聲音非常洪亮,在旁邊和姐姐打鬧玩耍。
我就問,是這個孩子嗎?她說是的,這孩子特別調皮,他第一次做化療之後蔫了一陣子,後來好像他就適應了,特別調皮,特別活潑,醫生都覺得,這個孩子他真的得了病嗎?
我體會到,這個孩子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要好起來的願望。我也引領這個媽媽跟她的孩子來流動愛,告訴寶貝,媽媽愛你,媽媽相信你,你一定會好起來的。
這個媽媽說,之前那麽長時間她一直都特別焦慮,根本安定不下來,跟我谘詢之後,她感到平靜了。
我們的生命關愛小組主動打到武漢的電話比較多。疫情風暴中心的人,他們的情緒變化有一個曲線。
開始時,一床難求,他們的情緒中有一種絕望感。我們那個時候打電話過去,就是渴望穿過這份絕望,找到背後的那份希望,讓他們可以看到一道光,挺過那段艱難的時間。
等到方艙醫院建好,重症病人住進定點醫院,輕症患者住進方艙醫院,疑似病人進入集中隔離點兒,“應收盡收、應治盡治”,武漢人的情緒慢慢有了變化。
到現在,武漢人的情緒好了很多,我們收集到的求助信息也比之前要少。
還有不止一個求助者,說自己有咳嗽、胸悶等症狀,擔心自己是不是也被感染了。我跟他們溝通下來感覺,他們很多都是受過往經歷的影響。比如有的求助者在他剛剛成年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疫情深深勾連到了他的過往。
我會引導這些求助者,即便是有親人去世了,但愛比死大。
疫情過後,那些失去親人的人們、重症救治過來的患者,可能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來進行心理修複。創傷的經歷,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很艱難的時光,需要危機乾預和哀傷輔導。我很希望他們可以主動尋求各種各樣的機會求助。
很多人會回過頭來看痛苦和失去。實際上,我們要想到,愛比死大。你的家人、朋友,表面上是以後見不到了,但他們的愛都深深地存在你心裡,在你的生命裡。你需要在內心深處把這份情連起來,帶一份愛活出兩個人、三個人、更多人愛的模樣來。這才是失去的真正意義。
我希望告訴所有的人,在這樣一個巨大的風浪中,愛是唯一的救贖指導。
熱線我們會一直開下去。從3月11號開始,我們已經把熱線升級為全球中文服務,向全球華人提供谘詢服務。
我是劉洋,無法相擁,卻離你最近,讓愛流動起來,我是“武漢分之一”。

感謝馮佰仟,感謝童亞聖,感謝劉洋,感謝千千萬萬個在疫情期間幫助過武漢的平凡個體。在你們身上,我們看到了勇敢和擔當,看到了迎難而上的精神,這也是東風Honda的追求。
東風Honda也是“武漢分之一”。謝謝拐子們滴抬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