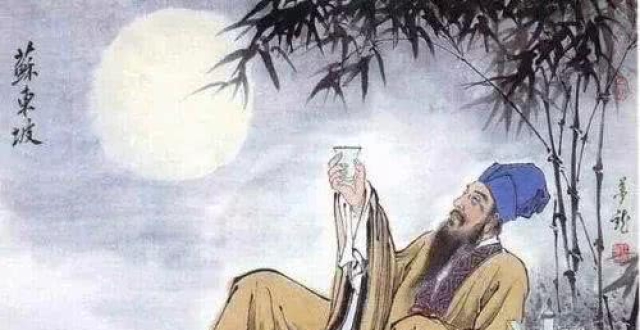北宋立國,既無大唐開疆的強大軍事實力,也談不上赫赫戰功立威,更無澤被四方之德,僅因舊朝擁兵自重,以陳橋兵變而登極。因此,統治者以重文輕武策略來防範武將效法奪權和地方割據。《宋史.紀事本末》載“帝即位,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以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如此,文官地位得以提升。宋承唐製,科舉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進士及第,即可為官,宋宰相十之八九為進士,其它途徑擢升官吏明顯偏少,且前途渺茫。文臣執掌權柄,文藝自然繁榮。同時,宋帝王彪悍雄強者寥寥,皆雅好文藝,更有徽宗耽於藝事而忘國之萬機。

上行下效,文藝、收藏,一時昌盛。由此,宋代精英文化的主要特徵首先是崇文,而非尚武,文士的儒雅、博聞、才學、多思,以及綜合的藝能成為時代崇尚的理想人格,堅貞、坦率,以及對聲色、敏感、浮豔、機巧的拒絕,成為士大夫具有歷史擔當的人文氣質。

歐陽修、范仲淹、王安石、蘇軾等成為文士的典範。不過,文士間的相互傾軋—黨爭也越演越烈,儘管歐陽修以《朋黨論》來對付夏竦等大官僚的攻擊,以此警示,也未能挽救文臣們為迎合帝王專製而分裂成新、舊兩黨的局面’以鞏固皇權之名,黨同伐異,排斥另類。
如此政壇與文場,米芾(一〇五一年生)注定是個異類。祖上為官者皆為武職(五世祖為北宋勳臣),父為襥州左武衛將軍,僅因母(閻氏)侍宣仁皇后藩邸,出入禁中(《東都事略》)。補為殿侍,非科考優勝者,官場生態成就了他的異類品性。同時,他對文事的浸淫與專注,甚至”不軌“,則為文士們所不齒。無論歐陽修還是蘇軾,原道功能是他們一再堅守的的文藝本分。

米芾儘管在藝事方面的成就得到了徽宗認可,但他變態式的專注嚴重背離了文士們的社會責任與藝文擔當,不斷挑戰精英社會容忍的極限,米芾雖沒卷入黨爭,但新、舊兩黨都視之為異物。宋周烽《清波雜誌》雲:”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因此,他被一再貶壓、異化,導致心靈的扭曲、變態’也就不足為奇了。“
執迷與玩世
米芾的不凡家世,內心自有驕縱和高邁的習性,雖非王孫,但錦衣玉食’富貴之神氣溢於言表,可仕途不暢,往往又把他打回現實,醉心藝事卻又被誤為玩世,內心之糾結,行為之矛盾,貫穿了米芾的一生。

米芾唯以書畫名世。對書畫的專擅源自家學,追慕高古,窮究物理,是米芾不同於其他文士的主要方面。米父擅於書畫,精鑒。據米芾《書史》雲:襥州李丞相家多書畫,其孫直秘閣李孝廣收右軍黃麻紙十餘帖,辭一雲白石枕殊佳……後有先君名印,下一印曰”尊德樂道“。今印在余家。先君嘗官襥,與李柬之少師以棋友善,意以弈勝之,余時未生。」
米芾幼承父學,好書畫、精鑒自在情理。米芾《自敘帖》雲“余初學先寫壁顏,七八歲也,字至大一幅,寫簡不成。”也說明其自小學唐人書,但隨著對魏晉書法的迷醉,覺得”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善於鑒藏的米芾,其激越、好極端的秉性已溢於言表。這樣的言語’在宋其他文士中是極為少見的。

當然,米芾的極端和變態行徑,自然成為文士們所不解與品評的焦點。北宋,文臣治國,文人的自信和歷史擔當是前朝所無法比擬的,閑暇之餘,重文玩、好收藏蔚然成風。如此,民間收藏與皇家典藏形成了鮮明對比,各種價值評判與由此產生的人生態度也從器物的收藏中顯露出來,歐陽修、蘇軾、米芾正是三個不同的類型。

歐陽修對變革藝術收藏觀念的最大貢獻在於,他拒絕了受限於偏狹的、以宮廷趣味為準的書法史。他在刻碑銘文中發現了書法之美,並且認為這種美比其「所書」的內容是否符合儒家正統更加重要。但這一議題在蘇軾、王詵和米芾的討論中發生了變化……米芾指出:一旦經過了足夠長的時間,任何功業都會被遺忘,但藝術卻能對抗遺忘,長時間保存。他甚至說藝術品即便有損傷也可以修複——他有點天真地以為時間不會對一件藝術品造成任何損害。(艾朗諾《美的焦慮—北宋士大夫的審美思想與追求》)
由此,米芾的藝術觀為什麽會比同時代人更為激越的原因也就凸顯出來,對藏品的佔有、欣賞角度、摹習深度等問題存在較大分歧。從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中基本可以窺探其收藏的觀點,即不論貴賤,不問出處,強調包容。對魏晉書風的態度更是謹慎,反對唐人對『二王』的神化,他的視野已經從皇家收藏的經典文本擴散到影響書法發展的更為寬泛的民間遺存、從而來調劑勤政之餘的心情,而愉悅功能和高度是如何保持一顆不滯於物、不為物役的素心,佔有是暫時的。

蘇軾雖也認為不可沉迷,以至於玩物喪志,把縱情聲色與耽於名貴字畫之賞玩一起歸納為低級趣味,尤其是對聚斂寶物的卑劣動機是蘇軾所不可接受的,這有違作為士大夫的人格擔當,真正的藝術品是不應該論價買賣的,對佔有器物的心裡一直保持著一種謹慎:米芾則不擇手段,對藏品必須嚴加鑒別真偽,不把精品當成一般的『物件』看待,而是具有超越於『煒煒功業』的恆久價值,對『錦囊玉軸,不惜巧取豪奪。不僅這樣,還對書畫作品進行深入窮究並達到技術上的再現,這又是歐、蘇所不能接受的。
『對面皴石,圓潤突起,至坡峰落筆,與石腳及水中一石相平。下用淡墨,作水相準,乃是一磧,直人水中?,不若世俗所致,直斜落筆。下更無地,又無水勢,如飛空中。使妄評之人,以李成無腳’蓋未見真耳。』(米芾《畫史》)
顯然,他已從愉悅的層面轉為對器物細枝末節的格物窮理、對治國功業的漠然,而斤斤計較於技藝。這種對藏品的細致描述,在宋人的詩文中是很難找到的。因此’從藝術的角度看,米芾對待書畫經典的態度可以看作是,歐、蘇、黃等關於藝術收藏及藝術審美層面的進一步深人。
蘇軾對仿造之作雖有譏評,但對假托之精品也可接受;黃庭堅也不大提倡臨摹刻畫古人,主張『遊目』強調入神,認為臨摹都是以意附會。而米芾必須糾錯窮理,技術手段也就在這火眼金睛中不斷提升,他也不斷仿作,格物致知,鍥而不捨,以至於不惜偷梁換柱,“竊取”他人藏品。混渚“視聽”,在窮理中獲得標榜、自詡的滿足。
尤其是“二王”作品的臨摹,當入神妙。“先臣芾所藏晉唐真跡,無日不展於幾上,手不釋筆臨學之。夜必收於小篋,置枕邊乃睡。”(《寶真齋法書讚.米元章臨右軍四》)這種刻意顯然為廣大士大夫所不齒,也成為自己不斷被同僚彈劾的依據。

米芾也正是從這種近乎歇斯底裡的執著中獲得了技術的高度,成就了米家書風。“劉郎無物可縈心,沉迷蠹縑與斷簡。”(《劉涇新收唐絹本蘭亭作詩詢之》)這正是米芾不同於常人的『怪癖』不過,米芾書畫作假,自有其時代背景。整個宋代,士大夫們為實現致君亮舜而“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進行了禮製改革,徽宗時期還設立『議禮局』。
於是,對古器物的輯錄和考證成為文士們一時之雅事,金石學應運而生,不斷提升的崇古意識,導致發生了規模巨集大的複古運動。古器物學知識與民間工藝相結合,一批仿三代的器物,如青銅器、玉器等,應運而生,書畫的仿作也達到高潮。因此,北宋時期,出現米芾高仿晉人書等仿古現象,是宋皇室與文臣們為合法統治,進行禮製改革的必然。米芾作假雖有偷梁換柱之嫌,但非買賣牟利,只能證明其崇古、人古境界之高,手段之精湛,而非泛泛之輩。

米芾以仿古誑惑世人,對『物』的過度沉迷,不僅是士人們不齒的緣由,由此衍生的古怪行為,即藝術的生活化所導致的行為副產品也成為了人們的笑柄。在米芾看來,經典器物本身的恆久價值勝過人生之功業,是米芾佔有、保護並究其物理的終極目標,凡夫俗子是不可觸碰並佔有的。
即便自己也得時時清洗,一塵不染,如是,方能把玩珍品。而潔癖就是米芾沉迷於『物』的行為表達。陳鵠《耆舊續聞》載有這樣的趣聞:別人拿了他的朝靴,便心生厭惡,不斷洗刷。以至於『損不可穿』。
《詞林記事》載:『米元章盥手用銀方斛瀉水於手,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這種兩手相拍而乾的作派,就是不想沾染身外塵埃,保持獨立而潔淨,這又何嘗不是米芾在魚目混雜的民間收藏大潮中保持獨立的思考和清醒的認識呢?這在常人看來卻已到變態的地步,甚至鬧出更大的笑話。《耆舊續聞》載:“世傳米芾有潔癖,方擇婿,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婿也。」以女妻之。

今天我們去博物館庫房觀看古舊字畫時,戴上手套已是一種職業習慣,而不再成為笑料。如果潔癖是米芾賞玩器物的沉迷所致,那麽,米芾的奇裝異服、拜石等怪誕行徑正是對器物古雅、意趣癡迷崇拜的又一表現《宋史·列傳.文苑六》載:米芾『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所為譎異,時有可傳笑者。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兄。又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
又《何氏語林》載:“元祐間,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者之手,恐為所涴。既坐轎,為頂蓋所礙,遂撤去,露帽而坐。”《拊掌錄》又載:“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靴紺緣。朋從目為卦影。”

米芾的異常行為實則是本真的變現,絕不掩飾而“與世俯仰”,也更非矯情飾行,即便在皇帝老兒處也不收斂。何菹《春渚紀聞》載:宋徽宗召米芾書艮嶽大屏,指禦案間端硯,令就用之。書成,即捧硯跪請雲:‘此硯經臣濡染,不堪複以進。’——宋徽宗無奈,賜之。米芾舞蹈以謝,抱硯而出,余墨沾染袖袍。宋徽宗道:“「顛」名不虛得也。”
米芾特立獨行的異端行為,不僅是耽於藝事的理解方式,也是一種玩世的人生態度,他正是以舍身藝事的抱負而有別於同代士人不滯於物的『道統』觀,直言了“功名不如翰墨”(嶽珂《薛稷夏熱帖讚》)他的執著、癡迷、較真的勁,顯然嚴重背離了士大夫精英階層可以接受、包容的極限,但他最終卻從沉迷於魏晉的複古中找到了解構唐人的密碼。

要知道,米芾《海嶽名言》對古人批評的苛刻程度是歷代書論中少有的,尤其是對待唐人,不是“惡劄”,就是“俗品”,米芾正由於這種較真的態度,不趨時調,從學唐人到反唐人,最終想超越唐人,雲“古人得此等書臨學,安得不臻妙境?獨守唐人筆劄,意格抵弱,豈有此理。”(《武帝帖》)
所以,縱觀米書,唐人影子蹤跡全無,不像蘇、黃、蔡等幾家,總能窺探出一絲魯公的筆意。儘管米芾自詡“一掃‘二王’惡劄,照耀皇宋萬古”(明毛晉輯《海嶽志林》),或“無一點右軍俗氣”(《畫禪室隨筆》)之類的自誇,從米芾大量信劄的面目看,仍是一派‘二王’景象。所以,對於器物的‘古’意,米芾不僅僅是停留在事物表面上,而是從生活的點滴開始,把醉心藝事的把玩生活化了,做到思想和行動的高度統一,而與“二王”的契合中追尋到了自我的真實。米芾不同於寒門子弟,生活在數代為官的家庭中,天然擁有與“二王”心性一致的貴族氣息。米芾自小受其父熏陶,並學過“二王”,以至於癡迷“二王”。

據《韻語陽秋》卷十四載:“元章始學羅遜書,其變出於王子敬。”而羅遜正是羅讓,羅讓書《襄陽學記》最為有名。《襄陽縣志·古跡》載:“襄州《新學記碑》:貞元五年盧群撰,羅讓書……讓書《襄陽學記》最有名。米元章始效其作,後乃超邁如神耳。”
後得蘇軾啟迪(元豐五年,三十一歲的米芾在黃州拜見了蘇軾)“始專學晉人,其書大進”,他以『集古字」為主要的技術手段,留下不少“二王”贗品。如《鴨頭丸》《中秋帖》等,這種高仿是絕無僅有的,這又何嘗不是米芾學書的一種異端行為呢?米芾的作假、“集古字”,是從摹習唐人開始的,進而摹習魏晉風流,不僅導致鑒賞觀念的顛覆性變異,也最終成就了“寶晉齋”之美名,而所謂的穿戴前朝衣服、拜石之類,與書寫的仿古等都是崇古的異端表現,同時也高標了自我的出塵與潔淨當然,從心理學講,米芾行為的怪異也有其隱情。

米家世代官宦,自然養就高貴個性,但在文人治國,強調進士“出身”的文人圈活得鬱悶、無奈。《宋史》載:米芾“以母侍宣仁後藩邸舊恩,補洽光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這都是些小官職和閑差。莊綽《雞肋篇》載:其母“出入禁內,以勞補其子為殿侍。”
楊誠齋《詩話》載:“蓋元章母嘗乳哺宮內”顯然,米芾以皇族的奶媽入仕是事實楊誠齋《詩話》還載一趣事,雲:“潤州大火,唯留李衛公塔、米元章庵。米題雲:‘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庵。’有輕薄子於塔、庵二字上添注‘爺’‘娘’二字。元章見之大罵。輕薄子又於塔、庵下添‘颯’‘糟’二字,改成‘神護衛公爺塔颯,天留米老娘庵糟’”對於米芾的出身,宋人筆記也多詬病,雲:“呂居仁戲呼米芾為米老娘”(《稗販》)
可見,米芾向以為傲的出身,卻為士林所不齒。米芾二十一歲出仕始,一直未有要職,雖有致君堯舜之念想,只能在一而再計程車林嘲笑間無奈而失意地糾結著——特別是元豐八年,據嶽珂《寶真齋法書讚》載,米母過世,米芾一夜頭白,“武林失恃,遂發白齒落,頹然一老翁。”
“失恃”當為母親去世,仕途更為暗淡之意。元符三年(一一〇〇)米芾已老,歎曰:“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一旦死,不得潤色帝業。”一一〇六年,米因書畫出眾得以遷書畫兩院博士,第二年擢七品禮部員外郎。未任前仍遭彈劾,“傾邪險怪,詭詐不情,敢為奇言異行以欺惑愚眾,怪誕之事,天下傳以為笑,人皆目之以顛。士人觀望則效之也,今芾出身冗濁,冒玷茲選,無以訓示四方。”吳曾(《能改齋漫錄記事》)於是,米被逐出,幾個月後死於淮陽軍上。
可見,米芾不得志的內心是苦悶的,“不得潤飾帝業”成為終生之憾。從其行為方式來看,米芾對字畫的專注,顯然也是一種仕途不得意的行為轉向、內心倔強的反常,“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宋史.列傳》)

越不得志,也就越專注於藝事,惡性循環,行為的放縱,對“物”的沉迷,也就不再顧及皇上、同僚及世人的感受了:而從米芾的書畫來看,顯然也有著遊戲筆墨的層面,縱橫感躍然紙上。
黃庭堅雲:“米黻元章在揚州,遊戲翰墨,聲名藉甚,其冠帶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既不偶於俗,遂故為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爾。”(《山谷題跋》)應該說,米芾

行為的異常,既有癡迷古代器物的執著感,也有官場失意的精神消極,兩者互為激發,導致了所謂“米癲”,甚至行為自殘。越是這樣,越是有悖士林精英的精神氣質和人格理想,而米芾越是挑戰精英階層的容忍度,受到的打擊也就更厲害。
因此,米芾內心是矛盾的,真率與飾行、驕縱與自卑的雙重品性在他身上集中體現,甚至出現思維的跳躍性,往往匪夷所思一如對張旭的態度,一方面譏笑為“張顛俗子”,另一方面則大加讚賞,雲:“人愛老張書已顛,我知醉素心通天。筆峰卷起三峽水,墨色染遍萬壑泉。興來颯颯吼風雨,落紙往往翻雲煙,怒蛟狂虺忽驚走,人間一日醉夢覺。使人壯觀不知已,齊筆為山倘無苦。由來精絕自凝神,滿手墨電爭回旋。物外萬態涵無邊,脫身直恐凌飛仙。洗墨成池何足數?不在公孫渾脫舞。”(《智衲草書》)
當然這也有他對待魏晉書法前後深入程度的因素所致這種跳躍性心理特徵,也導致詩文也常有怪誕之意,邏輯性不強,甚至難以理解。莊綽雲:“其作文亦狂怪。嘗作詩雲:‘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實,叩之,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莊綽《雞肋編》卷上)。
對於這種情況,曹寶麟講:“他的文章如《王羲之王略帖跋》,敘事多纏夾不清。這種情況在蘇、黃一類文學家中絕對不會發生。”(《中國書法史》)。相反,這種矛盾心理和異端行為,為世俗的羈絆就越少,“戲筆”、癲狂……行為的放縱、思想的跳躍性,成為書畫自成面目的催生素。無論是米點山水,還是“刷筆”書寫,都是米芾在書畫史上自立風標的典範。
因此,宋孫覿《向太后挽詞》跋雲:“米南宮躓弛不羈之士,喜為崖異卓鷙、驚世駭俗之行,故其書亦類其人,超逸絕塵,不踐陳跡,每出新意於法度之中,而絕出筆墨畦徑之外,真一代之奇跡也。”

可見,米芾精鑒的態度與方式,不僅挑戰著器物收藏的習慣套路,行為的真率與『癲狂』也顛覆了士林的社交習俗。其實,米芾的行為正是在這種文化、官場的生態中保持的一種特立獨行的人生態度的反映,而追慕魏晉書風不僅成其精神上的愉悅,也是解脫人生矛盾與病痛的途徑。

魏晉士人強調率直、任誕、清峻通脫之行為風格,顯現出一種遠離政治、回避現實、無關道德、蔑視俗物、內心澄明、超然物外的精神"從米芾的行為方式來看,這正是米芾所追求的。因為他已把功名比作“臭穢”的場所,“好事心靈自不凡,臭穢功名皆一戲。“?(米芾《題蘇中令家故物薛稷鶴》)
魏晉名士在本質上就是為個性而活著,尤其以“竹林七賢”為最,以此來顛覆當時權貴以“假道學”來謀取私利的行徑。“寧做我”成為生活的時尚,而社會上的聲名、排名是不重要的。米芾自小仰慕晉人書風,故而行為標新立異成為一種可能,這也是米芾行為詭誕的一個重要思想依據魏晉名士以個性化的自我表現,解構漢代士人為官、崇文、尚藝的類型化特徵。
而北宋為官、為藝的類型化特徵是顯而易見的,米芾也正是借獨特標識的古人形象來顛覆北宋士人的一貫風貌。而宋人進士即為官成了一種固化模式,這種類型化仕進特徵是米芾不願接受的,在他看來也是“俗物”,這種僵化的出仕模式正如唐楷中的“法度”一樣刻板,糾纏著米芾的內心,而米芾的個人化行為正說明了這一點,把法度嚴謹的唐楷比作“惡劄”也就見怪不怪了,當然這注定要受到時人的排擠和打壓。
因此,米芾的怪誕行為既是宋人尚意,追慕晉人的一種方式,也是翻越唐人的手段,更是其仕進不暢而采取的一種變態行為,以此來反抗仕進的固化模式。由此’米書筆墨中『墨戲』的成分,不僅僅是米芾沉迷於“物”、執著於“物”的“玩物”表現,也有著更為深刻的思想內涵。

儘管宋人都有“遊戲筆墨”的傾向,但沒有像米芾這樣玩得徹底,玩得純粹,玩得寬泛,什麽玩石、玩戲、玩飾、玩墨……“功名皆一戲,未覺負平生。”(米芾《畫史》)連人生、功名都是玩。由此,米芾的形象也完成了從“玩物”走向了“玩世”的飛躍。
當然,米芾行為的怪誕,諸如筆墨遊戲,功名一戲等,還與佛、道等思想有關,尤其是禪宗理念。宋代文士一般都受禪宗思想影響,如蘇軾、黃庭堅、王安石等,而宋人尚意書風的形成並突破唐人的主因,正是思想的解放,宋人的“臆造”“得意”“盡意”“一戲”等思維模式正是文士們生活失意而參禪後的異動儘管米芾官不大,但每到一處定遊歷僧院,向禪師問道。
從他的名號來看,諸如襄陽漫士、鹿門居士、中嶽外史、海嶽外史、淨明庵主、溪堂、無礙居士等,正說明他受佛、道思想的影響較深,還常與仲宣長老“廣惠道人、惟深禪師等交遊,在杭州寫有著名的《方圓庵記》。

另外,還寫有《僧舍假山》《十八羅漢讚》等不少禪詩,如“眾香國中來,眾香國中去。人欲識去來,去來事如許。天下老和尚,錯人輪回路“。(《臨化偈語》)
應該說,導致米芾的“癲狂”是多方面的,不過是米芾做得更為徹底、更為任性而已。無論是鑒賞,還是詩、書、畫創作,抑或其它如“玩石”等嗜好,都能浸淫其間,旁若無人。是仕途的糾結與人性的扭曲?還是執迷於“物”?還是狂禪式的淫放?可能都有。不過,米書風格的多樣性、豐富性,也正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