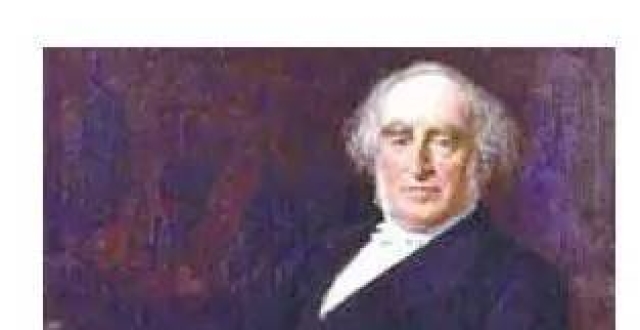關注並在對話框回復“搜索”
許惟一丨記者
雒文佳丨編輯
顧彬
德國著名漢學家,作家,翻譯家
顧彬對於自己身份的評價非常客觀, 他說:“我首先是一位哲學家,其次是一位作家。”而對於翻譯家這個身份,他說這是自己畢生堅持和信仰的事情。顧彬有勇敢的個性。這並非指他敢於以“偏激”的形象示人,而是在於他敢於將他的一切獻給翻譯。
他曾說:
“
一個烈士可能只需要死一次,而一個翻譯家或許每天要死好幾次。
”
對他而言,翻譯是任務,他將最好聽的詞匯給了別的詩人,給了夏宇、羅志成、鄭愁予、歐陽江河、王家新、梁秉鈞、翟永明……
顧彬至今依然定期為《南方周末》的個人專欄供稿,其中大都記錄了他的個人生活、思考和回憶。
他說:“德國最好的作家,也是德國最好的翻譯家。”王家新曾經在評論顧彬時說道:“他寫詩、他翻譯、他從事中國文學和思想研究,他還嘗試用漢語創作散文,就是為了從此岸到達彼岸,從已知到達未知,就是為了生命的更新和自我轉變。”

國際君:有人曾評價你是一個“跨語際的世界公民”, 那麽你是如何看待自己在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的穿梭和探索? 你對於語言的態度又是怎樣的?
顧彬:對我而言,當我到達一個新的國家時,第一件事情就是學習當地的語言。例如,我在波蘭和希臘生活的時候, 都會花一段時間自學當地的語言,從而能夠保證在那裡的日常交流需求;我在法國生活的時候,日常生活中也不會講英語,而是講法語;我在中國生活的時候,也始終將自己作為一名“中國人”看待。
對於翻譯者來講,語言是幫助他們理解和了解文化的重要途徑。通過學習他國的語言、理解當地文化的內涵,有助於形成譯者對於其他文化的認同感。
國際君: 當今世界語言雖然呈現出多元化發展趨勢, 但是依然存在主流與小眾的差異之分, 例如英語依然是世界出版的主導語言, 以至於英美文化也受到大多數人的熟稔和認同。從這一層面上來講,你的“語言觀”是否正在遭受挑戰?
顧彬:英語是目前國際學術的標準語言, 如果一個學者不能夠用英語寫作, 那麽他在國際學術界基本上是“透明”的。
這也是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當一個美國人來到德國,他在所到之處基本上都會說英語, 而並不會問德國人能不能用英語與他對話。
因此,我們能夠經常看到的畫面是, 德國漢學家能夠掌握多門外語, 而美國漢學家一般只會英語和漢語。這也導致了漢學研究“話語權”受到一定限制,即受到英美文化影響的“單一解讀”,而這也並不利於漢學研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開展和進行。
國際君:你曾經將很多中國作家的作品引薦到德國並獲得了成功, 例如北島、楊煉、張棗、梁秉鈞等等。在這一過程中,你曾經提到:“好的譯者需要通過翻譯將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 對此你是如何理解的?

張棗
顧彬:以香港作家梁秉鈞為例,我們是1985年認識的,我從1988年開始翻譯他的作品。從我個人角度而言,他的國語水準並沒有達到很高的水準,他的語言也不一定能夠滿足我對於美學的要求,甚至有的時候我覺得他的中文有些繁冗。但是這些都無礙他成為德語世界知名的中國作家,其中的原因是語言的轉化問題。
就我個人而言,我的中文是中國大陸培養的,因此我對於國語的了解要更加深入。然而,如果我通過國語語法和發音規則的角度去翻譯梁秉鈞的作品,那麽顯然是錯誤的,即使將它們翻譯成最好的德文, 那也是“文不達意”。我也始終認為,作品翻譯不應該是翻譯語言的問題, 而是理解作者思想、並將它以最好的方式表達出來的過程。

梁秉鈞
國際君:從翻譯的角度來看,你認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目前面對的困難有哪些?
顧彬:我覺得目前存在兩方面的問題。首先,從形態意識的角度來講,“走出去”工作應該盡量考慮“國外讀者是誰”的問題,例如女性讀者佔據讀書人群的絕大部分,而考慮她們的實際需求和閱讀喜好,能夠使中國文化傳播更有針對性。
其次,葛浩文、華茲生等世界知名漢學家在英文漢學研究領域享有極高聲譽,而對於不少中國譯者來講,他們目前還是比較依賴這些“漢學家前輩”的翻譯文稿,繼而形成自己的“二次翻譯”。
“借鑒”本身並沒有錯誤,問題的關鍵在於,美國漢學家的翻譯也是基於自身獨特的意識形態,因此“拿來主義”體現的是一種在思想和認知上的“複製性”, 缺乏對於閱聽人國家文化的獨立思考。
另一方面,很多中國譯者在英文使用方面, 還未達到駕輕就熟的地步,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能力。
國際君:你很多次提到“翻譯本質上是一門藝術,也是哲學”,那麽如何理解翻譯與哲學之間存在的聯繫?
顧彬:意識形態問題是當代哲學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而意識形態的不同也是因為我們有不同的個人歷史背景,這與我們的家庭、民族和國家都有著密切關係。
舉個例子,以《論語》中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來講,不同背景的學者對它有不同的理解和翻譯。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角度來講,很多學者將其翻譯成:“如果別人不理解我,我也不生氣,這不也是君子的表現嗎”,“人”被翻譯成為“老百姓”的意思;而在西方學者眼中,“人”則是“貴族”之意。這體現了意識形態的不同會造成翻譯上的差異。

實際上, 翻譯並不存在固定的標準,之所以會存在“主流翻譯”,其原因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存在。而目前的翻譯理論也認為, 翻譯是不存在“對”與“錯”的。
以中國古代經典為例,目前很多作品在翻譯學者眼中都充滿“神秘性”。我們不能將杜甫和曹雪芹重新喚醒,問他們《秋興八首》和《紅樓夢》有何深意。我們只能通過自己對於作品的理解和了解進行翻譯工作,而翻譯本身就是一項開放的工作。
中國有最優秀的翻譯學者,而我也會經常與他們會面,探討有關翻譯的問題,這種交流本身就是一種意見上的交換。從哲學上來講,人的生命有限,無法得到終極智慧,那麽就讓我們去探索有生之年可以得到的一切吧。
國際君:你對於中國作家語言習慣上的“激進”評價,也曾經受到過很多質疑。對你來講,會覺得不公平嗎?
顧彬:目前,少數中國作家確實在文學語言運用方面存在較大問題。我需要做的不是將他們的文字“直譯”,而是試圖理解和了解他們想要表達的意思,從而形成優美無誤的德文。
這種“重新創作”也是我對於翻譯本身的一項標準。最新的翻譯理論指出,翻譯者也越來越扮演著作者的角色。
文學作品在本土化的過程中,可能面臨著多方面的挑戰,例如某些國家的出版社會要求作品需要以喜劇形式收尾,或者根據本國民眾的接受程度作出一些調整。而這些工作在很多情況下都落在了翻譯者的肩上,因此翻譯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作者”。

國際君:王家新曾評價你為一個“嚴肅而又徹底的思想家”, 你如何看待這種評價?
顧彬:目前我對於翻譯的標準是,只要理解上符合邏輯標準,那麽它就是合適的翻譯。然而,目前由於社會及個人等多方面原因,很多學者不願意將自己真實的翻譯研究成果出版發表。
對我自己而言,我認為翻譯是一種服務,包括對於作者和讀者的服務。在這一過程中,我能夠提高我的母語水準,拓展我的思想範圍,修正我的世界觀。
翻譯工作對我來講,是一種責任,我覺得自己有必要一直從事這項工作,就像我長期在《南方周末》上發表專欄文章一樣。
同時,我也希望更多的譯者能夠勇敢地說出他們的觀點,這對於翻譯工作本身就是一種促進和共同提高。
國際君:中德文化交流目前存在哪些機遇和挑戰?
顧彬:隨著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持續推進和對於文化翻譯工作的日益重視,中國文化在世界範圍內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北京外國語大學目前有超過100個語種的專業, 這在其他國家是不敢想象的。但是就翻譯理論知識建設而言,中國高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德國是翻譯的民族,每年全國將近70%的圖書都是翻譯版本, 德國也相當重視中文翻譯工作。就德國波恩大學來講,目前關於中國文化方面的專業在整個學校中排名第一,德國的漢學家人數也非常可觀。我也始終將介紹中國當代文學作為我畢生的任務。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