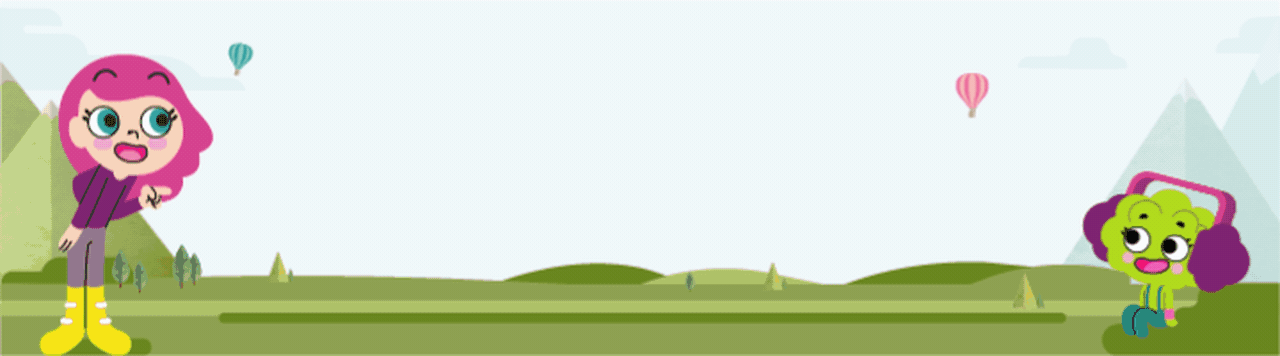開欄語
紀念改革開放暨恢復高考40年——院士憶高考
這兩天,正值2018年度大專院校招生考試期間。這一年一度為國家選拔和培養優秀備份人才的大事,涉及萬千學子,也牽動著整個社會。
當有家長老師送考、交警愛心護行的時候,這些懷揣夢想、充滿自信的“00後”或許根本想不到,在40多年前,能有機會走進高招考場卻是遙不可及的奢望。
正是震動世界、重塑中華的“改革開放”之舟起航,“恢復高考”號角吹響,為黨中央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為無數莘莘學子燃起了“進入大學深造、學成報效國家”的希望之光。
為紀念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本報與湖南大學黨委宣傳部、湖南大學出版社聯合推出“紀念改革開放暨恢復高考40年——院士憶高考”專題系列報導,特約請在1977年和1978年參加高考、1978年進入大學的數十位兩院院士發表署名文章,旨在讓行進在求學路上的青年學生熟悉國家歷史,學習前輩經驗,把個人遠大理想與國家前途命運結合起來,把自己的奮鬥目標與公民的社會責任連在一起,砥礪前行,不忘初心。
陳政清
1977年12月參加高考,1978年進入湖南大學力學專業學習。現為湖南大學土木工程學院教授,湖南大學風工程試驗研究中心主任。在柔性橋梁非線性設計理論和抗風理論與應用研究、結構減振技術領域取得一系列創新成果,曾先後3次獲國家科技進步獎。2015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改革開放40年了,我們這個曾經是“一窮二白”的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舉國上下充滿活力,各項事業欣欣向榮。
每當看到如今的年輕學子為實現自己的夢想,朝氣蓬勃,勤奮學習,刻苦鑽研,學業有成,常常無比欣慰:他們趕上了國運昌盛、民族興旺的好時代。
回想自己40多年前,當一名科學家的夢想就像天方夜譚,曾是那樣的遙不可及。恢復高考,如一聲驚雷,點燃了我們那一代年輕人實現夢想的激情。
我的高考遲到了11年
1966年7月我高中畢業,從那年算起,到1977年10月國內各大媒體發布恢復高考的消息,經過了正值青春年華卻近乎漫長而又無奈的11年。
我1947年在湖南省湘潭市出生,善良的父母與和睦的家庭給了子女們良好教育和個人修養氛圍。從小我向往當一名科學家或工程師,他們不僅學有所成,而且能造福人類。
然而,像那個時代的絕大多數青年一樣,當一名科學家的夢想突然成了泡影——1966年6月13日,我在湘潭市一中高中畢業,正複習備考,可中央決定高考推遲半年進行,而後就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全國所有的大中小學停課、停招。
我們這一批滿懷信心準備高考的學生都傻了眼,但除了無奈,還是無奈。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不是我們能左右得了的國家“大事”。歷史似乎跟我們開了一個很大的玩笑,許多人因此改寫了人生。
“文革運動”折騰兩年多之後,1968年12月,一紙通知,全體老三屆學生都下放農村,成了“知識青年”。我被下放到嶽陽市的錢糧湖農場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那是一段漫長、難熬的日子,知青們大都經歷了迷茫、失望與生活的艱難,我下放的嶽陽錢糧湖農場,屬於國營農場,經濟待遇比插隊落戶的知青好一點,但自然環境極其惡劣。我下鄉一年後就得了急性血吸蟲病。
1970年,毛主席批示,“大學還是要辦的”。國家試點首次從工農兵中推薦大學生,但採用推薦製,與我無緣。
1973年,“復出”的鄧小平主抓教育,提出“推薦與考試相結合”,我似乎又看到了一線曙光,參加了考試和體檢,但被告知“有血吸蟲病”,失去了推薦資格。當年又出了一個“白卷英雄”張鐵生事件,試行一年的考試制度又被取消,我的大學夢徹底破滅了。
1974年底,我結了婚,妻子是一同下鄉的知青,1976年我當了父親。那一年的10月,“四人幫”倒台了。
沒想到就在孩子出生的第二年,1977年的10月21號,國家正式宣布恢復高考。這個特大喜訊激活了數百萬知識青年荒蕪的心田。還算幸運,我提前20天得知了這個消息。
40多年過去了,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那一幕。十年來從未到過我工作的農場的母親,趕了一天的路,從湘潭老家來了。
當時我已在總場中學任教,看到母親的身影出現在教室外時,第一反應是家裡出大事了!
果然是大事,母親鄭重又堅信無疑地告訴我,“國家準備恢復高考了!”消息是來自我在湖南大學任教的大姐。
儘管消息來源可靠,我仍將信將疑,11年來多次失望,我早已沒有信心了。母親這次來的使命就是將我一歲半的小孩帶回老家撫養,讓我專心複習。
整整11年,終於等到了高考!多年後,我們這批“老三屆”相聚時談起這一幕,有人還引用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中的“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詩句,表達當時無法用自己的語言來描述的激動心情。
考了全地區數學第一
與很多荒廢了學習的考生相比,我算得上是天性愛知識的人。因為一是我畢業於省重點高中,學習基礎扎實;二是我下鄉後無論是參加勞動,還是任教,也從未放棄過學習。
一路走來,環境在變,年齡在變,唯一不變的是自己對自然科學的興趣。無論有條件還是沒有條件,我都堅持看書學習。
農村夏天蚊子多,我穿上長筒膠鞋看書,曾被當作笑話在“知青”中流傳。從大的歷史背景下看,我算不上遭遇什麽坎坷,只是走了一段曲折又漫長的路而已。
1971年春,我被“選拔”到農場的七分場中學當初中教師,1973年9月又提拔為總場中學高中教師。由於老師少,學校哪門課缺老師就安排我教哪門。高中的數學、物理、化學等課程我都教過。
就這樣,我利用教書的機會,閱讀了大量書籍,不僅自學完了大學的高等數學、無線電基礎等課程,連每天必讀的馬克思主義,我也能講得出一兩個道道。我經常自我調侃,“‘文革’十年,我是讀了一個文科大專”。
因此,經過這麽多年的知識儲備,我自信高考絕對沒問題。
終於有機會去實現讀大學的夢想了,1977年11月填報志願,我在報名表上鄭重地填下“複旦大學應用數學專業”和“湖南大學半導體專業”。

陳政清的高中畢業證書
之後,我就一邊當著高考補習班的老師,一邊作高考前的自我複習。一個多月後的冬天,我和我教過的學生一起走進了高考的考場。
那年高考語文題的難度,實在連今天的初中都不如。記得很清楚,第一道題是把一句拚音寫成漢字,就是《毛主席語錄》中的一句話:“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作文題是《心中有話向黨說》。可是有的人除了寫“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外,就寫不出更多的話來,可見“文革運動”真是革了文化的命,很多人沒能好好讀書。
那年的數學試卷中有一道幾何題,我任教多年,偏偏沒教過幾何,有些生疏,最後是用解析幾何的方法做出來的,算是有驚無險。數學附加題是一道高等數學基礎題,我自學過高等數學,很容易就做出來了。
成績出來後,大家都知道那個農場老師的數學成績考了嶽陽地區第一名,我自己也沒想到。
記得考完數學後,考場上的人一場比一場少。高考停了這麽多年,誰都不知道高考怎麽回事,很多人根本沒來得及複習,多數抱著這樣的心理:今年先試一下,不行明年再考。
終於,我等來了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錄取“湖南大學力學專業”。整個農場都傳開了,不少人來道賀,但是我有些悻然:為什麽數學考第一,複旦沒有錄取我?為什麽湖南大學沒有把我錄取到半導體專業?
後來,從各個管道知道,當時認為年紀大的考生今後發展潛力不大,錄取偏嚴。加之我眼睛體檢“色弱”,所以被錄到了力學系。
儘管不是夢想的專業,但年齡不允許我再有選擇的機會,從此開始了我與湖大40年的緣分。
贏回時間才能實現夢想
1978年3月入校時我已經30歲了,是全班年齡最大的同學,還是一個兩歲孩子的父親。
跨入大學校門,面對年齡比我小許多的同學,我也曾常常感歎,惋惜流逝的時光。但那曾經遙不可及的科學家夢想卻逼著我和時間賽跑,咬著牙也要把時間贏回來!
進到大學課堂,大家都十分珍惜這遲來的學習機會,當時感到時不我待的不止我一個人,而是歷經艱辛終於得以改變命運的這一代人。
高考恢復改變了以往許多人聽天由命的觀念,大家都覺得有了盼頭,也有了奮鬥的目標,知道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處境,所以都如饑似渴地學習著各種知識。
當時學習上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學英語。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幾乎沒有學校開設英語課程,大學都是從零開始。回憶起來,當時的湖南大學學英語有三個之“最”。
一是每晚8點半開始“最安靜”。由於改革開放了,收聽“美國之音”英語會話節目不再是違禁,其中的《英語900句》就成了那個資料匱乏的時代,大學生學英語的寶典。
每晚8點半,整棟樓可以聽到各式收音機發出的歡快開場音樂《音樂瞬間》,緊接著就是“歡迎各位收聽由何麗達主持播講的《英語900句》”。節目的那段時間裡,整棟樓除了廣播,聽不到別的聲音,連走廊裡也看不到有人。
二是每周日晚電影場有五分鐘“最熱鬧”。當時大學生們周末唯一的樂趣就是看電影。大操場上架一個高大的電影幕布,大家搬個凳子,買張一毛錢的電影票。
那時只有一台放映機,一場電影至少要換一次膠片,換片時間有五分鐘。每到換片時,大家趕緊拿出英語書讀,整個操場一片英語朗讀聲,那場景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甚為壯觀!
三是每天排隊打飯時“最長龍”。當時糧食定量,飯菜票分開,食堂買飯速度很慢,每個視窗都要排長隊。於是在湖大的學生食堂,每天都可以看到一手拿著便當,一手拿英語書的排隊“長龍”。
比起其他的同學,我學英語除了年齡大,還有一種特別的困難。因為有神經性耳聾,高音頻的音標聽不太清楚,第一堂英語課幾乎沒有聽懂教授的一句話,當時非常恐慌。
為此,只好咬牙花“巨資”買了一個小收音機,連睡覺都戴著耳機聽,一個星期後才開始聽懂課。英語書不離手更是標準配置,每晚10點熄燈後在路燈下看半小時,每天早上6點起床晨讀一小時。四年堅持下來,學習英語不再是難題。
隨著時間推移和學習的深入,對力學專業也越來越喜愛了,開始領略到力學科學的無窮奧妙。
在湖南大學的7年期間,師從當時被譽為國內塑性力學“三巨頭”之一的熊祝華教授和結構力學的王磊教授,相繼獲得學士、碩士學位。那時研究生像大熊貓一樣珍貴,我也沒有忙於去找工作和賺錢。
到1984年,又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學固體力學的博士研究生,師從清華大學杜慶華教授(後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和嵇醒教授。
等到博士畢業時,我已經40歲了,卻還想繼續學習。1991年,英國有一個面向中國政府的專項資助項目,我順利地通過了由英方組織的考試,獲得英國文化委員會獎學金。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學習期間,學習到了結構抗風與減振的最前沿科研成果。從1977年算起,用了15年時間完成了一個現代科學技術工作者必需的教育與訓練。
因為40年前的那次高考,自己有幸進入湖南大學學習,真正得到了最好的教育機會,兒時的夢想,終於在“而立”之年揚起了風帆。
當時在講台上授課的都是非常有名的老師。如熊祝華教授,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但師生感情非常親近。30多年過後,我去看望他,聽說我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時,已經90歲的熊老師竟然激動得流下了眼淚,依然像當年教學時一樣勉勵我。
這一切都令人難忘!
(曾歡歡、李妍蓉整理)
《中國科學報》(2018-06-08 第1版 要聞,《40年前,我的夢想終於揚起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