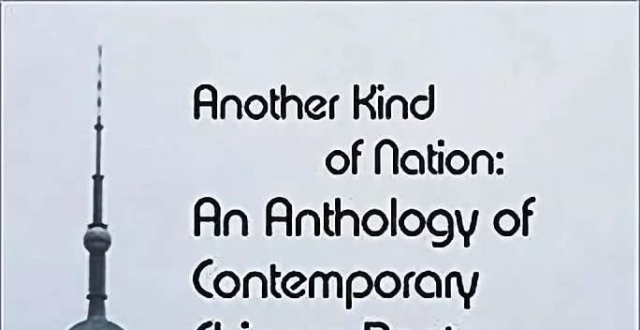澎湃新聞記者從許淵衝先生友人處獲悉,我國翻譯界泰鬥、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許淵衝先生6月17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2021年4月18日,著名翻譯家許淵衝先生年滿100歲。澎湃新聞曾為此發文。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這個歲數被稱作“期頤之年”,意思是真正到了頤養天年,一切需期待別人供養或照顧的時候。可這話放在許老身上卻不大合適——三年前,夫人照君過世後,他的生活起居雖然都有保姆照料,卻依舊保持著每天翻譯寫作到凌晨三四點鍾,次日上午十點又雷打不動起床繼續工作的節奏。
四月間,他的新書《許淵衝百歲自述》由華文出版社推出。托福出版人俞曉群先生和草鷺文化劉裕女士的介紹,澎湃新聞記者在3月底登門拜訪了這位百歲老人。

許淵衝先生的家,位於北京大學暢春園教工宿舍住宅區。說起來,“暢春園”三個字還是康熙帝命名的,取自《易經》“乾元統天,則四德歸之,四時皆春”,寓意“六氣通達”、“順天而治”。住宅區的質樸無華,同昔年皇家園林的規製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供給皇室休憩養生之所,而今同一區域辟出一方地讓德高望重的老教工們安享晚年。尤其是,從這裡到北大西門不足一公里,往返完全可以安步當車,倒是讓人不免有一番古今交感的感慨。

春和景明的日子,走進寧靜祥和的小區,先就看到路口一株臘梅抽枝發芽,顯得滿園生機勃勃。小區內沒有新樓,五層的紅磚樓房一望即知是上個世紀80年代的產物。許淵衝的居所在小區五號樓。2019年時,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出資為這裡的老樓加裝了電梯,免去老師們上下爬樓的辛苦。

《許淵衝百歲自述》有則推薦語。俞敏洪寫道,“許淵衝教授是我們大四的翻譯老師,其上課風格和激情,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我們當年最喜歡的老師之一。我們全班(80年入學北大英語專業)20周年聚會的時候,請了許老師來參加。當時他已經80歲,依然侃侃而談、氣勢恢宏,能夠把我們班大部分同學的名字叫出來。”學生的情誼自然要領,可在點評那屆所帶的學生時,老師依舊顯示出自己的耿介,“(俞敏洪)還不是最出色的了,王強都比他強。”
進到許老家中,他剛剛起床,身著一件厚厚的寶藍色毛巾布睡衣,兀自伸胳膊抬腿做著晨操。回首往昔,1938年秋,許淵衝以第七名的成績考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這套徒手操是他當年在昆明讀書時,體育老師馬約翰根據國人的體質情況和特點編寫制定的。如果說喜好凌晨工作,夜間睡眠不足八小時,嗜好吃甜等生活習慣都是人類健康長壽的“天敵”。許淵衝對運動的貴在堅持——常年堅持游泳,96歲時還能獨自騎車出門,以及日日不輟,練了八十餘載的晨操,當是他延年益壽的“法門”之一。

96歲時騎自行車摔了一跤後,雖然康復良好,並不需要坐輪椅,室內行走終究離不開左、右手各擎著的拐杖。聊天時,他說自己現在喜歡坐著保姆的小摩托出門,“我不喜歡坐汽車,沒意思。坐motorcycle,還能下來運動運動。”無需別人攙扶,許淵衝顫顫巍巍地走到盥洗台漱口。在等待保姆小芳準備一天的早餐前,他自己淘洗熱毛巾,焐在臉上醒神兒。洗漱完畢,又不知從哪裡摸出一把木梳,一絲不苟地打理起頭髮。不由得讓人想起夫人照君曾對夫君的評價,“許先生很愛美的,一生都在追求美,唯美主義。”

早餐有一碗熱牛奶,盛在白瓷碗中。許淵衝習慣用湯杓舀進雀巢咖啡杯,舀上幾杓後,再捏起杯耳小口啜飲。喝完牛奶,他拿起刀叉,緩慢而嫻熟地分食一塊奶油夾心蛋糕。看得出這些動作早已化入肌肉記憶,整個過程他幾乎都眯縫著眼,感到身前有人走動,才會偶爾撩起眼皮。小芳告訴我們,除了普洱茶,老人什麽茶都喝。咖啡原來也喝,近幾年才戒掉。他一天隻吃兩頓正餐,早餐定時定量,第二頓飯則要依據午後何時結束工作而定。有時晚上工作得太晚,也會吃點夜宵。

趁著吃早餐的當口,環視他的家。衣帽就掛在進門處門後的牆壁上,家什擺放略顯雜亂,卻打掃得乾乾淨淨,看不到幾天前被滿城風沙洗禮後的浮塵。70平米的房間還是水泥地面,嚴格來講算不上三室一廳。朝北的一間屋子被用作許淵衝的書房。書桌上擺著台式機和鍵盤,一疊《中國翻譯》期刊堆放在旁邊。放大鏡壓在一本早已翻爛的《新華字典》上,除了黑色、紅色的簽字筆,一把刀柄上刻著維納斯的拆信刀顯示出房間主人的老派。

朝南的兩間屋子,是夫婦兩人各自的臥室。前者基本保持逝者生前的樣子,床鋪的枕頭上甚至還套了層塑料薄膜。許淵衝那幅自況的對子,“自豪使人進步,自卑使人落後”掛在窗戶兩側的牆壁上。這間臥室的書架上,擺放的多是老兩口的合影以及家人合影。尤為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許淵衝獲得“北極光”傑出文學翻譯獎,是首位獲此殊榮的亞洲翻譯家,證書就放在這間屋子的書架上。

電視機放在許淵衝的臥室。書桌上方懸掛一幅書法,大有來頭,“譯古今詩詞,翻世界名著,創三美理論,飲彤霞曉露。”書架上擺放的多是他和友人的照片,兩張黑白照片被放置在白色的木質相框中,一張攝於1949年的巴黎,西南聯大的校友在香榭麗舍大街的餐館設宴歡迎清華校長梅貽琦(左二),左四為許淵衝。對於梅貽琦校長,許淵衝向來敬重。採訪中,他回憶說1942在西南聯大畢業前,出演德克的英語劇《鞋匠的節日》,“當時我是男主角,梅校長的女兒梅祖彬演我在戲裡的夫人。我演的是鞋匠,追求一位女店員(梅祖彬飾演)。梅祖彬身高一米七四,是西南聯大個子最高的女生。一開始她還不想和我配戲,結果我和她比,我的身高是一米七五,正好比她高一厘米。”老人哈哈大笑。

坐在臥室米色的皮沙發上,許淵衝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和拍攝。由於耳背,你必須靠過去大聲說話,他才聽得見。而同大多數老人一樣,他的回答有時並不限於提問本身,而是陷入對往日時光的回憶中。曾有報導稱許淵衝會在談話過程中“睡著了”,在近一個小時的晤面中,老人精神矍鑠,談興頗濃。末了,請他在《許淵衝英譯毛澤東詩詞》上簽名,題寫日期時他原本遵照日/月/年的英式排序,卻把29號記錯成了30號,於是將錯就錯改為中式排序“2021,03,29.”“花體字”簽罷,許淵衝得意地笑了。本次採訪以受訪者本人口述形式呈現。

【口述】
“這是我能做到今天的妙法”

在西南聯大的時候,馬約翰規定頭兩年體育是必修課,後兩年松一點。他強調(鍛煉身體)是經常性的,每天早上都要做早操。課間操不是太嚴格,也有許多人(自覺)做。因為西南聯大正處於抗日戰爭時期,還是要注意學生的體魄。後來,我們全部入伍了,我是第一批參加了陳納德的“飛虎隊”做翻譯官,重視體育其實和這個(入伍抗日)也有關係。一二年級每次體育課上,我們都要先跑八百米,要在規定時間內達標的。我能活到一百歲,和注意身體鍛煉不能說沒有關係。從不到十八歲考入西南聯大,一直到現在,83年了(一直堅持不輟)。

我現在每天起來做早操,不是完全按照當年的動作(要求)。馬約翰當時的規定是針對年輕人的體質,運動量現在不一樣了,而且馬約翰對於體育的認識也是發展變化,不是一成不變的。我現在做操也是結合身體具體情況,需要多運動的地方(指手臂)就多做,做不了的(動作)就不做了,總的來說還是根據當年學的那套。


英國詩人托馬斯·摩爾有句話,“延長生命最好的方法,是從夜裡偷幾個小時的時間。”這是我能做到今天的妙法啊!我現在是累了就睡,能夠做就盡量做。今天凌晨四點才把工作做完,你們看到了,我起來要花一個多小時(鍛煉、洗漱、吃飯)然後才開始工作,但我做事還是不錯的,頭腦還很清楚。馬約翰活了七八十歲,我活到一百歲了。生活有恆,活得很有規律。
“沒有完美的文學,也沒有完美的人生”
說老實話,沒有完美的文學,也沒有完美的人生。翻到《暴風雨》,400年前的東西,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就太多了。翻到一半,我現在暫時停了,最近在翻譯現代的東西——二十世紀的太新了,我不翻。莎士比亞是十六世紀的,我接著翻十七世紀John Donne(鄧約翰),之後是Wilde(王爾德)的,現在是十九世紀末的 Henry James(亨利·詹姆士) 。這個翻譯完,接下來就看情況,但不翻譯最現代的,這類留給年輕人去翻譯。

我能有今天的成就,是要靠表叔(翻譯家熊式一)。他有兩出英譯劇目最有名,《牡丹亭》和《王寶釧》。在英國演出時,英國女王都來看,蕭伯納都誇獎他翻譯得好。我當年讀書時,父親就跟我說,你能達到他(表叔)的成就就不得了了,但現在我的成就早已超過他了。我和他最大的差別是,他翻譯的是散文,我翻譯的是詩歌,(翻譯)詩歌比散文難多了。他翻譯過的,我如果再去翻,就要超過他,不超過他再去翻有什麽意思呢?

《西廂記》中有一句最著名的‘露滴牡丹開’,這句話別有深意。表叔譯的是,“露水滴下來牡丹盛開”。後來我譯《西廂記》,認為露水代表張生,牡丹代表的是崔鶯鶯,這一句描繪的是他們美好的愛情,是在寫男女之事,有這個意象但不能明說,又要人能理解到這層意思。我的譯本就譯成,“The dew drop drips/The peony sips with open lips.” drips、lips還押著韻,翻得簡直絕了!現在我敢吹這個牛,後人要超過我也很難、很難。
這次新冠疫情,我看新聞看報紙(都知道了)。你們拿來我這本《許淵衝英譯毛澤東詩詞》,裡面有毛主席當年寫的一首詩《送瘟神》。毛主席寫詩很文雅,說的很客氣,而且他寫詩往往既寫悲,又寫歡。悲呢,是好像站在瘟神的立場上為他著想,問他要去往哪裡“借問瘟君欲何往?”我翻譯成,“May we ask the Plague God whither he would take flight?”但其實是巴不得他早早地滾蛋,“Burn paper boats with tapers to light his skyward way! ”所以翻譯毛主席的詩詞不能簡單按字句翻,好像是送別他(瘟神),實際上是歡慶人間的勝利。要用悲歡的筆調,來翻譯這首詩。
“怕過生日,想說些親近的話”
我一向不大過生日的,生日基本上沒有印象。十歲生日是在家裡過的,同大人吃飯加了個菜,就是這樣而已。二十歲的生日是在聯大,那時在打仗,可能根本就沒有過生日。三十歲生日是在巴黎過的,四個老同學打橋牌吃個飯。四十歲時,我已經回國了,大概是沒有過過(生日)。五十歲下放,心裡記得(生日)日子,但不敢過。回國的後頭二十多年,我隻出了四本書,已經不得了了。

六十歲生日,那時還沒回到北京,但心情是好轉了。七十歲生日好像也沒有過,我到了北大,我是個新人啊(笑),當時我和太太還有親戚去青龍峽(位於北京懷柔)玩。八十歲生日也沒有印象了。九十歲時,清華大學約了三位90歲老人一起過生日,有王希季(1921年生,“兩彈一星”元勳之一)、何兆武(1921年生,歷史學家),還有楊振寧、翁帆夫婦等,大家一起吃了個飯。

一百歲生日怎麽過?我給你講,我是怕過(生日)了。已經有三批人來了,他們也在商量怎麽分開(批次)給我過生日。(搞得)那麽隆重,四面八方、國外內國內的都來,我真不知道怎麽辦了。那麽遠來,我不好意思啊。我希望大家平常沒事來聊聊就好,不要集中的人太多,我也不好說話。每個人都不一樣,我的話要(針對)每人都合適也挺難,我倒希望說些親近的話,可以照顧到每個人,一個一個去談,就不會說那些一般般的話。我不想去養老院,怎麽呆得住啊?我願意和年輕人在一起,只要是談業務有關的,我的經驗畢竟也有一百年了,和年輕人談得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