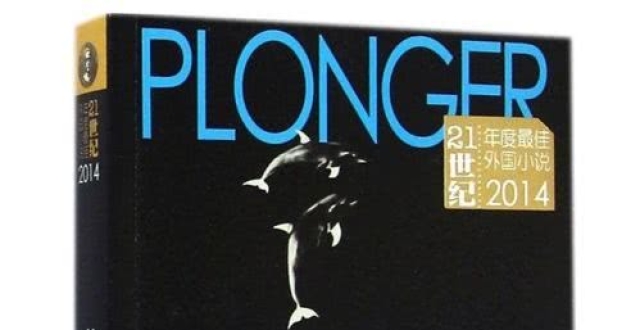作家小白的中篇小說《封鎖》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著名文學評論家、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平,是最早向讀者推介《封鎖》的學者,現代快報讀品周刊特邀何平對話獲獎作家小白,來談談《封鎖》背後的故事。

小白
上海市作家協會專業作家。作品包括隨筆集《好色的哈姆雷特》《表演與偷窺》,長篇小說《局點》《租界》,中篇小說《特工許向璧》《封鎖》等。

何平
著名文學評論家、南京師范大學教授。
__1
何平:兩年前初讀《封鎖》是參加《收獲》文學排行榜,當時我對這篇小說給了很高的評價,所以這次《封鎖》獲得魯迅文學獎,我覺得我們應該注意到魯迅文學獎趣味和文學邊界的微妙變化。
小白:是啊,謝謝何平老師從一開始就喜歡、而且點評了這小說。也要感謝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的各位評委,他們都是前輩、老師和行家,對於一部小說來說,都是難得的“專業讀者”,得到他們的共鳴和肯定,對作者絕對是一種莫大快樂。文學無論作為一種藝術,或者作為一種社會機制,總是不斷在變化中。我們作為文學從業人員,確實需要跟隨時代步伐,不斷觀察、學習和調整。
何平:小說的標題,相信有現代文學閱讀經驗的人都會想到張愛玲的同名小說。似乎兩篇小說“尷尬”地撞題,但看你已發表的小說,標題都取得有些“隨心所欲”,你似乎不太重視小說的標題。在講究原創性和陌生性的文學創作中,這並不多見。你是如何想到以《封鎖》作為小說標題的?
小白:被你這麽一說,好像這些小說名字起得是有點平淡的感覺。我一般都到定稿交稿前才開始考慮標題這件事。到這時候,整個結構、故事、人物、視角甚至語調風格都反覆調整,推倒重來過好幾回了。對我來說,這個小說寫完了是真寫完了,各種可能性都試過了。可能到起標題那時候,就好像勁兒都過了,就隨便給起個名兒交稿了。也是編輯們都比較縱容我哈哈。
何平:從《局點》《租界》《特工徐向璧》和《封鎖》一路看來,偵探故事(或懸疑推理元素)似乎是你在創作中最鍾愛的元素之一,《封鎖》中的鮑天嘯也是一位擅寫公案小說的作家。有別於通俗小說,在“純文學”作品中,作為解謎過程的偵探故事形式似乎是最不重要的一個要素。但是在《封鎖》中,層層嵌套的偵探故事卻成為核心要素,甚至可以“用故事殺人,用故事救人”。你是如何看待偵探故事(或懸疑推理元素)在小說中的運用的?
《租界》
小白 著
小白:“純文學”是一個充滿了錯覺、歧義、訛用、循環定義的可疑詞語。它假定了它的反面,然後靠反面來定義自己。也許最初它確曾努力定義過自己,設想一種“純粹” “絕對” “理想”的文學。但它本來應該像“高尚”之類的詞語,一個人可以在心裡默默地對自己說:我要做一個高尚的人,但他總不能當眾宣布說我現在正在做的就是一個高尚的人。於是它就有點亂了,純文學成了一個托詞,你們要的那些我做不到,我做的這個是純文學。
母題類型從來都不是商業概念,莎士比亞戲劇每一部都套用了某種故事類型。文學史上大部分重要作品都套用了它那個時代某一種故事類型,作者完全不顧他的同時代讀者閱讀偏好,自行發明一套,這種事情雖然有,其實不多。我那些小說,確實都包含了很多犯罪、間諜、懸疑破案情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現代故事類型本身就是都市化產物,無論從敘事環境、從心理意義上都相當適合這些以上海為背景的小說。
這種故事模型包含完整的敘事裝置,事件及其意義的逐漸呈現,相互衝突的人物行為目標,人物表面言辭與隱含其下的心理動機,它們都特別適合用來講述一個複雜故事。《封鎖》利用了這些裝置,通過幾場審訊剝解了事件過程,在這裡,審訊雙方如同《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國王和山魯佐德,一方聽故事,另一方講故事,這又有點像小說家和讀者/評論家的關係,在這個層面上嵌入了某種對虛構敘事本身的隱喻。
__2
何平:說起“故事”,就不可避免地要論及“虛構”,鮑天嘯最後用“虛構”做了致命一擊——一個小人物完成了一件壯舉;重慶方面的來人也憑借“虛構”授了勳,升了官。“虛構”在《封鎖》中似乎無所不能,甚至讓人產生錯覺——它才是小說的第一主角。由此,《封鎖》既完成了精妙的文學技巧遊戲,也達到了對人性和政治的深入剖析。你曾說《租界》“都是杜撰的,偽造仿造的,是一個贗品的歷史事件”,“這部小說更像是一種實驗”。那麽,《封鎖》是“虛構”實驗的繼續嗎?相比之前的作品,這一次的“虛構”有了哪些方面的突圍?
小白:《租界》那個小說有一些敘事目標,我幾乎一意孤行地完成了它們。比如其中包含的幾乎遊戲般的敘述圈套,刻意模仿的那種間諜機構檔案的含糊其詞語調,某種類似於英語現在進行時態的“此時此刻”視角,高密度資訊分布(很多關鍵情節在小說中隻用了一兩句話交代),甚至連分章節字數都很嚴格地控制在3000字左右。它把敘述中的完整行動線隱瞞掩蓋到背後(通過模糊語調和儉省資訊),而著重解析了重重覆蓋的動機、關係和謀略。它像一部假想中的電影《租界》的反面,那部電影有一條密集迅速的行動敘事線,而把動機和關係放在敘事背後。
《封鎖》跟一個更大的寫作構想有關。我讀了一大堆檔案文獻,也包括很多如今已不大有人願意去讀的30-40年代出版物。好多年了,我一直想寫一個長篇,也動手寫了好多片段,人物、場景、事件,但總感覺沒有找到一個完整結構。那個長篇圍繞著一種關於歷史與文本之間關係的主題,當然,它不是主題先行,因為首先在頭腦中出現的是一些人物和一些事件,以及一個反覆出現不斷縈繞的句子,就好像說——一個幽靈在歷史上空徘徊,但這個幽靈是在圖書館誕生的。《封鎖》最初的構思或多或少來自那些草稿片段,話說回來,如果不把它寫成這個中篇,它也未必能成為那部構想中的長篇小說的一部分。
霍布斯鮑姆在《帝國的年代》序言中提到過兩種歷史:一種是仍存有私人記憶的歷史;一種是私人記憶完全消失的歷史。而在這兩者之間,有一個模糊的過渡區域。理解和寫作這個模糊地帶十分重要,因為它很容易被歪曲變形。30-40年代的上海,我覺得就相當於霍布斯鮑姆所說的那個模糊地帶,我記得小時候隔壁老伯伯在樓頂露台上乘涼講的故事,也記得小時候城市太空上幾乎完整保存的30年代面貌。這些私人記憶正在消失,人們如今能看到車墩偽造的繁華街景,上海家化廣告牌上的夢幻生活方式。《租界》和《封鎖》試圖在那個歷史模糊地帶重新構造一些人物,和一些事件。
何平:《封鎖》中的林少佐既是一位“偵探”,也是一位頗具藝術氣質的“反派”,在他的手中,甜蜜公寓的303室從爆炸案的案發現場變成了審訊室,變成了戲劇舞台。如果說鮑天嘯用小說虛構了一個世界,那麽林少佐則用戲劇表演建構了另一個世界;前者是文字的藝術,後者則是情景的藝術。你在小說創作中一直很重視戲劇性,這次更是直接設計了一個熱愛戲劇藝術的日本軍官,甚至在“密室”之中搭建了一方舞台,如何看待林少佐這個人物?審訊室在小說的情節演進中起到了何種作用?
小白:我確實一直都喜歡在故事中加入更多戲劇元素。因為性格與面具、自我與表演這些人性和心理的表現常常讓我十分感興趣。另外一方面,給予恰當的戲劇性衝突關係,人物對話就可以特別新鮮生動,富有層次,蘊含資訊和敘事動力。林少佐熱衷戲劇,身上全是面具,一會拿出一副,層出不窮,但骨子裡十分冷酷殘暴。
而這個由林少佐臨時布置起來的審訊室,就像一個舞台,甚至在物理太空上都像一個舞台,凸室高窗,對面房頂上有大量記者,這個舞台——一方面存在著某種歷史現實的邏輯可能性,當時入侵上海的日本軍隊確實常常封鎖包圍抗日分子的行動現場,用來顯示武力,用來“膺懲”,有時候也用來向租界外國勢力顯示他們有能力維持治安。另一方面,它也包含了某種隱喻意義上的邏輯合理性,這起事件因為發生在上海,它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某種表演性事件。這跟這座城市的歷史性格有關。
__3
何平:幾年前,我讀到了你的第一部個人文集《好色的哈姆雷特》,其中收錄的文章短小精悍,展現了你對於知識的極大探究興趣,這種寫作氣質也同樣順延到了你的小說創作中,《局點》一書的勒口上印著這樣的句子:“幾乎每個細節、場景都經過反覆推敲、仔細查證的傳奇故事。以考古學家的周詳以及詩人的偏僻趣味構建的知識分子小說。”《封鎖》中,你以邏輯嚴密的智性寫作對歷史罅隙進行了深入探察,這是一場暢快的思維狂歡,但是也可能陷入“曲高和寡”的局面,在故事等於“輕閱讀”,等於“爽文”的今天,你是如何看待智性寫作或知識分子小說的?

《好色的哈姆雷特》
小白 著
小白:讀者當然有權挑選作者,作者同樣也有權挑選讀者。傳統上,讀者挑選作者的方式很簡單:讀,或者不讀;買,或者不買。作者呢,則利用某種閱讀門檻來挑選自己的讀者:增加敘事複雜性、提高知識資訊密度、各種敘事密碼和文本遊戲、反諷和言外之意,或者其他各種在互文語境上的陌生化處理。這是一種古老遊戲,秘密只能講給能夠理解這個秘密的人聽。現代作者理當繼承這種遊戲精神,它既是一種驕傲,也是一種責任,因為作者有責任告訴讀者世界的秘密,人生的秘密。
今天的讀者不僅擁有傳統的選擇方式,讀或者不讀。他們也擁有了新賦予的權利和手段,他們可以隨時在扁平網絡中廣播自己的判斷和選擇,讀者正在享用著這種最新獲得的閱讀民主,他們自由而輕率地在微信微博知乎豆瓣上發表自己的讀後感。我自己作為讀者,很少參與這種評判,因為我覺得在享用自由背後應該有某種責任:我真的理解作者意圖了麽?作者實現了他的寫作意圖了麽?對這兩個問題,讀者有責任去尋找答案。而身為作者,我倒是常常把這視為寫作遊戲的一部分,當我看到某條古怪離題、言不及義的評論時特別開心,覺得又蒙住了一個家夥哈哈哈。
我相信這種寫作/閱讀機制上的失衡只是暫時的,在作者和讀者之間,漸漸總會形成一種新的契約方式。到那時候,不管輕閱讀,爽文,或者智性寫作,複雜文本,都會找到各自的讀者,達成寫作和閱讀雙方的各自意願。
何平:《好色的哈姆雷特》一文中,你虛構了一位“時間的旅行者”,這位“熱心的當代戲劇觀眾”穿越到1601年的倫敦,在目睹了伊麗莎白時代的莎劇和觀眾後,“他對英語語言文學素養的自信,以及自以為是的對莎士比亞的鑒賞力被徹底顛覆”。此處涉及對經典作品的“誤讀”問題,後來的讀者似乎很難擺脫“受製的視角”,面對一部被經典化的作品,閱聽人往往通過“被限定的理解方式”進入其中。《封鎖》此次獲得“魯獎”,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正在成為“崇敬的接受者”,它有著極大的“被經典化”的可能,你能否設想一下,若乾年後,讀者會如何看待《封鎖》?
小白:一部作品逐漸“被經典化”,這個問題十分複雜,牽涉某種歷史機制。作者不應當對此懷有期待。我自己對寫作最大的期待,可以用歷史學家芭芭拉·塔奇曼在她那本“Practicing history”隨筆集中評論英國作家吉卜林的一句話來概括:Kipling had a peculiar gift for recognizing history at close quarters.——吉卜林有著近距離認清歷史的才能。
何平:有許多人談過你的《封鎖》,這中間,黃昱寧的對談和但漢松的評論都特別關注《封鎖》技術層面的東西。有意思的是他們兩位都是外國文學的行家。對比一下他們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出身的人,現在很少有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文學批評家能夠這麽精確到細節去談論小說的技術。我看中《封鎖》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也是其技術的繁複。從小說技術層面,我覺得許多當下中國小說技術含量很低,你對中國當下小說敘事技術有怎樣的觀感?
小白:小說敘事技術的複雜性跟人們的生活方式密切相關,我們不可能事事都到傳統中去找辦法。比如大家常說我們城市小說比較弱,為什麽?城市化生活的人口密度,禮儀規範下的人格表演,城市事件的複雜性,多重多變視角,多層次語調語義,這些都有待於中文作家們在寫作中不斷創造發明。
《封鎖》
小白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