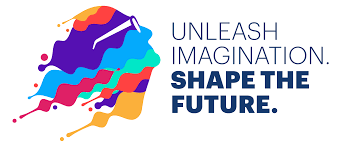美國東部時間2018年11月8日晚,由亞瑟·克拉克基金會(Arthur C. Clarke Foundation)主辦的2018年度克拉克獎頒獎儀式及晚宴,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西德尼·哈曼劇院(Sidney Harman Hall)舉行,劉慈欣被授予了2018年度克拉克想象力服務社會獎(Clarke Award for Imagination in Service to Society),以表彰其在科幻小說創作領域做出的貢獻。

劉慈欣領取克拉克獎後的演講現場。
劉慈欣曾憑借科幻小說《三體》,成為第一個拿到“雨果獎”最佳長篇小說獎的亞洲作家。同年,《紐約客》專欄作家約瑟華·羅斯曼(Joshua Rothman)將劉慈欣譽為“中國的亞瑟·克拉克”。亞瑟·克拉克(1917-2008)是英國著名科幻作家和發明家,與艾薩克·阿西莫夫、羅伯特·海因萊並稱為二十世紀三大科幻小說家。克拉克最知名的科幻小說作品是《2001太空漫遊》,此書由著名導演斯坦利·庫布裡克於1968年拍攝成同名電影,並成為科幻電影經典。
作為劉慈欣訪美行程的一部分,在領獎後的第二天晚上7點,劉慈欣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政治與散文(Politics and Prose)書店,和《華盛頓郵報》科幻小說書評編輯伊夫狄恩·梅森(Everdeen Mason)舉行了對談。伊夫狄恩·梅森本身是一個科幻迷,她每個月都會在《華盛頓郵報》的科幻專欄上,點評這個月新出的科幻小說。他們廣泛地交流了對女性的看法、東西方的科幻小說的異同、科技與文學的關係還有對人類未來的看法。劉慈欣也透露了他對他筆下人物的看法,以及對人類沉溺於資訊技術的擔憂。
在劉慈欣的小說裡,是男是女並不重要
劉慈欣對女性角色的描寫,一直以來都會被女性主義者們詬病。比如《三體》系列裡的女性角色就很臉譜化。故事會經常因為某些女性人物的“女性特質”,比如非理性、泛濫的愛心等而走向悲劇,反而男性角色則顯得很理性,最後往往是男性英雄拯救了被女性毀滅的世界。伊夫狄恩·梅森就問劉慈欣,這是否意味著自己的一種女性觀?

劉慈欣與伊夫狄恩·梅森在政治與散文書店的對談現場,王玉琪攝。
劉慈欣則表示,其實自己根本就沒有想過性別問題。他寫小說的第一步,是先想象未來科學技術的樣態,之後才能產生故事,最後才產生人物。他甚至認為,人物在小說中的地位並不重要,這在小說創作中可能不是一個很正確的做法,但在科幻小說中會比較常見。
比如《三體3:死神永生》中的程心,最初設定是男性,之後才改為女性。劉慈欣認為,其實男性和女性的行為方式並沒有什麽大的不同,在他的小說裡,人物是男性還是女性,這並不重要。從科學的角度來看,男女並沒有什麽大的差別,如果有差別,也更多是後天的而非先天的。比如《球狀閃電》裡的女主人公林雲,就非常積極進取,而不是被動的形象。
那麽為什麽在《球狀閃電》中,要選擇以陳博士的視角,來講述女主角林雲的故事呢?是不是意味著劉慈欣無法代入女性的視角?劉慈欣表示,這只是方便講故事罷了。另外,林雲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英雄人物,她有著很多性格缺陷,比如她癡迷於武器。從第三人稱的角度來描寫她,這會讓這個人物顯得更加客觀可信。

《球狀閃電》
作者: 劉慈欣
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5年6月
東西方的科幻小說有什麽異同?
伊夫狄恩·梅森認為,最近中國有許多優秀的科幻作家湧現出來,比如郝景芳、韓松、寶樹等。其中,劉慈欣在這個領域樹立了榜樣,功不可沒。劉慈欣則認為,這本質上是一個文化話語權的問題。最近進入西方視野的新中國科幻小說,不一定是受他的小說刺激出來的,而是因為他的成功,中國科幻從而能夠進入西方人的視野,受到了更多關注。因此許多優秀作者的作品,有機會被翻譯成英語,從而被西方認識。
西方讀者往往會關注中國科幻小說裡的“中國性”,劉慈欣認為,其實中國和西方的科幻小說大同小異,科幻小說是跨國界的。科幻小說比其他的文學體裁,更容易能被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人理解。因此我們經常能看到,在各國的科幻小說中,人類都經常作為一個整體出現。而且科幻小說的主題,也是全人類共同關心的主題,比如外星人入侵和烏托邦等。
當然,不同還是有的。因為美國科幻小說有比較濃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所以克隆人、人造生命等題材,在美國科幻小說中比較敏感。美國科幻作家和讀者都會鄭重其事地對待這些倫理議題。而在中國,這些有關於人造生命、克隆人的作品就不會顯得那麽重要。
中國的科幻小說也受中華傳統文化的一些影響,比如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中國人會比較傾向於 “天人合一”,而不是像西方,人與自然的關係是建立在對抗與征服上的。
劉慈欣舉了他《流浪地球》的例子,這部小說被改編成了電影,並且即將上映。《流浪地球》主要講述了一個在太陽發生災變時,人類如何逃學生的故事。如果這是西方人寫的,人類肯定會傾向於坐著飛船逃學生。但是在小說裡,人類選擇把整個地球推進到無垠的太空中,以這種方式逃離太陽系。這種選擇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影響,這是一種人與家園、與大地無法割捨的情結。

電影《流浪地球》劇照
科幻小說裡的文學性和科學性,孰輕孰重?
科幻是科學和文學的結合,但是讀者往往關注的是科學幻想的那部分,那麽小說的文學性到底在科幻小說裡有多重要呢?劉慈欣透露道,說到了文學,俄羅斯文學影響他最深,尤其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排在第二位是科幻作家亞瑟·克拉克,第三位是寫《一九八四》的喬治·奧威爾。不過,劉慈欣表示,其實自己不是因為熱愛文學才寫作的,而是因為熱愛科學幻想才寫作的,科幻小說中的文學性並不重要。
因為令劉慈欣沉迷的是科學幻想,所以他在寫作時,對筆下的人物並沒有代入感,也沒有特別喜歡的角色。他認為,人物在小說只是符號,比如程心只是一個象徵著正義的符號而已。劉慈欣表示,自己雖然說不上來喜歡哪個角色,但是可以明確地說出討厭誰。林雲就是劉慈欣不喜歡的角色,因為她的侵略性太強了;章北海也是一個令劉慈欣恐怖的角色,因為章北海會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有讀者可能會喜歡章北海,誤認為劉慈欣也喜歡他,甚至推崇他這種做事方式,但其實並不是這樣的。
談到科學,劉慈欣則顯示出了巨大的熱情。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會試圖去表達,人類在面臨宇宙的浩渺時,一種類似宗教般的敬畏。他認為,這種宗教般的敬畏感是科幻小說的核心精神。因為像物理學,本身就蘊含著巨大的想象力,令他癡迷和敬畏。他說:“物理學本身就是一部科幻小說,隻不過物理學的想象力是通過方程式表達的”。劉慈欣所做的只是抽取物理學中的一部分,構造出能被廣大讀者理解的故事。
比如,在《球狀閃電》小說中,球狀閃電被解釋為像西瓜一樣大的基本粒子,在巨集觀上呈現量子行為。其實這種解釋不是接近真實情況的,但是,把這種解釋寫進小說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小說把量子力學這種微觀的東西巨集觀化了,能讓讀者更真切地感受到物理學這種瘋狂的想象力。
劉慈欣補充道,自己接下來想寫一部和《三體》非常不同的作品。但是,由於現在科技已經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失去神秘感了 ,寫硬科幻小說,只會變得越來越難。
人類存在的意義在於向外拓展
科幻小說站在很高的位置去審視人性,關心全人類的命運。伊夫狄恩·梅森認為,在《三體》系列裡面,劉慈欣似乎透露出對人性和人類命運的悲觀看法,認為我們當下的人性注定會使我們的命運步入黑暗。
劉慈欣回應道,在自己大部分的作品裡,其實人性在本質上並不黑暗。人性並不是永恆不變的,而是沒有本質的,會隨著自然和社會環境而變。在《三體》中,人性在面臨滅頂之災時,就會發生改變,如果拒絕改變,就會和環境產生衝突,這就會被環境淘汰。
所以,在未來,長期呆在太空的人類,會不會越來越不像地球上的人類?劉慈欣說,生物從海洋走向陸地後,陸地生物和海洋生物就變得完全不同。這同樣會發生在人類進入太空之後。人的定義會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變化,而這種變化將會在接下來幾十年裡不斷加速。
“這一點不管我們喜歡還是不喜歡,都一定會發生。”劉慈欣說,“我自己本來以為這種變化會發生在人類進行星際開拓的過程中。但現在看來,在人和機器在生理上不斷地融合,人的定義就會發生變化。比如,手機已經成為人類的另一個器官了,隻不過手機和人體暫時還沒有生理上的連接而已。”

對談現場的觀眾踴躍提問。
“人們可以天真地認為,自己能夠堅守一種‘本真純潔’的狀態,但當‘人機結合’的時代真正到來時,這種堅守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這種改變是不可抗拒的。”劉慈欣補充道。
既然人性都是可以改變的,那麽人類這種生物的存在的意義是什麽呢?有什麽價值是可以值得堅守的嗎?劉慈欣則表示,生命到底是什麽東西,這其實沒有確切的答案。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裡說,生命隻不過是基因的容器,這是一個讓人絕望的定義,但這也是對的,不過在這個時代裡,大多數人不能接受這個定義。
劉慈欣認為,人類存在的意義在於向外拓展。人類應該不斷地向宇宙深處擴張自己的生存太空,不斷地向宇宙彰顯自己的存在,這本身就是意義。我們如今卻沉溺於資訊技術的安樂窩中,變得越來越內向。“這種內向發展到極致,世界就會變成這樣一個圖景:地球表面恢復了森林和草原,生命都很繁榮, 但是整個地球表面看不到一個人。同時,在某個地下室中,有一台超級電腦,在這台電腦裡,生活著幾百億人,就像《黑客帝國》一樣。這種影像一旦變成了現實,人類的生命將不具有任何意義。很不幸,人類正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劉慈欣認為,矽谷企業家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是人類的希望,這樣的人越多越好。馬斯克對星際太空的向往,以及把人類的存在擴展到其他星球的願望,是人類很本源的欲望。但是,目前時代的主流還是在往內走,而不是向外擴張。劉慈欣認為,對星空和宇宙沒有興趣的文明,不會有長遠的發展,不管他們在地球上多麽繁榮。
當然,這種向外擴張是一種冒險。劉慈欣表示,不管在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人類為了生存而犧牲自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人類不去為了未來冒險,結果只是把更大的風險留給了子孫後代。人類的確很可能會在向外開拓的過程中死傷無數,但是如果不這麽做,一旦地球發生了滅頂之災,人類沒有一個可以備份的世界,死的人只會更多。所以,探索和開拓過程中的犧牲,並不是人類可以選擇的。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碩士生王玉琪提供現場速記整理,在此感謝。)
新京報記者 蕭軼 實習記者 徐悅東
編輯 沈河西 校對 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