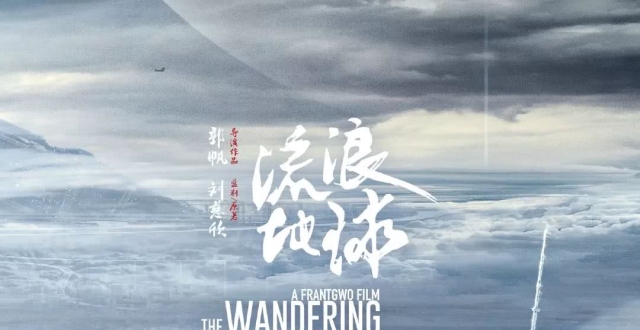從迷茫,到心血來潮,到失去鬥志,到人們口中的“幼稚”和“惡心”,到反思,到堅持,再到“中國科幻第一人”,劉慈欣已隻不是一名單純的科幻小說家,他已成長為一名關心人類未來命運的文人,對宇宙奧秘和太空文明熱烈渴求的學者。
本文已獲授權
來源 | 拾遺
ID:shiyi201633
其實早在童年時期,科幻的種子就已在劉慈欣心裡埋下。
劉慈欣出生在河南羅山的一個農村,“文革”期間,整個家庭被下放到山西陽泉。
7歲時的一個夜晚,在羅山老家的池塘邊上,擠滿了男女老少,他們望著夜空竊竊私語。
劉慈欣好奇心頓起,就跟著來到池塘邊,望向夜空。許久,漆黑的天幕裡,緩緩飛過一顆小星星。霎時,喝彩聲此起彼伏。

萬眾仰望“東方紅一號”
“那是1970年4月1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了。”劉慈欣隻覺一股莫名的嚮往之情莫名而生,如同當時“腹中的饑餓”一般不可遏製。
就在這年,附近村莊被洪水洗劫,58座水壩轟然決堤,鄉民流離失所。衛星與星空、貧窮與饑餓、“文革”與“批鬥”、洪水與難民,這些懂或不懂的元素糾結混雜。
“我早年的人生,也塑造了我今天的科幻小說。”

劉慈欣朗讀獲獎感言(圖片來自不存在日報)
整個大學生涯,劉慈欣都泡在圖書館裡,卡夫卡、博爾赫斯、奧維爾、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就坐在圖書館裡,讓管理員一本一本拿給我看。”
當時,他對寫作方向仍是不太明了,但他的腦子裡,已將關於親身經歷和文學套路的零散細節,慢慢銜接成一段段重工業色彩的科學幻想。
多年後,他寫下《球狀閃電》,裡面有段話,很好地概括了他當年的心境:“我明白自己是一個追夢人,我也明白在這個世界上,這樣的人生之路是何等的險惡莫測。即使那霧中的南天門永遠不出現,我也將永遠攀登下去——我別無選擇。”

劉慈欣工作的地方
那時候,劉慈欣並不知道,一部作品的誕生,不是自嗨,要符合時代,要對出版社負責,要考慮讀者喜歡什麽。
劉慈欣迷茫了:或許自己真不是寫科幻的料。

劉慈欣部分作品的創作時間表
1987年以後,劉慈欣幾乎不再寫作,他結了婚,職位也升為工程師,小日子滋潤而幸福,“那時候稿費低微,千字才100來塊,還不如我接點私活。”
十年時間倏忽而過,科學的幻想與夜空的星辰,成了兩條平行線。

婚後生活寧靜緩慢,但劉慈欣總感覺缺少點什麽。
他明白了自己所缺的東西:他是一個追夢人,除了攀登,別無選擇。
輾轉兩年後,他終於找到了《科幻世界》。《科幻世界》沒有發布他這兩部回歸之作,而選擇了他那兩年創作的另一個環保反戰科幻短篇:《鯨歌》。
發表後,市場反響一般,而且不少人吐槽“文筆幼稚”。這個“幼稚”的短篇,是他從1978年斷斷續續的創作以來,第一部正式印在紙上的作品。

有了第一塊敲門磚,劉慈欣的作品開始在《科幻世界》頻繁發表。在一次次磨練中,他的筆鋒越來越老辣犀利,行文越來越流暢,思想也越來越宏大,並陸續斬獲好幾個“銀河獎”。
但他也陷入了困惑:“雜誌上只能發表中短篇,長篇發表不了。”
而娘子關電廠給了他另一條出路:娘子關山西省最早擁有互聯網的地方。他決定在網上連載長篇。

劉慈欣長篇處女作
於是,劉慈欣連載了《魔鬼積木》,這是一本糅合了恐怖、軍事和基因技術的小說。由於他所構建的虛擬世界破綻太多、元素太多,再加上這是他的長篇處女作,並不能收放自如,《魔鬼積木》成了四不像。
讀者們都說“被惡心到了”。在當時,劉慈欣在科幻圈已有一定的名氣,但這本書給人的感覺就像《鯨歌》那樣,純粹是個門外漢寫的。
他開始反思,為什麽克拉克每一部作品都叫座叫好——那是因為克拉克本來就在美國皇家空軍工作,他是用自己的經歷來完成小說的藝術升華。
他明白:只有真實的經歷,才會讓人身臨其境。整頓思緒,劉慈欣新建了一個文檔,打了四個字:《地球往事》。

劉慈欣最初的構想,是很詳細地描寫“文革”時代的大人物,把豐富的童年經歷融入進去,“從‘文革’開始,一直到八十年代。”其間,外星力量不斷參與進來。
最後,“文革”只是成了《地球往事》的一個引子,外星世界及神秘文明的塑造成了重點,托爾斯泰的大氣蒼涼在故事裡彌漫,奧維爾的殘酷寓言在情節中滲透,而克拉克式的末日情懷,則成為《地球往事》的核心主題。
“科幻小說不該只是幻想烏托邦或反烏托邦的生活,不該只是賽博朋克那樣狹窄和內向,它應該是星辰大海一般的瑰麗和廣闊。”
2007年,小說連載完畢,這是“文革”結束後的第三十年。2018年1月,《地球往事》正式出版發行,書名被改成兩個字——《三體》。

《三體》三部曲並非劉慈欣最滿意的作品,“比如第三部,沒有個三四年,我是不會寫完的。但實際時間隻用了一年左右。那是被出版方催出來的。”而就是這部被“催出來”的作品,卻拿獎拿到手軟,拿到劉慈欣害怕出門。
2015年,拿滿國內獎項的《三體》,入圍雨果獎。8月,雨果獎揭曉前夕,劉慈欣打電話給主辦方:“如果不去,會不會影響得獎?”
主辦方回答:“不會的,我們希望你能夠出席,但實在出席不了也沒關係。”
一句“沒關係”,劉慈欣待在了老家,他成為五十多年來唯一沒到場的獲獎得主。

雨果獎
後來,有人問他是否遺憾?他說:“遺憾肯定是有的,但我反而挺平靜,因為雨果獎對於我這樣的科幻迷已逐漸陌生了。它的目光不再投向那些星辰大海,不再是人類探索宇宙的激情。”
他還說:“沒有一個國家或者政府,成立一個象徵性的機構,來應對外星文明,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提出這方面的研究。”
從迷茫,到心血來潮,到失去鬥志,到人們口中的“幼稚”和“惡心”,到反思,到堅持,再到“中國科幻第一人”,劉慈欣已隻不是一名單純的科幻小說家,他已成長為一名關心人類未來命運的文人,對宇宙奧秘和太空文明熱烈渴求的學者。
劉慈欣的故事所展現的,是一個真正的偶像,會有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會驅動一個人不斷向上生長。現實生活或許是一個泥沼,一副爛攤子,但不管身處怎樣的糟糕境地,偶像的力量總會讓我們不安現狀。
它如同一束星光,讓我們為之著迷、嚮往和奮進;它偶爾也如同一記耳光,讓我們疲憊、失望、駐足和退縮。但它最終會讓我們重新振作,再度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