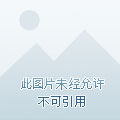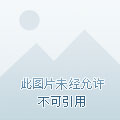雖然賀友直先生離開已有兩年,但他的作品和生前的點滴卻一直被人惦念。在先生辭世兩周年之際,“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thepaper.cn)特刊發相關紀念文章。本文作者回憶了與賀友直先生及其家人的交往,從浙江美術館2013年舉行的“‘談情說愛’——賀友直藝術展”的籌備開始講述賀友直先生一家的幽默和直率,正如賀友直先生所寫的“既見君子”。

一
認識賀友直先生之前,先認識他的女兒賀小珠、女婿張海天。
記得浙江美術館開館不久,我向當時的馬鋒輝館長建議征集賀友直先生的作品,說賀老是我從小就敬仰的大畫家,他是寧波北侖人。馬館長說他與張海天是浦江同鄉,還與他們夫婦是好朋友。浦江禮張村人傑地靈,出了張書旂、張振鐸、張書簡等十幾位畫家,是名副其實的“畫家村”,張海天也是其中一位。他的父親張世恩是中共的老人,前幾年逝世了。海天夫婦每年都選時間回到這裡度假。
2012年5月的一天,張海天、賀小珠夫婦回老家,王犁在浦江的朋友石棟邀他和我去禮張海天的老宅做客。王犁是他們的老友,我是第一次見。我坦言認識他們的目的是為了認識賀友直先生。賀小珠晚宴燒了一桌菜接待我們,席中一直是賀小珠在說話,半百的人了,卻天真、幽默而直率,話題幾乎都是圍繞得她的父親。雖是初見,張海天的溫和、賀小珠的真率,使我們相見恨晚。張海天說小珠從外貌到個性完全缽承了她的父親。

通過賀小珠的介紹,大略了解賀老是怎樣的一個人。她說父親不願意輕易接觸生人,老人每天晚飯後有散步的習慣。上海作協離他的家近,一次路過偶遇吳亮,吳亮上前招呼:“您是賀先生吧?”老人擺手:“對不起,我不認識你。”目不斜視便過去了。這樣的例子很多,小珠說不知要替人解釋過多少次。記得北京《讀庫》張立憲寫過文章,說是電話向賀老約稿,未曾開口,也是一句“我不認識你”便將電話擱了,還好老五執著,不斷給他寄《讀庫》,一來二往才終於采訪上老人。其實,賀老也是多情善感的人。詩人王寅曾有過一次與他的訪談。訪談中他對“文革”中貼過老友劉旦宅大字報事一直耿耿於懷,不能自諒,每次談起便淚水盈眶。“文革”結束後,他總感無顏見劉。一次劉旦宅舉辦畫展,命兒子邀賀友直,一句“賀伯伯”的招呼,令他嚎啕大哭。這麽多年過去了,他經常逢人要提起這件事,一直在自責,每次都會落淚。其實,“文革”中互相寫寫大字報,在那個時代很普遍。比起很多那個時代過來的文化人,忌諱自己文革中的作為,甚至掩蓋事實,堅決否認的做法,賀友直表現的是磊磊君子的人性之光,讓人尊敬。
海天與小珠,是那種一見面便宛如老友的人。從禮張之後,我們之間時有通電話。電話那邊,通常多是小珠熱情的笑語,每次基本都會告訴我賀老的近況。記得隨後他們回浦江過春節,還給我帶來了賀老在春節那一天為我簽名的連環畫《山鄉巨變》和《賀友直說畫》兩書。賀先生年九十有二了,字端莊有力,還蓋了印章。這是一份珍貴的禮物。

二
我有一個願望,希望浙江美術館能征集到賀友直的作品。馬鋒輝館長說,我們先給賀老辦個展覽吧。2013年“五一”節中,馬館長與我及其他同事去上海拜訪賀先生,商議展覽事。馬館長說他喜歡老酒,一路拎一壇黃酒去上海巨鹿路695弄賀老的寓所。
在賀老生活幾十年的老屋裡,他的生活每天幾乎一樣的規律。8時起床,早點親自烹的面條,吃了早餐後,就在蝸居裡開始畫畫,一直畫到11時,出來問夫人:“我可以收工了吧?”午覺要睡到下午3時,起床寫信,去郵局領稿費、寄信兼散步。途中有陌生人向他打招呼,他一概冷面回答:“我不認識你!”但也會與街坊親切的寒暄。晚飯後,看一會電視後睡覺。每餐都要喝黃酒,過去每餐一瓶,近年改每餐半瓶。

一進他小小的畫室,兩三人便塞滿了,張海天向他介紹馬館長。馬鋒輝說:“我們特地從杭州來看您。”老人伸過臉來說:“好,看過了,可以了吧!”馬館長連忙稱是專門來征求在浙江美術館舉辦畫展的意見。“展覽你們辦,我不參與,征求我的意見,我沒有。”他說一輩子最怕麻煩,複雜事情簡單處理。場面一時有一點尷尬,師母插話說:“少不正經!”拉他出來。
賀老從裡間出來,到客廳見我們,臉繃著,長長的壽眉一上一下,目光如炬,對來人個個巡視一遍。客人的恭敬與老人的嚴肅,形成了一個頗為喜感的場面,有一點冷幽默,第一次接觸還真不知道怎麽接招。馬館長向他介紹展覽準備情況,慢慢引出了他的話來。他說前次為上海展覽寫了一篇小文,題目《談情說愛》,意思是表達他這一輩子對連環畫的感情。看得出來,他對這個容易讓人誤會和聯想的詞有一點得意。馬館長會意,接口建議這次展覽就用這個題目如何?老人不答,露出得意的笑靨。
賀老早年創作的連環畫作品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所有,後期的作品悉數捐給了上海美術館。我們計劃這次展覽向兩家部門借,由浙江美術館與上海人美、上海美術館共同作為主辦部門。由於歷史原因,他早年創作的連環畫原稿歸他的老部門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所有,對此他深感無奈,也頗耿耿於懷。他調侃說:“上海人美如不提供原作,就不要讓他們參與主辦。展出作品下面就標明‘上海人民美術館出版社佔有’。如果讓他們發現,你們就說是字打錯了,原應該是‘所有’的,落了一半。”大家都笑開。
我們討論展覽開幕的時間,恰夫人過客廳,插一句話說:“13日、14日開幕不好,不吉利。”賀老臉色故作深沉狀,待夫人出房間,冷不丁說了句:“我最怕是后宮參政。”我們大笑。賀小珠一直躲在父親背後的門邊,靜靜聽著。賀老不時斜眼瞄身後,每瞄一次,小珠便如小孩一樣退後一步,做個鬼臉。馬館長邀小珠作展覽的特約策展人,我們喊她“小珠老師”。賀老指著小珠說:“她還小珠老師呢,狗屁老師!”小珠只是陪笑。

間有電話來,小珠接,說是有熟人找賀老。老人站起來接電話,一邊說:“麻煩,煩死了!”電話聽了一半,他就對那頭喊:“我從沒臨過字帖,我不會寫字,再見!”馬館長連忙說:“‘談情說愛’四個字可還是要您老親自寫哦。”老人落座,笑笑點頭。我說:“先生當年在中央美院講課很有影響,展覽時您老也做個講座?”看來我拍對了馬屁,他立馬滿臉春風,說自己沒什麽文化卻做了教授。前不久,一所大學請他作講座,談文化產業,他對文化產業化頗有微辭,說:“文化建設重要不在建了多少劇院,而是有沒有好劇本、好演員。”他慢慢來了興致,話題也輕鬆了起來,他說:“前不久,韓羽寄來他的新著《楊貴妃撒嬌》,我給他寫信,告訴他,我好好消受。” 小珠附我耳:“老爺子說得高興,話就沒有遮攔了。”
我們擔心影響他休息,勸他回屋。他說:“你們如果覺得我礙事,我就回宮。”我們連忙稱絕無此意。恰時,汪大剛來商量展覽拓展事,他是賀老好友畫家汪觀清的兒子,賀老對他特別信任。老人迎於樓梯口,對我們說:“你們注意了,此人極可怕,像一頭雄獅,可別嚇著你們。”汪大剛進來,果然長須長髮,如蒼松老柏。
這樣愉快的談話直至中午,賀夫人一直在廚房忙乎燒菜做飯。賀老的客廳兼作餐廳,一張小飯桌顯然容不下一屋的客人,海天夫婦在附近的一家老餐廳,請我們吃了一頓精致的中飯。

三
浙江美術館要給賀老做一個最好的展覽。
從上海回來後,我和同事們多次召開賀友直展覽“神仙會”。大家集思廣益,對展覽的學術定位、展覽結構、展覽方式和教育推廣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討。展覽分“時代線描”“紙上做戲”“塵世紀趣”三個版塊。賀友直以為連環畫就像是一出戲,需通過豐富而完整的情節來表達主題和塑造形象,“戲做足了,就好看了”。他筆下的人物刻畫精準,情節處理絕妙,在看似不經意處,做足了戲,常常讓讀者會心一笑。他說,一個連環畫作者,在創作時既是“導演”,也是“演員”,又兼“美工”。《山鄉巨變》《李雙雙》《朝陽溝》《小二黑結婚》《十五貫》《白光》人物形象無不活靈活現,每個情節精心刻劃,讓人記憶深刻。晚年的作品都帶有漫畫色彩的幽默,處處融入他的處世觀點,一個個充滿“賀家調”風趣特質的藝術形象躍然紙上。他的筆下處處詮釋著他的處世態度:簡單。這是人生至境,是大徹大悟,是最大快樂。我們在讀他作品的笑聲中發人深思,他的作品表達了一個簡單通達、風趣可愛的人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2013年6月12日,由浙江美術館主辦的賀友直藝術展開幕。開幕式上,台上長官嘉賓的發言依舊官樣套路,最後賀老說了一通最不像答謝辭的“答謝辭”。他說:“我老了,耳朵不靈了,前面嘉賓的發言一概聽不清。辦這樣規模的展覽,不是我畫的特別好,是因為比我畫的好的畫家一個個都死了。”又說:“大家來看畫展,最好多說好話,不必提意見,提也白提,這麽大年齡了,來不及改了。” 他的話中會偶而插個英語單詞,俏皮的表情與語言引爆全場的笑聲、掌聲。
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陪同他一起看展覽,一再表示是他的粉絲,要求賀老在送他的連環畫上題“贈許江老粉絲”。接受記者采訪時,賀小珠說,來的都是美女記者,賀老立馬一臉莊嚴瞪她。記者問:“為何這個展覽叫談情說愛?”他凝固起嚴肅的表情,略停片刻,一本正經地說:“我是很正經的人,你別想歪了。我女兒在這,話馬上就會傳到夫人那裡。”記者一下適應不了老人的冷幽默,場面一時尷尬,不知如何接話好。

展覽開幕後,賀老興致勃勃在展廳為觀眾做了一場講座,不時引發大家的歡笑,老人秀足了場面。從他的笑靨中,看得出這個展覽的策劃布置讓他感到滿意,觀眾也特別多,我們都松了一口氣。
在展覽期間,我認真看了展廳播放的賀老專題片。這個片子拍得很生活,老人的豁達、輕鬆、樂觀、溫情都在一個個鏡頭中表現出來。一個與夫人吃飯的場景,歡快的講話間,他忽轉臉親了一下夫人的臉頰,夫人似乎並不意外,一副像是習慣了的表情。我看著忍不住笑出聲來,從這些的場面捕捉中,我進一步了解他是個怎樣的一個人。

賀小珠給我看她寫的文章《我眼裡的爹爹》,寫得樸素而感人。在她的筆下,父親更多的不是一個藝術家,而是一個明明白白的平凡人,是一個外冷內熱、踏實自足的父親形象。她寫到:“以前總感覺爹爹對我們很冷,缺乏親情。隨著年齡漸漸大起來,自己也是做父母的人了。對爹爹也越來越理解了,他給我們‘隨風入夜,潤物無聲’的愛,是在他的內心深處。”
四
2013年9月,我接到賀小珠電話,她說父親最近完成54余件“走街穿巷憶舊事”系列作品的創作,將於28日在上海舉辦展覽,這批作品有意要捐贈給浙江美術館。小珠說:“為了完成這些作品,今年夏天高溫,老人在酒店公寓住了將近兩個月。作品完成後,覺得有點力不從心,說是再也畫不動那麽多幅的作品了。”小珠感到心痛,老爸真的是老了!
我們去上海看展覽,由於展覽條件的限制,展出的是複製品,並不是原作。賀友直的白描很有特色,人稱“賀家樣”。我讀過他自述習藝的經歷,線條深受陳老蓮的影響。早期連環畫白描線條流暢細膩,晚期多作風俗畫,線條多了一份拙樸老辣,與畫面的幽默氛圍渾然一體。他沒有上過正規的學院訓練,卻是中國最高美術學府裡教授連環畫的第一人。在他的身上有很多的傳奇,這些傳奇卻又簡單無華。他的藝術來自他的執著與勤奮,來自他對工作與生活達觀的態度,這是學院所不能培訓的,他是一個真正明白自己的人。

有一次,我陪同賀小珠夫婦參觀敦煌藝術展,小珠講起父親去敦煌的往事。為了能學習更好的壁畫,他“賄賂”管理員一幅畫,管理員給他一大把洞窟的鑰匙,對他說:“你挑藍色的鑰匙去開洞窟門,是特別好的洞窟,一般不對外開放。”賀友直進窟臨摹,窟內很暗,須開門借光,時間很緊,就以麵包充饑,蹲著趴著,片刻不敢停,臨了一大冊。這些臨摹的作品,後來捐贈給了上海美術館。
賀小珠的回憶文章生動記錄賀老的工作狀態:“父親退休前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工作。部門離家很近,走路大概不到十分鐘。我們從來就知道爸爸很忙,他不僅在部門畫畫,很多時間還要帶回家畫,有時候到很晚他還沒回來,家裡等著他吃飯,媽媽會派我們去部門找他。一個很大的辦公室,見他一個人在辦公室靜靜地伏案作畫。他在家畫畫的時候我們都要識相地不能發聲,大房間窗邊的寫字桌上一盞台燈亮著,他在寫字台上工作。我們五個都擠在小房間,如果偶爾有事需要進大房間都得躡手躡腳進去,生怕驚擾了他。儘管這樣,見有人進去,爸爸還是會抬起頭,停住筆,用他那特別亮和有神的大眼盯著你,盯得你汗毛直豎,那眼睛一直跟著你的腳步直到你退出房間,以後你再不會敢跨進房。爸爸的大眼在他們那一輩老連環家中是有名的,記得一次去社裡替爸爸領工資,爸爸的老朋友們跟他開玩笑,包錢用的是一張卡紙,上面畫了兩隻大大的布滿血絲的‘彈眼’”。

在上海展出的“走街穿巷憶舊事”展覽結束後不久,賀老因中國美術學院邀請來杭州講課。我隨馬鋒輝館長去象山校區與他見面,談這批作品的捐贈事宜。臨別他總要來一句幽默:“你們可要祝我長壽,才有可能給你們多畫。”
轉眼又是新年春節,我們接到賀友直為浙江美術館畫的新作《賀家班子》,薈集了他連環畫代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畫角蓋有一枚“永未畢業”的章。小珠知道我喜歡每天記一點瑣記,送我賀老親筆簽名的筆電,上題“陳緯先生記事,記好事。”不久,他率家人到寧波老家北侖賀友直藝術館度假,托信來要我們去接收“走走街穿巷憶舊事”這套畫。賀老一張張向我們介紹畫裡的往事,沉浸於他的嘉年歲月。老人談興很濃,說在上海巨鹿路的老屋生活了幾十年,在那樣的蝸居裡作畫很滿足,以他特有的賀式語言表達“屋大不如心大”。中午他一定要招待中宴,席間你一言我一語談論某大畫家,此畫家先是發表“去國聲明”叛國,在外國呆不下去了,又向中央寫信,表示懺悔要求回國。賀老忽然播話:“別提他,免髒我口!”

五
真正算與賀友直先生成為知交是一年之後的一次飯局。
2015年4月29日,賀小珠來電話,稱她陪父親來杭州參加國際動漫節,領評委會頒的特別獎,晚上邀在杭的親友聚一聚,有幸我與王犁也受邀。賀老一落座便很興奮,妙語聯珠。他說:我不懂動漫,但他們把我的連環畫作品展出了,評委會總不能評我動漫獎吧,比較特別,所以給了個“評委會特別獎”。動漫關鍵在於以肢體語言來表達,不是靠對白。這是外國動漫與中國動漫的區別。卓別林為什麽偉大,就是善於以肢體的語言傳遞人的世界。中國過去有一部《三個和尚》就很好,全劇沒有一句對白,外國人都看得懂,在國際上獲了獎。現在中國的動漫劇就是傻瓜,比如《喜羊羊與灰太狼》,沒有動作,只有對白,要說話跳到前面,不說話就往後跳,特別傻。王犁轉述韓羽先生講的故事。《三個和尚》阿達、韓羽、馬克宣合作的作品,當年在捷克獲獎後,韓羽說,既然獲獎了,總有獎金吧。建議大家向文化部要,那個年代誰敢向政府要錢啊,阿達他們沒有去,韓羽說自己當時在保定,實在太窮了,愣是跑到北京去要,結果三人中只有韓羽得到獎金。賀老接話說:“韓羽很有趣,讀了很多雜書,讀得精,讀得透,讀得通。前年還給我寄了新著《楊貴妃撒嬌》,恰好北京有一作家也寄了本有關楊貴妃的書,我便給韓羽去信說,一個楊貴妃已不能讓老頭消受了,還來倆,不是要我命呀!”賀老喜歡喝黃酒,王犁硬蹭在賀老座邊,要為他斟酒。王犁專心聽賀老講話,每次都忘了加滿,老人敲著杯子說:“你這個司酒的不稱職。”酒過半,師母阻止不讓加,賀老不高興,趁師母不注意,揮起手朝老婆的腦後故作搧狀。夫人回頭,他急抽手摸自己的頭,說別誤會,我撓頭呢!大家大笑。海天說,老人過了九十歲,就不知多少年齡了。
前年賀老在浙江美術館展覽前一天,我給志願者講座,說到他年輕時,又窮又不出名,也不是帥哥,百思不得其解,怎麽就抱得美人歸?師母接話:“他有手段。”賀老得意,朝著夫人用食指做勾引的動作。小珠為父親抱不平,說老爸當年很帥的,倒是母親年輕時很瘦,賀老說她像“白骨精”。說到容貌,賀老回憶當年在新加坡做展覽,潘受先生親自為展覽剪彩。潘先生非常喜歡他的作品,到處宣傳說,賀友直只有小學文化,可全新加坡沒人畫得過他。賀老貌有瑞相,長著一雙壽眉,仔細一看,一邊毛朝上,一邊朝下。小珠要大家猜是什麽緣故。師母接話說,他沒頭髮,洗臉總是順著腦門抹,滿腦袋畫圈,久之久之,眉毛就一上一下了。
這餐飯就在這樣戲謔開心的話題與笑聲中進行著,老人越來越來勁,不停催著添酒。酒沒了,時間也不早了。老人從口袋裡掏出一隻橙色錢包,裝著鼓噔噔的錢,要小珠去埋單。小珠說他不喜歡用卡,一張一張數著付錢痛快。賀老說他的錢包永遠要保持著鼓鼓的,目的是有份量,緊緊的塞在褲袋裡,扒手偷不了。小珠告訴單埋過了,他將錢包放回去。王犁說:“別急,賀老這麽洋氣的錢包我要拍下來。”王犁認真擺在台布上拍錢包,他手指彈著王犁頭說:“這十三點!”
回家的路上,我與王犁一遍遍回想酒桌上賀老的話,可不知怎麽一片空白。我說一點,他說一點,我們努力還原。王犁怕忘記,急著要回家將晚上的事寫下來。當夜,我也將晚上的聚會“白描”記敘下來。第二天與他一起將各自的文章寄給賀小珠,讓她轉給賀老看。賀老看後,說:“以後與他們喝酒,再也不說一句話了,省得被他們抓住把柄。”我對小珠說,那還不給他憋死!小珠大笑稱是。
我與王犁一唱一和哄老人開心,給賀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時時念叨著要邀我們再去上海聚一聚。小珠說:“老人從來沒有這樣念想著人,看來他真的喜歡上你們了。”
六
不過兩月,我與賀老又聚在一起。
賀友直在浙江美術館舉辦展覽期間,我收到一封觀眾的來信,信是與他一起參加抗戰青年軍(1944年)的老戰友淳安人毛均榮寄來的。毛老先生聞訊來杭州觀看展覽時,賀先生已離開杭州回上海,沒有見上,便寫了一封信託我轉交賀先生。賀老收到信後感慨萬千,說只有那個年代的老戰友才會喊他“阿直”。在上次聚會上,賀先生聊起此事,王犁是淳安人,力促賀先生與老戰友見個面,他答應去淳安一趟。王犁還將此事寫成文章《叫我“阿直”的老戰友,我想來淳安看您》在《錢江晚報》發了出來,正好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的版面。第二天,毛均榮老人電話就打到了報社。

沒過多久,賀友直夫婦在張海天、賀小珠夫婦陪同下去淳安,王犁與我,還有我的妻子也一起見證這個特殊的見面會。王犁將會面的地點安排在遠離縣城的左口鄉橋西龍塢村 “老田莊”民宿,安靜的山山水水便於朋友暢聊。賀老93歲,毛先生少他5年,抗戰勝利那一年當的兵,還沒碰到日本人就勝利退伍了,兩人分手整整70年。我與王犁去淳安縣城接毛先生,老人捧一束花來見賀老,一路上很平靜,沒有一句話,又很莊嚴。我知道他的內心此刻翻江倒海。當年賀友直兵銜是下士,毛均榮是中士,兩人一見面,賀老立即立正行軍禮,眼淚便突眶而出,隨即掩面而泣。兩人都忘記了坐下,迫不及待回憶當年,敘說各自的人生經歷。毛均榮老人解放後由於歷史原因被判了28年的刑,說起自己的遭遇,語氣平緩,仿佛是在說別人的事。賀老問他:“您在監獄吃了不少苦吧?”他平靜地說:“還好,管教人員對我很好,其中一個還把女兒嫁給了我。”賀友直說自己幸虧是在上海,歷史有問題的人多,又是業務骨乾,否則也不知會是吃什麽苦。當年他們的老戰友中不少人還被槍斃了。“他們到底犯了什麽罪啊?”賀老悲憤地說。晚上大家一起吃飯,兩位老人的手拉住,很久沒有放開。

第二天,千島湖下起大雨。賀老忽記起曾於桐廬吃過的“桃花魚”,想再嘗一嘗。什麽是“桃花魚”?賀老說不明白,我們也不明白,我便電話請桐廬的高華君安排找。中午,我們一行抵桐廬,高華君接至富春江畔一家魚館,窗外即是江景,山色空濛。高華君說此處正是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之最初段。其實所謂桃花魚即鱖魚。我們還點了一道富春江刀魚。賀老興致一來,就說了一段關於刀魚的段子。他說,某大官到揚州,要吃刀魚餃子。廚子將刀魚釘在鍋蓋的背面蒸,水面上鋪一層紗布。刀魚多刺,蒸爛後,刀魚便從鍋蓋上掉下,經紗布過濾,魚肉溶入水中,魚刺留在紗布上。魚肉及湯和面做餃子皮,這就是刀魚餃子。我問他是否吃個刀魚餃子,他說,哪能吃得上,我又不是大官。他說自己最怕見大官名家。在中央美術學院任教七年中,同事建議他去拜訪李可染,他一次也沒去。他說從不沾名人的光,早年請錢瘦鐵、來楚生刻印章,給兩塊錢一個字,老先生們說潤資太豐厚了。現在聽說上海某篆刻家要好幾萬元一個字,賀老來一粗口:狗屁!
飯後,我們各自回程,賀老夫婦回上海,海天、小珠去浦江,我與夫人及王犁回杭州。
沒過幾天,王犁電話來,說是接賀先生的來信,邀王犁與我月中去上海做客。賀小珠電話裡對我說,為這事老人十分重視,特意與她商議我們到滬後住哪家賓館合適。我說,賀老給王犁寫了信,怎不給我寫信?小珠說:“父親說你字寫得太好了,不好給你寫。”這真是太冤了。
因氣象火熱,去上海的事就緩一緩。但老人記掛著,讓王犁給他通一電話。電話拔通, “你是誰啊?”“我是王犁,給老爺子請安來了。”“又見不到面請什麽安。”他吩咐來滬一定帶上夫人。王犁說夫人在台灣,就自己來。他來勁了:“哪夫人能放心啊?食色性也,人之常情,控制不住的,除非把那東西掛在家裡的牆上再出來。”王犁接上:“就聽老爺子的,我掛好了再來。”
轉眼到了秋天,接賀小珠電話,說是老人近來身體不適,但不去醫院,說是怕檢查出什麽毛病來。她請我與王犁近來上海一趟,與老人見面樂一樂。老人一直記掛著與我們會面的事。
又過近一個月,老人身體稍好。我攜妻子和王犁一起去上海見他。賀老在他的“一室四廳”鬥大的畫室中等我們。一進門,他故意板著臉,用冷峻的目光盯著我們,怪罪我們拖這麽久才來。王犁遞上新出版的散文集《排嶺的天空》。賀老卻向我豎大拇指,對王犁說:“你就會耍嘴皮子,寫不過他。”我好得意,王犁故意急老人:“您還沒看我的書怎麽知道,我比他寫得好。”賀老對我說:“我接到《經緯齋筆記》,一翻便翻到曹聚仁抗戰時期與那對流浪母女的糗事,你專挖這些東西。”小小的鬥室裡滿溢著我們的笑聲。賀老說中午要一醉方休,賀小珠將聚宴安排在離賀老家不遠的“浙裡”酒家。這段路不長,老人卻走得蹣跚。與他半年不見,明顯老了許多。
席中,賀老談起往事,數度失聲落淚。先是憶起與他的老鄉、女畫家賀慕群病逝前的會面,禁不住落淚。談起“文革”中的老長官呂蒙,他竟痛哭失聲。當年呂蒙招他進出版社。反右的時候,一次呂蒙將他喊到戶外的草坪,小聲提醒他要珍惜自己的才華,運動中要注意保護自己。事後,在“文革”的批鬥中,他沒有頂住壓力將這件事給兜了出來。前些年,上海美協的一次紀念呂蒙的活動上,他勇敢地把這事說了出來。呂蒙夫人對他說:“呂蒙在天也會原諒的。”他再次說到了劉旦宅。早年他與劉旦宅結下深厚的友情,兩人惺惺相惜,無話不說。“文革”中他卻給劉旦宅貼了大字報。“文革”結束後,他羞見劉旦宅,倒是劉家人大度,沒一點前嫌。劉旦宅去世後,劉夫人每年春節都要遣兒子向他拜年。他說,劉旦宅的一家都坦蕩蕩。
這一次的聚餐,吃得不比前幾次的輕鬆歡愉,有一點沉重。
七
2016年春節期間,我在浙江美術館做了一個賀友直“走街穿巷憶舊事”的小型展覽。原定賀老要來,由於身體原因不能來。這個展覽結束後還計劃移至寧波北侖賀友直藝術館展出。賀老說,等身體稍好,到北侖展出時再去。
2016年3月16日的下午,我在江西三清山上參加一個活動,接到賀友直藝術館館長賀惠忠微信,詢問到北侖展覽的時間。這個展覽早與交付負責流動美術館安的同事劉佳波落實,因正逢春節,還未確定具體時間。我立即與佳波通電話,我莫明感到焦急,聲音有點大,我們當即商定4月1日開幕。

晚上用餐時,我接到賀小珠的電話,報來噩耗,賀友直先生於半小時前,即8點30分逝世。我當即急急離席,回到房間,不禁失聲痛哭。緊接著,《錢江晚報》記者鄭琳的電話來采訪,要我談談賀老,一時不知從何說起。賀小珠告訴我,早上他還自己煮麵條吃,上午接待寧波美術館的客人,談展覽與捐贈的事。近午,他上衛生間,夫人見他15分鐘沒有出來,進去一看,老人已吐了半臉盤的血休克在地。11時30分送瑞金醫院搶救,一直處於昏迷之中。直至下午4時清醒過來,對家人交待說“要好好照顧好你們的媽媽”。隨後又是吐血不止,至晚8時30分,搶救無效逝世。我想起下午在三清山上與同事佳波君通電話時的焦急心情,正是賀老與死神掙扎的時候,我驚詫於與老人冥冥之中的相通。記得老人曾說過:“上帝要我走時,我不會拖拖拉拉!”與王犁通電話時,王犁說《文匯報》催他一定趕寫一篇紀念文章,就取這個題目。
很長時間,我都無法接受賀老的離去,他的言行那麽的鮮活具體,想到一些對話如在耳旁,一點沒有遠離我們而去的感覺,這就是賀老的魅力。雖與賀老交往時間不算長,但老人晚年短短的時光裡,與老人忘年的交往,是我人生的莫大榮幸。我常常會想起與他相處的時光,會自己笑起來,那些流露點點滴滴的生活態度和藝術態度,注定會影響我一生。好在賀小珠送我一小片賀老的遺墨,寫著四個小字“既見君子”,我將之懸掛於壁上,每抬眼都讓我會心一笑,心裡充盈了溫暖,謝謝賀老!(文/陳緯)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