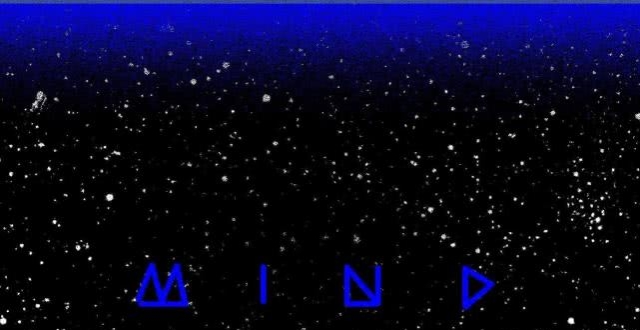春節檔《流浪地球》電影的熱播和大眾對於本作的肯定,讓劉慈欣老師(以下按科幻迷對他的愛稱,稱為“大劉”)又在科幻文學的圈子之外火了一把,實現了“票房評價兩開花”。回顧數年前的《三體》三部曲熱,大劉多是以嚴肅的科學設定和較為冷峻的劇情示人。在這些作品中,他毫不掩飾在面對危機的時候,對於人類知識體系中技術層面的極端重視,以及“壓縮”其他方面在教育體系和人類活動範圍中的傾向:
“學校教育都集中在理工科上,藝術和哲學之類的教育已壓縮到最少,人類沒有這份閑心了。這是人類最忙的時代,每個人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流浪地球》
在另一篇《朝聞道》中,可稱之為超級文明的排險者(包括人類在內其他文明的“監護人”,防止因為這些文明的危險科學探求舉動危害到宇宙穩定),在面對“霍金”對於宇宙意義的詰問時,只得保持沉默:
“ ‘宇宙的目的是什麽?’
天空中沒有答案出現,排險者臉上的微笑消失了,他的雙眼中掠過了一絲不易覺察的恐慌。
……
‘你不知道?’
排險者點點頭說:“我不知道。”這時,他的面容第一次不僅是一個人類符號,一陣的悲哀的黑雲湧上這張臉,這悲哀表現得那樣生動和富有個性,這時誰也不懷疑他是一個人,而且是一個最平常因而最不平常的普通人。
‘我怎麽知道。’排險者喃喃地說。”——《朝聞道》
在讀過這些描寫之後,加上爆出十數年前大劉老師“怒吃女主持人”的對談大新聞,有一種對於他作品的批評觀點非常流行:在技術上想象精湛,但是缺乏“人文關懷”;作品似乎暗示,為了生存,人們做任何事情都是合理的,而生存之上的東西如宗教、哲學、藝術等,都可被視作無物。更深層次的憂慮在於:作品中表露的這樣一種“技術主義”,是否會影響我們對於那些精神性東西的價值判斷,並在日常生活和真正災難的來臨之際影響我們的選擇。
這種憂慮是直擊要害還是有失偏頗呢?筆者以為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大劉老師的另外一個作品系列或應得到更多重視:它們包括《詩雲》《夢之海》與《歡樂頌》,分別是關於詩歌、繪畫和音樂的作品,亦被稱為“大藝術三部曲”。這三部作品展現了大劉對於藝術的看法,或許能夠給螢幕前諸君以一種不一樣的體驗。閱讀這些作品更重要的意義可能在於:如果未來真的類似於大劉所描繪的那樣的世界,那麽藝術,以及她背後更廣闊的人類對於“美”的追求,也未必會缺席,或者直接被生存的需求“精簡”掉。
《詩雲》:打出十四行詩的猴子是十四行詩詩人嗎?
文藝複興以降的哲學界關於還原論(reductionism)有許多討論。最著名的口號是,“只要時間足夠長,猴子也可以打出十四行詩”。在讚同還原論的哲學家看來,一切人類表達,如果不是毫無意義的鬼話,那麽就能夠被轉寫成科學的描述。一個例子是:《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這句話與 “恆星已在行星的山後面落下,一條叫黃河的河流向著大海的方向流去,哦,這河和海都是由那種由一個氧原子和兩個氫原子構成的化合物質組成”是一個意思。
《詩雲》這部作品中,超級文明已經能夠實現質能轉換,能夠進入十一維空間,能夠隨意熄滅太陽和製造白洞,以致被其他文明作為神來敬拜。然而,在和已經淪為吞食者(恐龍)帝國家禽的人類中的一員,詩人伊依的對話、分歧與互動中,該文明的一個個體仍然對看似微不足道的“方形文字組成的小矩陣”——中國詩詞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不但通過伊依提供的資料親自化身為“李白”感受人類詩人的生活方式試圖作詩,而且為了“終極吟詩”,不惜拆解太陽系,毀滅吞食帝國(同時也拯救了人類),以造就窮舉出所有的詩詞排列組合的“詩雲”。然而,雖然所有漢字按照詩詞規則的排列組合都置身其中,“李白”卻因為編寫不出“具備古詩鑒賞力的軟體”無從檢索出自己所需要的詩,藝術最後的堡壘依然沒有被技術所攻克。
《詩雲》從哪些方面展現了大劉對於藝術的觀點呢?首先也是最為淺表的,借助先進的技術手段,運用暴力的窮舉法,並不能消滅藝術——即便使用最先進的枚舉技術和存儲技術,採用最少的格律限制,最終得到的成果還是需要通過“具有鑒賞力”的主體來取出來。在小說中,在技術上可謂登峰造極的神級文明亦在此處折戟沉沙。

這樣對於藝術“自留地”的捍衛,仍然會面對一定的責難:沒有人可以保證鑒賞力就不可被科學分析、還原為某種生物化學過程。如果超人工智能的構想是現實的,或許我們甚至不需要了解“鑒賞力”是什麽——將其視作黑箱,只要AI能像模像樣、“符合智能生物口味”地挑選出佳作即可。如果《詩雲》對於藝術的看法僅及於此,那麽它的啟迪價值或將大打折扣。
在筆者看來,《詩雲》更重要的一點,是點出了藝術和(基於還原論的)技術手段在“思維方式”上的不同:如果將兩者粗暴地看作是生產各自產品的“生產線”,那麽他們的產出和生產過程都有著極大的差異。
先論產出。小說中伊依與李白的這番對話值得玩味:
“想像一下,用一把利刃把她切開……把肌肉和脂肪按其不同部位和功能分割開來,再把所有的血管和神經分別理成兩束,最後在這裡鋪上一大塊白布,把這些東西按解剖學原理分門別類地放好,你還覺得美嗎?
……
李白眼中的大自然就是你現在看到的河邊少女,而同樣的大自然在技術的眼睛中呢,就是那張白布上那些井然有序但鮮血淋淋的部件,所以,技術是反詩意的。”——《詩雲》
如果說上述關於鑒賞力的討論是從詩作欣賞的角度討論了“鑒賞力”的不易,那麽伊依的這番話則是區分了詩歌創作下眼中的自然(乃至更廣闊的“外部世界”)和運用科學手段得到的自然圖景之間的差異。將河邊人看做是解剖學部件在科學上是有價值的,甚至也有可能作為某種藝術的根基,甚至有一定可能會對傳統詩詞創作者產生啟迪,但決不能因此就否認了伊依等詩人觀察自然方式的合法性。倘若柳永來到江邊僅僅想著水流的侵蝕堆積作用和霜風的風向風速,那凝愁怕是與《八聲甘州》中的相差甚遠。
再言生產過程。“李白”為了寫詩,過了一種與科學探究或者神級文明都不同的生活:
“這時的李白已有了很大的變化,他頭髮蓬亂,鬍子老長,臉曬得很黑,左肩背著一個粗布包,右手提著一個大葫蘆,身上那件古裝已破爛不堪,腳上穿著一雙已磨得不像樣子的草鞋。”
“李白”不僅借助伊依和資料庫提供的古代詩人信息“道成肉身”,從能量體物質化,而且試圖效仿歷史上的那位李白過活,“浪跡於這山水之間,飽覽美景,月下飲酒山顛吟詩,還在遍布各地的人類飼養場中有過幾次豔遇”,才創作了一些他自己仍不甚滿意的詩。
大劉在這裡生動地表現了一個詩歌創作者的自我修養。與科學探究中所追求和遵循的主體間性等原則不同,詩人恰恰是在他們的個體感覺經驗層面工作,而這也是“李白”大費周章,放下身為神級文明成員的架子,像一個普通人類那般生活的動力所在。
至此,我們或許可以大膽斷言,藝術在三個方面不完全等同於科學-技術的思維以及他們的成品:
1、使用窮舉的方法試圖窮盡藝術創作的邊界(或者宣稱有一種“能行的”方法),並不等同用這種手段將所有的藝術可能“創作”出來;
2、 技術手段和藝術創作者的觀察外部世界的視角不同,導致產品的旨趣有著根本差異;
3、技術手段和藝術創作者在探究過程中遵循不同的原則,對於個體感覺經驗的態度亦不同。
這或許是《詩雲》能夠帶給我們的寶貴啟示。
《夢之海》與《歡樂頌》:藝術作為文明的價值與動力源
以上一個部分的討論,說明了對藝術創作進行還原論嘗試的困難。然而,這僅僅解決了藝術“是什麽”的事實命題。以下關乎價值的命題或許更加重要:在科幻作品所描述的未來中,藝術有何價值呢?《夢之海》與《歡樂頌》兩部作品展現了大劉的思考。
《夢之海》中塑造了兩位低溫雕塑藝術家的形象。一位是文明發展到極致、低溫藝術創作成為唯一追求的外星文明;一位是既具有藝術追求,又不忘自己工程師本職和日常生活的顏冬。外星文明經過地球時,看到了地球上的冰雕藝術展,激發靈感,毫不在意地取走地球上的海水,圍繞地球搭建起美輪美奐的“冰雕環”;顏冬以藝術家同行的身份勸說無效後,在醉心於這夢之海的炫目之餘,仍然積極參與迫降冰塊的工程行動,最終為人類奪回了海洋。
筆者看來,兩位主角都表達了大劉對於藝術價值的肯定。在外星文明——自稱“低溫藝術家”眼中,無論生存、政治、科學,都僅僅是文明嬰兒和少年時期的必修課程,當衣食無憂、個體與群體統一、宇宙的原理得到徹底解明,這時便“只剩藝術,藝術是文明存在的惟一理由”。低溫藝術家對於創作的癡迷和其他“瑣碎”事物的不關心,正是因此而生。
另一位主角——顏冬的形象更是“文理兼通”,既能夠創作出讓外星文明都讚歎的冰雕作品,又可以在地球上的水被取走的大旱之時,獨立想到導光管方案,並最終目睹它被實行。大劉在這裡表達了他對於藝術家的揶揄:
“‘你去回收部能幹什麽?那裡可都是科學家和工程師!’禿頭藝術家驚奇地問。
‘我從事應用光學研究,職稱是研究員,除了與你們一樣做夢外,我還能乾些更實際的事。’顏冬掃了一眼周圍的藝術家說。”——《夢之海》
但是,決不能因此就認為大劉完全是在diss藝術的價值。實際上,大劉固然不認同(現階段)的人類文明應該像低溫藝術家那樣,眼裡只有藝術,而忘記了走好腳下的生存之路;但他亦不會同意完全拋棄藝術的行為,即便日子艱難。小說的結尾正表達了這樣複雜的情緒:
“‘咄,日子難怎麽了,日子難不能不要藝術啊,對不對?’”一位老冰雕家上下牙打著架說。
‘藝術是文明存在的惟一理由!’另一個人說。
‘去他媽的,老子存在的理由多了!’顏冬大聲說,眾人都大笑起來。
然後大家都沉默了,他們回顧著這十幾年的艱難歲月,他們挨個數著自己存在的理由,最後,他們重新把自己從一群大災難的幸存者變回藝術家。”——《夢之海》
如果說《夢之海》還是在表達外星文明過度沉迷藝術給地球造成的災難性影響和對人類追求藝術的肯定,《歡樂頌》則更進一步,設想了欣賞音樂這一藝術活動對於人類和平發展的積極作用。小說的背景是,因為爭執不休,類似聯合國的“GA”已經行將就木。然而,超級文明“鏡子”來到了地球上空。這面非實體、零質量的光滑幾何平面,以太陽為琴,以被改造成脈衝星的比鄰星為節拍器,開辦了一場太空音樂會,向著全宇宙發出信號。人類在聆聽曠世旋律之中,仿佛置身於生命演化和文明發展的全過程中,對於文明的來歷和文明一種可能的發展方向與意義(通過反射宇宙來表現自己的存在)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增強了解決地球上問題的決心。

這篇小說無疑是非常“浪漫”的,沒有對沉重的生存問題的顧忌。利用恆星向宇宙主動發出信號,在《三體》中有極為相似的橋段,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無論是三體的入侵,還是最終的二向箔帶來的二維化,某種意義上都是“紅岸的鍋”;這樣的行為也被歌者文明不屑地稱為“彈星者”,只是黑暗森林裡必須被清除的一個對象。同樣的例子還有超新星。在《超新星紀元》中,超新星的爆發抹去了除孩子以外的所有人,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災難;而在本作中,4光年外比鄰星的改造並沒有給人類帶來負面影響。鏡子對於藝術的追求,並沒有威脅到人類的生存。更進一步,這場音樂會帶來了積極效應(這或許也是大劉所想要傳達的):當各國領導人認識到宇宙浩渺、文明珍貴,對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有著更深入的了解,解決腳下藍色星球上的文明內部問題,就顯得相對沒那麽艱難了:
“‘與未來所能避免的災難相比,我們各自所需做出的讓步和犧牲是微不足道的。’R國總統說。
‘我們所面臨的,畢竟只是宇宙中一粒沙子上的事,應該好辦。’E國首相仰望著星空說。”——《歡樂頌》
莊子所述蝸角之爭,當如鏡子眼中的人類間爭端。
回到我們最初的話題:在大劉看來,在科幻所描繪的世界中(有時竟像黑暗森林般殘酷),藝術究竟有什麽樣的作用呢?
“人類的價值在於:我們明知命運不可抗拒,死亡必定是最後的勝利者,卻仍能在有限的時間裡專心致志地創造著美麗的生活。”——《歡樂頌》
為了創造美麗的生活,生存以及專為生存發展的科學技術(注意:不是說科學技術僅僅有幫助人類生存的價值)固然為奠基石,但是藝術也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回顧歷史,即便在最艱難困苦的為生存而戰的石器時代,人類依然執著地在洞穴的深處留下並不實用的壁畫。考慮藝術在科技發達的未來社會中的位置,重視藝術以及背後人類對美的追求及其反映出的人類尊嚴,或是本身就是“藝術創作”的大劉“大藝術三部曲”給我們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