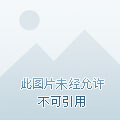媒介、“作者死亡”與知識轉型
——網絡時代的人文學
■主持:吳子桐
■嘉賓:戴錦華(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炎(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吳子桐:網絡時代帶來了種種新變化,在這種形勢下,人文學科的傳統研究方法失靈了嗎?比如文學研究,傳統的文學觀還能應對這些轉變嗎?
王炎:傳統的比較文學講求在國別與語種之間比較,中國文學比較德國文學,或法語文學比較英語文學。但今天的比較文學,應該是媒介之間的比較。舉個例子,名著《悲慘世界》,既有雨果的原著,也有無數戲劇和電影版本,更有百老匯的音樂劇,還有最近2012年好萊塢音樂劇的電影版。許多名著都經歷了不同媒介和版本的漫長旅行。傳統文學觀隻關注原作者和作品的原意,改編不過是原著的衍生品。如今須得轉換思路,每一媒介承載的新版本都只是受原著啟發的新作品。原著不能規定作品的未來命運,每一次改編都是在文化生產過程中經歷一次創新。因為改編作者不能不顧及媒介的特點與限制,如舞台的大小、劇場的規模和位置、觀眾的品位、電影技術的更新(有聲、無聲、黑白、彩色、膠片、數位等),所以新版本必然賦予原作不曾有的新意。有的改編與原作漸行漸遠,最後只剩下品牌或一些符號上的象徵聯繫。比如新近對福爾摩斯的影視改編,除剩下主人公的名字提示一下閱讀的懷舊情懷之外,作品完全是新的。今天的文學研究,應該分析名著在媒介技術的時間隧道裡旅行、不斷獲得新生命的現狀,這比研究語言之間的互譯或接受有意思得多。通過媒介與載體的比較,我們才能揭示知識型的嬗變。
另一層面上,傳統文學觀總認為,電影一定基於文字文本,要麽根據小說改編,至少也得有個文字腳本。其實,新的電影生產方式,不一定先有文學後有電影,可能是先有一部電影,票房獲得巨大成功,然後將電影改編成小說,小說再次暢銷。更不用說奇觀影片往往連帶玩具、T恤衫、電子遊戲、主題公園等副產品,形成一條生產流水線。文字的腳本不是必需的,“故事板軟體”(story?boardsoftware)可以直接製作視覺的故事腳本。
戴錦華:經典文學文本的影視改編始終是大學英語系、中文系學生論文生產的熱門。但是多數情況下,大家都將“原作”與其影視改編視為平行的、同質的文本序列,討論的重點是人物形象上的變化,情節增刪,“是否忠實於原作”,如此等等——滯留於這些角度,而忽略了王炎所強調的媒介層面。其實,從小說到電影、電視劇、網劇,或者從小說到劇場,首先是媒介的轉換,是不同的“語言”系統間的翻譯。因此當我們在文學課堂上講授簡·奧斯汀的時候,以簡·奧斯汀的電影改編版本替代對名著的閱讀,看似同樣把握了情節主部,了解了人物,卻喪失了對小說介質——語言文字的感悟和把握,同時也無視了電影的視聽語言和時空結構及兩種“語言”之間的翻譯轉換。
類似討論同樣經常忽略了的是,對文學經典的影視改編事實上已成為命名經典的進程的組成部分,我們至少可以說,這是一個同步乃至同質的過程。可以說,每部文學經典的形成自身便構成了某種歷史線索;某些作品一經經典命名,便開始了一個近乎無盡的闡釋和意義增殖、疊加的過程。一部作品被反覆、無盡地閱讀、闡釋,愈加豐厚、愈加華美,莎士比亞、拉伯雷們作品中的俚俗語、黃段子漸次隱沒,經典便在經典化的過程中儼然成為經典/正典。而持續的重新闡釋的直接意義不僅在於一次再次地確認經典的價值,而且在於重新賦予其當下性,令現實湧入歷史,激活歷史文本。這就是影視文學改編研究經常忽略的所在:每一次新的改編,每一次媒介的轉換與翻譯過程,都必然是對原作的又一次當代闡釋。闡釋與闡釋勾連,新“譯本”與舊“譯本”對照,構成了自身的線索,成了原作所標識的一道有趣的、巨大的、綿延的文化拖痕。
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們的人文學自身尚未徹底完成20世紀的知識轉型:語言學轉型。因為以索緒爾為源頭之一的語言學轉型,其真正的指向——建立某種普通語言學的訴求,不僅體現為以狹義語言學為範式的結構主義符號學,而且以充分的自反性指向媒介自身。事實上,用德國理論家基特勒的話說,以留聲機、電影、打字機代表的媒介革命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已然發生,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隨著電視的出現,整個社會才開始產生某種媒介意識。但媒介研究很快成了新興學科——傳播學(com?munication)的專利,沒有受到人文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的真正關注。因此可以說,我們前面討論的那種問題——對媒介自身的忽略,幾乎是整個人文學的盲點。如今,麥克盧漢的那句名言“媒介即資訊”已經成了學院口頭禪,但事實上,我們幾乎並未去思考和理解這句話究竟傳遞著何種資訊。這是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則是我們已經提到過的數位技術革命和網絡時代的蒞臨。這場技術革命令媒介——所謂新媒體凸顯在人們面前,“舊”媒體也在回望中重獲發現。於是,所謂“媒介考古學”開始成為學院生產的新寵。然而,即便如此,對人文學科說來,媒介仍更像是一個能指——一個空洞的能指,而不是一個思考與反思的對象和起點。人們忽略了數位技術——具體說是互聯網,尤其是智能手機/移動終端的普及——為此前的單向傳播媒介賦予了不同程度的雙邊互動性。
回到文學上來,在宣布“作者死亡”很久以後,我們才開始從另一個形而下的角度遭遇這個真切的、無可回避的事實。因為20世紀的“作者死亡”,更多是在形而上的意義上宣告一個神話的碎裂,而今天,它卻是一個在網絡媒介的雙邊互動意義上的基本事實:我們不再能在嚴格意義上區分作者與讀者,不再能清晰劃定文本的邊際,不再能如舊日那樣討論互文關係。
諸如,暫時擱置雅俗之爭,大概不會有人懷疑J.K.羅琳——《哈利·波特》的作者是20世紀最成功的作家之一,那是為圖書全球銷售的碼洋所佐證的;從另一個角度上說,《哈利·波特》感召全世界一兩代人恢復了文字閱讀習慣,可謂了得。但人們較少談及的是,她也是20世紀第一個遭遇互聯網寫作生態的作家:大約從這部系列小說的第三部起,她在自己的寫作過程中,分秒必爭地與自己的粉絲群——小說瘋狂的熱愛者競爭;她的寫作過程伴隨著無數同人文的同步寫作,經由無盡的重複閱讀與細讀,同人作者參照原作者的情節和人物設定、伏線,甚至先於作者生產著小說文本——到了第五部之時,情形愈演愈烈,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令羅琳作為獨一無二的《哈利·波特》之母的地位變得曖昧、岌岌可危。錯綜而海量的互文(即使擱置由羅琳親自編劇的系列電影)乾預、介入、製約了小說作者對於作品世界原本近乎上帝的權限。用既有的文學批評或文本研究的路徑,《哈利·波特》自第一卷到第七卷,似乎在想象力的飛揚、情節的自洽性、結構的嚴密性上不斷遞減。但在作家個人生活、創作能量等等原因之外,造成這份下跌的,正是這持續不斷的、偶像級作家與她的全球粉絲間的“相愛相殺”。她必須不斷地繞開諸多先於她而面世的同人文——很多時候,也是繞開她自己的原初構想與設計而不偏離既定結構(粉絲們亦是這既定結構的狂熱而強悍的護衛者),也必須在接受粉絲們挑戰的同時在微妙的限定間挑戰粉絲群,挑釁並滿足、撫慰他們的期待——對人物的、對劇情的、對意義的。
在此浮現而出的新的文化生產機制、傳播—接受心理與社會文化生態,在改寫、抹除了所謂“詩神的迷狂”式的創作狀態之時,也改變了讀者閱讀經驗中文學或曰敘事類文本之為“封閉的小宇宙”,甚或“平行世界”式的沉迷體驗。用一個不準確的描述,互聯網時代的典型閱聽人,是某種作家—編劇型的讀者—觀眾,他們熟悉作者的思路與流行文本的種種套路—橋段,他們在消費文本的同時享有或消費著與作家、編劇間的智力較量,他們扮演著某種推理型文學偵探的角色,他們深知人物的命運、劇情的走向只是作家的選擇,因此不斷提出自己的索求和挑戰。對於邊寫邊更的網絡小說或邊製邊播的電視劇、網劇而言,寫作過程近乎於作者、編劇與讀者、觀眾之間的談判、協作或競賽。因為讀者—觀眾或直呼消費者有隨時棄文、棄劇的權力。或許更為有趣的,是這份“買家”挑剔、討價還價的“理性”心態並置於粉絲這個稱謂所昭示的:閱聽人投入的極為巨大的情感含量和力度。
第三個層次是王炎提到的衍生品的生產。二戰以後,新好萊塢同時面臨著社會政治的激變和電視的衝擊。後者導致了以影院為中心的電影工業的萎縮,作為回應,好萊塢工業發展的一個重要路徑就是圍繞著電影作品發展出巨大的產品鏈,即衍生品的生產。衍生品的種類越來越豐富,越來越繁雜。我認為這使得影院的電影放映逐漸成了某種意義上的系列產品廣告。當VCR、VCD、LD、DVD、藍光和網絡下載等電影傳播途徑開始形成的時候,這個產品鏈就更突出了。對於成功的好萊塢熱賣片來說,影院收入在影片總收入中佔比並不高。同樣,聯繫著媒介意識,網絡時代也改寫了衍生品觀念。不僅同人創作(同人文,相關動漫、歌曲、剪輯影片等等)成為外在於文化工業的龐大的衍生品群,而且類似衍生品亦為文化工業攫取,重組入文化工業體系內部。
今年的突出一例,是好萊塢的《復仇者聯盟3》。在傳統的文本意義上,影片劇情可謂蒼白殘破,但它作為漫威電影十周年之作,無疑在“漫威粉”中引發觀影狂潮。因為劇作的情感衝擊或曰“悲劇”力度不在於劇情中的惡勢力滅霸消滅了一半漫威英雄,而在於參照、“引證”著同人創作及漫威粉“知識”的“拆CP”——每一對在粉絲構想中的情侶死掉了一個。於是,便形成了影院中漫威粉的涕泗滂沱和非粉絲的冷眼旁觀且莫名其妙。可以說,類似漫威英雄電影本身正是衍生品的衍生。這確乎挑戰著文本細讀、互文研究的人文學方法論,要求著文化研究的自我質詢與更新。
其四,我想第N次正名所謂的IP概念。在今日的中文世界中,IP這個概念被等同於某個流行的、擁有自己粉絲群落的作品。因此有炸裂般擴張的影視工業對“大IP”的爭奪和炒作。人們間或忽略了IP原是英文中知識產權的首字母縮寫。而IP/知識產權的出現確乎聯繫著與網絡媒介同時出現或曰借助網絡媒介而出現的一場巨大變革——知識經濟。換言之,這是資本對“知識”生產的又一輪規模、力度空前的再入侵。所謂IP是一個有趣的法學和經濟學的概念。它令此前人文學曾持有的文化藝術的超越性的、非功利的定義和想象甚至難以成為一紙裝飾。這同樣溢出了人文的疆界,再度提示著跨學科或政治經濟學的維度。
與IP或衍生品相關,我想提及在日本文化工業內部率先形成的全媒體產業鏈。諸如某一個網友創造的卡通形象可能衍生為一部漫畫;依其受歡迎的程度可能改編為動畫;動畫可能衍生為輕小說或音樂作品(歌曲、音樂劇);當然也可能衍生為真人電影或電視劇。有趣的是,動畫的聲優/配音演員的選擇增加了形象/顏值要求,以便在動畫流行之際衍生出種種真人影視、音頻產品或樂隊組合。這大約是新的產業生態中的IP的製造。IP不再意味著某一確定作品或確知介質的文本形態。我參加了今年騰訊的產品規劃會,主題之一正是所謂“次元破壁”。又一次,日本的文化工業生產領先,好萊塢正在試圖全速跟進。這才是漫威宇宙會成為這些年來好萊塢唯一熱門的重要原因——漫威公司擁有在冷戰以來的幾十年中形成的諸多IP,並不斷延伸著自己的產業鏈。
另一個與之相關的問題是諸多關於網絡寫作抄襲的爭論,大多討論都因各執一詞,難於認證,無果而終。與所謂抄襲相對的,無疑是文學藝術作品的“原創”觀念;而面對著新的媒介生態——數據庫、寫作軟體、衍生品的衍生,我們如何定義“原創”與“抄襲”,便不僅是新的法律議題,而且提示著人文學自身的省思與自我更新。當然,我們還可以問,我們的時代是否仍擁有真正的文學?回答是肯定的。諸如波拉尼奧的《2666》便向我們展示了我們時代的偉大文學。但這是另一個議題了。
吳子桐:我們談到一個IP可以有多種載體,以往的觀念是文字載體比影像載體更深刻,現在是這樣嗎?如果文學藝術是通過影像來抵達目標人群的,傳統人文教育具有的熏陶作用還有效嗎?
王炎:相信載體能決定文學水準或思想的高低,是一個誤會。文字載體也分好作品與爛作品,在影像、網絡載體或社交媒體上的作品,上乘與下乘之差也判若天淵。所以,媒介不決定藝術水準,也不決定真理的含量。但各種載體本身的特質,卻蘊含了巨大的探索潛質。藝術是開放的,創作就是與媒介搏鬥,然後物我相融。媒體技術日新月異,作品才推陳出新,評價參照系也應時而變。原來影院是電影最佳的放映太空,電視出現後,既播放新電影,也重播老影片,這樣一來,電影不再是按檔期放映的一次性藝術品,而具有電影史的整體意義。經得住時間考驗的才算好作品,自此,電影與文學一樣追求深刻。
後來有線電視出現,美國有線電視網的電影頻道如HBO、Showtime等,盈利模式漸漸超過影院。再後,網絡電影平台出現,Netflix訂閱電影套餐的盈利模式,更勝過有線電視和實體影院。結果,影院漸漸蛻化成新片推廣的太空。所以,載體變化不止於發行管道的變更,也意味著內容的改變。好萊塢大片廠製作的電影,越來越多科幻奇觀,其主要考慮是投放大銀幕,與電視和網絡形成市場區分。所以其鏡頭的運用與特技方式都為大銀幕量身定做。而Netflix或HBO製作的電影,則考慮在線播放和電視播放的特點。Netflix製作內容尖銳、非主流的實驗影片,因為可按類型與品位分不同套餐精準推送到細分觀眾。而有線電視台製作的內容趨於保守,它不能按分眾製作內容,只能取欣賞口味的最大值,所以最怕第一集試播失敗,而盡量貼主流品位。更新的現象是亞馬遜網店,從開始賣紙質書、電子書到音頻、影片,如今也嘗試拍電影,它將內容與自己的商品勾連,或許因為劇本強是其特色。
總之,我們以作者為作品本源的舊觀念,需要重新審視。仍以為文學藝術家是創作的主體,而忽略生產與媒介對內容的製約,不是完整的人文研究。在當下文化生產與新技術難分難解的時代,看不到媒介與生產過程,只會從概念到概念、從文字到文字,如此研究既沒有生命力,也走不長遠。
戴錦華:首先,在某種意義上,我認同於電影死亡這個說法。不是因為新媒體——種種網劇、影片、APP的衝擊,而是基於數位介質全面取代了膠片。對我來說,膠片死亡可能延伸為電影死亡,因為電影藝術的規定性曾經大部分建築在膠片的光學物理功能之上。當這個介質被數位媒介取代的時候,電影和電視、卡通、錄像藝術之間彼此區隔的牆坍塌了。
像王炎提到亞馬遜開始製作電影,它仍然遵守著電影的一些基本規則,我以為,這多少是出自歷史的惰性和慣性——似乎先在的藝術更崇高:電影優於電視,電視劇優於網劇,如此這般——因此數位媒介製作的音像製品仍蜷縮在電影的光焰下。但就亞馬遜這個全球最早以電商起家的跨國公司而言,它製作的數位電影已沒有必要恪守膠片(及影院放映)限定之下的關於電影時長、有別於日常經驗的奇觀、明星等等設定。它完全可以製作五小時、五十小時的“電影”,因為無論長度如何,觀眾都可以接受,因為觀影狀態的規定已不在。但是,當介質的改變抹除了電影長度的規定時,關於電影敘事的定義也將隨之消失。毫無疑問,組合了視聽時空元素的敘事藝術將繼續存在,甚至發揚光大,但電影,這第七大藝術是否仍將存在?這是問題所在。
當然,中國電影業的逆市崛起是一個出人意表的新事實。對膠片死亡之際持續萎縮的全球電影工業而言,龐大的新興中國電影市場無異於一劑強心針。中國電影市場能否刺激進而挽回全球電影工業的頹態,這是尚待時日方能回答的問題。
當然,我討論電影死亡是為了呼喚電影不死。不僅因為電影是我一生摯愛,而且對我說來,呼喚保衛電影,同時旨在保衛社會。在此,我也許會將此處的電影翻譯成Cinema,強調的是鎖定影院太空的電影藝術。因為在類似VR的技術充分成熟並且全面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之後,“宅”可能意味著徹底封閉,城市中,影院太空也許會是最後的社會性太空,最後的異質性人群相遇的太空。某種意義上,影院在20世紀的歐美充當著教堂和心理診所的替代物,和“洞穴”狀態、“鏡像階段”相關,和集體地“獨自”觀影的心理體驗相關,影院太空作為電影媒介系統的另一部分,太空的規定也是社會的規定。儘管如上種種規定也曾用作電影的媒介批判,但影院作為工業革命時代的社會建構,其太空區隔也連接起幻象與現實,區隔並連接起個人,在今天的文化生態中,其社會性價值不言自明。我討論電影死亡是為了標注媒介的在場,也是以某種蒼白的方式,嘗試通過保衛電影以保衛社會(性),保衛我心中仍攜帶著種種可能性的未來。
其次,說到人文學的作用,大學人文教育,或者文學教育,在現代教育系統中曾經被視為一種基本的、必需的教養,而這種基本教養,我認為是所謂同理心的獲得,是令人們能夠跨越國別、階級、性別、種族等所有的疆界,去理解、體認他人,獲得同情心、同理心,進而形成社會意識、社會責任。在其原初的訴求中,通過文學所完成的人文教育是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在這些規定性前提下,對文學作品的閱讀,是不可以為其他媒介所取代的。
問題在於,人文學追求的社會功能今天是否仍然有效?今日大學正在強調博雅、通識教育,但是,何謂通識、共識?何謂同理心?誰人的同理?全球化、互聯網時代,對這些問題的追問也在刷新並顯現了緊迫性。
王炎:這是不是聯繫著技術進步以及大眾社會的形成?
戴錦華:我不這樣認為。因為大眾社會的形成經歷了17世紀到19世紀漫長的歷史過程,所有關於現代社會的討論,都圍繞著大眾社會的形成,所以不能說這一次的技術革命才特別地使人文學議題降落於大眾。我認為正是依托著大眾社會,才有人和人文精神的概念,依福柯所言,人這個現代歷史的發明是在解剖台上獲得更新更新的。我們只能說,在20世紀的歷史變遷過程中,人的概念的內涵和覆蓋面在不斷擴大。先是“土著”要做人,奴隸要做人,然後女人要做人。所以,人文學、人文主義所覆蓋的大眾從原來的歐洲社會的大眾/白人男性變成了全球大眾(不如說在市場和消費意義上的全球中產),同時也成為了難以想象、無從把握的分眾或諸眾。這便再一次回到了既有知識的失效和對新的知識型的呼喚與創造之上。
活字文化
成就有生命力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