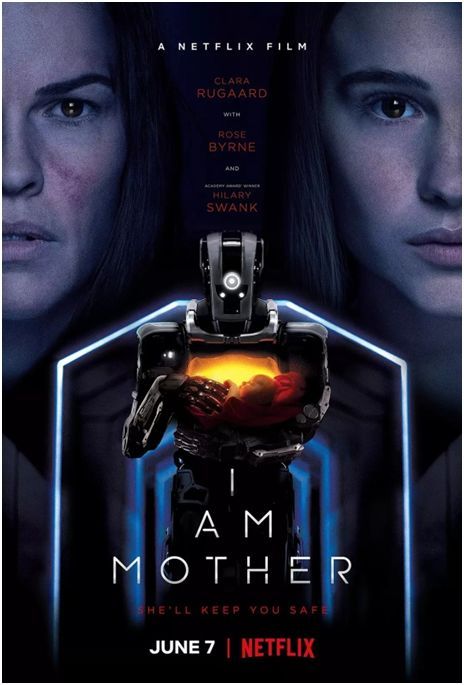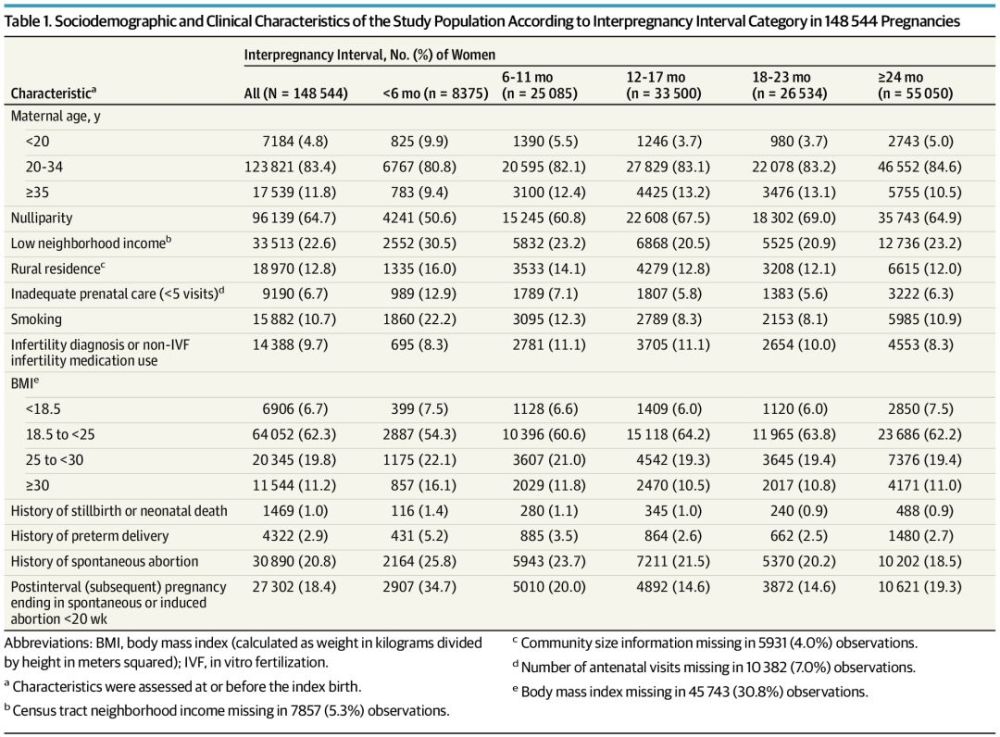作家閻連科


閻連科長篇非虛構《她們》首刊2020-2《收獲》,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跨過了那扇最高的門
——閻連科長篇非虛構《她們》
文 | 俞露
非啼非笑,久久無語——這是讀完《她們》第一遍的症候。
我仿佛海上坐船,處於人與人之間同情心的一種難以言表的上下起伏之中。
我仿佛看到人類的同胞之間,當一個流下了辛酸的淚水,另一個在無聲地哭泣,卻比她哭得還要傷心。
一個片段加一個女人的靈魂:母親、姐姐、姑嬸、妻子、女友、表姐……她們遠近錯落,自歲月的蜿蜒小徑,由作者牽著手,走到了這部相關中國(鄉村)女性的散文集裡。
一、母性
女人的母性像菜裡的鹽,它在親情裡,也在幾乎所有其他感情裡。
相親初見面,說不上幾句話就去倒垃圾、做飯,作者離家時,背來一袋捨不得吃的糧食送行——這個只能拿拚音寫信的姑娘,最終還是因為對其身份的憂慮,被退了婚。
但她獲知此情的最後一封信沒有用拚音,且字字端莊地寫著“你放心,我不會到你們部隊去告你。也不會給你們部隊寫封告狀信。儘管我知道我一告你你就全完了,不能提幹了,要回來和我一樣種地了。我不會怪你閻連科。我隻怪我沒有好好讀過書。隻怪我的命不好。隻怪我們都是農民誰都想過上好日子!”
而她的這種“寬容”不是一種良心上的姿態,而是遠嫁深山、不斷生育的代價,以至於再見面時,“她就那麽慢慢拖著腳步走,背負著我留給她黑暗的人生和命運,像馱著世界上所有鄉村女性的苦難朝我走過來”,以至於我只能拉著兒子,躲進“上帝設在那兒的男廁所。”
這種寬恕著實太過莊嚴,當道義都站在其一邊可幫其泄私憤時,她的選擇卻和包庇偷了銀燭台的冉阿讓的神父無兩,簡直像開放在最高山崗上的道德花朵,足以彪炳史冊。然而,這種偉大功績在女性身上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司空見慣到了不足為奇:
大姐剪去美麗的發辮,變成錢,變成一家人一人一瓶的汽水,變成給弟弟的“能買一個小的雞蛋或兩顆小糖吃”的兩分結餘,變成回憶,流淌進土地,這土地繼而長出麥穗,變成弟弟拾不夠的工分,“急得要尿在褲子上”,再變成二姐往弟弟筐裡面倒的麥穗,而用這麥穗飽腹的姐弟倆,在二選一的時候,變成二姐把讀高中的機會讓出來——這是那個和弟弟一樣拉五百斤煤、磊石頭煮飯,成績還更好一些,會在那個筋疲力盡的深夜,問出“你長大後準備幹啥”的二姐。
這如此自然的命運循環,就像女人內部的循環一樣往複——去給予,在照拂他人的體外循環中反哺自身。
母性,好像是一種她們自己的心靈能辨的語言:男人們自私而自取,女人們利他而自取。
它就這樣成了女人和世界的臍帶,令她們有視天地外物做“嬰兒”般滋養的習慣,而這份看到弱者,看到需求時的擔當與照拂的本能,並非教養而來,更不受限於血緣。
這也是為什麽在和三叔的紛爭裡,父親被逼迫後要抱赴死之心才能走到對方的鐵鍬下,嫂子不用被逼,就能坦然地站出來。
這是一種屬於人的世俗力量,沒有比一個想救嬰兒的母親,更有想象力、創造力和意志力的人了。這種力量既廣且深,它的本質是一種精神性,令女人往往有一種聖徒的傾向——比起她們最流暢不經的動作來,一切宗教儀式、“施比受有福”的教誨,都顯得造作膚淺。她們好似一匹拉磨的馬,蒙住雙眼繞著碾磨轉圈,不知道磨的是什麽東西。其中不作鏗鏘之聲,而是滿含令人傷感的快樂和近乎孩子氣的溫存。
莫裡哀所說的“女人,就是要人愛她”,其實應該注意到更重要的一種可能:比起女人的奉獻來說,她們想從男人那裡得到的愛情,不過像是把手伸進他們懷裡,暖暖凍僵的手指罷了。
因此在塵世間水土不服也不足為怪了——正像是作者的發問,“女人、女性的善良又最常招來惡或悲劇呢?”
或因人類仍處在童年期,或因資源永遠僧多粥少,或因所有的規則制定,不過是柔化了的弱肉強食和實用主義,上演的只是悲劇的不斷再分配——所以在男性社會中,母性是種必然要被矮化、利用的東西,當它和男人的善良、自覺相互交集之後,這種感情被稱為“婦人之仁”。
於是母性的召喚,簡直成了一種自戕的誘惑,她們最禁不起熱情的考驗。女人平衡起它來,就像男人平衡他們的野心一樣困難。是啊,在前女友那裡,就連一筆一劃寫漢字的那股子抬起頭來的自尊,也無法把母性的力量所壓垮啊。
難怪女人的社會化,是比男人更嚴重的削足適履,沒有一雙鞋裡不是獻血淋漓,而這何嘗不是女人們的“伸屈不得,車輪流水”:她們推己及人地相信善和真,假借一些美好的品質給他人他事,常有一廂情願的嫌疑,她們有風鈴般隨時搖曳著的同情心,身為弱者卻為強者灑淚,她們往往在感情上不肯平庸,很容易被“崇高感”和“犧牲欲”所俘虜,將其塗抹上浪漫的光暈,甚至無視在這一過程中,自己已墮入底層,而母性那種可愛而可怕的,含垢忍辱也可當眾就戮也行的力量,那種把鮮花和刀子同時踩在腳下的力量,那種能上天堂也願下地獄的力量,也隨之成為籠中之獸。
而諷刺的是,人的幾乎所有的迷茫和憤怒背後,都是對自身無力的一種詰問。
在世情風氣下,人生成為了一連串縱橫捭闔的把戲,卻也只有聽任其隨心所欲。也許大慟才會有虔信。當人類這個孩童再摔些跟頭後,等它變成一個巨大的傷口的時候,是否會進行一場集體內觀,繼而發現“母性”這種包含著憐憫的覺悟,本是一種中性的巨大力量。
歸自然而自愈,將是多麽堅定而涼爽啊。當我們終於筋疲力盡,連接著天地最深處、散發著土壤河流草木之氣循環不已的母性,是我們會得到的答案之一。就像二姐為弟弟拾起麥穗的手腕之力,那樣自然,還有那只會寫拚音的女友的寬恕之力——是的,再也沒有比人類更需要自我寬恕的生物了。
二、悖論
女人,又充滿著俯仰皆是的悖論。
在我心目中超越畢加索、莫奈的那幅畫,是少女時代在“辣椒和蒜辮下”讀書不倦的大姐。但她之後的數十年人生卻掙扎在“民轉公”的路上,退休後更是靠跑醫院才能打發日子,罹患憂鬱症——勞動是一種摧殘,空虛是另一種。
大姐的一生,歷經了自覺到不自覺的悖論,而小姑追求愛情就要遠嫁深山,又是愛情的自由和地理上的不自由的共存。而趙雅敏為最愛手錶的愛人買齊一百塊表去賣身入監,則是比歐亨利賣頭髮買梳子的荒誕還要荒誕的現實,成為精神堅貞和出賣身體的矛盾,而仝改枝為性的原因而出軌離婚,更是為追求生命質量放棄“道德”質量的取捨,至於這種愛欲和能力的悖論,還出現在為追隨愛人而被兒子殺死的母親身上,更不要說那“少而又少”的女同性戀吳芝敏。
女人的悖論,無非是願望和社會資源及被賦予自由之間的衝突。而“她們”這章的女犯人們,似乎都為試圖解開它,而懵懂地蹈獄。
她們賣淫、私奔、殺人,這些敗壞和罪的底下,是一種最根本的罪行,“性別罪”——在法律和道德上犯罪之前,她們早在心裡伏了法,此後再激進的行為,也不過在坐實這種無力感——
安泰俄斯是希臘神話中的巨人,力大無窮,而且只要他保持與大地的接觸,就不可戰勝的,赫拉克勒斯發現了安泰俄斯的秘密,將他舉到空中使其無法從大地獲取力量,最後把他扼死了。女人們,就是一個個是被舉到空中、雙腳離地的安泰。
女人們的真正悖論,在於她們是“無力的巨人”。
我想勘破三嬸“通靈神化”、治病救人的秘密,三嬸回以“科娃兒,你是男的,你要是女的三嬸就告訴你那筷子怎麽能直立在光溜溜的盤子上”時,考慮的恐怕更多還是兩性世界、男人終難體會女人的無奈。
“因為女人才是神,男人都是凡人啊。是女人生了人,創造了繁華大世界……可男人們有力、有錢、有勢(權)後,從此就開始統治世界,暴虐、敵視這世上的女人了”,三嬸用神鬼之說,吐露的不就是離地的安泰?
女人是神,那也是不得安住、無法使勁的神,她們赤手空拳,茫然若失地扮演著“女人是人,但不是男人”——可又“不得不是男人”的第三性,而這,就是失去力量的根源。
可是人類那種紛紜的、大膽的欲望總是不買脆弱行為的账,女人裡非但不缺吳芝敏那樣的掙扎者,還有割完麥的中午“把自己上吊拘死在了棗樹上”的方榆花。
就像老師這堂課講的不好,會溜號逃學的頑童。會自殺的人,都有一股不安分的活氣,都有種對生活的批判眼光。方榆花對處境也有著最淳樸的自覺——她留下的遺書是“我每天每年都相(像)男人一樣乾活兒。可我不是男人呀!看不到頭,不想活了呢。”她的平靜一死卻令人聯想到,這本書裡的其他女人們,她們那些傷心慘酷的日夜,有沒有那種一眼把前途看清的時刻?
看清在這片土地上,生活、和活著,本是一組悖論。麻木是必須接種的疫苗,只因看清真相無非是看清沒有希望,自殺也就成為方榆花們最大的反抗——只是在最後一刻,她的雙腳依然離著地啊。
而大地又是什麽、在哪裡?
大地的名字就是“人”。
男人女人,都要做回成“人”。
只要女人的雙腳踩回到“人”的大地上來——其實男人女人都一樣,一個人但凡有了做“人”的自由,就好比被冠以了真名實姓,就接了地,就有“天好地好”的力量了。
而所謂做人,又是怎樣?就是不一定要怎樣,就是能夠這樣,也能夠不這樣的伸屈皆可。而這樣地做人,不就是肉骨凡胎與生俱來的常態,我們之所以發出第一聲啼哭,不正是在與此締約?這種腳踩大地的降落,其實只是“回來”的自由啊。
然而她們中的大多數,是回不來的,甚至她們的墳塚,“在男權社會所左右的家族倫理記憶裡,女性總是被記憶很快地遺忘並抹去。以婚嫁和墳陵的記憶路道的鄉村記憶線,沒有女兒(女性)從成年至墳墓的記憶簿”。
作者對女性這位無力的巨人仰頭注目後,繼而悲悼她投向大地的陰影,卻又發現在巨人之上又有真正的巨人存在——
漂浮的巨人,是命運呵,不光是女人、男人,而是人的命運。
三、命運
苦難生平等,它生出的平等就是命運,而命運就是姐弟倆,拉的那個煤車,拉又拉不動,又不能半路給撂下。
而《她們》,哪裡只是在寫女人呢,寫的是人啊,這裡面有著被命運攪擾不已、被人性的軟弱和自審羈絆不已的作者啊!
“我”竭盡全力做著離開土地努力,成了“把連隊早上打掃衛生的掃帚、鐵鍁藏在被窩裡,目的是在第二天早上起床號沒有吹響前,可以獨自在軍營裡掃地和除灰”的好兵後,卻“突然下文鏗鏗鏘鏘說,以後所有部隊都不從士兵直接提幹了”,我登上返鄉的車,又在最後一刻得到“人生的一份最偶然、額外的幸運通知書”,因為創作獎就這樣提了乾。而這一切,又何嘗不滲透著二姐出讓上學名額的犧牲,和偶然因我上過高中而得以入伍的因素?
渺渺人世,有多少是個人意志,有多少是命運使然?還有那隻人永遠無法找到這分界線的眼。
出生、家庭、情感、婚姻、前途……命運這個詞在你想拿它來解釋生活時,處處管用,就像你想把握它時處處不管用一樣。但另一面,它似乎又熟諳“要想打動人心,就要傷害人心”的萬物為芻狗之法則。
命運還包括著個人的局限、環境的局限、時機的局限——往事的意義,就是幫我們在回頭時發現當時當刻的偶然性:如果妻子沒在我“逼婚”後從巷口帶回“同意”的消息,結尾的最後一章,騎在旋轉木馬上吃冰淇淋烤腸的那個要和我“結婚”的孫女,又將是誰?
對老天來說,我們精於算計拳打腳踢的全部努力,就像在對百萬富翁炫耀自己的貧困。只是那些糾結、輕率的選擇,偏還彈撥和涉及著其他人的一生:好比命運女神在紡線,個人之線的經緯,總要紡進別人的那根,對方也是如此,甚至連一本書也不例外——
大姐借我的《安娜﹒卡列尼娜》,千叮嚀萬囑咐仍不翼而飛,結果是被豬拿去抱了窩。父親安慰說“怕是老天不想讓我們家出個讀書人,就把那書收走了”,這向天推諉似的下一句,則帶著對命運的求告意味,“老天收走了書,只要把人留著就好了”。
也許父親恰恰處理了個人意志和宿命之間的繁複:我接受,我也請求,同時,我保持謙卑。
母親說“老天安排男人的命,就像安排他親生兒子的命。安排女人的命,就像安排後娘女兒的命。”其實比起命運對人類最普遍的捉弄,它對男女之別只有相對的偏頗。至於那些五十步笑百步的男人,是愚蠢軟弱的,而意識到不可阻擋的共同受難,以及為其公平和均勻一辯的男人,是了不起的,他們更像人類推選的代表,在向老天發問:
為什麽表姐被離婚、幾乎尋死,再次遠嫁後不知所蹤,起因只是嗜睡?這個在日本作家筆下能把玩出詩意的癖好,在這裡為什麽令人成為一隻瘸腿的牛、一部買回去不轉的風扇?
為什麽小姑為愛逃嫁貧瘠之地,反倒在饑荒年代囤下了糧食,為什麽“吃不愁穿也不愁”反倒是對她這位“中原鄉村那方隅地自由與婚姻的奠基人”的告慰?
為什麽母親的時間會停在傻子叔叔被榆樹砸中的那天,會停在被親生父親的新家排除在外的那天?
為什麽女性的勞動量是最高的產出和最低的回報?而為了勞作,母親承受農藥的毒性,早衰的痛苦,眼睛的昏花,用薑絲的刺激換來淚下後的清明,為什麽連這點清明也只是為了繼續勞作,為什麽這眼淚竟一點也沒傳染給鐵石心腸的命運?
為什麽我們被穿上無形的鼻環,被牛馬一樣地往看不見的路上引?“風天雨天都在家裡坐著有飯吃,有衣穿,那和神仙有什麽差別呢,”為什麽有飯吃有衣穿後,仍然不是神仙?反倒不如那淳樸的心靈、簡單的頭腦、隻容得下一種感情,一個念頭?
痛苦才是人間最通行的語言,因此提的也只能是些沒有答案的問題啊。
就像不知怎麽,母親就對生父有了靜默不滅的等待,還有那雙搶救外甥女時能跑的飛快的腿,“朝鎮上的醫院瘋了一般跑過去。腳步的快,怕是她這一生唯一一次如此拚命地跑”,就像不知怎麽,外甥女就寫來了“那貼顛倒了的八分錢的小郵票”的為母親要錢的信。
活在世上,如果對人和命運都不相信,那人間也就成了地獄。所幸寫字尚且“歪扭得如被風吹落在地上的枝葉般”的她,已萌發了興致勃勃地去愛別人的樂趣,在微茫的天地和未卜的前景裡,也是不知怎麽,她們就學會了相依為命。
好像二姐那雙有繭,但依然柔和的手,在一點點地撫摸命運似的,令它昏昏欲睡,或胳肢的它發癢,人也就得以喘上口氣,不知怎麽,就有了哀而不怨、樂而忘返的能力,就像過著“八個孩子、兩個大人十口人,冬天大雪孩子們沒有鞋襪穿,必須光腳踏雪是很正常的事”的日子,卻“永遠要哼著小曲唱著戲,如她是公主嫁王子”的大娘。
而人類的處境就是這一點驚人——沒有一宗幸福不是靠糊塗得來的,也是因此,人才可以活的遠談不上快樂,但卻相當幸福。
也是不知怎麽,女人就在命運面前千姿百態了:母親第一次看到海就發出了“天……水也太多了!” “這沙要是糧食,人就不愁沒有吃的了”的感慨——一個對生活敏感的農民,是可以過的比一個麻木不仁的帝王更廣闊、更充實、更豐富多彩的。
女人對哲學的興趣,和孩子對精神王國的洞見往往一樣,這也許和她們總在還是孩子的時候早熟,在成熟之後卻保持天真有關。至於這種“又熟又生”,好比天亮和黃昏時都有的明暗交接線,將伴隨她們一生。譬如母親葆有的坦率好奇、愛憎分明,還有那股英雄氣概,這又使她的心靈,波及著整個家庭的心靈。
女人小起來很小,勢利之極,就像相親時拒絕我的姑娘,在後來看到版面浩瀚的“文章介紹我,還登著我的彩色大照片”時質問“為什麽給她介紹對象時,沒說我會寫作和愛寫作”,頂多不過是買賣失算的惋惜;女人大起來很大,就像母親半夜起來看海,想的卻是“既然神總是對人好,那為啥不當初創世時,讓缺水的地方多點水,山高的地方多條路。住在水邊天天泡在雨裡、水裡的人,也讓他們少些水災和大風”的問題。
然而她們對日常生活絕不放肆,反倒無師自通地中庸:母親為促成叔伯哥的相親借家具裝門面,而蓮嫂子到結了婚才說出當年看破不說破的心思。她們深知世事都有表裡兩面,自有一股和現實討價還價的頑皮和狡黠,她們個個都像“通曉世故的詩人”,既靈活,又有那麽點神秘莫測。
這就是母親(女人)面對命運的基本態度了:人吃五穀雜糧,再沒有比懂得生活更實用的學問了,但對無用之用乃大用的莊子,則不止愛惜、簡直是要敬畏了——“我把帶回去的書分給大家時,母親會接過其中最厚的一本在手裡掂掂重量道:‘我老了,不能識字了。你寫那麽多書我認不下來一句話。早知道你這輩子是乾寫書這事兒,我就該在年輕時候多認一些字,也好知道你在書裡都寫了一些啥。’”
所幸不識字。這樣的心靈若是識字,要徒增多少和平庸的現實的矛盾之痛苦啊。而不識字也知道你做的是件無法稱量的事,而我只能用份量來慚愧地掂掂了。
還是不知怎麽,從土地裡來的母親,“坐在那深邃靜亮的大海邊,望著寂寥茫茫的世界和天空,等著我的解答如等著大海水乾樣”時,就因為憂鬱,而帶上高雅、雋永之氣了。這又是多少雕刻家未曾涉及的題材——這不是一望而知的美,卻是真正的藝術家為之傾倒的那種,不亢不卑,似乎承載著整個人類的自尊心的最高水準。
問題就這樣被消解了,命運就像頂玫瑰色的草帽了,人就像那草帽上的緞帶了,雖被束縛,又飄逸自在著。
即便“生活就是伸曲不可、又車輪流水的這樣呀”,還在隱約地耳語呢。
結語
在這光明與黑暗交織的大千世界,在這眾神對人不停開著的玩笑之間,為了生活,她還有什麽沒犧牲的呢。
記憶和眼淚,她沿著生命的歷程一路失去它們,就如一個旅客把錢財撒在沿途的一家家客棧裡,而作家替她們搜集起來,成了《她們》。
作者像是互為不解之謎的解謎者又仍然疑惑重重。是啊,女人是多麽奇異多變:她們可能刁鑽古怪卻又毫無私心、無欲無求卻又多情多思、睚眥必報又善於忘記,精明過人又笨拙出奇……她們也備受軟弱人性的搖撼,在追尋幸福的路上顛沛流離啊。
《她們》寫的其實是個體,波及了女人,歸根結底,是從“人”的立場出發,回到了“人”。作者在超然處統一了它們。
一切悲憫女人的作家,都是人性的悲憫者,讓女人回到“人”——這不是一種思維,不是一種主義,而是一種感情。
比起心靈,頭腦有時倒是需要警惕的東西了。
至於作家,未必告訴人們該怎麽做,卻是對自己最誠實的一群人,誠實到心驚肉跳的程度,而誠實也有著血和淚的代價。
而正是這代價,讓作品跨過了性別、包括自己,這扇最高的門——
這是一部通過女人看人性、看命運的作品,
這是一本寫給每個“人”的,寫“人”的讀物,
《她們》,是《人們之她們》。
最後。對女人最善意的舉動,就是不去歌頌(鼓勵)她們的美德,甚至替她們警惕著那些美德,就是像作者那樣赤誠地,替她們戒備,替她們疲憊,甚至在她們本身被磨滅得既無悲苦亦無矜憫時,替她們在人世間的風劍霜刀下打開一頂傘,而寒意讓傘下的她們,摟在了一起,摟得更緊。
至於希望,至於許願?
只有人性改變,才會有烏托邦,而人性若是改變,也就不再需要烏托邦。因此所謂烏托邦,遠不如孫女說的“餓了吃烤腸,渴了吃盒冰淇淋”的紫竹院公園。
只可惜對於那個“騎騎、吃吃和喝喝的日子”的世界,對於孫女這個吃著冰淇淋的哲學家所指出的世界,我們無能為力。
當我們終於意識到自己做不了什麽的時候,原來已經做了很多:
由著《她們》,她們的時光綿延不盡地展現在有關乎過去、以及未來的圖景上。
由著《她們》,在迢迢的煤石小路,灑下了金粉——是為回家的路標,是為存在過的淡痕。
這是一部值得深深感謝的書。
2020年5月15日
來源:鳳凰網,作者授權分享


1
《收獲》長篇專號春卷。微店75折,簽名版隨機發送,全年四卷7折
《收獲》長篇專號2020 春卷的特色之一,是特邀本期作者熊育群、須一瓜、張忌、孫頻,在扉頁簽名後裝訂進雜誌。簽名版雜誌將隨機發送,你會不會拿到?又會是誰的簽名呢?
春卷57萬字,440頁。採用230克瑞典白卡紙,80克金龍書紙。
2
2020年第3期,作家嚴歌苓手書卡片,贈予《收獲》讀者
作家嚴歌苓手書卡片,贈予《收獲》讀者
2020-3《收獲》刊載嚴歌苓最新長篇《小站》,其中人與熊的故事動人而憂傷。《收獲》文學雜誌社特請作家嚴歌苓手書“愛動物吧,因它們遠比我們單純、率真、忠勇、知恩、易感且鍾情。”,限量印製兩款卡片,贈送給《收獲》微店訂閱全年雙月刊6本的讀者。其余少量微店零售第3期時,讀者先到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