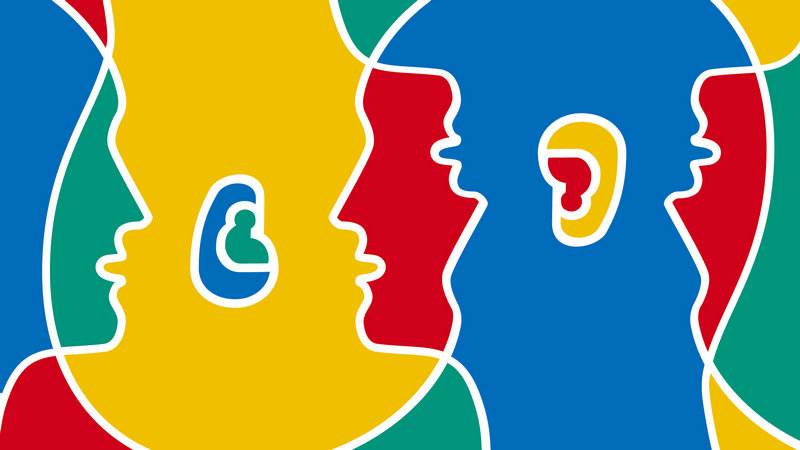編者按
《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是歐美文化研究中的經典作品之一,按照二十六個英文字母排列而成,形式頗像辭典。不同於辭典所要努力呈現的客觀的、非個人的、權威的學術面目,雷蒙德·威廉姆斯的工作是通過詞條的選擇以及對詞條間相互關係的分析,表達對人們的思想和經驗的廣闊領域的關注,展示發生在語言中的社會歷史的某些過程,指明意義的問題是和社會關係的問題內在相關的。
關鍵詞與文化變遷
文|汪暉
(原載《讀書》1995年2期)
“沒有共同語言”是我們生活中的日常事實。只是這一現象過去經常發生在兩代人之間,而今更經常地發生在同代人之間,發生在一個極短的時段內。有時是因為出現了新的語匯,有時則因為同樣的語匯有了完全不同的意義。媒體與資訊空前發達,“交往”與“對話”空前艱難。我們似乎正在面對一個聽起來有點荒唐和誇張的局面:在說話之前,必得先清理和說明各自的詞匯和句法,否則就難以溝通。“這人太保守”,這話幾年前聽起來刺耳,現在聽起來就未必。“這人是精英分子”,這話幾年前聽起來很動聽,今天聽起來就有幾分嘲諷。語義的變化中隱含的是價值的轉移,深究起來,這種價值的轉變體現著人們對政治和社會的態度的變化,而後者顯然是社會變遷的一個有機部分。一九九二年,我初到美國時見到幾位舊日的朋友,把盞之間說起中國,恍如回到了五六年前的北京,因為大家說的話、判斷問題的方式一切如初,仿佛時間並未流逝。語言方式將許多東西凝聚起來,造就了一座過去的生活的活化石。後來一位朋友從紐約給我打電話說,“這就是停止生長。”我心裡明白,停止生長的只是經驗的一方面,經驗的別一方面則是春華秋實、生生不息。其實,就是在北京,即使是在學術圈內,各說各話也是日常的現實。你把話語/權力的一群、原道/原學的一群、終極關懷/人文精神的一群、市場/改革的一群放在一起,無異將他們放在相互隔絕而透明的玻璃罩內:看得見嘴巴和身體的扭動,“聽”(理解)不見“聲音”連成的句子(意義)。遠遠看去,我們只能從那些或調侃、或莊嚴、或憤然、或貪婪的姿勢中知道他們是不同的人群,而各自使用的語言就是將他們隔開的玻璃牆。

300 x 410 jpeg
我們已經習慣於這種“沒有共同語言”的狀況,甚至一點也不驚訝,所謂習焉不察。但半個世紀前戰事初定的歲月裡,一位剛從英軍裝甲師退役、重返劍橋大學的年輕人卻對這種狀態深感不安。那年他僅二十四歲,名叫雷蒙德·威廉姆斯。四年半的時間不算太長,但戰時的軍隊生涯與大學的寧靜之間隔著死亡與恐懼的深淵。兩種完全不同的經驗匯聚在一個人短暫的“回歸時刻”,威廉姆斯在戰後的劍橋大學感覺到一種既陌生又熟悉的氣氛。在這樣的心境中,他終於見到一位戰時第一年曾在軍中共事的朋友。我們可以想見他們交談時的急切心情。談話的主題不是回憶剛剛過去的戰爭歲月,而是談論使他們感到新奇而陌生的周圍的世界。幾乎不一而同,他們說出了我們今天已不陌生的感覺:“事實上,他們(周圍的人們)說的不是同一種語言。”當然,這些人都是英國人,講的是英語。威廉姆斯所謂不是一種語言是指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群體在運用他們的母語時,各有不同的價值判斷和價值標準,不同的感情強度和重要觀念,不同的能量和利益——我猜想,還伴隨著不同的姿勢和表情。儘管佔強勢的群體可以將自己的判斷標準作為唯一正確的標準,但實際上按照語言學的標尺來看,這些不同的群體及其所使用的語言沒有一個是“錯”的。威廉姆斯和他的朋友所感覺到的陌生和不安感很大程度來自這個語言的變異過程:詞匯、語音、節奏、語義以及它們喚起的感覺方式。與這個語言變異過程相伴隨的,是人們對於政治和宗教的某些一般態度也發生了改變。這一切使威廉姆斯想到的是一種“生活方式”(Way of life)的變化,他把這種生活方式理解為“文化”,這種“文化”與社會如此地緊密相連,以至你不可能離開社會的範疇來討論文化,正如你不能離開文化來解釋語言,反之亦然。語言、文化和社會就這樣在威廉姆斯的研究中關聯起來,成為他理解文化和社會變遷的獨特視野。在長達二十多年的研究生涯中,雷蒙德·威廉姆斯寫作發表了《文化與社會,一七八〇——一九五〇》(Culture and Society,1958)、《漫長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1961)、《傳播》(Communications,1962)、《鄉村與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1973)、《關鍵詞》(Keywords——A Vocabularyof Culture and Society,1976)、《馬克思主義與文學》(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唯物主義和文化的若乾問題》(Problems of Materialism and Culture,1980)、《文化》(Culture,1980)、《文化社會學》(Sociology of Culture,1983)等大量著作,開創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新範式,而他的問題意識和方法就是在戰後的那種獨特的語言氛圍中形成的。

《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的不同版本(從左到右: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Fourth Estate Ltd, 1988;Routledge, 2011;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一書發表於一九七六年,而今已幾經再版,成為歐美文化研究中的經典作品之一。這本書起初是威廉姆斯發表於一九五八年的成名作《文化與社會,一七八〇——一九五〇》一書的附錄(當時有六十多條),後來被出版社的編輯刪去。但雷蒙德·威廉姆斯並未放棄收集和解釋這些關鍵語匯的工作,在其後的二十多年的歲月裡,他逐漸積累,擴展他的詞條筆記和短文,到一九七六年成書時他從中挑選了一百三十一條作為文化與社會中的關鍵詞單獨出版。這本書當然不是交代詞源、給出定義的尋常詞典,而是了解文化與社會的一種獨特的地圖。如同作者本人說的,這些詞其實有一個變化的普遍的模式,這種模式可以被當作一種特殊地圖,通過它人們有可能看到生活和思想的更為廣泛的變遷——一種與語言變遷明顯有關的變遷。換言之,《關鍵詞》一書雖然是按照二十六個英文字母排列而成,在形式上頗像詞典,但這個“詞典”卻是有內在結構的。這種內在的結構一方面體現在作者對詞條的選擇上,另一方面則體現在他對這些詞條及其相互關係的解釋之中。這兩個方面如同經線與緯線一樣,編織出十八世紀後期直到二十世紀中期的歐洲的社會與文化的變遷軌跡和地圖。說明《關鍵詞》一書屬於何種學科的著述並不容易,它曾經被歸在文化史、歷史符號學、觀念史、社會批評、文學歷史和社會學的名目之下。這本書中收錄的詞條及其相互關係經常與這些學科相交叉,但是,它不是任何一個學科的詞匯表,它是人們的思想和經驗的廣闊領域的表達,是社會實踐中最重要、最具影響力的詞匯的日常用法的分析,是討論人們的共同生活的主要過程時必須使用的詞匯的匯集和解釋。作者關注的是這些詞匯的一般用法,而不是特殊規定。與其說它是有關詞源和定義的注釋性讀物,不如說它是對一個詞匯表進行質詢的紀錄:它既是我們的最普通的討論的詞匯和意義的匯集,也是將我們組織成為文化與社會的那些實踐和體制的表達。在《關鍵詞》一書的序言中,威廉姆斯一再強調這本書的寫作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實際上是暗示這些關鍵詞的意義不斷地在變化,以至根本不可能離開這些詞匯所討論的問題來理解這些詞匯,而這些討論最終可能將解釋者引到未知的終點。威廉姆斯在兩層意義上將這種寫作中的經驗理解為詞匯的問題:已知詞匯的待選的和發展的意義需要穩定下來,詞匯之間的明確而含蓄的關係形成了意義的結構,這不僅涉及討論問題的方式,而且還在另一層次上涉及我們看待自己的中心經驗的方式。所以,作者所作的不只是收集詞匯,查找和修訂它的特殊紀錄,而且是分析內含在詞匯之中的命題和問題。他是在這樣兩層相關的意義上將這些詞匯稱為“關鍵詞”的:它們是在特定的活動及其闡釋中具有意義和約束力的詞匯;它們是在思想的特定形式中具有意義和指示性的詞匯。看待文化和社會的特定方式當然不僅僅與這兩個概念的運用相關,而且還與其他詞匯的運用相關。在上述意義上,關鍵詞的兩個要素是詞條的選擇和意義的分析——這既是記錄的方式,又是探討和呈現意義問題的途徑,文化與社會的意義就這樣形成了。

一次會議上威廉姆斯希望關鍵詞("nature")的複雜含義能得到重視(影片截圖,來源;http://uls-media2.library.pitt.edu/keywords/williams1.mp4)
因此,《關鍵詞》一書雖然收集了大量詞條和例句,但是它們並不是隨意地被編排在一起,所有這些關鍵詞都與“文化”和“社會”這兩個更為關鍵的概念和範疇相關連。這一點在他的《文化與社會,一七八〇——一九五〇》一書的結構中體現得甚為清楚。該書一一分析了從十八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英國思想和文學界的重要人物和他們的文化和社會論述。其中包括三個時期:伯克、科貝特、騷塞、歐文、浪漫派藝術家、穆勒、卡萊爾、蓋斯凱爾夫人、紐曼、阿諾德等人為第一時期,馬洛克、新美學的代表人物、吉辛、蕭伯納、休姆等人為第二時期,勞倫斯、托尼、艾略特、理查茲、利維斯、馬克思、奧韋爾等人為第三時期。威廉姆斯用文化與社會作為中心主題將這些人物及其論述組織起來,用以考察一個正在不斷擴張的文化觀念及其具體過程,這也涉及他對文化理論的理解:他把文化理論視為整個生活方式中各種成分之關係的理論。他似乎深信這些人物及其論述足以呈現特定時期的文化和社會的特徵,因而並不在意別人批評他的著作忽略了另一些重要的文化人物。從該書的整體結構來看,時期的劃分和人物的編排僅僅是一種簡便的敘述結構,在這個敘述結構中的更為內在的結構是由五個關鍵詞所構築起來的文化地圖。這五個關鍵詞是工業(industry)、民主(democracy)、階級(class)、藝術(art)和文化(culture)。這些詞在現代的意義結構中的重要性隨處可見。在一百七十多年的時間中,它們的用法在一些關鍵的時期發生變化,從而證明人們對共同生活所持的特殊看法的普遍改變。這些看法包括:對歐洲的社會、政治及經濟機構的看法,對設立這些機構所要體現的目的的看法,以及對人們自己的學習、教育、藝術活動與這些機構和目的的關係的看法。

《關鍵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我在此不能一一介紹威廉姆斯對這些關鍵詞的具體分析,但我想簡要地指出:他對這些詞匯的解釋特別集中於這些概念在特定時期的變化。如工業一詞從“技術、刻苦、堅毅、勤奮”等用法改變為一個集體詞,用以指稱製造與生產機構,以及這些機構的一般活動,這一變化發生在工業革命時期。民主概念從希臘時期的“由人民治理”到成為一個常用詞也是在相近的時期;階級一詞原指學校和大學中的級分和群體,直到十八世紀九十年代才成為社會等級的劃分概念。這不是說此時的英國社會才出現了社會等級的劃分,而是說這種意義的變化記錄了人們對這些等級劃分的態度的改變,因為這個概念不如等級(rank)那樣明確。威廉姆斯解釋說,這個詞的構造是在十九世紀的概念上建立起來的,是根據英國已經改變了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感覺建立起來的,當時的英國正在經受工業革命的洗禮,而且又處在政治民主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藝術一詞的變化模式與工業一詞甚為相近。從人類的一種標記即“技藝”轉變為一種機構,一種團體活動,以及想象性的和創造性的藝術(大寫的藝術終於代表一種特殊的想象的真實),這個過程產生出了藝術家與藝匠的區別,產生出了天才與才能的區別,產生出美學和美學家等新的意義。這些變化與前面提到的概念的變化同屬一個時期,它記錄了藝術的性質與目的、藝術與人類活動的關係、藝術與整個社會的關係等觀念上的一個顯著的變化。在所有這些詞匯的變化中,最引人注意的還是文化一詞。它的變化也發生在同一個時期。該詞原指“自然成長的培養”(tending of natural growth),後來引申為人類訓練的過程。但後一用法在十九世紀改變,從某種東西的文化(culture of something)改變為一個自稱一體的詞。此時的文化概念包含四個層面的意義,即“心靈的普遍狀態或習慣”,“在作為整體的社會之中的知識發展的一般狀態”,“藝術的總體”,“由物質、知識和精神構成的整個生活方式”。威廉姆斯指出,圍繞文化一詞意義的諸多問題,都是由工業、民主、階級等詞的改變所代表的歷史變遷引起的,而藝術概念的改變即是與此相關的反應。“文化一詞含義的發展,記錄了人類對社會、經濟以及政治生活中這些歷史變遷所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續的反應;我們不妨把這段發展的本身看成一幅特殊的地圖;借助這幅地圖,我們可以探索以上種種歷史變遷的性質。”


《文化與社會,一七八〇——一九五〇》的不同版本(第一行為英文版,從左至右:Penguin Books Ltd,1971;THE HOGARTH PRESS LTD,1987;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Spokesman Books, 2013;Vintage Classics,2017。第二行為中文版,從左至右: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1;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2011)
《文化與社會,一七八〇——一九五〇》和《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都是以探討“文化”這個在觀念上和關係上都極為複雜的詞為中心。但是,威廉姆斯發現,他越是緊扣文化問題,所涉及的範圍就必須逐步擴大,因為他在這個詞的歷史淵源及其意義結構中,看到的是一場在思想與感覺的領域中的廣大而普遍的運動。文化觀念不只是對新的生產方式、新的工業的反應,它還涉及各種個人的和社會的關係:既承認道德的和知識的活動與新社會的原動力的區別,也包含了對緩解社會過程的痛苦所作的選擇。“文化”觀念不僅是對工業主義的反應,而且也是對新的政治發展、對民主的反應,還涉及對社會階級的各種新問題的複雜而激進的反應。更進一步,文化的意義的形成不僅涉及這些外部的關係,而且還將回溯到一種個人的或私人的經驗之中,這種意義明顯地影響著藝術的意義和實踐。早期的文化觀念意指心靈狀態或習慣,或者意指知識與道德活動的群體,而今卻也指整個生活方式。這樣的文化觀念一方面成為解釋我們的共同經驗的一個模式,另一方面也通過這種解釋活動改變著我們的共同經驗。威廉姆斯顯然認為這種意義的轉變並非偶然,文化一詞的原初意義以及這些意義之間的關係的演變具有普遍的重要意義。
在這兩本書中,作者使用的參考框架不僅意在區別這些意義,而且是要將這些意義和它們的來源和影響聯繫起來考察。在《文化與社會,一七八〇——一九五〇》中,他所採用的方法不是分析一系列抽象的問題,而是考察一系列由各個個人所提出的論述,研究當事者的實際語言,研究這些人在試圖賦予他們的經驗以意義時所使用的詞匯與系列詞匯。在《關鍵詞》中,他注重的是這些詞匯的意義的歷史和複雜性,有意識的改變和不同的運用,創造、廢棄,特殊化,擴展,交叉,轉換,在許多世紀的有名無實的延續性遮蓋下的變化。所有這一切都使我們感到,給一個詞下定義是多麽困難的事。
在這樣的一種方法論視野中,《關鍵詞》獲得了與一般辭典不同的特徵。

首先,作者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討論也是在一個歷史地變化中的研究,從而他沒有像一般的辭書——如牛津辭典——那樣,在解釋活動中以客觀的、非個人的、權威的學術面目來掩蓋自己的社會政治價值和個人色彩,而是盡可能地試圖呈現自己的局限、立場和預設。

其次,一般辭典基本上是文獻學和詞源學的,長於解釋詞的範圍和變體,卻拙於分析詞與詞之間的聯繫與互動;而作者的工作集中於詞的意義和它的語境,他經常從似乎沒有價值的例證中得到相反的結論。

第三,一般辭典總是把書面語作為權威性的真正來源,似乎口頭語是從前者發展而來;威廉姆斯在現代語言學的影響下,也同時注重口頭語的分析和解釋。他曾舉例說,如果你要了解心理學(psychology)一詞當然就得尊重書面語的運用,但如果你分析的是工作(job)一詞,那麽很顯然在進入書面語之前,它首先是在日常口語中產生的。

第四,作者也超越了單一語言的界限,不僅是分析英語中的關鍵詞的用法,而且還根據需要分析關鍵詞在不同的語言中的複雜的和相互影響的發展。例如他曾經舉出基礎與上層建築這兩個馬克思的詞匯,他不只是追溯這兩個概念的德語詞源,而且還討論它們在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俄語和瑞典語中的形式和用法,從而顯示出在這項工作中比較分析的重要性。

第五,在當代語言的複雜多變和雅俗混雜的條件下,什麽才是正確的用法?傳統的做法是尊重該詞的詞源,而作者似乎力圖在二者之間達到一種適當的平衡,也關注那些粗俗用法的形式和含義。

第六,作者特別關注的是在具體的歷史的和社會的情境中的詞的意思(meaning)及其變化,而不是概念的正確意義(signification),這使他能夠將詞的分析與作為一種總體的生活方式的文化聯繫起來。當然,他並不是將意思問題完全轉變成語境問題,他也分析一些詞匯本身的內在發展和結構。
我一再強調威廉姆斯的語言分析與社會歷史過程的內在的聯繫,這並不是說他認為語言就是這個社會歷史過程的簡單的反映。我要說的是《關鍵詞》一書也同樣是在他的“文化與社會”的論述模式中產生的,該書的主要目的是展示發生在語言中的社會歷史的某些過程,指明意義的問題是和社會關係的問題內在相關的。新的關係伴隨著看待存在著的關係的新的方式,從而也就出現了語言運用中的變化:創造新詞,改變舊詞,擴展和轉化特殊的概念,等等。這就是為什麽《關鍵詞》一書特別注重語詞間的“相互聯繫”的根本原因。威廉姆斯在《文化與社會,一七八〇——一九五〇》一書的結論中說:“文化觀念的歷史是我們在思想和感覺上對我們共同生活的環境的變遷所作出的反應的記錄。”“我們共同生活的整體形態的改變產生了一種必然的反應,使人們注意力的重點放在整個形態上。特殊的改變將會修改一個習慣性的規則,轉化一項習慣性的行動。在普遍的改變自身完成之後,會促使我們回顧自己的一般計劃。……文化觀念的形成是一種慢慢地獲得重新控制的過程。”今天,我們似乎又一次面對“共同生活的整體形態的改變”,各種語言的混雜之中,隱含著我們看待生活及其無情變化的方式的差異。我們正在形成新的文化和社會觀念,進而重新把握和控制我們生活其間的世界。對關鍵詞的研究和分析也可以說是重新獲得控制的努力的一個必要的部分。
在本文的末尾,我想簡要地指出,威廉姆斯是繼利維斯(F. R. Leavis)之後的另一位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理論奠基者和伯明瀚學派的主要代表。他批評將文化脫離開社會的理解模式,批評將高級文化與作為總體的生活方式的文化相分離的理論後果,從而提出了“文化與社會”的研究模式。他的“作為總體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概念也可以說是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二分模式的一種重要的修正。在他之後,葛蘭西的文化霸權概念,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概念,布狄厄的文化資本和文化生產概念,等等,都對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論的視野。威廉姆斯的工作對於當代西方的文化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文化與社會,一七八〇——一九五〇》、《關鍵詞》等著作迄今仍是學者經常談及的著作。在我們面對社會的轉型、文化的變遷和語言的混亂的當代時刻,他的著作還能給我們以啟發。就關鍵詞的梳理工作而言,他對詞匯的分析與對文化的分析緊密相關,這種基本的取向和方法也適用於我們的當下的工作。所不同的是,晚清以降,中國的許多關鍵詞的語源是雙重的,既有漢字的語源,又有外來語的語源,這些概念的翻譯過程顯然較之威廉姆斯追溯的語源更為複雜。在這樣的條件下,語言的翻譯、轉義和傳播過程將更形錯綜交織,作為一種總體的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形態也更加豐富而混亂,中國的關鍵詞的梳理也更加困難。但路總是人走出來的,一位先哲早就這麽說過。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夜於古城
(Raymond Williams:Cultureand Society:1780-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Raymond 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of 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與社會》,吳松江、張文定譯,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10.80元)
* 文中圖片均來源於網絡
文章版權由《讀書》雜誌所有,轉載授權請聯繫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