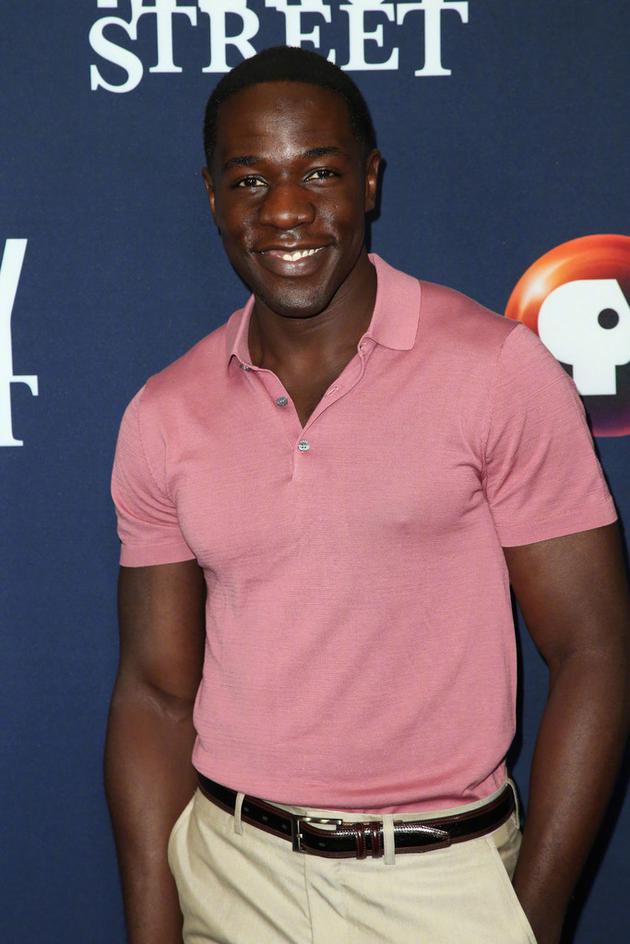《過勞時代》
作者:(日)森岡孝二
譯者:米彥軍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9年1月
日常焦躁的滋味人人都懂。呼叫等待、無休止的電話會議、不顧時間地點的強製性視頻會議、周末緊急出差……很多“社會人”可能會發現自己卷入了過勞的工作與加速的生活。為釋放這種茫然無措,我們炮製了海量具有鮮活生命力的日常吐槽。“狗屁工作”、“社畜”……不論來源是人類學研究還是流行語、影視劇,都斬獲人心,得到病毒式的傳播。
時間都去哪兒了?與速度纏鬥、與工作肉搏的情緒,不全然是負面的。有在“零工經濟”中樂此不疲的“斜杠青年”,也就有歌頌“懶惰”的消極分子,這些不同的工作態度與相近的速度體驗,都能在歷史中找到其源頭與脈絡。本期專題的發問是:我們如何卷入了加速的工作與生活?今天中國及世界出現了怎樣的工作趨勢及特徵?技術加速如何製造了時間緊迫感,而那些以懶惰作為對抗的(反)工作倫理,背後勾勒了怎樣的烏托邦?制度調整能幫我們解決工作意義危機的難題嗎?
“時間貧困者”被吞噬的閑暇
這是一個百年大哉問:為什麽技術進步沒能將人從勞作中解放出來?幾乎所有談論“工作”與“閑暇”關係悖論的文章,都近乎陳詞濫調地引述經濟學家凱恩斯的《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一文。1930年冬,凱恩斯在歐美經濟的蕭條寒冬中樂觀地展望未來100年的好日子:伴隨科技和生產力的提升,人們每周只需工作15個小時,現在就必須抓緊時間思考要如何利用那些將多到令人發狂的閑暇歲月。
引述此言的文章,接下來往往便是一番不約而同的驚詫:作為現代社會人的自己,竟然比原始社會的祖先擁有少得多的閑暇。朱麗葉·肖爾(Juliet Schor)的《過度工作的美國人》與森岡孝二的《過勞時代》,這些研究將“過勞死”作為某種意義上的“國家病”來觀察:一邊是豐富的物質享受,一邊是沉重的工作壓力。過勞的情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肆虐,儘管不同國家的勞動與閑暇時間存在差異,比如在歐陸發達國家,人們的閑暇往往多於英美和日本。
中國最新的工作時間數據,收錄在內蒙古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課題組撰寫的《時間都去哪兒了?中國時間利用調查研究報告》一書之中。2017年,我國工資勞動者超時工作(每日淨工作時間大於8小時)相當普遍,超時工作率高達42.2%。其中,低收入者、低學歷者、製造業從業者、生產製造及有關人員的超時工作尤為嚴重。中國婦女(尤其是單親母親)的時間尤其稀缺。的確,工作和家庭的雙重負擔使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時間貧困”。
數據顯示,從2008到2017年,女性與男性的無酬勞動(最典型的就是家務勞動)時間比由2.60上升到3.15。近年中國女性也出現了從照顧家庭和賺錢養家的“雙重負擔”,轉而向家庭回歸的趨勢。如何管理稀缺的時間,在工作、家庭、休閑與睡眠之間進行合理分配,已經成為所有人的難題。這種不均的時間分配顯然不只是個人選擇,也受到社會性別結構的牽引,以及政策及用工制度的製約。
婦女最容易成為脆弱的時間貧困者,而那些看似掌握自己時間的自由職業者,或者參與“零工經濟”的“斜杠青年”,也未必是時間的富裕者。經歷過現代工作倫理規訓的人都知道,“時間就是金錢”,而金錢總是叫人捉襟見肘。似乎如今,只有那些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們,才會將時間肆意揮霍:“他們太懶!不知道當今世界活著就得努力工作。”
因此,凱恩斯所惦念的為閑暇和豐裕而發愁的日子,與其說是展望未來,不如說更像是回顧原始社會。1969年《時代》雜誌7月號推出的“原始豐裕社會”布須曼特輯如是寫道:“想象一下,一個社會裡,工作時間幾乎從不超過每周19小時,物質財富被視為負擔,沒有貧富差距,失業率有時高達40%,但這不是因為社會管理無當,而是因為他們相信只有身強體壯的人才應該工作,且工作應該適可而止。食物豐富且易得。生活閑適安寧、充滿快樂。”
人類學家詹姆士·蘇茲曼在《不富足也豐裕:正在消失的布須曼世界》(譯文收錄於《扎根》輯刊即將出版的《後工作讀本》,王行坤主編)一書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布須曼人(官方多稱桑人)是非洲南部古老的狩獵采集民族,他們饑腸轆轆,啥也不做,坐等救濟。不過,在蘇茲曼看來,他們的貧窮既非懶惰所致,也不盡是厄運的結果。在白人殖民者到來前,他們祖祖輩輩都如此生活。
顯然,在經濟全球化之外的時間規則裡,存在時間的富足者,因為原始人對耗費時間提高勞動生產力和積累資本毫無興趣。這真是一個悖論,在經濟最落後的狩獵采集社會,人們似乎擁有凱恩斯夢想中的經濟烏托邦。那些西方反文化運動中戀慕原始烏托邦神話的人感歎,“每周15小時的工作製,是現代智人在大約過去20萬年中多數時期的主流”。
為何“狗屁工作”瘋狂滋生?
為什麽我們無法被技術解放而迎來閑暇?“狗屁工作”給出了一個似是而非的答案,無工可做也要創造工作。這個概念自身便有戲謔與吐槽的意味,認同或不認同的讀者都能感受到這一命名的“戳人”之處。2013年,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激進雜誌“Strike!”的網站上發表了名為《論狗屁工作現象》的文章,五年之後擴展此文成書,討論與爭議迅速在學院、媒體與社交網絡上蔓延開來。王行坤、房小捷在其研究中梳理了“狗屁工作”在海內外的相關研究。中國媒體諸如《三聯生活周刊》《南方周末》《新京報》的相關報導,也斬獲很高的閱讀量。類似於人們對於過勞、大加速的情緒宣泄,“狗屁工作”引起的無國界反響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時代共鳴。
因忙碌、快節奏的工作而惴惴不安,差不多是所有人共享的經驗。的確,今天無論窮人還是富人,都變得更加忙碌。在過去,富人除了揮霍有形的產品之外,還要揮霍自己的時間,這意味著他們擁有大量的閑暇。然而今天,富人也要使自己忙碌起來,忙碌是一種楷模的行為。今天我們熱衷抱怨忙碌,但一旦真正閑下來時,即沒有別人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會感到巨大的焦慮或失落。
窮人的忙碌和富人的忙碌,不可同日而語。想想一個忙碌的有錢人和他所雇傭的保姆:兩者可能都很忙,但他們之間的差別不僅在於收入,更在於對於自己時間的自主權以及各自時間的充實度——前者對時間的利用是充實的,或者說能帶來很大成就感;而後者則是單調的,很難說有什麽成就感。
格雷伯往往傾向於從主觀感受界定“狗屁”。不過,工作的意義感與工作性質之間存在矛盾,一份被格雷伯定義為“狗屁”的工作,可能給從業者帶來巨大的自我實現感。比如,在王行坤、房小捷對“狗屁工作”的研究中,基於有限的問卷調查和訪談樣本顯示,中國金融業的從業者對工作的主觀滿意度頗高,並不認為自己在做“狗屁工作”。
如何界定哪些工作屬於“狗屁工作”呢?保羅·巴蘭在《增長的政治經濟學》中提到,熊彼特這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認為律師這個職業在社會主義社會是沒有必要的,“許多聰明才智被用之於這類非生產性業務上,其社會損失是不小的。”
在保羅·巴蘭看來,如果從理想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角度來看,很多在今天消費社會看來是必需的東西,都可以是非必需的。比如,從事製造軍備、奢侈品和炫耀品的職業、官員、軍事設施人員、教士、律師、逃稅專家、公共關係專家,以及廣告商、經紀人、商人、投機牟利者等等——按照他的思路,這些人沒有為社會生產什麽使用價值。以廣告從業人員為例,他們固然為老闆賺到了錢,並且擁有不菲的收入,似乎對社會有用,但是沒有人會說我想通過閱讀或觀看廣告創意來增加見識或涵養精神——他們並沒有為社會生產出使用價值,而只是激發或者操縱了消費者的欲望,從而使生產機器更快地運轉下去。
“狗屁”本質的界定建立在這樣的判斷之上:在生產得到理性組織的理想社會,人的欲望並不需要激發或操縱,我們了解自己的需求,並且以民主且合理的方式生產出相關產品。某些職業會消失,某些職業會出現,人類的勞動時間必然會減少。在王行坤看來,一個真正做到對人和自然都友好的社會,與隻追求利潤或GDP的社會截然不同。到那時,我們將對任何職業追問,你能為社會貢獻什麽(為社會提供怎樣的使用價值和財富),而不是能為老闆或自己賺到多少錢。
格雷伯將近四十年來“狗屁工作”大量滋生的緣由,歸結為金融資本主義的崛起。但正如王行坤、房小捷的研究表明,格雷伯的數據是有問題的。社會平均工作時間之所以居高不下,並不是因為四十年以來看似高端上檔次、實則毫無意義的狗屁工作大肆泛濫,而是那些沒有保障、不穩定的“低端”工作的不斷擴張。西方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增加最多的是低工資、低技術水準的工作崗位,主要集中在零售、餐飲、醫療和教育這些所謂“真正的服務業”。比如,受雇於眾包平台的優步司機,作為獨立承包商的微商,他們隨時處於待命狀態,沒有穩定的雇傭關係,工作時間也因為工作的靈活性而被拉長,這種趨勢被稱為工作的優步化(Uberization)。
不辭辛勞地工作而將時間耗盡,很多時候看起來是個體的自發選擇,但純然“自發的”過度勞動,幾乎是難以想象的。對於美國優步司機來說,假如每周隻工作40小時,他們的收入就會跌破貧困線。現代社會似乎不存在時間的富裕者,沒有“時間饑渴症”被視為一種不正常。這正是作為意識形態的工作倫理所教導我們的,也是日益嚴厲的工作機制強加給我們的。
撰文/新京報記者 董牧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