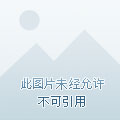熱心並有此才華的學者,為普羅大眾和青少年學生寫下他們願意讀、能讀懂、讀得開心且有收獲的書籍,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應大力支持。

讀完《“不敢說是寫的最好的,可敢說是最貼心的”——易中天複盤“中華史”書寫》(《南方周末》2019年4月4日關注版)這篇訪談,我想起台灣資深編輯、出版人老貓(陳穎青)回憶年輕時向詹宏志請教時,詹先生給了他一句畢生難忘的忠告:“編輯不要太有潔癖。”
大意就是,不管你是什麽類型的編輯,不要僅僅隻局限於自己的專業層面,而看輕其他出版物的價值。譬如你是一位從事嚴肅學術著作出版的編輯,請不要輕視心靈雞湯、成功大全、通俗小說、養生食譜、遊戲攻略這類出版物,因為你身邊的親友,他們非你的同行,他們有自己的閱讀需求。
我讀到這段話的時候是個中文系本科三年級的愣頭青,那時候對傳統學問特別感興趣,覺得除了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這三家出版社的書,買書借書一律要豎排繁體,別的都不值得一看。看到旁邊的同學在讀文藝理論,茶樓裡的阿伯研究股票跑馬,心中不由得泛起一絲鄙夷。這就是詹先生說的“潔癖”,更多的是出於自己的無知與自滿。
我還記得讀小學的時候,《百家講壇》正火得不得了,易中天《品三國》、閻崇年《正說清朝十二帝》、錢文忠解讀《三字經》,伴我度過許多個周末和假日,也為自己後來的求學之路打下了最初的基礎。
後來讀大學,常常看到一些學者的批評文章,比如說平易風趣的語言將學術娛樂化,大學教授講中學內容大材小用、浪費資源。如果我們以君子之心揣摩以上這些學者的批評——認為他們不是出於某種程度的嫉妒而是出於學術的公心,那麽他們也有一點“學術的潔癖”。
我在北大附中實習的時候,歷史教室裡就有一套易中天先生的《易中天中華史》,初一的孩子們下課常常翻看,以至於好幾冊都翻破了。這些學生,除非以後讀中文系或者歷史系,有能力閱讀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否則這部讀物可能是他們所接觸的最完整的中國通史讀物,使他們對中國古代史有一個大概的整體印象。以後從事相關專業學習與研究的學生,也會感念當年易中天老師編寫的這樣一部書給了他們最初的史學啟蒙。
有人說這套書語言風格過於輕鬆,不夠嚴肅,但往往真正把書讀通讀透的人才能做到這樣,這也是厚積薄發的一種。就拿北大的中古史課堂來說,大學者如閻步克、鄧小南老師,也是平實簡單的文字,不時一個幽默的典故、段子,博得滿堂的笑聲與掌聲,從來不玩弄什麽艱澀的概念與術語。往往一些沒讀通的人,才滿嘴的學術術語,糾纏於字面的概念,洋洋灑灑幾萬言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來,搞得讀者一頭霧水不知所雲,借以掩飾自己的空虛。
歷史是人類社會演進中人們共同書寫的記憶,它不是史家所獨有,也不單單是幾部史籍所能囊括。了解與研究歷史,並非是象牙塔裡禿頭博士的專屬,普通人也有閱讀了解歷史的權利與需要,或者僅僅是一天的勞累之後,下班回家洗了澡,閱讀幾頁,沉醉其中,忘記精神的壓力與肉體的勞累,漸漸進入夢鄉。
熱心並有此才華的學者,為普羅大眾和青少年學生寫下他們願意讀、能讀懂、讀得開心且有收獲的書籍,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我們應該大聲鼓掌、大力支持。
那些不肯放低身段,寫出親近易懂的文字,將閱讀心得與研究成果與民眾共享,而沉迷於常人難解的晦澀的學術語言與艱深的學術名詞,站在象牙塔的頂端,無視普通民眾的知識需求,只是洋洋自得,空虛十足的自滿,卻妄想得到民眾擁戴與膜拜的學者,無異於在海洋中礁石上固執地孤芳自賞的海怪,幻想著會有不計其數的朝聖者從陸地趕來膜拜。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
(南方周末App“hi,南周”欄目期待您的來稿。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