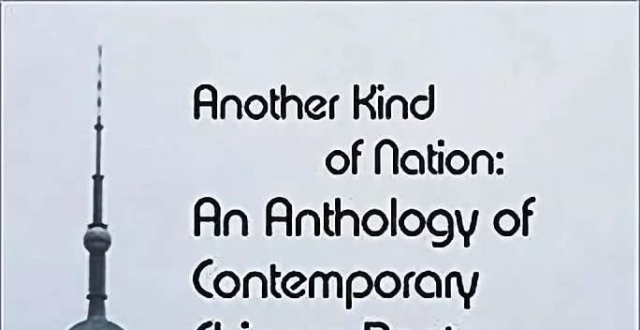《悲歡的形體:馮至詩集》由馮至先生的女兒馮姚平親自編選,共分為八個單元,涉及馮至先生一生的詩歌創作。由於深刻了解馮至先生的創作走向和人生軌跡,該詩集呈現出客觀、真實、清晰、準確、精煉又極具代表性的品質,值得信賴,可以幫助讀者貼近詩人馮至的詩歌天地和生命世界。
正因如此,我以為,《悲歡的形體:馮至詩集》不僅是一部詩歌小結,還是一部精神小傳和人生小傳。

馮至(1905-1993),詩人、翻譯家、學者。原名馮承植,字君培,河北涿縣人。早年就學於北京大學,參與組織沉鍾社,創作大量詩文,歷任同濟大學、西南聯大及北京大學教授等職務。著有詩集《昨日之歌》《北遊及其他》《十四行集》等。曾當選瑞典皇家文學歷史人物研究院外籍院士,並獲歌德獎章。
撰文 |高興
(《世界文學》主編)

《悲歡的形體》(作者:馮至版本:雅眾文化 | 新星出版社 2018年4月)
注重詩的音樂性
真正的詩與歌的有機融合
翻開《悲歡的形體:馮至詩集》,再次讀到不少熟悉的詩時,一種無比的親切感頓時湧上我的心頭。馮至先生十六歲時已寫出第一首詩《綠衣人》。我十六歲時剛剛步入校園,開始利用寒暑假大量閱讀文學作品,包括詩歌作品。記得江南一個雨天,坐在亭子間裡,偶然從一本書中讀到了一首小詩《橋》,激動不已:
“你同她的隔離是海一樣地寬廣。” “縱使是海一樣地寬廣, 我也要日夜搬運著灰色的磚泥, 在海上建築起一座橋梁。" “百萬年恐怕這座橋也不能築起。” “但我願在幾十年內搬運不停, 我不能空空地悵望著彼岸的奇彩, 度過這樣長、這樣長久的一生。"
這首詩採用了對話形式,自然、樸素、輕盈、意象清新,卻具有無限的能量,仿佛就是針對著少年一顆憂鬱、迷惘和多愁善感的心靈的,就是呼應著一個自由、開放、積極向上的時代的。少年閱讀,有個癖好,喜歡將令我心動的格言、警句、話語和詩歌抄錄於筆記。我當即就將《橋》抄錄下來,並牢牢地記住了它的作者馮至的名字。隨後,便有意識地閱讀馮至詩歌。於是,我的筆電上又增添了《蛇》《無花果》《饑獸》等短詩。就覺得這些詩好,說不出的好。這些詩還時常被我引用到文章、對話,甚至約會上。要知道,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同女生約會時,你若能不時地背上幾首優美的詩,在女生心目中的形象立馬就會高大許多。一個多麽純真而美好的年代!我時常在想:自己畢業後不去外交部,不去經貿部,而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世界文學》編輯部,是否也同馮至詩歌無形的影響有著某種關聯?極有可能的。況且馮至先生還擔任過《世界文學》的主編。

馮至先生參加《世界文學》紀念會。
時間推移,少年和青年時期喜歡讀的一些詩後來就不再讀了。但馮至的不少詩歌卻始終在一遍遍地讀,喜愛和欣賞之情絲毫不減。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那首著名的《蛇》:
我的寂寞是一條蛇, 靜靜地沒有言語。 你萬一夢到它時, 千萬啊,不要悚懼! 它是我忠誠的侶伴, 心裡害著熱烈的鄉思: 它想那茂密的草原—— 你頭上的、濃鬱的烏絲。 它月影一般輕輕地 從你那兒輕輕走過: 它把你的夢境銜了來 像一隻緋紅的花朵。
我們欣喜地發現,這首上世紀二十年代寫下的詩作,今天讀來,依然讓讀者感覺雋永、敞開、貼心,充滿了音樂和藝術的韻味。馮至先生極善於將抽象事物具象化,將寂寞比作蛇,絕對是神來之筆,實在是貼切。詩中由“草原”至“你頭上的、濃鬱的烏絲”的聯想十分自然,同時先生對音樂性的注重,在詩中也得到充分的呈現。比如,“輕輕”一詞的兩度出現,就讓我們明白了詩歌中有意的重複所具有的美學意味。音樂性是滲透於馮至先生的血液中的。沒有音樂性,就無法稱作詩歌。這是馮至先生這一代詩人堅定的詩歌美學。他的作品真正的是詩與歌的有機融合,因此他寫的是真正意義上的詩歌。

《給青年詩人的信》(作者:裡爾克譯者:馮至版本:雅眾文化 | 雲南人民出版社 2016年1月)
馮至不止是詩人,還以翻譯家而聞名。其翻譯的裡爾克詩歌及這本《給青年詩人的信》已成經典。
絕非象牙塔裡的詩人
擁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家國情懷
詩集中還有《吹簫人的故事》《帷幔》《蠶馬》《寺門之前》等好幾首謠曲特別引人注目。這些謠曲體現了馮至先生寬闊的寫作路子和全面的寫作才華。在這些謠曲中,馮至先生結構、敘事、鋪陳、描繪、烘托、把控節奏、提煉和提升的能力不得不讓人敬佩。因此,馮至先生並不是某些評論者所認為的那種隻善於寫短詩的詩人。而創作這些謠曲時,馮至先生正值弱冠之年。這不由得讓我想到了詩歌創作中的天才因素。
《十四行二十七首》無疑是馮至詩歌創作的巔峰。《悲歡的形體》全部收入。這是馮至先生沉寂十餘年後的一次爆發,是寂寞中唱出的不朽的歌。可以想見,積累、沉思、叩問、深入、閱讀,對於詩歌創作的重要性。這些詩中顯然已有馮至先生熱愛的裡爾克、歌德、海涅等詩人的影子。影響和交融,能使一名詩人永遠處於成長之中。這組十四行幾乎每首都是精品,其中,《我們準備著》《威尼斯》《我們聽著狂風裡的暴雨》《幾隻初生的小狗》《這裡幾千年前》《案頭擺設著用具》《從一片泛濫無形的水裡》尤得我心。
如果我是編選者,目光可能不會投向詩集中的某些詩,比如《我們的西郊》《登大雁塔》等。從美學角度上來看,這些詩稍顯蒼白、牽強,有點應景。從這些詩中,我們可以看出,馮至先生一直渴望跟上時代的節奏,但最終實在有點力不從心。但編選者本著客觀呈現的原則,不回避,不粉飾,盡量讓讀者看到一個真實的馮至。這恰好體現出了編選者的雅量和坦誠。
進入《世界文學》本身就暗含著同馮至先生的緣分。果然,有一天,《世界文學》老主編高莽先生要帶我去拜見馮至先生。建國門外,一套普通的公寓裡,馮至先生從詩歌中走出,出現在我的面前。一位樸實卻不失端莊,謙遜卻充滿大師風范的老人,坐在書桌旁,說起話來,聲如洪鍾,聽人說話,又那麽專注。馮至先生不是那種象牙塔裡的詩人,他關注現實,關注文學狀況和國家形勢。《悲歡的形體》中的詩歌其實準確地反映出了詩人的現實關懷和家國情懷。《綠衣人》《“晚報”》中的悲憫和同情,《北遊》中的陰鬱和悲傷,《魯迅》《杜甫》等詩中的禮讚和呼應,都一次次讓我們感到了詩人同現實世界和國家命運的深刻連接。此外,馮至先生晚年的反思姿態和批判鋒芒也讓我們感佩和感動。已故的高莽先生不止一次地提到馮至先生的一首題為《自傳》的小詩:
三十年代我否定過二十年代的詩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過四十年代的創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過去的一切都說成錯。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麽那麽多 於是又否定了過去的那些否定 我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裡生活, 縱使否定的否定裡也有肯定。 到底應該肯定什麽,否定什麽? 進入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 才明白,人生最難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要有點閱歷的人,才能明白這首詩的深意。”高莽先生輕聲地對我說道。不知怎的,我總也忘不了他說完此話後的片刻沉默和眼神不經意間流露出的憂傷。有些詩,你只能意會,不可言傳。這恰恰是詩的妙處。
嚴格而言,馮至先生的詩歌創作由兩部分組成:他寫的詩歌和他譯的詩歌。他所譯的裡爾克曾經深深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詩人。在談論《悲歡的形體》時,我們又怎能繞過裡爾克或者馮至的《秋日》。雖然目下此詩已有好幾個譯本,但我依然隻承認馮至先生的譯文,因為那是他的發現,他的開拓,他融入了自己心血的獨創和建設:
主啊!是時候了。夏日曾經很盛大。 把你的陰影落在日晷上, 讓秋風刮過田野。讓最後的果實長得豐滿, 再給它們兩天南方的氣候, 迫使它們成熟, 把最後的甘甜釀入濃酒。 誰這時沒有房屋,就不必建築, 誰這時孤獨,就永遠孤獨, 就醒著,讀著,寫著長信, 在林蔭道上來回 不安地遊蕩,當著落葉紛飛。
本文內容系獨家原創。作者:高興;編輯:宮照華 西西。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