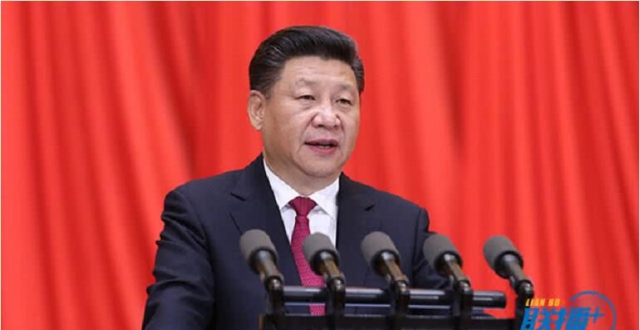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中國現代考古學肇始於1928 年,這一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始在河南安陽小屯發掘商代晚期都城殷墟。此次發掘是首次由中國國家政府開啟的考古項目。1928年至1937年間共發掘了15個季度,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被迫終止。在安陽的這一系列發掘並不是率性而為,而是以文化、政治和技術等的發展為前提,正是這些因素為創建考古學這門新學問奠定了基礎。可以說,中國考古學自1928年在安陽誕生之日起,就有一個明確的目標,那就是重建國族史或民族史。探尋中國文化起源開始成為很多知識分子知識追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考古學研究的原動力就和這個問題密切關聯。
*文章節選自《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劉莉、陳星燦著 三聯書店2017-9》、《思考考古》(陳勝前 著 三聯書店2018-2)
點擊閱讀

安陽出土的商朝刻辭卜骨
國族史和文明起源
文 | 劉莉 陳星燦
以“區系類型”聞名的研究模式,最先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由蘇秉琦提出(蘇秉琦,殷瑋璋 1981;Wang,T. 1997)。它主要建立在對陶器組合的研究上,強調不同區域文化傳統之間的獨立發展和相互影響。“區系類型”概念試圖為重建中國史前史提供一個方法論框架。就中國文明發展的研究而言,它從中心-邊緣模式轉移到多區域發展模式。蘇秉琦認為,一萬年以來,六大相對穩定的文化區域(區系),已經在後來歷史時期的中國範圍內形成。這六種區域文化又進一步劃分為多種地方類型(蘇秉琦 1991)。按照蘇秉琦的說法,在中國文明發展過程中,每個區域都有自己的文化淵源和發展序列,且與其他地區互相影響。嚴文明針對“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也提出了一個類似模式,把中原地區看作一個花朵的花心,而把周邊地區的文化傳統看作層層花瓣(嚴文明 1987)。與蘇秉琦的假說把所有區域文化置於同等地位不同,嚴文明的模式更關注在文明進程中中原地區的長官作用,同時也承認史前時代邊緣地區文明因素的存在。
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注意到中國文明從單中心向多中心轉移的一般趨勢(Falkenhausen 1995: 198-199),也反映在張光直第四版的《古代中國考古學》中。該書是數十年來用英文出版的最具綜合性和權威性的中國考古學參考書。在1963 年、1968 年和1977 年出版的前三版中,中原地區被認為是複雜社會和王朝文明發祥的核心地區。這個觀點在1986 年的第四版被“中國相互作用圈”所取代。中國相互作用圈的太空範圍遠超中原地區,這也為三代文明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更加廣闊的基礎(Chang 1986a: 234-242)。
中國考古學中這樣的範式變化似乎和重建中國上古史的新觀點相得益彰。

多區域文明共同發展
中國考古學自1928 年在安陽誕生之日起,就有一個明確的目標,那就是重建國族史或民族史(按照孫中山的觀點,在中國,國族和民族概念相通)。然而,國族/ 民族的概念,因而也是國族史/ 民族史的概念,不斷隨時間而改變。重建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新的國族史/ 民族史觀的影響。
20 世紀50 年代以來,隨著國家試圖將中國的多民族人口納入一個政體,中華民族的概念已經等同於國家,最好的描述就是費孝通提出的“多元一體”(費孝通 1989)。正如費孝通所言,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是在數千年間逐漸發展起來的。這個形成過程是融合的過程,它以華夏- 漢族為核心。但是,華夏- 漢族與其他族群之間的文化互動,並不是單方面的傳播,而是互相影響的。按照費孝通的觀點,這個民族實體,包括現在中國疆域內居住的所有民族(56個)。這個民族認同的新概念和考古學上的“區系類型”範式相得益彰,和“統一性與多樣性”的假說尤其吻合。很顯然,在民族史的重建方面,考古學和社會學的模式相互支持。
伴隨著區域考古學文化知識的增加,學者們有了強烈的意願,要在考古資料和歷史記錄相結合的基礎上重建文化史。現在有這樣一個趨勢,就是把考古學文化、時期、遺址甚至器物與傳說和歷史文獻中的某些古代人群、人物和地方對號入座。關於幾個青銅時代城址歷史歸屬的持續爭論,如二裡頭、二裡崗、偃師商城以及靠近鄭州的小雙橋等,就是這種嘗試的最好例證。通過這樣的研究,考古遺存(主要由陶器類型界定)開始具有歷史意義,儘管兩組資訊——陶器類型和族屬——之間的邏輯聯繫並不十分明了。

二裡頭陳列室的陶器
中國普遍使用“五千年文明”一語概括中國歷史,考古學家則致力於追溯其起源並展示這個歷史過程。因為王朝歷史,正如後代所追述的那樣,不早於公元前2070年(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 2000),所以學者們做出很多努力,希望把區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展,與前王朝傳說中的王和聖人的可能活動聯繫起來,比如所謂的五帝(英文經常錯譯為“五個皇帝”),以此來填補這一千年的間隙。學者們也還嘗試把某些文化成果,比如均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玉器生產和大型禮儀性建築的建造和文明曙光聯繫起來。結果,不僅把傳說視為信史並用之解釋新石器時代考古,而且還把中國文明起源前推了1000 年甚至更久,以便與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媲美(蘇秉琦 1988, 1997)。20 世紀早期,當“疑古派”質疑傳統文獻時,他們希望考古學家從田野中發現可靠的古代歷史。對今日的很多考古學家來說,這些傳說被認為是重建史前史的藍圖,“疑古派”則成為被批判的對象(如李學勤 1997b)

山東嘉祥武梁祠東漢石刻畫像,其內容表明了(從右向左)傳說中三皇五帝的接續
20 世紀90 年代,國家主導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將這一努力推向頂峰。在訪問埃及時,國務委員宋健看到埃及王朝始於公元前3100 年的詳細年表。由於對中國王朝年表不滿意,除了這個年表比埃及晚1000 年外,而且也遠為粗略,因此宋健動議設立課題以重建一個更加精確的三代年表,以便於中國文明與埃及文明相媲美。這個課題,被稱作“夏商周斷代工程”,在1996 年正式啟動。花費了差不多四年時間,共有200 多位歷史、考古、古文字、天文學和14C 測年等方面的專家參加了這一工程,主要有九個課題,下面細分為44 個子課題。該課題已經取得了它最初設定的四個目標:①為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 年)以前,包括西周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前半期各王,確定了比較準確的年代;②為商代後期,從商王武丁到紂確定了比較準確的年代;③為商代前期,提出了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④為夏代,提出了基本的年代框架。這個工程結束之後,三代的年表確實比以前更加準確和詳細了(Lee, Y. 2002;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 2000)。然而,這一工程並沒有使中國文明的時間與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古老文明比肩,甚至還引起了很多關於斷代工程在目標、方法和結果方面的質疑( 蔣祖棣 2002;劉起釪 2003;劉緒2001;Shaughnessy 2008)。
暫且不管還在進行的有關工程結果細節的爭論,夏商周斷代工程又催生了一系列研究項目,這就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通過使用多學科研究方法,該工程旨在早期王朝的溯源和最早新石器時代文明的揭示(王巍,趙輝 2010;Yuan, J. andCampbell 2008)。

漢代畫像石拓片,大禹像
20 世紀早期現代中國考古學的誕生,是引進西方科學方法、民族主義興起和尋找民族文化起源的產物。這三個因素一直影響著學科發展,結果是中國考古學長期穩定地被置於廣義的歷史學科之下。其研究目標和解釋經常受到不同國家政治綱領的深刻影響——尤其是在某些特定時期不斷改變的民族主義概念(張光直 1998)。
在動亂時期,考古學家努力工作以克服各種經濟、社會和政治困難,並在該領域做出了傑出貢獻。由於這些考古學成果,我們對於古代中國的理解已經有了顯著提高。在許多情況下,考古學被同時期多民族民族主義概念的浪潮所驅使,並以之為工具支持而不是評估或檢驗某些理論議題或政治綱領。在其他情況下,它為創造新的範式提供了獨立資料,因而改變了中國國族史/ 民族史的傳統觀點。國家倡導的民族主義確實在指定學科發展方向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對於很多考古學家來說,參與國史的建設體現了中國公民的尊嚴和自豪。
考古學的發生和發展,離開了社會政治環境的大背景是很難理解的。在很多國家,民族主義塑造了考古學的假設、方法和實踐,考古學的調查和研究成果也影響了與構建民族認同有關的思想(如 Diaz-Andreu 2001;Kohl and Fawcett 1995;Smith A. 2001;Trigger 1984)。正如炊格爾觀察的那樣,在感到政治威脅、不安或者被強權國家剝奪集體權利時,民族主義考古學往往會變得非常強大(Trigger1984: 360)。考古學最初在中國誕生時,顯然是處於這種情況。如今,儘管中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但構建民族認同的需求依舊未減。因此,儘管近幾十年來西方思想和技術的影響不斷增加,它們在很多領域也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中國考古學的主流目標並沒有發生重要改變,學科旨趣還是重建國史。這一使命很可能持續下去(蘇秉琦 1991)。然而,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更加多樣的研究方法已經出現。一些考古學家仍在研究區域歷史問題,另外一些則開始從事理論構建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賦予該學科更加國際化的前景。
中國考古學研究的轉型
文 | 陳勝前
聽到一種說法:中國考古學在20世紀90年代發生了研究轉型,從物質文化史研究轉向古代社會研究。與前者相適應的方法主要是考古類型學、地層學、測年以及鑒定技術;而後者因為要研究社會所依賴的環境、經濟與技術、社會與組織、思想與文化,因此需要多學科的技術方法,需要拓展不同資訊之間的關聯。我對這樣的說法很有興趣,我們能不能看出這樣的變化呢?這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變化呢?是什麽導致了變化的發生呢?
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何為“物質文化史”?蘇聯考古學中有這種說法,因為蘇聯不願意採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定義的“考古學”。從實踐的角度來看,所謂物質文化史跟西方的考古學並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不過,因為蘇聯考古學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強調通過物質材料研究社會發展史的演變。從中文字面的意思來理解,“物質文化史”就是通過物質來研究文化的歷史。如果這裡所謂的文化包含精神、傳統在內的話,那麽這個定義就跟金石學有幾分相似。顯然,這是不可能的。如果將其理解為西方的“文化歷史考古”似乎也不合適。蘇聯考古學20世紀70年代後重走類型學的路線,就表明它此前所走的路線並非“文化歷史考古”。如果我們追溯一下馬克思所受摩爾根《古代社會》影響,那麽我們就有理由相信,馬克思的文化觀可能是人類學式的,文化包括從環境、經濟、技術、社會組織到意識形態等方方面面的內容。蘇聯的“物質文化史”就是要研究這些內容,這跟中國90年代轉型後的古代社會研究沒有太大的差異。因此,從概念上來說,中國考古學90年代轉型——從物質文化史到古代社會研究——沒有確切內涵上的差異。
那麽中國考古學90年代究竟有沒有發生轉型呢?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路線是比較特殊的,從一個文化遺產豐厚的國度變成了半殖民地,再經過艱難的民族獨立戰爭與國內革命戰爭而建立起獨立的學術體系。這樣的發展背景與路線選擇決定了我們恐怕不能簡單地套用西方考古學史中所用的概念,比如用文化歷史考古來定義中國考古學。即便使用了,我們仍然需要明白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形態不同於西方典型的文化歷史考古。這樣的歷程決定了中國考古學必然會受到四個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以金石學為中心的中國傳統學術的影響;二是在爭取民族獨立過程中所需要的民族主義思想,通過考古來尋求民族認同,贏得民族尊嚴;三是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這是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四是西方近現代考古學,作為一種秉承科學精神的學術,其影響自然是不能忽視的。圍繞這四個方面影響因素的此消彼長,我們或可以看到中國考古學發展的形態轉變。還值得一說的是,我們說存在四種影響,須知它們之間所存在著的矛盾與糾葛,還應該知道中國考古學作為一門學問,其發展有自身的邏輯。

何尊銘文
在中國考古學發軔的初期,金石學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現代考古史家通常將金石學理解為萌芽狀態的考古學,很不完善。從科學考古學的角度來看,的確如此。但是,如果從人文的角度來看,金石學非常好地保存與傳承了中國文化,假如沒有這些物質材料,中國文化僅憑文獻來傳遞無疑是非常單薄的。在後現代思潮崛起的今天,應該是我們重新審視金石學的價值的時候了。它也許不那麽科學,但是它具有科學考古學所不具備的人文價值。
民族主義的思想不是中國的發明,而是殖民主義世界中的被動選擇。中國一直是強調中華一統的,中國的民族主義跟歐洲的近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所依賴的民族主義所產生的環境是不同的。這裡伴隨著屈辱、壓迫、剝削等,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幾乎無一例外地懷著強烈的民族救亡的思想來從事考古學研究,讀中瑞西北科考的故事,這樣的感受尤其深刻。
後兩種影響都帶有明顯的現代性,即人類社會為統一的整體,強調從整體的角度進行研究。馬克思主義與科學觀在社會現實中的巨大成功使人們不得不正視其合理性。民族的、傳統的……這些都不大合乎現代性的要求,是需要被批判的。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史中暗含著傳統與現代這兩種力量的博弈,這種博弈可以不是零和遊戲。當然,處理不當,就會既傷害了考古學研究的科學性,也傷害了它的人文意義。中國考古學發展的曲折路線上就有過兩者皆失的教訓。
簡要地回顧中國考古學發展史之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90年代的轉型,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呢?從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背景來看,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考古學新的一頁。改革開放似乎可以分為兩個階段,90年代以前與以後。前一個時期是現實條件多不允許,但人們的思想遠遠走在了前頭;後一個階段似乎正相反。所以,從考古學發展史的外在關聯的角度來說,沒有理由認為90年代出現了考古學的轉型,如果有的話,更有理由將之視為回歸。

1978 年二裡頭二號宮殿基址挖掘拍照,從地面到頭頂11米
當然,事情沒有這麽簡單,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仍在高速發展中,現實推動思想前進。從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來看,廣泛的國內外合作、多學科的合作、大量的考古發現,以及人才規模擴大等,都為中國考古學研究的轉型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也許我們無須考慮這些背景,而是直接面對中國考古學研究的現實,看看真實的發展狀況。如果我們瀏覽一下近些年出版的中國考古學的綜合著作,就會發現所謂90年代發生了研究轉型的說法並不那麽令人信服。雖然生計與技術、聚落形態與社會組織、宗教禮儀與意識形態已經在書中有專門的章節,但是,這些內容是作為特徵羅列出來的,還是一種靜態的存在,而沒有關聯起來構成邏輯上不可分割的整體。因為缺乏關聯的力量,所以我們對古代社會的認識更多的是一種推測,而非論證。當代中國考古學的這個特點還是非常明顯的,它跟真正的古代社會研究還有一定的差距。把所有有關古代社會的特徵綴合起來,這是過程考古學的先驅瓦爾特·泰勒(Walter Taylor)的主張。泰勒終生不得志,有個人健康的原因,但純粹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那就是他立足的基本概念——文化,還是一些靜態的特徵(也是唯心的,即假定所有共享這種文化的人都認同某種共同的標準),而不像後來的過程考古學將文化視為功能的——文化是人適應外在環境的手段。泰勒在緣木求魚,所以他無法成功。簡言之,從中國考古學的研究實踐來說,並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發生了研究轉型。

二裡頭考古隊陶器陳列室裡的白陶酒器
從思想基礎、社會背景、考古學的研究實踐歸納等方面都難以看出20世紀90年代中國考古學的研究轉型。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雖然中國考古學整體上的研究格局沒有實質性的變化,但是在少數考古學者與分支領域中確實可以看到明顯的變化,這些研究帶有明顯的功能的色彩。而且這樣的學者越來越多,既包括受過西方考古學訓練的學者,也包括國內訓練出來的學者。這樣不約而同的發展讓人不得不產生這樣一種認識:考古學的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無須刻意去劃分什麽學派或階段,發展到一定程度,也必然會發生改變。
這麽說來,我們也許應該說,90年代以來,中國考古學研究整體上看不出轉型,但是局部上還是有的。這種轉型主要體現在從強調形製的時空特徵走向強調考古遺存的功能與關聯,或者說,中國考古學研究開始從考古材料時空框架的建立走向人類行為的重建了。可能中國學者更喜歡用“社會”這個概念,所以將之稱為“古代社會的複原”研究。可以想見,中國考古學還會向這個方向繼續走下去。從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來看,有趣的是,老一輩的學者也在推動這個轉型。中國考古學並沒有出現美國考古學那樣的“革命性”的變化。實際上,“新考古學”(過程考古學)最為人詬病的一點就是其“革命性”的態度。中國的經驗似乎表明,即使沒有高調的“革命”,考古學也會按照自身的邏輯發展下去。

《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
劉莉 陳星燦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09

《思考考古》
陳勝前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02

《學習考古》
陳勝前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