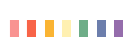撰文/袁征,學者
編者按:江燕女士是本文作者袁征先生小時候在中山大學校園裡一起成長的玩伴,袁征先生通過回憶和採訪,記錄了江燕女士從孩童到成為專業小提琴手的經歷,有很多1950年代出生人共同的時代記憶。
一
1977年春節,廣東省歌舞團在廣州友誼劇院表演。其中一個節目是小提琴獨奏《漁家姑娘在海邊》。江燕在舞台前拉琴,挺大一支管弦樂隊在她身後伴奏。這時她十九歲。

1977年,廣州友誼劇院演出
接著,她在不同的劇場拉了《流浪者之歌》之類提琴曲,廣播電台不時放她表演的錄音,《南方日報》還發了採訪文章。
那時中國的大學像個小城,教師職工幾乎全住裡頭。於是,在中山大學的校園裡,大家都誇江靜波老師的小女兒有出息。後來,江燕在美國當專業提琴家,說搞音樂原來“非本人所願也並不是本人所好”。
大家可能覺得她故作謙虛,唱低調,但我知道那是真的。
二
江燕是我認識的最貪玩的女孩。
她出生在中大護養院(就是校醫院),父親是生物系的副教授。1952年以後,大學評職稱一直不正常,副教授已經很是個人物。1978年,國務院批準教育部《關於高等學校恢復和提升職務問題的請示報告》,江靜波先生立即被評為教授。他在教會辦的協和大學和嶺南大學念本科和研究生,後來在嶺南大學工作。1952年,中山大學遷進嶺大校園,他成了中大的教師,是很受尊重的動物學家。
中大的院子挺大,公共汽車在外頭馬路從東校門到西校門要跑三個站。我們小時候,校園裡人少,房子也少,樹林、水塘和空地很多,絕對是孩子們撒野的快活林。江燕住東北區一座帶花園的房子,就是現在蓋東區食堂那地方,前面、後面和東邊不遠都是小朋友的家。
那年江燕大概八九歲。有一天,她看到魚塘的岸上擱著一條木船,船底破了幾個洞。她到同學家的院子撿了喂貓喂狗的盤子,然後對正在玩耍的小朋友們喊:“想不想去坐船?”五六個腦袋轉過來,小猴子們都跟著她飛跑。大家“一二三”、“一二三”地把破木船推進池塘。江燕指揮他們坐好,告訴小朋友要不斷用盤子舀水,不然船會沉掉。她用竹竿一下一下地撐,小船慢慢駛到魚塘中央。
一個小朋友的父母經過,看到孩子們的英雄壯舉,嚇得不輕,大聲叫:“危險!危險!趕快回來!”小孩子們玩得正高興,聽到喊聲,一下亂了陣腳,破船左右搖晃。江燕慌忙把船撐向岸邊,快到的時候把竹竿的一頭伸給岸上的大人。船兒一靠岸,小猴子們踩著池塘邊的淺水,啪啪啪啪,四散逃跑。
江燕在外頭繼續玩,天要黑的時候回家。她遠遠見到媽媽站在院子門口,怒氣衝衝,知道大事不妙,加快腳步,想從母親身邊溜過。媽媽饒不了她,撿起籬笆下的一根小竹竿抽她的屁股,說:“你自己玩就算了,竟敢裝一船小孩子劃到魚塘中央!”
這樣的胡鬧數不勝數。江燕會爬上大樹摘白蘭花和捉蟬子,在漆黑的防空洞裡亂竄——當時上頭老說要準備打仗,校園裡挖了不少防空洞,養了好多蚊子。她跟小夥伴用爛泥把小溪攔起來,潑掉裡面的水,活捉小魚、小蝦和螃蟹,然後炸了吃。那年頭食油是定量配給的。他們一次就用掉小朋友家整個月的油。江燕經常跟小朋友在學校木工廠泡在水池的原木上跑跳追逐。要是樹身翻轉,小家夥就掉到水裡,渾身濕透。男孩脫下衣服曬晾,女孩只好繼續穿著,等幹了再回家,省得挨罵。
東北區那一片哪家找不到孩子,那家媽媽就往江家跑,擒賊先擒王。
三
江先生在新加坡當過記者。那邊的朋友時常拉他去聽音樂會,江先生很快就著了迷。成家以後,他希望每個孩子都學點音樂。
江燕的哥哥江橋大概在七八歲的時候學小提琴。那太耽誤玩兒了,江橋像吃苦苦藥一般。江燕是家裡最小的孩子,跟哥哥一樣調皮。江橋撅著嘴巴練琴的時候,她經常跑過去幫忙,跟哥哥一人拉一下。房間裡琴聲吱呀響,爸爸媽媽以為兒子在練習。
有一天,哥哥學琴,江燕在邊上湊熱鬧。老師轉過頭問她想不想學,江燕猶猶豫豫地點了點頭。那時她五歲,只是一個小不點。江先生特意到廣州樂器廠定做了一把特別小的提琴。

江燕五歲時拉琴
江燕先跟哥哥的老師顧應龍先生學,後來投到鄭重門下。鄭先生是很有名的小提琴老師,挑學生特別嚴。江先生知道鄭老師隻收立志當專業提琴家的孩子,交代小女兒:“如果他問你,長大了是不是要專門拉小提琴,你就說是。”
其實江先生並不準備讓女兒以演奏為業,江燕也不想以後當專業音樂家。她經常到爸爸的實驗室玩,江先生會把一些標本放到顯微鏡下讓她看。平常用眼睛瞧不見的細小生命優雅地遊動舒展,色彩繽紛。有趣的動物世界給她帶來許多奇妙的幻想。她下定決心,長大了要像爸爸一樣,當個科學家。
她聰明,拉得挺好。鄭重老師低頭問她將來要不要當專業提琴家。小女孩望望父親,遲疑地點了點頭。於是她成了名師之徒。後來江燕還跟其他老師學過。當時經濟情況不好,食品缺乏。有一位老師每次來家裡教琴,江太太都要給他煮麵,放很多瑤柱、魷魚乾和蝦仁之類。那些東西江家自己平常都捨不得吃。
江先生是中大工會主席,有時候會讓小女兒在學校的晚會上演出。老師教的是歐洲的練習曲,而江燕在晚會上拉的是《社會主義好》、《風之歌》、《五月歌》和《很久很久以前》之類的流行曲目。她還很小,像個洋娃娃,大家都很喜歡她。小女孩自己也挺高興:別人用嘴巴唱歌,我能讓提琴唱歌。但練琴太苦了,孩子最喜歡的還是玩兒。
媽媽叫她練一個鐘頭琴,江燕會把鬧鐘撥快十五分。有一次,她想到一個高招:先把鍾調慢十五分,等媽媽設好鬧鈴,又把鍾調快十五分。半個小時後,鬧鐘一響,她就放下提琴,從窗口跳出去。那時各家的窗戶不裝鐵條,江燕是爬窗高手。她跟小朋友的喧嘩驚動了媽媽,江太太提著雞毛撣子把女兒趕回家。
江燕不但惹媽媽發火,還讓姐姐生氣。大姐和二姐學過鋼琴,知道學好樂器不容易。大姐時常陪她聽課,為不懂事的妹妹做筆記,幫助她練習。她拉錯了,兩個姐姐就告訴她。但那小東西不要別人管。姐姐說她拉得不對,她拉到那裡就有意再錯。大家拿她沒轍。
不過江燕機靈,學琴進步很快。江先生高興,又到樂器廠定做了不同尺寸的三把琴:她不管長多大都有琴用。
四
1966年,江燕念小學二年級。還沒到期末,學校就停了課。不久,一幫人衝進江家,把江先生夫婦和孩子都趕到客廳,他們在房間裡亂翻。江燕聽到裡頭啪、啪的巨大響聲,覺得不對,衝進自己房間,看到四把提琴全被砸成碎片。小姑娘“哇”地一聲就坐在地上大哭。
沒有了提琴,沒有了教琴的老師,江燕突然覺得:會拉琴真好!江先生不知從哪裡又搞來一把琴。江燕有時躲在屋裡練習,這時她很自覺,也很認真,把窗戶關得緊緊,生怕別人聽到惹麻煩。1968年夏天,學校又開門了。跟大家一樣,江燕兩年沒上課,照樣升上五年級。
但是,上頭不喜歡江先生的“秋風勁”小組,說他有特務嫌疑。江燕看著父親被抓到中大小禮堂前面,裝上卡車,送去監獄。七個月之後,江先生被押回學校,關在“廣寒宮”大樓審查,接著送去在英德的“五七乾校”。江太太照顧家庭,一直沒有出去工作。江先生的工資凍結了,家裡每人每月只有十二塊錢生活費,度日艱難。江燕十一二歲,經常爬圍牆到校外挖野菜。有時江太太也挖,跟孩子一起鑽牆洞出去。
五
1970年,江燕升初中。老師知道她會拉琴,叫她參加學校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下她就可以大模大樣地練習了。
當時廣州全市中學分成幾個片。因為江燕拉琴拉得好,廣州南片中學宣傳隊很快就把她要去。幾個月以後,全市中學的宣傳隊又把她要過去。那宣傳隊在省裡各地跑,到學校、工廠和農村演出。江燕拉獨奏,參加樂隊合奏,給舞蹈伴奏,跟大家一起布置和拆卸舞台,乾得挺歡。
她念初一,是宣傳隊裡最小的。好些隊友是高中生。其中一個男孩上高二,是演員的孩子,會作曲。江燕覺得他特別了不起,像個聖人。小姑娘懵懵懂懂,跟著別人跑,拉些流行的革命音樂,還拉那個男孩用簡譜寫的提琴曲。其實她對宣傳隊的崇高使命沒有一點了解。小孩子愛睡覺,宣傳隊的夥食太次,營養不夠。隊裡一開會,江燕就犯困,經常睡得呼呼響。
有一次宣傳隊巡回演出,江燕整整一個學期沒上課,老師照顧她,讓她別考試。她爸爸一介書生,本來就沒有任何罪過。審查的人也挖不出什麽東西,於是解除了對他的控制。江先生從“乾校”回來探親,覺得女兒不能不念書,自己給江燕補課。日夜不停地弄了一個星期,江燕居然門門都考了高分,只有化學不及格。江燕不是神童,混過幾科考試,主要因為學校上課不正常,沒教多少東西。
六
工商業萎縮,容不了幾個中學畢業生。上頭規定,每家隻留一個孩子在城裡照顧父母,其他都到鄉下,“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毛主席說:“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中學從六年減到四年。1972年夏天,我和江橋高中畢業,江燕從初中升高中。因為兩個姐姐已經去了農村,江橋分配到工廠。這意味著,兩年後,江燕幾乎肯定要下鄉。

江燕的姐姐江心竹(右)和江心梅(左)在農村
當時城裡的孩子到農村,不但乾得很辛苦,而且自己養不活自己,要家裡貼錢。剛好廣東省歌舞團公開招收學員。為了逃避下鄉,江燕在家裡拚命練琴,然後去考試。那年她十五歲,是姐姐帶著去的。她拉莫扎特第五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的獨奏。考官問她幾歲開始學琴,然後讓她離開考場。過了一會,學員隊的隊長走出來,對江燕說:“你被錄取了,下星期搬過來吧。”

1972年,江燕即將報考廣東省歌舞團
過了幾天,江燕帶著行李去省歌舞團。學員每個月拿二十塊錢津貼。她下半月報到,得了十塊,挺開心。
學員總共三十多個,有的學舞蹈,有的學唱歌,有的學器樂。大家住集體宿舍,星期六下午可以回家,星期天晚上回歌舞團。江燕是最早錄取的小提琴學員、唯一的器樂女生,跟八個學聲樂的女孩住一個大房。她在班裡年紀最小。大家用廣州話管她叫“細路仔”,意思是小孩子。
學員各人學自己的本行,另外學《毛主席語錄》、“老三篇”、報紙社論,還學一些樂理知識。歌舞團軍管,學員要參加軍事訓練。軍訓是排隊操練和打槍。音樂家的耳朵很重要,對聲音特別敏感。步槍後坐力大,聲音也大,江燕很怕。每次實彈射擊,她總是閉錯眼睛,子彈不知飛到那個星球。各個小組互相比成績,哪個組都不肯要她。
七
江燕練琴很拚命,一般早上五點多就開始,練到七點半到食堂吃早飯,吃完接著練。好些舞蹈學員也練得很瘋。
那年頭食品奇缺,食堂沒有多少東西給大家吃。另外,演員們工資收入也低。正式演員每月工資四十七塊五,舞蹈和銅管吹奏演員加八塊錢營養費。多數人每餐就買五分錢一碟的青菜。如果青菜上面攤幾片薄薄的肥豬肉,那要一毛錢。少數人吃一毛五的菜,裡頭有一些瘦肉。
一次,江燕排隊買飯,跟在黃河和牛得利後面,他們是舞蹈隊裡最重要的男演員,演舞劇《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裡的主角大春或者洪常青,上台要領舞一兩個鐘頭,平常每天排練五六個小時,體力消耗很大,但都買五分錢的菜。他們結婚了,要負擔家庭,只能節省。牛得利叫食堂師傅多給一點菜汁,好讓他吃下五兩米飯。當時上頭說要準備打仗,得儲存糧食。廣州的百姓平常吃放了幾年的“三級米”,不容易下咽。
如果有機會慰問軍隊,從團領導到清潔工都會參加:那邊有大魚大肉招待。另外接待外國官員講排場,宴會擺很多桌,實際上接待的官員並沒有那麽多,就拉表演團體的人湊數。江燕和她的同事到廣東迎賓館吃過好幾次,那飯菜的豐盛和精美是當時老百姓沒法想象的。江燕對宴會的豪華記憶很深,但對接待什麽人一點印象都沒有。大家就是衝那飯菜去的,根本不在意款待的是哪國的嘉賓,也沒有想過,在舞蹈明星跟食堂師傅講“買五分錢菜,多給點汁”的時候,是不是該搞那麽奢侈的宴會。
八
江先生已經從“乾校”回到中山大學,正在研究瘧疾防治。那是毛主席決定幫越南人搞的,叫“523項目”。後來江先生在世界聞名醫學雜誌《柳葉刀》(Lancet)上發表了中國人第一篇研究青蒿素的英語論文。按道理他屬於中國的優秀公民,在當時卻被當作“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是改造和利用的對象。歌舞團給江燕選了個特別革命的指導老師,幫助她改造思想。這位老師是孤兒,被解放軍的文工團收留,學會拉琴。因為真誠的感恩,她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主席簽上名寄回來。這是不得了的事!從此她有了很特別的地位。
江燕跟老師學琴很認真,但平常還是大大咧咧。除了樣板戲,那年頭百姓沒有多少娛樂。文藝團體的人能看到一些不公開放映的“內部電影”。那是難得的機會,票很少。歌舞團學員班的小孩子要發揮那些票的最大作用。假設有三張票,他們就進去三個人。其中一位帶著全部票出來,於是又進去三個,不斷循環。有一次江燕被抓住,在電影院值班室關了一晚,等歌舞團的頭兒來領人。還有一次,看完電影,大家上了歌舞團的交通車。團領導也在車上,人人都小心管住自己的嘴巴。江燕一坐下就大大咧咧地發表不合時宜的議論。邊上的女孩使勁踩她的腳,把她弄得很疼。下車以後,那女孩說:“你胡說八道,就不怕關大牢?”
跟大學一樣,歌舞團的多數職工也是住在同一個大院。江燕每天高高興興的,跟大家都挺好,特別喜歡跟一些不大激進的演員玩。誰知這讓她的指導老師很不高興。學習時間是三年,大概學了一年半,老師就不教她了。那天,江燕按時帶著提琴到老師家上課。老師說:“你的頭腦已經被別人俘虜了,還有啥好教的!”從此不再理睬她,還跟團領導講,江燕的思想有問題。
於是小姑娘成了音樂孤兒,每天一個人在琴房裡自己練習。過了好一陣時間,江先生知道了這件事,挺著急,坐兩個多小時的公共汽車,到歌舞團賠禮道歉。他敲開了指導老師家的門,小女孩跟在後面。江先生說:“江燕不懂事,非常對不起!我想跟你談談。”那位老師隔著紗門說:“有什麽好談的!”砰地就把木門關上。江先生在中山大學是很受尊重的專家,卻受到這樣的對待。江燕非常傷心。
她繼續當孤兒,繼續用功,三年期滿,順利畢業。江燕成為實習演員,工資三十四塊五。她還是天天帶著提琴去練習。琴房靠近創作組高士衡先生家。高先生曾經給《草原上的紅衛兵見到了毛主席》譜曲,風靡全國。但他是大家出身,知道家裡有點錢,不見得就是壞人。一次閑聊,高先生知道了江燕的處境,就熱情地叫小姑娘到他家上課。他本來就是小提琴家。於是江燕又有了指導老師。
九
1975年夏天,經過中央政治局審查,電影《海霞》上映。現在看來,這部講女民兵鬥壞人的片子挺幼稚,但在那時已經非常難得。特別是《海霞》對形式美的追求,給觀眾印象很深。它的主題歌立即唱遍全國。過了幾個月,《海霞》被說成是“右傾翻案風的典型”,禁止放映。1976年10月以後,形勢改變。高士衡先生根據《海霞》的主題歌,創作了管弦樂隊伴奏的小提琴曲《漁家姑娘在海邊》。
高先生把作品交給歌舞團領導。他了解江燕的水準,推薦江燕擔任獨奏。江燕當時並不知道,幾十年後才從高太太那裡聽說這事。團領導覺得江燕拉得不錯,還認為她出身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把她樹為典型,歌舞團也有功勞,批準了高先生的建議。其實江燕的父親一輩子沒開過商店,也沒辦過工廠,“資產階級”不知從何談起。
1977年,廣東省歌舞團在廣州友誼劇院辦春節文藝晚會。江燕獨奏《漁家姑娘在海邊》。原來踢開她的指導老師坐在江燕身後的管弦樂隊裡,為她伴奏。江燕的演奏受到好評,以後還演了幾次。於是,她成了歌舞團的重點培養對象,接連獨奏了好些中外名曲,現場錄音時常在電台廣播。
十
1980年,江燕在上海廣播電視藝術團的音樂會獨奏《安德路莎浪漫曲》、《塔蘭泰拉舞曲》和《斑鳩與小提琴》。這時她在上海交響樂團進修。
兩年前,江燕到了廣州樂團。這個樂團跟她一般大,1957年建立,比中央樂團小一歲,是共和國最老的交響樂團之一。1962年以後,極端主義風氣越來越猛,流行的口號是“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好些交響樂隊解散了,連中央樂團的生存都受威脅。周恩來總理說:“咱們中國多了不搞,搞四個交響樂隊,北京一個,上海一個,廣州一個,沈陽一個就夠了。”廣州樂團留了下來。
後來對“封、資、修”的批判越來越猛。在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之前,搞過一些文化交流。一次,費城交響樂團到北京演出,雙方商量好的節目單上有貝多芬第五交響曲。這部樂曲外號《命運》,突然被指責為宣揚宿命論。當時費城的演奏家已經出發。他們一下飛機,美國駐中國聯絡處的官員就跟樂團指揮講,中國領導人多數是農村出身,應該改演貝多芬的第六交響曲《田園》。費城交響樂團臨陣磨槍,匆匆排練《田園》,避免了一個外交事件。在這樣的氣氛裡,廣州樂團當然活不下去。
1965年,廣東省的文藝團體集中演出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第二年3月,演出結束,廣州樂團、華南歌舞團和梅州山歌劇團合並成廣東歌劇院。劇院裡有歌舞團、歌劇團和樂團。到1968年底,歌劇院的人下鄉去辦“五七乾校”。第二年春節以後,上頭從“乾校”抽了一百一十多人,回廣州建立廣東省歌舞團。但到1978年,廣州樂團才恢復。
樂團挑走了江燕,隨後送她去上海交響樂團進修。上海的氣象不像廣州那麽溫和,那時樂團的條件還挺差。江燕夏天練琴,腳底一灘汗;冬天練琴,穿了厚棉襖,戴上專門的保護手套,指頭還凍得硬邦邦,不聽使喚。
進修計劃兩年。大概過了一半時間,她在廣州樂團的好朋友黃麗平到上海跟林俊卿大夫進修。林先生原來在金陵大學和北平協和醫學院學醫,然後跟意大利音樂家學聲樂,是優秀的男中音和出版過多部專著的聲樂理論家。江燕跟麗平去看林大夫。老先生很喜歡江燕,知道她在住的地方不能練琴,離樂團又遠,就熱情地請她搬到自己家。林家很寬敞,有三層樓。大夫的女兒是很出色的鋼琴手。大家談得來。林先生喜歡聽江燕拉琴,跟她聊天。江燕又有了一個很溫暖的家。

江燕(後排右一)在林俊卿先生(前排右一)家
十一
1977年底,中國的高等學校恢復了中斷十一年的公開招生。想進大學的年輕人都很興奮。1980年,江燕參加上海音樂學院的考試。不久,她接到廣州樂團的加急電報,命令她馬上回去。
江燕匆忙離開林先生家,坐上開往廣州的火車。下了車,她直奔樂團。原來上海音樂學院把錄取通知寄到了廣州樂團辦公室,團領導很不高興。團長和副團長把江燕帶到會議室,很嚴肅地說:“你沒經過組織批準,就私自報考上海音樂學院,你的錄取不合國家規定!叫你回來是給你一個改過的機會。”江燕一下子就癟了。
後面三個月,她跟著樂團的一個分隊在廣東各地農村表演。隊員有唱歌的,還有演奏民樂的。只有江燕挨罰,臨時帶著一把提琴摻進來。她獨奏《慶豐收》和其他提琴曲,伴奏的是琵琶和揚琴之類民族樂器。別人演奏,她壓根幫不上忙。
睡覺的床是鋪在地上的稻草,刷牙洗臉就在門口的小溪。那時沒啥工業汙染,溪水透明見底。農民在上遊刷耕牛。牛兒洗痛快了,隨便拉屎。看著一塊牛糞飄來,樂團的人趕快拿開毛巾和杯子,等牛糞飄過再蹲下,接著洗漱。後來突然想起,牛尿到了水裡是看不見的。
其實農民挺喜歡他們。每頓飯都像宴會一樣,有整條的清蒸大草魚、燉雞蛋,還有鮮蠔。晚上,他們坐農民劃的小船到各個村莊演出。月色溫柔,大樹和竹叢在水面投下搖晃的倒影,演員們低聲哼著優美的歌。江燕一時忘了不能上大學的失落。

江燕下鄉演出
她回到廣州。林俊卿先生去美國探親,寫信問江燕想不想出國學習。“當然想!”江燕回答。她對著家裡的卡式錄音機拉琴,把三盒磁帶寄到上海。林先生把它們交給了新英格蘭音樂學院(New England Music Conservatory)、克里夫蘭音樂學院(Cleveland Institute of Music)和博靈格林大學(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三個學校馬上錄取了她,都給全額獎學金。江燕不懂英語,害怕對付不了大城市的生活,選了博靈格林大學。
十二
1981年9月,江燕到達美國俄亥俄州。
美國熱帶衛生協會秘書長霍肯格博士(Dr. M. Hoekenga)是她爸爸的朋友,從機場接她到家裡住了幾天。霍肯格和太太很熱情,但江燕幾乎天天挨餓。
他們家的餐廳特別漂亮,上面是高雅的水晶吊燈,下面是精致的紅木餐桌。晚餐先上蔬果沙拉。中國人不習慣那些沒煮過的菜和沒有味道的牛油果,江燕吃得很少。接著霍肯格先生給大家分烤肉、火雞、肉餅之類主菜。各人摻上麵包或者土豆一起吃。過一會,霍肯格先生會挨個問,還要不要加點肉。因為中國傳統的客氣,江燕說No。誠實的主人就把她實際上想吃的東西端下桌。美國佬就是這樣,完全不懂得婉轉客套。晚上睡覺,江燕發誓第二天一定要改掉心口不一的習慣。可是,到下一次晚餐,又是舊戲重演。直到最後一天,她才坦率地說出Yes。
霍肯格夫婦開了兩百五十英裡汽車,把江燕送到博靈格林大學。那時中國開放不久,她是學校裡唯一的中國大陸學生。外國學生要先參加英語考試。一百分的試卷,江燕拿了二十四分,打破學校紀錄。校長請一個華裔的泰國女孩陪江燕到他的辦公室,很和氣地說:“我們沒法接收你。你的英語程度太低,要去語言學校。一年以後,看你英語水準怎麽樣,我們再考慮讓你重新入學。”江燕知道這是對的。不懂英語,以後的日子沒法熬。
她回宿舍,把剛打開的行李收拾起來,等待發配語言學校。第二天一早,頭天那個泰國女孩敲門,又把她帶到校長辦公室。校長告訴江燕:“我們不能讓你去語言學校。這個大學是你的法律保護人和經濟擔保人。你如果離開我們學校,政府會把你送回中國。怎麽辦呢?我們決定讓你留下,看你能不能學下去。”
江燕一咬牙,拚了!她跟其他同學一起上課。整整一年,江燕覺得自己沒見過太陽,不是在燈下拚命學習,就是倒頭睡著,死記硬背,野蠻至極。結果所有考試都過關,學校正式承認她的學生資格。後面三年,江燕學音樂理論和小提琴技法,上物理、高等數學、地理和其他基礎課。她沒有學過基礎英語,原來只有小學二年級的文化底子:1966年以後就沒有上過正經的文化課。在大學裡,除了拉琴,每門課程都是殘酷的打拚。
美國同學知識面之廣、業餘愛好之多,讓江燕震驚。他們從小學就開始到圖書館查資料,做自己的研究。各個小學和中學都有多種多樣的體育和藝術活動。有一次,江燕看國際體育比賽。邊上的人問她:“你喜歡美國隊嗎?”她說:“喜歡。”江燕知道,美國隊的運動員不是集中訓練出來的。他們平常在普通的中學和大學念書,跟大家一樣聽課和考試,自己業餘參加體育運動。國際比賽開始之前,最拔尖的業餘運動員湊成國家隊。邊上的人追問江燕為什麽喜歡美國隊,她回答:“因為他們是普通學生,因為美國的體育是真正的大眾運動。”
十三
江燕拉琴拉得好,很快就得到全額獎學金參加有名的阿斯彭(Aspen)音樂夏令營,跟茱莉亞音樂學院的迪蕾教授(D. Delay)學習。迪蕾教出過帕爾曼(I. Perlman)、沙罕姆(G. Shaham)、林昭亮、敏茲(S. Mintz)和薩拉·張(S. Chang)等國際明星,是世界聞名的小提琴教母。
她和藹可親,講話不多,但很有啟發。能得到迪蕾的點撥,學生們都覺得幸運。迪蕾坐私人直升機從紐約去阿斯彭上課,到達時間不準確,早的在上午十點,晚了會過下午一點。有時她來遲了,學生們怕失去聽課的機會,連午飯都不敢吃,在琴房裡一邊練習一邊等。現在大名鼎鼎的約書亞·貝爾(Joshua Bell)和高島米多莉(Midori Goto)也在那個夏令營,一個十四歲,一個十一歲。
學校給的獎學金能負擔全部學雜費,房租和吃飯得靠自己。離開中國的時候,在新加坡的一個堂姑姑給了江燕六千美元,解決了一年的住宿費。到頭一個暑假,她已經成了窮光蛋。江燕在美國沒有任何親戚。那時中國人收入很低,家裡沒法給錢讓她在美國生活。她的英語還不行,想到麥當勞、漢堡王和必勝客打工,都沒去成,只好在學校食堂洗碗。巨大的洗碗機有十多米長。江燕先用滾燙的熱水衝碗碟,把餐具放進洗碗機,然後走到機器另一頭,將洗淨烘乾的碗碟拿出來。衝碗碟,肮髒的食物濺滿前胸。沖洗的水很熱,剛烘乾的餐具更熱,江燕的手總是燙得通紅。她拉提琴,保護雙手很重要;但她要活命,保護肚子更重要。
江燕還到別人家做衛生,每個禮拜一次,擦窗戶,洗廁所,給地毯吸塵,擦家具,乾六個鐘頭,得四十八美元。另外是到飯店拉四重奏,去托裡多交響樂團(Toledo Symphony Orchestra)兼職。
四年過去,江燕按時畢業。兩千多學生參加全校的畢業典禮,優秀學生裡成績最拔尖的叫summa cum laude,有三四個。其次是magna cum laude,有十來個。再下來是cum laude,有二十多個。江燕是第三等級的優秀畢業生。當校長念名字,讓他們站起來,全場鼓掌的時候,她自己也不敢相信。
本科畢業,江燕進了托裡多交響樂團,接著念碩士生,然後在新奧爾良和弗羅裡達等地的交響樂團工作。她的女兒三歲開始學琴,念高二時開始在弗羅裡達交響樂團當兼職小提琴手,隨後到普林斯頓學國際政治,畢業後進音樂學院念研究生,今年6月得到指揮專業的博士學位,指揮不同的樂團演奏過貝多芬、舒伯特、馬勒的交響曲和布魯赫的幻想曲。

江燕在弗羅裡達交響樂團
(作者感謝江燕女士接受採訪、提供回憶材料和照片,感謝廣東省歌舞團的朋友熱情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