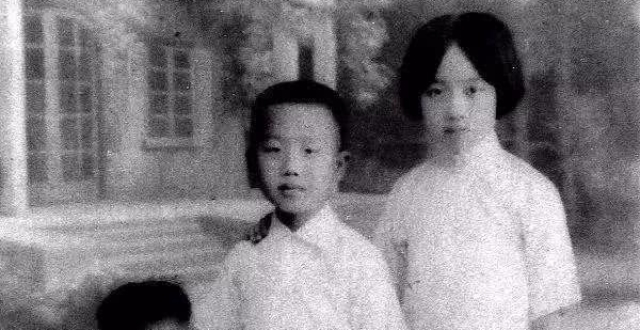顧隨和他的弟子葉嘉瑩
文丨趙林濤

大學畢業時的葉嘉瑩
葉嘉瑩,號迦陵,1924年生於北京。她一生從事古典詩詞的研讀與教學,是公認的顧隨先生的傳法弟子。葉嘉瑩說:“我最該感激的有兩位長輩,一位是在我幼年時教我誦讀唐詩的我的伯父狷卿公,另一位就是在我進入大學後,擔任我們詩詞曲諸科之講授的我的老師顧羨季先生。伯父的引領,培養了我對詩詞之讀誦與寫作的能力和興趣;羨季先生的講授則開拓和提高了我對詩詞之評賞與分析的眼光和境界。”
妙音迦陵
葉嘉瑩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熏陶。她的父母認為人在“童幼年時記憶力好,應該多讀些有久遠價值和意義的古書,而不必浪費時間去小學裡學些什麽‘大狗叫小狗跳’之類淺薄無聊的語文”,因此請她的姨母做家庭教師教她讀《論語》。另外,她的伯父有很好的詩詞修養,耳濡目染,使她在學詩的興趣和領悟方面得到很大的啟發。
1942年秋,在顧隨先生的“唐宋詩”課上,她的天賦才華得到了充分展示,並且得到老師的讚賞:
作詩是詩,填詞是詞,譜曲是曲,青年有清才如此,當善自護持。勉之,勉之。
這是顧隨先生對葉嘉瑩大學之前幾首習作的評語。而自“上過先生之課以後”,葉嘉瑩自喻“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內的飛蠅,驀見門窗之開啟,始脫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萬物之形態”。在葉嘉瑩看來,顧隨先生“對於詩歌具有極敏銳之感受與極深刻之理解,更加之先生又兼有中國古典與西方文學兩方面之學識及修養,所以先生之講課往往旁征博引,興會淋漓,觸緒發揮,皆具妙義,可以予聽者極深之感受與啟迪”。而她“既因聆聽先生的講授而對詩詞的評賞有了較深的體認,更因先生不斷的啟發和鼓勵,在創作方面也有了逐漸的進步和提高”。甚至於習作的風格,也受到顧隨先生的影響。

葉嘉瑩的輔仁大學獎證
我們不妨就來看看,大學二年級時的葉嘉瑩已經有了怎樣的手筆。
小令《落梅風》:
寒燈燼,玉漏歇。點長空亂星殘月。一天風送將冬至也。擁柴門半堆黃葉。
顧隨先生評曰:“結二語逼真元人,未可以其看易而忽之。”與此同在一紙的還有兩首小令,先生的總評是:“小令妙在自然;深刻之思力,健舉之筆力,須要使人不覺。此作庶幾近之。”
套數《般涉調耍孩兒》:
〔一煞〕見只見蜂蝶紛紛爭嫩蕊,聽只聽杜宇聲聲啼斷腸。春魂冉冉隨風蕩。今日個是踏青士女如雲聚,明日個我立馬西風數雁行。事事堪惆悵。說什麽吹簫擊築,訪酒侶到高陽。
顧隨先生旁批“立馬七字好句”,並建議將最後一句中的“訪”字和“到”字去掉。

1943年夏,顧隨與國文系41級女生在輔仁大學女院垂花門前合影(後排右五為葉嘉瑩)
《顧隨與葉嘉瑩》一書中收錄了顧隨先生批改葉嘉瑩詩詞曲習作五十七首,從中我們也能略窺為師的才思與敬業。《鷓鴣天》末句“幾點流螢上樹飛”,“上”字改為“繞”字,並注以“上字太猛,與螢不稱,故易之”—這是一字之易。《春遊雜詠》之七“年年空送夕陽歸”句,“年年”改為“晚來”,並注以“年年字與夕陽字衝突”—這是一詞之易。《寒假讀詩偶得》“詩人原寫世人情”一句,改為“眼前景物世間情”—這是一句之易。有的改動可以看到是經過了反覆的推敲,如《楊柳枝》之七“而今大似琅玡木,誰撫長條為泫然”二句,先說:“木字改樹字何如?”後又建議:“末二句擬改作‘而今誰上琅玡道,為撫長條一泫然’。”

顧隨批改葉嘉瑩習作
葉嘉瑩言及老師為她批改作業的情形時說:“一般說來,先生對我之習作改動的地方並不多,但雖然即使只是一二字的更易,卻往往可以給我極大的啟發。先生對遣辭用字的感受之敏銳,辨析之精微,可以說是對於學習任何文學體式之寫作的人,都有極大的助益。”
除了斟酌文句之外,顧隨先生更對弟子的詩心細加呵護。如對套曲《仙呂賞花時》總評曰:“穩妥,有似明人之作。欠當行者,以少生辣之味耳。”對《臨江仙·連日不樂夜讀〈秋明集〉有作》詞評曰:“是用意之作,但少自在之致耳。”對《楊柳枝》八首之總評曰:“近作詩極見思致,但音節中稍欠和諧生動,不知作者以為何如耳?”對《初夏雜詠》四首之總評曰:“錘字堅實,想見工夫。但此更希望保存元氣也。”對《憶蘿月》詞評曰:“太淒苦,青年人不宜如此。”如此等等,足見顧隨先生對這位才華橫溢的弟子欣賞之至、呵護有加。
有時,師生之間還互相唱和。1944年秋,葉嘉瑩寫了六首七言律詩,顧隨先生發還時不僅一字未改,還附以六首和詩;葉嘉瑩疊韻再和,顧隨先生複作長句六章。
多年以後,葉嘉瑩在文章中寫道:“先生對我的師恩深厚,但因我年輕時的性格拘謹羞怯,很少獨自去拜望先生,總是與同學一同去。見到先生後,也總是靜聆教誨,很少發言,我對先生的仰慕,只是偶然會寫在詩詞的作品中。”五古《題季師手寫詩稿冊子》所敘寫的便是葉嘉瑩對顧隨先生的詩與字的種種感受和內心真誠的仰慕:
自得手佳編,吟誦忘朝夕。吾師重錘煉,辭句誠精密。想見醞釀時,經營非苟率。舊瓶入新酒,出語雄且傑。以此戰詩壇,何止黃陳敵。小楷更工妙,直與晉唐接。氣溢烏絲闌,卓犖見風骨。人向字中看,詩從心底出。淡宕風中蘭,清嚴雪中柏。揮灑既多姿,盤旋尤有力。小語近人情,端厚如彭澤。誨人亦諄諄,雖勞無倦色。弟子愧凡夫,三年面牆壁。仰此高山高,可瞻不可及。
葉嘉瑩聽顧隨先生講課,自1942年後即未間斷,包括畢業以後已在中學任教之時。那時顧隨先生除了在輔仁大學擔任唐宋詩的課程以外,還在中國大學教授詞選和曲選,葉嘉瑩經常騎車趕去兩校旁聽。
1947年初,弟子們要為老師五十周歲生日舉行一場慶祝宴會,葉嘉瑩受推撰寫祝壽籌備會的通啟:
蓋聞春回閬苑,慶南極之輝;詩詠閟宮,頌魯侯之燕喜。以故麥丘之祝,既載齊庭;壽人之章,亦播樂府。誠以嘉時共樂,壽考同希。此在常人,猶申祝典,況德業文章如我夫子羨季先生者乎。先生存樹人之志,任秉木之勞。卅年講學,教布幽燕。眾口弦歌,風傳洙泗。極精微之義理,賅中外之文章。偶言禪偈,語妙通玄。時寫新詞,霞真散綺。寒而毓翠,秀冬嶺之孤松;望在出藍,惠春風於細草。今歲二月二日即夏歷丁亥年正月十二日,為我夫子五旬晉一壽辰,而師母又值四旬晉九之歲,喜逢雙壽,並在百齡。樂嘉耦之齊眉,頌君子之偕老。花開設帨,隨淑氣以俱欣;鳥解依人,感春風而益戀。凡我同門,並沐菁莪之化,常存桃李之情,固應躋堂晉拜,侑爵稱觴。欲祝嘏之千秋,願聯歡於一日。尚望及門諸彥,共襄斯舉,或抒情抱,或貢詞華。但使德教之昌期,應是同門之慶幸。日之近矣,跂予望之。
葉嘉瑩的才華在同學輩中是公認的,而這一篇華美的文字,也當是獻給老師最好的賀禮了。

顧隨致葉嘉瑩書(1946年7月18日)
早先,顧隨先生欲將葉嘉瑩的作品交給報刊發表,曾在課堂上問她有沒有筆名或者別號,葉嘉瑩說沒有,先生要她想一個,她想起佛經上提到的一個鳥名——迦陵,發音並與“嘉瑩”相近,遂以為號。“迦陵”,系音譯“迦陵頻伽”的簡稱。《翻譯名義集》卷六:“迦陵頻伽,此雲妙聲鳥。”並引《正法念經》:“山谷曠野,其中多有迦陵頻伽,出妙音聲。如是美音,若天若人,緊那羅等無所及者。”
傳法弟子
顧隨先生常用禪宗古德的話“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勉勵學生,希望他們能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1946年7月13日,顧隨先生在信中表達了對葉嘉瑩莫大的期許:
年來足下聽不佞講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卻並不希望足下能為苦水傳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傳,則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盡得之。此語在不佞為非誇,而對足下亦非過譽。不佞之望於足下者,在於不佞法外,別有開發,能自建樹,成為南嶽下之馬祖;而不願足下成為孔門之曾參也。
“南嶽”指的是唐代高僧懷讓,馬祖道一隨懷讓學禪十年,嗣後開宗門、建叢林,對禪宗乃至中國佛教做出重大貢獻。顧隨先生以馬祖為喻,告誡弟子不要亦步亦趨為老師所局限,而應勇於突破開創屬於自己的天地。至於如何能夠“達到此目的”,信中說道:“除取徑於蟹行文字外,無他途也。”所謂“蟹行文字”,指的是橫向書寫之字母文字。信中還說:“至少亦須通一兩種外國文,能直接看‘洋鬼子’書,方能開擴心胸。”顧隨先生此語,既是因材施教,又是經驗之談。“先生幼承家學,對古典早有深厚之修養,其後又畢業於北大之英文系,在為學方面能融古今中外為一體”,“這正是何以先生在論詩談藝之際,能隨時有高論妙悟的一個主要原因”。

葉嘉瑩,1948年3月攝於上海
1948年春,葉嘉瑩要去南京結婚。顧隨先生為賦《送嘉瑩南下》一首相送,中間有句:“十載觀生非夢幻,幾人傳法現優曇。分明已見鵬起北,哀朽敢言吾道南。”“鵬起北”,因為葉嘉瑩當時要離開北平去南方;“吾道南”,用的是禪宗典故,禪宗五祖弘忍傳衣缽與六祖慧能時說“吾道南矣”。詩的意思是說,自己教了這麽多年書,希望能夠後繼有人,而他的希望就寄托在葉嘉瑩身上。
1948年11月,葉嘉瑩隨在國民黨海軍供職的丈夫趙東蓀去了台灣。在《懷舊憶往——悼念台大的幾位師友》一文中,葉嘉瑩說:老師“在信中殷殷向我介紹了在台灣任教的他的幾位友人,那就是當日在台灣大學任教的台靜農先生、鄭騫先生,還有一位李霽野先生。顧先生在信中還附下了幾張介紹的名片,囑我抵台後去拜望他們”。

顧隨致台靜農書(1948年12月10日)
葉嘉瑩赴台之初,師生之間尚有通信聯絡。1948年12月4日,顧隨先生在日記中寫道:“得葉嘉瑩君自台灣左營來信,報告近況,自言看孩子、燒飯、打雜,殊不慣,不禁為之發造物忌才之歎。”此後不久,葉嘉瑩與同在台灣的先生二女之英,便都失去了音訊。1949年7月25日,先生在致弟子劉在昭的信中流露出內心的焦慮:“嘉瑩與之英遂不得消息,彼兩人其亦長長相見耶?”劉在昭是葉嘉瑩最要好的朋友,先生此問,或許不無試探消息的用心吧。
事實遠比顧隨先生了解和想象的嚴重。1949年12月,葉嘉瑩的丈夫因“白色恐怖”被捕。次年夏,她帶著吃奶的女兒也被關了起來,雖在其後不久獲釋,但卻失去了教職和宿舍,無奈寄身丈夫的一個親戚家。而她的丈夫則繼續羈押在左營軍區附近的一個山區,三年之後才重獲自由。至於顧隨先生為葉嘉瑩所寫的那封薦書,在她的丈夫被捕之時即被搜沒,尚且未到台北送呈台靜農等。然而,時隔六十餘年,令葉嘉瑩激動欣喜的是,在整理丈夫遺物時,發現那封信竟然一直混雜在當年發還的物品中,意外地“失”而復得了。

葉嘉瑩20世紀60年代在台灣
1956年,已在台灣大學任教的葉嘉瑩先後撰寫發表了兩篇評賞文章。一次,鄭騫見到葉嘉瑩,說“你所走的是顧羨季先生的路子”,儘管鄭騫認為這條路子並不好走,因為“作者要想做到自己能對詩歌不僅有正確而深刻的感受,而且還能透過自己的感受,傳達和表明一種屬於詩歌的既普遍又真實的感發之本質,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仍對葉嘉瑩十分讚賞:“你可以說是傳了顧先生的衣缽,得其神髓了。”從“為一己之賞心自娛的評賞”而至“為他人的對傳承之責任的反思”,是葉嘉瑩詩詞路線上的一個重大轉變,並由此轉入理論研究的新階段。在多年教學、研究的實踐中,葉嘉瑩對老師當年關於取徑西方文化的叮囑亦逐漸有了自覺和深刻的認識。在《我的詩詞路線》前言中,她說:
一般說來,由於我自幼所接受的乃是傳統教育,因此我對於傳統的妙悟心通式的評說,原有一種偏愛。但多年來在海外教學的結果,卻使我深感到此種妙悟心通式的評說之難於使西方的學生接受和理解。這些年來,隨著我英語閱讀能力之逐漸進步,偶然涉獵一些西方批評理論的著作,竟然時時發現他們的理論,原來也與中國的傳統文論有不少暗合之處。這種發現常使我感到一種意外的驚喜,而借用他們的理論能使中國傳統中一些心通妙悟的體會,由此而得到思辨式的分析和說明,對我而言,當然更是一種極大的欣愉。直到現在,我仍然在這條途徑上不斷地探索著。
……我個人做事原有一個態度,那就是願望與盡力在我,而成功卻不必在我。我只希望在傳承的長流中,盡到我自己應盡的一份力量,庶幾不辜負當年我的尊親和師長們對我的一片教誨和期望的心意。
文章節選自《顧隨和他的弟子》中華書局2017年出版
圖片轉自“章黃國學”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