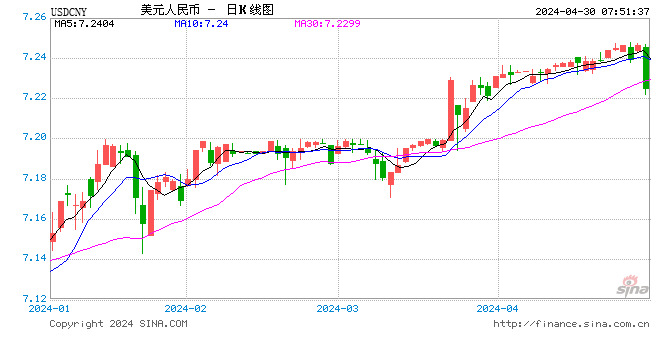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管濤
2015年“8.11”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呈現有漲有跌的雙向波動。2018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最高升破6.28,最多升值近4%,最低跌破6.96,全年最大振幅達11%。如果國內企業被動而非主動地管理匯率風險,則主業利潤可能會被嚴重侵蝕。2005年“7.21”匯改後,豐富外匯交易品種、大力發展外匯市場是匯改的重要內容。
目前,中國外匯交易除即期外,還有遠期、外匯和貨幣掉期、期權等人民幣外匯衍生品交易。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2014年底發布的匯發[2014]第53號文《銀行辦理結售匯業務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的規定:“銀行對客戶辦理衍生產品業務,應當堅持實需交易原則。客戶辦理衍生產品業務具有對衝外匯風險敞口的真實需求背景,並且作為交易基礎所持有的外匯資產負債、預期未來的外匯收支按照外匯管理規定可以辦理即期結售匯業務”。簡而言之,就是能夠辦理即期結售匯業務的外匯收支活動,都可以辦理外匯衍生品交易。下面,我們基於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外匯市場交易和銀行代客結售匯統計數據,來分析國內企業的匯率避險現狀,得出了以下幾點觀察及結論。

一、匯改後境內外匯衍生品交易趨於活躍但企業匯率避險的積極性依然偏低
根據外匯局的外匯市場交易統計,2019年上半年,即期貨易佔到外匯市場總成交量的37.0%,較2014年佔比下降了19.9個百分點,這反過來意味著境內外匯衍生品交易的運用程度上升。具體來看,遠期貨易佔到1.3%,下降了3.4個百分點;外匯和貨幣掉期佔到58.8%,上升了21.8個百分點;期權交易佔到0.9%,上升了0.4個百分點(見圖1)。可見,外匯和貨幣掉期是中國外匯市場的主要匯率避險工具,也是即期貨易佔比下降的主要受益者,而遠期和期權交易的運用程度均有所下降。

2016年,全球即期貨易佔到外匯市場總成交量的32.6%。與之相比,中國外匯市場的產品結構隻落後3~6年。而“8.11”匯改前,這個差距至少在20年以上。從衍生品交易的佔比看,2016年,全球遠期、外匯和貨幣掉期、期權交易佔比分別為13.8%、48.6%和5.0%。中國與之相比,對於遠期和期權交易工具的運用程度偏低,而對於外匯和貨幣掉期工具的運用偏高(見圖2)。

中國外匯衍生品交易趨於活躍,不等於中國企業運用匯率避險工具更加積極。根據外匯局公布的外匯市場交易數據,2019年上半年,中國境內銀行對客戶的外匯市場交易(又稱銀行代客交易或外匯零售市場)中,即期貨易佔到82.8%,較2014年提高了3.6個百分點;遠期貨易佔到7.6%,下降了6.2個百分點;外匯和貨幣掉期貨易佔到2.9%,下降了2.6個百分點;期權交易佔到6.7%,上升5.2個百分點(見圖3)。可見,儘管匯改以來國內企業運用衍生品工具總體不夠積極,但在人民幣匯率走勢不確定、期權交易成本較低(相同條件下,期權交易的外匯風險準備金是減半徵收)的情況下,運用期權交易工具避險的傾向有所提高。

而且,與國際水準相比,中國企業對外匯衍生品的運用明顯偏低。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16年,全球非銀行金融機構及非金融客戶即期外匯交易的佔比僅有35.5%,遠低於中國企業佔比80%多的水準;遠期、外匯和貨幣掉期、期權交易的佔比分別為17.3%、41.3%和5.8%。可見,國際上,非銀行金融機構及非金融客戶也主要是以外匯和貨幣掉期貨易進行匯率避險,但對於遠期和期權交易工具的使用較中國企業程度更深一些(見圖4)。

中國外匯市場的產品結構接近國際水準,主要貢獻來自於銀行間市場(又稱外匯批發或同業市場)。2019年上半年,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量中,即期貨易佔比30.1%,較2014年回落了16.6個百分點;遠期貨易佔比0.3%,回落了0.3個百分點;外匯和貨幣期貨交易佔比67.2%,上升了16.1個百分點;期權交易佔比2.4%,上升了0.9個百分點(見圖5)。而國際清算銀行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16年,全球報告交易商即期外匯交易的佔比為27.5%,領先中國銀行間市場3~6年;遠期、外匯和貨幣掉期、期權交易的佔比分別為8.6%、56.4%和7.6%,中國與之相比,對遠期、期權交易的運用程度要低於國際平均水準,但對外匯和貨幣掉期的運用程度則高於國際水準(見圖6)。此外,從批發與零售市場外匯交易量的對比看,2019年上半年中國的比例高達671%,而2016年全球平均水準為75%(上世紀末也只有175%)。這也反映了中國外匯市場與成熟市場之間的差距。


前述方法是比較靜態分析,可以查找中國外匯市場與國際市場發展的差距。但是,由此仍不能了解外匯衍生品交易到底幫助國內企業對衝了多少跨境交易的匯率風險。以下,本文擬利用國內外匯交易統計數據,從存量和流量兩個角度做些嘗試。
二、從對外金融資產負債角度看近年來國內企業運用匯率避險工具對衝風險的力度降低
“8.11”匯改之前,人民幣匯率長期單邊升值,這助長了資產本幣化、負債美元化的利差交易策略,造成了民間部門較為嚴重的貨幣錯配。匯改引燃了貶值預期,觸發了市場增持外匯資產(即藏匯於民)、減少美元負債(即債務償還)的操作。截止2018年6月底,民間貨幣錯配(以剔除儲備資產的國際投資淨頭寸衡量)降至1.14兆美元,較2015年6月底(“8.11”匯改前夕)減少了52%;與年化GDP之比降至8.6%,較2015年6月底下降了13.3個百分點(見圖7)。這在2015和2016年導致了資本集中外流、外匯儲備下降。但由於民間貨幣錯配大幅改善,當2018年下半年遭受外部衝擊,人民幣匯率二次跌至心理關口附近時,卻沒有再引發市場恐慌。
增持對外資產、減少對外負債的市場後果之一是,市場匯率風險管理行為突變。匯改當月,由於貶值恐慌,銀行代客遠期購匯簽約大幅增加,未到期遠期淨購匯餘額翻番,這招致了外匯風險準備金制度的頒布(見圖8)。所以,可以用衍生品交易對於對外金融資產負債的套保比率來觀察國內企業的匯率風險對衝狀況。


一種方法是用未到期遠期淨購匯與民間貨幣錯配狀況之比來衡量。截止2019年3月底,銀行代客未到期遠期淨購匯頭寸454億美元,相當於同期民間對外淨負債1.25兆美元的3.6%,略高於2015年6月底1.5%的水準,但處於“8.11”匯改以來最低,且遠低於2015年第三季度至2018年第四季度該比例平均為7.8%的水準(見圖9)。

還有一種方法是以未到期淨購匯(含期權)與民間貨幣錯配之比來衡量。外匯局自2017年起公布外匯期權交易的統計數據。將未到期的期權Delta敞口考慮在內,則對民間貨幣錯配的風險對衝覆蓋率有所提高,2019年3月底達到6.1%,但遠低於2017年3月底14.3%的水準,也是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見圖10)。

再一種方法是用遠期結匯(或購匯)未到期累計額與民間對外金融資產(或負債)之比來衡量。截至2019年3月底,銀行代客遠期結匯未到期累計額為555億美元,與民間對外金融資產之比為1.3%,略高於2015和2016年貶值預期較強時1%以下的水準,但低於2014年之前單邊升值預期時5%~10%的水準;銀行代客遠期購匯未到期累計額為1099億美元,與民間對外金融負債之比為1.9%,為2011年初以來最低,甚至較2015年第二季度末還低0.8個百分點(見圖11)。可見,國內企業對對外金融負債的匯率風險管理依然薄弱。
這三種方法按照權責發生製而非現金收付製,符合衍生品交易跨期性、不用立即交割的主要特徵。但不足之處是,一方面,國際投資頭寸表反映的對外金融資產負債是低頻的季度數且公布時滯較長,使用不方便;另一方面,期權和掉期貨易的數據顆粒較粗且時間序列較短,特別是不能用於對比“8.11”匯改前後市場行為的發展變化。

三、從基礎國際收支交易角度看近年來國內企業匯率風險對衝力度也是呈下降趨勢
前述方法是以存量比存量,但數據頻率低、時間序列短。還有一類方法是以流量比流量,可以彌補上述不足,並提供不同的觀察視角。
一種方法是用外匯衍生品交易的簽約額,來衡量國內企業基於基礎國際收支交易的匯率風險對衝狀況。鑒於外匯和貨幣掉期主要用於管理利率風險,故從外匯衍生品交易中剔除。為平滑數據波動,對數據均做3個月移動平均處理。根據外匯局自2015年起按月發布的外匯市場交易數據,2019年5月,銀行對客戶外匯衍生品交易額總計585億美元,相當於基礎國際收支交易額(即貨物和服務貿易收支額與非金融部門跨境直接投資額合計)4443億美元的13.2%,同比回落了3.7個百分點,更遠低於2015年7月(“8.11”匯改前夕)的18.9%(見圖12)。

另一種方法是簡化的基礎國際收支交易外匯風險套保比率。鑒於服務貿易收支和期權交易的時間序列較短且數據顆粒較粗,而遠期結售匯數據自2010年起發布,且有對應的收入和支出數據,所以,可以像第二部分的第三種方法那樣,用遠期結售匯簽約數來衡量區分基礎國際收支交易方向的匯率風險套保狀況。為平滑數據波動,對數據均做3個月移動平均處理。2019年6月,以此衡量的運用遠期結匯套保的比例為9.3%,同比回落了2.1個百分點,且低於2015年7月的8.5%;運用遠期購匯套保的比率為3.3%,同比回落了11.2個百分點,且遠低於2015年7月的18.0%(見圖13)。

第三種方法,考慮到近年來隨著跨境人民幣業務發展,以人民幣計價結算成為一種匯率風險自然對衝的手段,還可以構造一個用遠期結售匯簽約額與銀行代客涉外外匯收付(即銀行代客涉外收付剔除涉外人民幣收付)之比衡量的外匯風險套保比率。對數據同樣做3個月移動平均處理。2019年6月,以此衡量的遠期結匯對衝風險的比例為9.6%,同比回落了1.6個百分點;遠期購匯對衝風險的比例為2.8%,同比回落了9.6個百分點,更是遠低於2015年7月的13.8%(見圖14)。企業利用外匯收入或外匯存款對外支付,減少本外幣兌換,也是一種自然對衝匯率風險的做法,但缺乏這方面的公開信息。從這個意義上講,前述方法測度的外匯風險套保比率偏低,但這並不影響基於可比口徑的動態比較分析。

四、主要結論
雖然隨著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加,“8.11”匯改以來中國境內外匯衍生品交易的活躍度增加,但國內企業運用匯率避險工具的程度依然偏低。這既反映了國內企業匯率風險意識較弱的問題,也反映了因為國內金融市場深度廣度不足,以及金融管理政策原因導致的交易成本偏高,抑製了企業匯率避險的積極性。
“8.11”匯改以來至今,境內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或收盤價三次逼近重要心理關口。第一次是2016年12月~2017年1月,第二次是2018年10~11月,第三次是2019年5月。除了第一次引發了市場恐慌外,後面兩次市場反應均較為平靜。從積極的方面看,這反映了市場對於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適應性增強。但各種指標衡量的遠期用匯套保比例普遍偏低甚至仍處於下降趨勢,顯示如果匯率出現超預期變化,仍有可能導致市場出現過激反應。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三次成功守住重要心理關口,重塑並增強了匯率政策公信力,但也帶來道德風險、隱性匯率擔保的問題。如截止2019年6月底,銀行代客未到期遠期淨購匯額為128億美元,同比回落了734億美元,且遠低於2015年7月底的474億美元(見圖8)。因此,對外匯市場參與者開展持續的匯率風險教育,幫助企業牢固樹立財務中性意識,仍是一項艱巨的工作。這本身也事關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的微觀基礎。
本文原發於《中國貨幣市場》雜誌2019年第8期
(本文作者介紹:武漢大學經濟學博導、董輔礽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