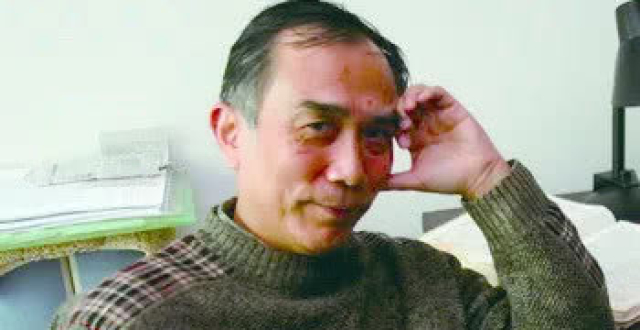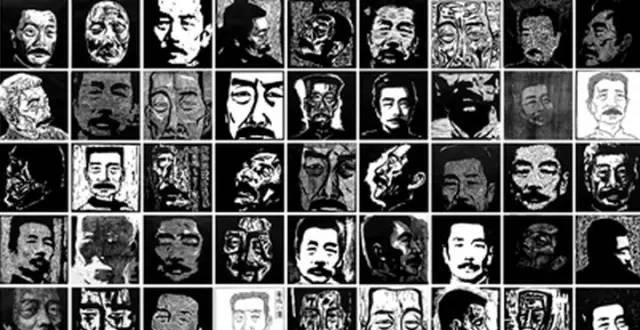近日,第一次來到濟南的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長江學者郜元寶,在山大、山師文學院作了題為《魯迅“遇見”王獨清——放大一個文學史細節》的演講。郜元寶此次濟南行還收獲頗豐,在濟南收藏家徐國衛的“倉庫”裡,見到了他苦尋的王獨清的抒情長詩《11DEC.》。
郜元寶的文學批評是敏銳的,在學界引起巨大影響的《魯迅六講》中,郜元寶發現了魯迅特殊的“心學”,並系統講解了魯迅著作中所見“心”字的含義,解開了魯迅研究一個長久的難題,成為魯迅專家。
郜元寶的學問和研究起於美學,後又經魯迅研究走到更廣闊的批評領域,從現代文學到當代文學,從周氏兄弟、張愛玲、汪曾祺到莫言、賈平凹、張承志、張煒、王安憶等都有深入研究,而諸多文學領域的新現象也是郜元寶的關注對象。

齊魯晚報:您如何看待魯迅的語言?
郜元寶:魯迅的語言很到位。1938年第一次出版的《魯迅全集》由蔡元培作序,他認為魯迅是文學的天才,在於他的“字句之正確”。
魯迅熟悉中國的語言,他能從中國語言的庫存中找到最合適的。當然,魯迅的語言也不是他生造的。魯迅的文學生命力,也在於他對中國語言文化的深入了解。
我們生為中國人,未必像魯迅那樣了解中國的語言文化,但魯迅卻有這樣的能力,用時髦的話說,魯迅的語言天賦有一種碾軋的效果。魯迅的很多話,別人也說過,意思差不多,但就是那一分一毫的差別,卻是致命的。我們只能驚歎魯迅語言的到位、精準。
齊魯晚報:孫鬱教授有一篇文章談你,說“如果不是因為與魯迅相逢,後來的批評不會有如此的鋒芒。”那麽,對魯迅深入的接觸和思考,對你的文學批評有什麽影響?
郜元寶:在魯迅研究以前,我追趕的是批評界時髦的東西。但通過魯迅這麽一個特殊的作家所打開的窗口,我更切實地了解了中國歷史、文化,其中也包括中國的文學。有了魯迅,對中國文學來說,就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坐標。在看待當代文學現象時,就不至於因失去穩定的參照,而變得充滿隨意性。
我們對魯迅的研究,在注意到魯迅文章的絢爛、多彩時,往往容易忽略另一方面,就是他作品的本色、樸實、簡單。五四新文學以來,不少中國作家很容易標榜自己,認為把自己的文章寫得越漂亮、越豐富多彩越好,導致很多假大空的東西堆積起來,文字多於作者的想法,而且混亂。魯迅的文章很絢爛,但幾乎看不到他自我標榜。查遍《魯迅全集》,除了被迫地自我辯護外,他很少從正面說“我是什麽樣的人,我怎麽樣”。這是魯迅最為精髓的一面。
歌德有一種觀點認為,在一個健康的時代,文學藝術家、整個社會的思想是朝外的,朝向這個世界的;當一個時代不健康、衰弱了,就整天在糾結內心,挖掘內心。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界談了太多魯迅的內心糾結。但他除了在《野草》中有一半篇幅寫自己的內心糾結外,絕大部分時間都是正眼看世界的。他既沒有把自己封閉在身邊的瑣事中,也沒有封閉在一己的感情中。魯迅更多的時間是朝著外面的,魯迅的著作談論的都是具體的事情,在處理大家都面對的世界的公共問題。
這是魯迅給作家、批評家們的啟示,不只是給我一個人的啟發。
>>說當代文學超越現代,需要理論而不是態度
齊魯晚報:你的文學批評也涉及賈平凹、余華等當代作家,在研究上,打通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範疇對批評家有多難?需要具備怎樣的研究路徑?
郜元寶: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大學中文系就存在一個問題,現代文學研究與當代文學研究幾乎沒有交流,研究現代的專家不研究當代,研究當代的也不研究現代。但陳思和教授有一種說法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研究是不能中斷的,不能人為隔閡。這句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太難了。
中國100年文學依托的社會背景變化太大,雖然同在20世紀,但真把現當代作家打通,如把魯迅的隨想錄《熱風》與巴金的《隨想錄》結合研究,太難了。儘管如此,在對當代文學進行總體評價時,若沒有100年新文學的視野、眼光,就往往把握得非常不準確。
具體研究中,比如魯迅與王蒙、張愛玲與王安憶的對照研究,需要從更宏觀的角度進行評判時,難題就出現了,不是靠一兩個批評家的具體研究能完成的。有人說王安憶超過了張愛玲,但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作家群體是很複雜的,有些人活得很長,但文學生命很短,而當代作家不僅長壽,創作生命力也很強。雖然純文學內部研究還有很多分歧,但也逼著有些人站出來研究,去打通現當代文學研究,而不是隻發表下態度,說誰超越了誰,需要從理論上來論證。
齊魯晚報:批評家們大多對市場化程度很高的作品不太關注,而您認真地寫了一篇《向堅持“嚴肅文學”的朋友介紹安妮寶貝》,對郭敬明小說也有關注和剖析批評。
郜元寶:我談安妮寶貝時的著眼點是,很多自封為嚴肅文學、純文學的作家,他們的東西不好,不是說他們沒有贏得市場,而是本身就不好。不能因為沒有市場,就拿這個當幌子,認為比有市場的人高,那可不一定。有市場的作家,有的是迎合、庸俗的,但也不能因為有市場就一竿子打翻所有的人。要從市場化作家中,看到其某些積極的因素。而我批評郭敬明,是因為他亂用文字,他用花裡胡哨的東西,來迷惑那些本身文字修養很差或是文字基礎薄弱的中學生,我很看不慣這一點。
“你是研究魯迅的,怎麽突然研究郭敬明、安妮寶貝這些好像不是高大上的,不是純文學的作家?”會有人發出這種疑問。但文學批評家不應該人為給自己設立禁區,不應有分別心。
魯迅說要讀雜書,他對歷史和現實的很多評價,其論據不一定來自經典,反而很多材料來源於上海的小報。魯迅是“人間魯迅”,跟他沒有禁區有關。魯迅小說最大的成功,就是把中國過去的文學中看不起的小孩子、婦女、農民寫活了。他談論作家,不一定要談論大作家,也經常談一些不入流的作家,反而更容易談出問題來;而人家都談梅蘭芳時,他不談,他要談自殺的阮玲玉。在一些學者看來,那些市井小報的消息、謠言,魯迅完全可以不管它,但魯迅為此寫了很多雜文。
齊魯晚報:最近學界對賈平凹的《山本》有諸多批評聲,你則寫了長文《“念頭”無數生與滅——讀〈山本〉》,怎麽看待不同觀點的對撞、爭鳴?
郜元寶:我過去也寫過文章批評莫言、賈平凹,我也不是一貫認為他們的作品都是好的。作為一個批評個體,不用管同行多麽噓他,你看準了,你就肯定他;相反,同行都在肯定一個作家,你看準了他的問題,就站出來說問題,這都是正常的。
當下的批評環境當然有不好的因素,如“紅包批評”、人情關係批評,還有文人相輕的東西在裡面。在當下,批評家確實面對著複雜的當代文學,站在不同角度,看到的風景不一樣,這就一定要小心。也許別人看到的東西,你沒看到,別人沒看到的你也沒看到。接受者和文學對象在兩個不同的空間,都很複雜,都要謹慎。

齊魯壹點客戶端版權稿件,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