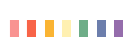我也曾擁有一個夏天,我在他的名姓中燃盡了自己。”
——波爾基亞
從知道阿璞的名字,收到他和朋友4年前合作完成的書,到我落筆寫下這些文字,不過短短10天。而阿璞本人早已在今年6月22日離世。和無數個清晨一樣,那天一早,他還惦記著頭天沒畫完的畫,紙上隻寫了標題:戈德馬克《鄉村婚禮交響曲》,第5樂章:終曲。沒人知道他打算如何完成那幅未盡之作。隻一瞬間,突然發病的他緩緩倒下,永遠揮別了他視之如生命的音樂與繪畫。匆忙翻看著他的書,手止不住地抖,一幅又一幅,被他的畫擊中。轉給美術家朋友,留言說,阿璞的筆下是命運的交響,每一幅都是他靈魂的樣子。
每一幅都是他靈魂的樣子。沒有比這更準確的描述。
想起另外一位智障畫家,作曲家羅忠鎔的兒子羅錚。1992年的一個春日,早飯時間,羅錚問:“爸爸,你的《第二弦樂四重奏》能畫嗎?”羅忠鎔隨口搭音:“當然。”羅錚沒作聲。當天下午,油畫《第二弦樂四重奏》放在了驚呆的父親面前:四個方形構圖,線條、外形並無差異,卻具有極強的理性色彩。羅忠鎔情不自禁地跟朋友說:“一看見這幅畫,我感到太貼切了。確實還是我的基本設想。大的節奏非常規整,其中卻又充滿變化。”那以後很多年,羅錚至少畫了600余幅。不可思議的是,所有的技巧似乎與生俱來,畫風一直在變,但一出手就是神來之筆。表現手法既抽象,又暗合音樂的視覺成像。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鳥》,濃烈的色彩、誇張的線條,只有寥寥數筆。而德彪西的《大海》是波光閃爍的海市蜃樓,深藍色的夜堆疊著樓宇歪斜的倒影。
阿璞的身世完全兩樣,“畫音樂”的路也踉踉蹌蹌。
小學四年級,因為完不成作業被留級,他遭到嚴父的懲戒。到醫院檢查,發現患有輕度精神發育遲緩症。以後的幾十年,阿璞數度住院,從智障到精神病,再到中風,癱瘓,幾乎十年一劫。最後因“脊椎良性海綿狀血管瘤”破裂造成高位截癱,腰部以下全無知覺。只有“傷口”才能以自己的言語訴說,冥冥之中,阿璞撞開了另外一扇生之門。3歲他開始塗塗抹抹,一畫就是七八個小時。大一些的時候,幾次考少年宮未果,幸而被慧眼識珠的老師領進門。他喜歡去動物園,回來就畫小動物,還有農貿市場上看到的雞、鴨、鵝,他養的龜,樸拙的筆觸所到,巴望著他的那些生靈皆是善良的眼神。14歲那年接觸到古典音樂,他發現了更好的表達,從畫動物轉為“畫音樂”。這是一個全新的轉變,幾十年中一共畫了4000多幅,有2700幅為古典音樂而作。
如果說羅錚的畫是靈光乍現,一發而不可收,那麽阿璞“畫音樂”則是自我宣泄與救贖。累積的病痛讓他不斷有一種生命的緊迫感。寫自傳、立遺囑,隨時都準備迎接死神。35歲那年,阿璞把寫好的遺囑給朋友看,開頭的一行寫著:誕生時的音樂,肖斯塔科維奇第八交響曲。朋友問,誕生時的音樂指什麽?答,這首曲子就是我的出生。“生下來我什麽都不吃,在保溫箱裡待了半個月,好無奈。你說這難道不是悲劇嗎?”早期的畫多以黑白為主,理查·施特勞斯的《日出》形式感和裝飾意味很強,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鳥》飛動、絢爛,西貝柳斯第五交響曲有著木刻般的紋理:層漫的凍原和漫天的大雪。這些畫裡少有悲苦。到後來,隨著他不斷聆聽,不斷接納生命給予的沉痛撞擊,作品的衝擊力、生命感和悲劇意識日漸加深。“那些經典的古典音樂是大師們用命寫出來的,而我的畫也是用命畫出來的。”他找到了兩個知音,一個是馬勒,一個是肖斯塔科維奇。巧的是,兩個作曲家也多年與我心有戚戚。
馬勒的音樂對於阿璞來說,乃他人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我跟馬勒一樣,跟那些猶太人一樣,到處都把我們當作傻子和玩物,不把我們當人。”正所謂感同身受。從2012年底動筆,阿璞描繪著他心中的馬勒。畫了大半年,一共112幅。之前我看過國畫家李庚先生的《馬勒組畫》,為第一交響曲而作的那幅,水墨暈染、陰晴明晦之外,可以感受到作曲家從平靜到狂喜的內心世界。而在阿璞筆下,同樣的作品竟然讓他感覺“大地崩裂,火山熔岩爆發,周圍的樹木全都燒焦了”。那種熾熱燒灼著馬勒,那又何嘗不是他自己的寫照。不得不說,這種噴湧、奔放的表達,讓我這個聆聽了馬勒三十年的愛樂者不得不重新認識這個作品。阿璞喜歡馬勒“復活”中弦樂的尖銳和恐怖,這樣的音樂讓他感到充實與解脫。累累白骨之上,是一個醒目的十字架,中間大面積的留白,仿佛是火焰蒸騰在天穹。一、二樂章的葬禮進行曲,黑白線條拉得很長,雲團和十字架的四周是細細密密的墳塋。在呼告與救贖、向死而生的絕境中,阿璞跟隨著馬勒“復活”了,他聽到了偉大的召喚。到畫第四交響曲時,筆下的線條柔和了很多。第二樂章的圖畫有很強的對稱性,彎曲的線條圈著四個骷髏吹著天使的號角,仿佛是飛翔的精靈。從燃燒、解脫到得救,阿璞在馬勒的音樂中走向超越。就像他所說,飛翔得越高,在那些不能飛翔的人的眼中,你就越渺小。
越到後來他越有心得。第九交響曲和《大地之歌》是馬勒的晚期作品,生命的回光返照。但在阿璞的畫幅中不見了早期的躁動和奔突,顫栗與死亡,反而呈現出東方人的淡泊與超然。筆觸變得愈發柔軟,心情雲淡風輕,生死置之度外。
如果說畫馬勒時阿璞還拘泥於個人命運和馬勒之間的應和,那麽到了肖斯塔科維奇,他的視野已經拋棄了小我。在老肖那裡,他聽到了人性的陰險與眾生的錯愕。不是所有的人都作惡,但惡指控所有人。不同於常人的從第五、第七和第十一交響曲入手,阿璞獨獨看中第四、第八、第十三和十四交響曲。眼光非比尋常。寫第四交響曲時,正值作曲家遭逢人生不測的前夜,音樂充滿了緊張和不祥的預感,而高懸之劍一直沒有落下來。寫於二戰期間的第八交響曲彌漫著家國的多重不幸,安魂曲般的慢板樂章深沉、悲憫。第十三交響曲《娘子谷》來自詩人葉甫圖申科的同名敘事長詩。1941年9月和此後的兩年,被納粹坑殺於此的猶太人和戰俘達10萬人。作曲家用原詩譜寫了這首聲樂交響曲。雖說詩風各異,但都直面著死亡:橫死、冤死、戰死、自盡……第四樂章“恐怖”歷數了令人發指的告密:敲門聲之前的恐怖,和外國人談話的恐怖,同妻子談話的恐怖,自言自語的恐怖,凡此種種,讓人想到《古拉格群島》。其他樂章阿璞隻畫一幅,第四樂章則畫了再畫。讓我驚詫的是,以他這個年齡,如何與作曲家生存的特定年代產生共鳴,如何表達作曲家高壓之下的惴惴不安。
阿璞是一個內心極度柔軟的人、敏感的人,也是一個眼光犀利、有同理心的人。在這幾部沉甸甸的作品中,他洞察到其中的核心:愆尤、虐行、殺戮,文明世界的坍塌,生命的脆弱與暴亡。自然少不了妖魔鬼怪、魑魅魍魎的猙獰。畫面如歷史長卷般鋪展開來:飛機投擲,士兵射殺,坦克的推進,大樓的倒塌,無辜百姓的囁喏,大大小小的墓坑,堆疊的白骨橫七豎八,受到驚嚇的幽靈四散而逃。也有很多倉室,像一個個小囚牢,密密麻麻關了很多人。還有很多疊加的畫面組合:冬日的寒冷,熊熊的烈焰,有魔鬼的恐嚇,有人鬼的對話,有扛槍計程車兵,有做手術的醫生,有車馬的前行,也有匍匐的人形。芸芸眾生無不是驚弓之鳥,在靈魂和肉體的擠壓下狼奔豕突,無所逃遁。圖像如風刀割面,讓人痛不欲生。每一筆每一幀都在敘說著殺人,淒厲之聲不絕於耳。無聲的控訴陳述著生命的渺小,以及作畫者對流無辜者的血的怒目圓睜。
相比那些彩色和尺幅很大的作品,我更喜歡那些黑白調子。除了少年宮的習得,尚不知道他畫風的來源。說無師自通太過輕巧,但塗抹中無不有著生命的熱度和殫精竭慮的探索。最終形成了自己木刻般的簡潔風格。有的粗獷、有的細膩、有春風化雨、有抑揚頓挫。有點與塊面的結合,有線條飄逸的盤旋,有版畫的粗糲,也有鋼筆畫的細密,亦有遠古洞穴壁畫的筆法。就是這樣一個病弱之軀,竟然是野心勃勃,生前打算把整個西方音樂史畫完。對於阿璞來說,生存的每時每刻都是磨難,浩如煙海的音樂作品,他硬是一首首地聽,一幅幅地畫。一度曾因為治療精神方面的疾病,藥物造成他思維遲鈍,幾年不能動筆。那種時刻的阿璞,生命處於失血的懸停。狀態稍一恢復,他立刻披掛上陣,援筆而書。最後中風倒下,想來也與他過度勞累有關。某種意義上說,他是“畫”死的,但他甘願如此,也不願吃抑製神經的藥而無所作為。在沒有光明的地方,黑暗也是一盞燈。這盞燈照著他,從黑暗一直走到天明。明明生命的初始就是一場劫難,卻讓他拚拚殺殺,成就了一場無限接近神性的試煉。
阿璞的那幅未盡之作,卡爾·戈德馬克《鄉村婚禮交響曲》我從未聽過。出於好奇,特地找來。一個比馬勒早一代的猶太作曲家,老派的寫作手法。沒寫完的第五樂章是歌舞曲。我把聲音調大,二拍子的舞蹈歡快、喜慶,把熱鬧的鄉村婚禮推向高潮。畫了那麽多淒惻悲慘,阿璞竟然在瀕死的前一天轉向如此這般的歡天喜地。所為何來?忽然想到他2005年的一則日記:“我今年快28歲了,這是青春男女談婚論嫁的年齡。我這個問題(的解決)比健康的正常人更有難度。我把對優秀女性最美好的感覺,轉化成對藝術創作的動力。這是人類的美好境界。”
塵世的最後一瞥,阿璞把美好的祝福留給世界,遂而踏入了天堂之門,義無反顧。正如阿根廷作家安東尼奧·波爾基亞在《聲音集》中所言,我倒下犧牲的時候,我會真心實意地對自己說:好了。
來源 北京晚報
作者 曹利群
流程編輯:王夢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