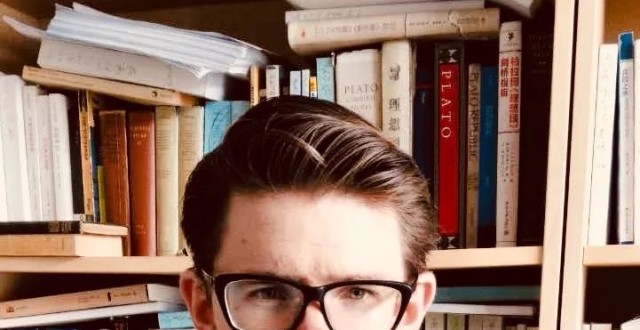雷立柏在中國人民大學 圖 / 本刊記者 梁辰
“人類文明源頭的存在倘不被一再的思考,我們可能只在流行的文化裡思維,失去原本的內動力。而雷立柏做的工作,恰在這個人們陌生的領域”
雷立柏(Leopold Leeb)奧地利人。1995年來中國大陸,北京大學哲學博士,2004年以來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在人大、北師大和後浪出版公司對社會教授拉丁語、古希臘語、古希伯來語,並開設中世紀文學史課程。著有《張衡、科學與宗教》、《古希臘羅馬與基督宗教》以及上述西方古典語言和漢語對照詞典、辭書約50本(少數已寫成、還未出版)。2017年出版散文集《我的靈都》。
Parvulos sinite et eos prohibere nolite(不要禁止孩子)
Ad me venite, Jesus dixit ad discipulos(到我這裡來,耶穌對門徒說……)
兩個月以前,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的學生楊喻琦在B站上看到法國音樂劇《搖滾紅與黑》。節奏強勁的電子音樂一響,舞台上的於連泰然自若地對著將信將疑的貴族們唱起拉丁語的聖經,楊喻琦一下有些麻酥酥的。“那是用一種前所未聞的語言演唱出來的奇特感。”9月一開學,楊喻琦便報名了雷立柏老師的拉丁語課。
9月26日晚上6點,人大三教3406教室。楊喻琦正坐在我的前面三排右側,再往前兩排,便是講台上那位戴著耳麥、頂著微微啤酒肚、手裡拿著白色保溫杯的文學院教授、奧地利人雷立柏:語速中等偏快,和眉毛同時上揚的,還有一股帶著些微異國腔的國語。白熾燈光照射下,隆起的頭頂和光潔的前額越發顯得光亮。他的微笑讓人放鬆,但上課可不輕鬆。
“講完名詞,我們來看看形容詞和分詞的變格。拉丁語很重女輕男是吧,所有重要的概念都是陰性……”

2017年9月26日晚,人大雷立柏的辦公室內,幾名古希臘語愛好者和他一起閱讀、討論《神譜》。左一著白T恤者為Danny 圖 / 本刊記者 鄧鬱
從2004年開始在人大和校外教授拉丁語、古希臘語和古希伯來語以來,雷立柏有數千個小時都在講授這樣的古典語言基礎語法。他把這三門語言戲稱為他的“三個代表”:古希臘語及其背後文化代表哲學、歷史學、文學等輝煌瑰麗的人文科學,拉丁語及其承載的羅馬文化代表法律意識、嚴謹思維和包容的胸懷,希伯來語和猶太傳統則貢獻了一神論以及他們獨特的律法和歷史觀。
在北京居住了22年的雷立柏當自己為世界公民。從搖滾劇裡產生好奇而來的求學者或許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但若能通過古典語言這門工具,從世界的源頭去理解文明的本質,何樂而不為?
上課那天夜裡,雷立柏一如往常穿著自己印製的標誌性黑T恤衫:在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希伯來語、古希臘語和拉丁語的前5個字母之下,最後一排用中文寫著“精神使人活”。
看到雷立柏,會忽然想起明代以來西方學人與國人的互動。他自己就延伸了利瑪竇等人的傳統,也讓我們看到了今天文化進化裡重要的內驅力。他的一些思考,和晚清、民國的學人很像,獨立的精神彌漫在字裡行間。人類文明源頭的存在倘不被一再的思考,我們可能只在流行的文化裡思維,失去原本的內動力。而雷立柏做的工作,恰在這個人們陌生的領域。
——人大文學院長孫鬱
人大的伯利恆
◇◆◇
從3406教室出來,雷立柏行色匆匆,三步並作兩步。
“您去哪兒?”
“接下來有個讀書會,讀古希臘語的《神譜》。你要去嗎?”他邊走邊說。
我跟著他來到斜對面人文學院辦公樓的211室。沒成想發現了一個安寧如伯利恆(據聖經記載為耶穌降生地)的奇妙新世界。一間不到10平米的小屋子。除了書架、書櫃、書桌,別無他物。書架對面桌子上立著一個小尺寸的白板,雷立柏每每講到要解釋處便直接把手抬過去書寫。
坐在雷立柏身邊的熊啾啾,北師大學生,剛剛來三次。張潔,研究生在讀。田老師,幾人當中年紀最大,語言功底也最深厚,和他旁邊的IT人Danny常常就語法問題“舌戰”。
當晚讀書會的文本是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的經典著作《神譜》,厚厚的《古希臘語漢語詞典》是最主要的工具書。然而,古希臘語語法繁複、詞語變化靈活,即便手頭有詞典,看到一個詞很可能也難以獲知原型。

2017年9月26日晚,人大文學院雷立柏的辦公室,四名古希臘語愛好者和他一起閱讀、討論古希臘語的《神譜》。這既非必修也非選修課,純屬一種共同興趣。但閱讀者來之前都要做扎實的功課並在讀書會上發言。古希臘語語法繁複,幾乎每個單詞的原型都需要辨認(有詞典在手也不一定能查到),在句子當中的功能也頗費思量,使得這種閱讀更像是一種曲徑通幽的解析。
做課前預習時,Danny會在列印的紙上畫無數的橫格。“第一行原文,第二行是詞的原型,第三行是語法形式,第四行是句意,第五行是備注。”薄薄不過百頁的《神譜》,閱讀筆記做五六本很正常。“需要看每個詞的詞尾變化推斷出它的語法功能,再想辦法梳理成一個完整的句子。”難怪知乎上的自學者王樂天感慨,整個過程有種做數學題的感覺,在其他語言學習中是很難體驗到的。
獨自做“數學題”也許像黑暗裡的摸索,來讀書會參加小組討論,往往能讓人茅塞頓開。
當天的內容涉及福柏孕育生下赫卡忒,宙斯如何對待。不過二三十行內容,五個人逐字逐句解析、交流花了一個半小時。“主格、屬格、與格、賓格、呼格,直陳式、虛擬式、主動態、被動態……”旁人如聽天書,他們樂此不疲。
為了參加讀書會,在南五環外上班的Danny,每周二下午6點下班後,一共要輾轉29站地鐵,趕到西北三四環間的人大。讀《荷馬史詩》,Danny發揮自己的搜索優勢,下載過牛津校勘本的原文,從Goodreads上發現新的英譯本,然後在Amazon.com上買電子版。
每天去公司13層上班,別人坐電梯,Danny卻要走著上去——無他,可以背經典。他張口便用古希臘語來了一句《伊利亞特》的開篇:
??νιν ?ειδε θε? Πηλη??δεω ?χιλ?ο?(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憤怒!)
他說第一次讀到古希臘語的《荷馬史詩》,自己激動得有點發抖。“雷老師給我們安排讀《伊利亞特》的第二十三卷和第六卷,還有《奧德賽》的第十一卷,我想他是很有深意的。赫克托爾和妻子告別,這樣一個英雄知道他出去必死,還是選擇義無反顧地出城,後面就是他戰死的場景。”Danny有點羞赧地說,自己可能比較敏感,會設身處地地想象書中人的處境。“這樣的作品可以說是用生命寫出來的。如果不投入情感的話,理解不了。”
“讀譯本,不會有同樣的感動嗎?”
“讀翻譯時,總還是隔了一層。”Danny回答。“古希臘語、拉丁語有些詞本身包含的意義很豐富,原作者使用時有雙重甚至多重含義在其中,但不管羅念生還是王煥生,他翻譯的時候只能選擇一個中文詞。這裡頭對於理解和判斷是有損傷的。”
立體的人
◇◆◇
通讀經典,在文學和審美的收獲之外,雷立柏更對詞源津津樂道。“學生可能很早很早之前就知道了這些詞,然後你突然知道它的來源在哪裡,覺得特別有意義。”他開始滔滔不絕地舉例:
伊斯坦布爾附近有一個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很奇怪的名字,但如果你知道希臘語裡,bos是牛,porus是一個渡口、一條路,所以這個單詞本來的意思就是“牛津”,哈,世界上至少是有兩個“牛津”的。比如famous,有名的,還有一個詞fate,命運。這兩個詞有什麽關係呢?fa在拉丁語裡是說話的意思,famous意味著很多人來說你,你就很有名。Fate是神的話,也就是預言,即是人的命運。還有小孩子infant,in是否定的,不說話的那就是小孩,fa和ph有關係,pro是提前,prophet是提前說的話,就是預言家。一個詞根可以記住很多有共同詞源的單詞,所以詞源學是有很大樂趣的。
梁啟超在百餘年前便說過:“先習拉丁然後及其他,則事半功倍,而學益有根底焉。”
16歲的天津高中生焦浩洋是讀書會最年輕的常客,剛剛學習兩年便能啃下一些初級經典。為了來參加周五的閱讀討論,過去一年裡他每每坐著高鐵趕來人大雷立柏的辦公室。但提到外人對這些付出的怎舌,他和Danny一樣不以為然。

辦公室書架上擺著雷立柏這二十多年在北京完成的部分著作。他不打算結婚也不想要孩子,他總是說“書就是我的孩子” 圖 / 本刊記者 鄧鬱
“以前見到英語的單詞,沒有能力分析。學了拉丁語和古希臘語,很多英語詞根是從這兩個語言來的,就有能力去分析歐洲的語言。比如生病時看到很多藥、人體器官,英文詞很拗口。大腦與延髓之間的連接處叫pons(腦橋),學了拉丁語便知道,這個詞本來就是橋的意思。”
採訪前兩天,他也充當了一回老師。當課堂上講到意大利等國嘉年華(carnival)的由來,老師囫圇兩下便過去了,同學也沒人多問。“就像我以前一樣,沒有好奇。”
焦浩洋不幹了,“不能保持沉默,要給大家打開一扇窗戶。”
他上台給同學們講了一下詞根。原來carnival來源於拉丁語,最初的含義就是“告別肉食”。源自耶穌在復活節前40天中的荒野禁食,為了紀念和懺悔,這40天中,人們不能食肉、娛樂,生活肅穆沉悶。演變到後來,在齋期開始前的一周或半周內,人們會專門舉行宴會、舞會、遊行,縱情歡樂。
“看到同學們聽的時候眼神裡放著光,他們是很有興趣的。”焦浩洋感到了播種式的欣喜。
最近一次見雷立柏,是幾周前去北外圖書館聽他關於中世紀教育的講座。那天騎著小黃車到圖書館門口,我下意識地把鎖一拉,將車停在一邊。
“不要停這邊,那邊是停車的地方。”正站在門口等人的雷立柏指指我身後。
我頓生慚愧,依言而行。
要知道,“亂停車”可是課堂上雷立柏最愛講的一個例子。
路過人大附中的大門口,經常有人在人行道上停(汽)車,有的還為自己行動方便而留下一點兒太空,使人行道只剩下半米或更小的太空,行人必須繞過去。為什麽那些司機能夠如此肆意侵犯別人的權利?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問題在哪裡。對於中國人來說,這個問題可能有點兒難理解。它是一個拉丁語單詞,被稱為ius,意思是“合法的權利”。在西方法學上,這個詞非常重要。如果不做關於“合法權利”的反省,北京交通的“霸道行為”永遠無法解決。
雷立柏認為,拉丁語是所有古代語言當中最現代化的語言。在拉丁語裡面有“投票權、競選、共和國、委員會”這樣的單詞。他因此得出結論,現代(中國)社會追求的核心價值觀跟拉丁語的關係比較近,而跟古漢語的關係很遠。
這固然是一家之言,但在研讀過羅馬法和中世紀歷史的大學講師、雷立柏的學生、摯友孫懷亮看來,這並不偏頗。“羅馬人嘗試了我們迄今為止(除總統製外)所有的制度。但我們今天對羅馬法的理解,和日益崛起的經濟地位不相配。如果不了解帝製是終身製,我們就不太理解美國的聯邦黨人防範什麽。也不了解蘇聯長官幹部的終身製內在的制度機理,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羅馬人對此考慮得很精深了。”
追根溯源,會帶出西方古典時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形態與後來的沿革。新星出版社的副總編輯劉麗華跟雷立柏學習三門語言近10年,漸漸學會了“雷式思考和聯想”。
有一個詞virtus,它在拉丁語裡面第一個意思是“力量、能力、才能”,第二個意思是“德行”,意義是重合的。因為在古希臘古羅馬,人們認為精英是力量與德行合一,社會應該交由這樣的人主導。但後來這個詞就慢慢分化,只有“德行”。今天我們不管你身體好不好,有沒有財富,是不是天才,你只要有德行,大家就基本認為你是一個好人,但是在古代不是。古代對人的要求是特別完美的。從這個詞的變化,就可以看得出來政治學的變化,以及人們道德觀念的變化。我覺得這個特別有意思。
帶著古典語言的基礎,劉麗華再看日本戲劇巨匠鈴木忠志導演的《特洛伊女人》和《酒神狄俄尼索斯》,讀俄羅斯作家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的名作《大師與瑪格麗特》,便越來越看出門道。“這本書講的是蘇聯的東西,實際上他講的也是信仰、寬恕、宗教的問題,他也是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相似的魔幻現實主義,但是你再讀一遍就不一樣了。你就知道為什麽那個人腦袋掉了,撒旦怎麽怎麽樣。你的知識立體之後,這個人就豐滿了甚至是完滿了。成為一個立體的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值得追求的境界。”
啄木鳥的催促
◇◆◇
也是在如同劉麗華們的不斷求索和驗證裡,雷立柏立下並實現了兒時的志願。
本名Leopold Leeb的雷立柏生在奧地利的小山村。父親是建築工人,沒上過大學,卻懂得很多中世紀歷史。上世紀70年代末,並不富裕的父親花重金買了厚重的20卷百科全書,每一卷厚達七八百頁。所有人把書攤開擺在地上,一頁頁、一卷卷翻開,成了全家一樁很大的歡喜。“紙張很光滑,色彩鮮豔,有不同的字體,印刷也很清晰,這樣的書很讓人喜歡看。”
三年級放假時,小Leo在筆電上寫了一個10頁左右的故事。上課時老師讓他讀,他因此覺得自己很會寫“故事”,立下長大要寫書的巨集願。後來父母去非洲當志願者,他一度想過要和他們一樣。但在台灣輔仁學習漢語的經歷,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剛剛學半年,他便自己買了《論語》《中庸》,跑到樹底下去背誦。一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過目,他發現每一個字都能明白,“比柏拉圖都容易多了。”成就感滿滿,也對中國的古典哲學產生濃厚興趣。
1996年春,他在北大哲學系師從湯一介。“湯先生對我說他的長期目標,就是讓西方走向中國,讓中國走向西方。這也是我的願望。”

1999年6月雷立柏與博士導師湯一介先生合影
經過中國社科院宗教所卓新平和人大文學院楊慧林兩位師長的舉薦、提攜,他從一個寂寂無名的外國學生、訪問學者,終於拿到了人民大學的古典語言教職。
2005年,他申請開古希伯來語課,頭兩周來聽課的學生只有五個,教務處通知還不夠格開課。“能來的這些學生可是真正要聽課的。”怎麽辦?當時的雷立柏連獨立的辦公室都沒有。只能把學生都叫到人大林園自己的單身宿舍裡,大家就坐在他客廳的桌子和床邊,擺幾張凳子椅子上了兩年。
他常把在人大、北師大和校外講課比作“小學老師的基礎教學”,而無償的讀書會交流,更有點“精英”層面的共鳴。是做大眾普及,還是專注於精英培養,有時他會有點矛盾,在沒有答案之前,還是兩者並舉吧。他這一乾,便是十多年。
學校分給他林園的這套房子,似乎還保留著15年前的模樣,從外到裡沒有任何現代裝飾,他住得很滿足。稍微熟悉雷立柏的人都知道他的嚴格作息:早晨6點起床,喝杯咖啡,做精神體操——用希臘語或希伯來語讀《聖經》;七八點開始工作;中午自己做飯(多半是炒胡蘿卜或者番茄雞蛋),打個盹兒。下午兩點半繼續工作,6點開始上晚課、讀書會。10點必安然入睡。
他說人大校園裡有一隻啄木鳥。儘管很少看到它,但經常聽到它的聲音。“一聽到它‘篤篤篤’的啄木聲,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工作。它提醒我:不要偷懶!”
他不用微信,和學生講課、同行交流之外互動極少。與他見面七八次,採訪問答之外絕不多寒暄。“吃飯、睡覺、看電視這些都浪費時間”——他給自己安排的寫書、編詞典任務已經排到了至少三五年後,乃至漫漫的後半生。
孤獨,自然有。可是他時常以西塞羅、哲羅姆這些先賢為目標。“越身處孤獨,越沉浸於經典和你的工作,也越不孤獨。”
靈都之愛與惜
◇◆◇
不結婚、不生子的雷立柏,在北京一住22年。今年,他出版了自傳體的散文集《我的靈都》,寫盡了一個奧地利人對這座城市的赤誠。
1995年參加漢語水準考試時需要填寫“民族”一項,他在這一項填寫的是“匈奴族”:“從血統來說,我是半個中國人。”
在他眼裡,北京是一個“學城”和“文都”,但“學”和“文”都是為了建立友好關係,為了“輔仁”。他給北京起的新名便是:“橋都”。
每到一個地方,他都要問:這個房子是誰建的,歷史有多長?《論語》裡有一句話“子入太廟,每事問”,他說他和孔夫子一樣:“每事問”。
他曾經從通州騎自行車去盤山爬山,盤山下來就是河北薊縣。看薊縣市中心的獨樂寺,他感慨:好一處遼代老建築!下面一句緊接著——北京市裡這樣的老房子還有幾處?!
“我知道沒有第二個外國人把北京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寄托,我在感情上跟北京有很多關聯,這些關聯是別人可能產生不了或者表達不了的。”這些關聯,來自於對他友好的capital(首都)居民——他說這是這座城市最大的capital(資產)!也來自於那些充滿歷史感的墓園、石刻、碑文,和一個個充滿人道關懷,卻幾乎被我們遺忘的名字。
“我覺得我的一個任務就是幫助中國人回憶、想起來這些人,他們的文化貢獻,作為一個文化的橋梁是抹殺不掉的。”
例如第一個留學海外的中國人鄭瑪諾。旅途的困難、西方世界的分裂、外國語言的多樣性、中國傳教士在華所受的限制、中國教會的需要、疾病的可怕以及當時醫學的落後,都沒有影響到他遠赴重洋傳播經學。雷立柏忍不住問,北京什麽時候會建立一座鄭瑪諾紀念碑或一個早期留學生博物館呢?
好在,他在車公莊和五塔寺耶穌會士墓群尋得了些許安慰。前者讓他見到了利瑪竇等人的安葬之所,也發現了鄭瑪諾的墓碑拓片和照片。後者則收藏有白晉等數十位在雍正、康熙年間傳播過各種自然和人文科學知識的西方人(含華人)墓碑。

位於北京市委黨校內的利瑪竇墓,雷立柏說這裡能讓他感覺到北京是自己的故鄉
法國人白晉曾教過康熙皇帝數學,進行過漢學研究,前後在中國生活了43年。他是最早將拉丁語和漢語做比較和意義聯想的西方人。三百多年後,雷立柏也出版了一本名為《拉丁語橋》的小書。其中舉出了很多這樣的“橋梁”:比如“手”在拉丁語和漢語都有控制、掌握的意思:“你完全在我的手裡。”
他因此將自己喚作白晉的門徒:“我也在現代漢語和西方語言之間不斷尋找著共同點和橋梁,讓更多中國人對西方語言產生興趣,同時讓更多西方人對漢語產生興趣!但願我們的‘搭橋工程’能夠結出豐碩的果實!”
生長的樹
◇◆◇
還在社科院讀中古史的研究生時,孫懷亮便對當時的訪問學者雷立柏提出,“能不能教我們拉丁語?實在找不到人教。”那成了雷立柏教書生涯的開端。也是卓新平、孫懷亮等人建議雷立柏,多做一些中國學者不願或者無力做的工作——例如編撰詞典。
“中國大學教授的考評體系裡,教課、編詞典和職稱沒太大關係。國內學者,如果不是國家項目,個人幾乎沒有編寫辭書的。又費力,又不能帶來直接價值。”孫懷亮指出。
雷立柏卻甘之若飴。他平生最佩服那些能編寫詞典和百科全書的人,“因為他們是知識的傳播者,而不是自己空想或感受的傳播者。一百年前中國很缺乏高級的雙語詞典,而在今天,中國仍舊很缺乏好的詞典。”
他以司徒雷登為榜樣,這位教育學家在古典語言上的成就在他看來被大大忽視。“司徒雷登在20世紀初便編譯了一部《新約希臘語語法教程》和一部《希漢英新約詞典》,在他以後大概沒有人再編過一個三語希臘語詞典。約摸100年後(2015年9月),我自己的小《希漢英詞匯表》在北京出版。天上的雷登叔叔,你會不會因此感到欣慰呢?”雷立柏向自己的偶像、戲稱為“親戚”的司徒雷登發問。
兩年前,他編寫的《拉英漢詞典》終於完成,校對工作至今還未結束。這三種語言都不是雷立柏的母語,所以他參考了吳瑞金、謝大任的拉漢詞典和十多部拉英、拉德詞典。編寫這部200萬字、1000頁上下的中型詞典成為雷立柏這輩子目前最大的翻譯項目。儘管如此,他說這已經是極力壓縮篇幅、減少例句後的結果:只為方便讀者使用和攜帶。

雷立柏在演示“雷體字”,他自創的漢字造字法:左半邊保留漢字的偏旁,右半邊標注拚音與音調,目的是“方便外國人學習漢字”。他的這個建議影響不大,他也不以為意 圖 / 本刊記者 梁辰
如今,清華、北大、北外、人大這些高校,在哲學、古典學等學科之外,法學等學科也開始注意到拉丁語的重要。
“但並不是每學年都有合適的外國老師,常常是待個一年半載便換人。找中國老師?原則上沒有什麽困難。問題在於,教授不願意教。他們認為教語言語法too simple(太小兒科),找個博士便能去教下。老實說我也是。偶爾去教教學生要麽是怕自己忘了,要麽是想再有提升。但這事本身沒有專業含量。你便知道雷立柏內心多強大。”孫懷亮說。
“對語言興趣並不大、職業當中也用不上的人,會說,學這些‘死了’的語言究竟意義何在?”我問孫懷亮。這種爭議,在學界和民間至今都存在著。
“是的。這些古典語言到今天最主要就是閱讀典籍,不再適用於交流。從實用角度,可以說學了有個屁用?”(笑)緊接著,他正色起來,“但在這樣一個全球化時代,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也好,雅典、羅馬、麥加也好,都是我們的精神家園。我們是要回身去學習我們人類以往璀璨的東西。”在孫懷亮看來,這麽多年中國的外語教學,越來越傾向於所謂“快樂法、激情法”,仰視卻沒有了。“這些不是主乾。缺乏對於古典文明的敬畏。而在雷立柏的事業裡,你能看到一種生命的進展感。”
這幾年,雷立柏每周在人大、北師大上課,有時也會為人大附中的學生講課,按每所大學每個學期100人學計算,兩所學校才200人,一年400人,10年4000人。他始終覺得少了一點,“你看學英語的人有那麽多啊。”
2012年,雷立柏萌生過一個想法:創辦一所小型的語言學校,專門教授那三門古典語言。出書尚且不易,更何況辦學校?他因此更敬佩《大公報》和輔仁社(輔仁大學前身)的創辦者英斂之。
沒想到,給他出版辭書的民營出版公司後浪很積極,老闆吳興元說願意提供教室。他從此每周六上午在後浪南鑼鼓巷辦公區域提供的教室上課。“雖然不是我的語言學校,但還是部分實現了我的夢想——最重要的是,有人可以學習古典語言。”他因此覺得,事不易,知音和貴人卻總能遇見,也是福祉。
學習外語是學習平等的一種方法,就是能夠更好,更平等地與世界上的人溝通。
我們喜歡自己的傳統,好,但是更平等對待周圍的人,包括周圍民族,比如菲律賓人、印度人、日本人,有沒有這個情懷?現在的中國人就像一棵樹,中國人的意識是很穩定的,而且在不斷、快速地生長。原來沒有人對非洲,對歐洲中世紀歷史感興趣,現在很多中國人都對這些感興趣。中國人對世界的理解會越來越全面、深入、有感情且客觀的。但是也需要更多的老師、書、旅遊。也需要更多辨別:哪些是真正重要的,被忽略了,是不是應該被忽略。
和雷立柏有過一面之緣的中國近代史寫作者沈迦,在加拿大定居多年。雷立柏譯介過的韓寧鎬,沈迦研究過的蘇慧廉,都身處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初的中國亂世。在沈迦看來,今天的中國雖處在國際地位上升的繁華盛世,卻有著“人心如兵荒馬亂”的現實一面。“整個世界都在世俗化,西方校園裡的學者也很難見到純粹如雷立柏者。90年代初,他在中國經歷的歲月到現在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他自己沒有變。”
(參考資料:《我的靈都》,感謝所有受訪者以及新星出版社的大力幫助。實習記者張宇欣、郭雪岩、付端凌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第535期
原標題《雷立柏 搭橋者、古典學教師與愛上北京的奧地利人》
文 / 本刊記者 鄧鬱 實習記者 劉芮 發自北京
影片 / 鄧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