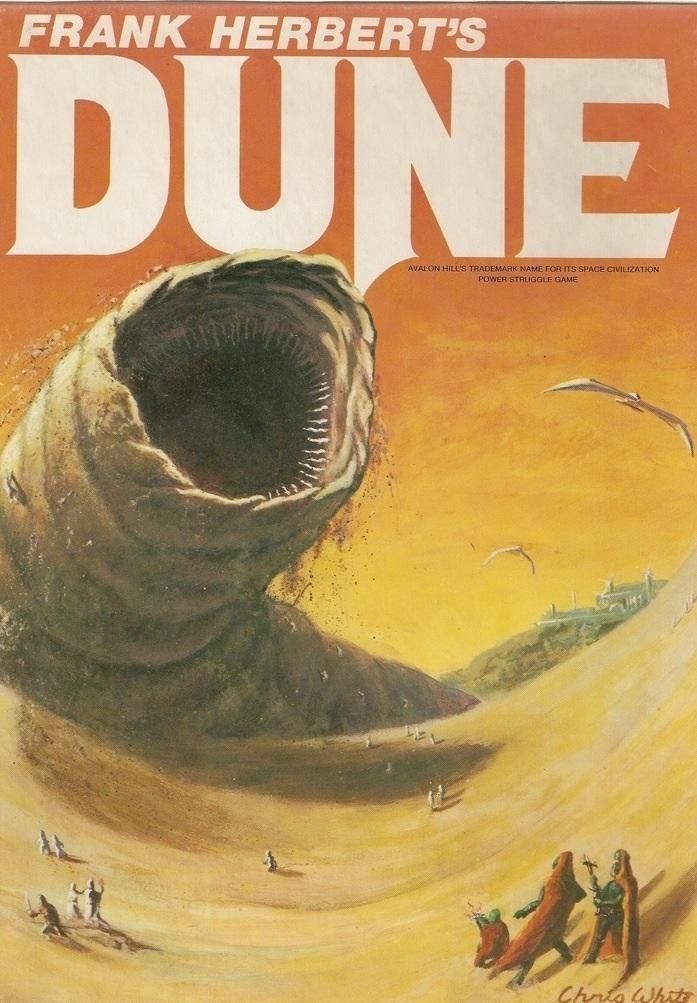“在小說中以豐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詩意的表達方式使美國現實的一個極其重要方面充滿活力。”——1993年托尼·莫裡森諾貝爾頒獎詞
199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尼·莫裡森是在當代美國乃至世界都享有盛譽的非裔女作家,頒獎詞中所表彰的“極其重要的方面”,指的是“種族主義與男權制度下的美國黑人女性與兒童”。托尼·莫裡森一開始就以反抗的姿態闖入文壇,作為黑人女性,她將女性主義和後殖民主義貫穿於自己整個文學創作之中。《最藍的眼睛》是她的處女作,這部發表了二十五年的小說一直沉寂,直到托尼莫裡森獲得諾貝爾獎才“終於贏回尊嚴”。
《最藍的眼睛》是一部禁忌的悲劇。故事發生在1941年美國北方的秋天,布裡德洛夫一家支離破碎,大兒子薩米離家出走,小女兒佩科拉被酗酒的父親喬利強姦懷孕,最終嬰兒早產,喬利死去,佩科拉精神失常,沉浸在擁有一雙藍眼睛的幻夢之中。悲劇的源頭令人無奈——佩科拉的醜陋和對一雙藍眼睛的渴望。

除了敘述者克勞迪亞,幾乎所有黑人都生活雙重審美標準的壓迫之下,其一是以洋娃娃“秀蘭·鄧波兒”為代表的白人審美:白皮膚、藍眼睛、金頭髮、翹鼻子,乾淨、優雅、精致的生活。其二是以莫麗恩·皮爾為代表的有色人種審美:棕色、淺褐色、灰白色的皮膚,得體的打扮,她們不斷通過“向上”走的婚姻使膚色和瞳色變淺,迫切地想要擺脫黑人的所有習性,使自己無限趨近於白人。由膚色劃分出的等級標準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而在一層層的鄙視鏈之下,最底層的“醜陋”是黑人小女孩佩科拉。
“我們所有人——所有認識她的人——借助她滌蕩了自己後感到無比健康。我們在與她的醜陋比鄰時都感到自己無比美麗。……她允許我們這樣做,因此她理應受到我們的鄙視。我們拿她來磨礪自我,用她的懦弱來襯托我們的品格,在自我強大的幻覺中心滿意足。”
《最藍的眼睛》創作於上世紀六十年代興盛的黑人藝術運動(黑人美學運動)與黑人權利運動背景下,莫裡森試圖打破的正是這種被歸為“常識”的審美標準,塑造出身兼雙重歧視的黑人女孩。在白人審美標準之下,黑人女孩佩科拉把老師和同學的排擠、父母的爭吵和傷害、貧窮的生活全部歸因於自己的“醜陋”,而萌生出“想要擁有一雙藍眼睛”的想法。因為“藍眼睛”是一種資格,它意味著被人肯定的美,意味著被人接受和愛的美。
“她經常對著鏡子,一坐就是好幾個鐘頭,試圖揭開醜陋的秘密——醜陋得讓學校的老師和同學都不理睬她、看不起她。……她就這樣陷在緊緊束縛著她的信念中,只有奇跡才能讓她解脫,如此她將永遠都看不到自己的美。她只能看到自己能看到的東西:別人的眼睛。”
《最藍的眼睛》


種族性自我歧視的毒氣侵蝕著所有黑人,尤其是佩科拉的母親布裡德洛夫太太。她厭惡自己的生活和家庭,只有白天在窗明幾淨的大房子裡為白人家庭工作時候,她才覺得自己活著,她對女兒佩科拉的醜陋感到憤怒,把主人家的孩子當作寶貝,她感激白人家庭賜予了她綽號,感激大房子裡的地毯不再讓跛腳發出聲響。當她作為“布裡德洛夫太”的時候她抬不起頭來,而當她成為“理想仆人”的時候卻趾高氣揚,她既卑微又高傲。
伴隨十九世紀“白人至上主義”和“西方中心論”,黑人群體一直處於“失語”狀態,白人文化的強勢剝奪了黑人的話語權利,在“藍眼睛”審美標準滲透到學校、家庭、文化、流言、衣著之中時,黑人群體的自我否定也在蔓延,繼而加入到否定其他黑人的白人權利機制中。卷曲的頭髮、黑皮膚、曾經為奴方身份、種族的激情、自我意識,都被黑人群體一樣樣拋棄,剩下的只有自卑感和滲透在“他者”中的一具肉體。


但是,用“藍眼睛”代替“黑眼睛”後,黑人得到救贖了嗎?看看書中的其他有色人種。傑拉爾丁和她的兒子朱尼爾小心翼翼地、努力地學著擺脫本性,“有色人種與黑人之間的界限並不總是特別分明。個別細微卻可能透露真相的標誌會威脅著抹去這種界限,因此必須始終保持警覺。”混血姑娘莫麗恩通過譏諷克勞迪亞與弗裡達姐妹倆來獲得肯定:“我就是漂亮!你們就是難看!又黑又醜。我就是漂亮!”。
然而正如黑人的醜陋不是自己的,莫麗恩的漂亮也不是自己的,“我們可以毀壞娃娃,可我們無法摧毀遇到這世上的莫麗恩·皮爾們時父母與阿姨甜美的嗓音、同伴順從的眼神、老師熠熠生輝的目光。秘密到底在哪兒呢?我們究竟缺少什麽?為什麽那一點如此重要?如果缺少了它又將如何?我們當時天真爛漫,毫不虛榮,仍然喜愛我們自己的模樣。……真正讓我們感到害怕的,是那些讓她而不是我們顯得美麗的東西。”
“目光”,佩科拉一直生活在別人的目光裡,在整個故事中,她是沉默的。被黑人男孩圍攻的時候她是沉默的,被母親打倒在地的時候她是沉默的,被傑拉爾丁叱責為“小黑婊子”的時候她是沉默的,甚至被親生父親強姦的時候也是沉默的。在拚接式的非線性敘述模式裡,多種聲音和多重角度相互交織,怨恨的、惡毒的、隨意猜測的、軟弱無力的聲音,都在莫裡森詩歌般絢爛的敘述技巧中流淌,但佩科拉只剩下沉默和自言自語。“她從來沒有看到過自己,直到她幻想出一個自己。”她不知道自己的美,她不認為自己值得被愛。面對白人嫌惡而虛無的目光,面對有色人種的嘲弄,面對黑人社群對“藍眼睛”審美的歸順,佩科拉只能蜷縮和躲避。

克裡·詹姆士·馬歇爾的非裔身份強烈得影響了他的創作,他的作品大多聚焦於美籍非洲裔人的社會存在和身份認同。
“醜陋”只存在在他者的目光之中,應該打破的不是黑皮膚,而是既定審美標準下的目光,莫裡森道出了醜陋的真諦:
“你看著他們,心裡好奇他們為何如此醜陋;你仔細觀察,卻找不出根源。然後你意識到這醜陋來自信念,他們的信念。感覺就像有個無所不知的神秘主人給了他們每人一件醜陋的外衣,讓他們穿上,而他們毫不質疑地接受了。主人說:‘你們是醜陋的人。’他們打量自己,找不出任何證據來反駁這個判決;事實上,迎面而來的所有廣告牌、電影以及目光都提供了支持這一判決的證據。……他們把醜陋接過來,像一件鬥篷一樣披在身上,穿著它在世上招搖。”
莫裡森在後記中說到:“對種族美的維護不是為了回應在各類群體中頗為常見的對文化或種族缺點充滿自嘲和幽默意味的批判,而是為了防止那種由外部注視引發的永恆不變的自卑感發生有害的內化。”她通過《最藍的眼睛》點明了黑人審美的獨立不是簡單的黑白置換,不是對一雙“藍眼睛”的病態渴望。她超越了六十年代黑人美學運動中提出的‘以黑人為美’的口號,看到了它背後與白人審美標準的相同邏輯。
莫裡森以福柯權利話語理論為引導,在小說中展現出:“美醜”並不是一種絕對的標準,而是規訓權力運作的產物。“審美標準不過是規訓權力控制個體的一種手段。所謂審美標準本身就是一種壓迫機制,它通過鼓吹外貌的重要性來貶低不合乎標準的個體。建立新的標準只是對‘以外貌決定論’這種邏輯的翻版。”


早在兩千年前,柏拉圖就在《大希比阿斯篇》中說過:“美是難的。”無數美學家為美折腰,苦苦思索著“美是什麽?”在對外貌追捧至極,乃至發出“顏值即正義”口號的當今世界,莫裡森《最藍的眼睛》或許能為那些因外貌惶恐不安、審美模式化、不懂得欣賞美、不知何為美的人一些啟迪。
“多年來我始終認為姐姐的話是對的:是我的過錯,我把種子埋得太深。我們倆誰都沒有意識到可能是土壤本身太貧瘠。”
在四季輪回的世界裡,在貧瘠的土地上,金盞花拒絕發芽。在種族性自我歧視之下,在主流文化的排斥之下,在他者的注視之下,《最藍的眼睛》中那些被目光壓碎的黑人、女性、兒童身邊,即使沒有陽光,影子仍無所不在。
自黑人解放運動開始,經過哈萊姆文藝複興,美國黑人文學傳統一直延綿不絕,從讓哈珀·李一書成名的《殺死一隻知更鳥》,到最近甚囂塵上的電影《綠皮書》,這是一份為全人類關注的命題。


詹姆士·鮑德溫的《向蒼天呼籲》,賴特的《土生子》和埃利森的《看不見的人》被並列為20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黑人文學的典範。鮑德溫的作品聚焦父子關係,在種族主義和黑人解放問題上極具開拓意義。賴特的《土生子》則用冷酷血腥的筆調,表現出黑人青年對白人社會的恐懼和仇恨。《看不見的人》從書名開始就展現出黑人被漠視和忽略的深深無奈,歷史的缺失,身份、地位、藝術、名聲這些都是黑人不配擁有的,埃利森想要找尋的正是一份空白多年的社會認同感。
西方評論界普遍認為托尼·莫裡森繼承了五十年代的黑人文學傳統,為了種族問題奮鬥,為黑人作家發聲,她不僅熟悉黑人民間傳說、希臘神話和基督教《聖經》,而且也受益於西方古典文學的熏陶。在攻讀碩士期間,她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伍爾夫和福克納,伍爾夫啟迪了她的女性主義思想,比起前者,不論是從寫作內容還是寫作形式,抑或現代主義技巧,福克納都對莫裡森的小說創作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結構布局的高度自由,敘述順序的前後組合,情節上刻意營造出支離破碎,時空的跳躍和人物意識流動,用細膩的隱喻展現神秘灰暗感,對自然界意象的格外親近……

福克納以白人的視角構建起恢弘卻暗淡的南方世界,其一系列“約克納帕塔法”小說奠定了他 “南方文學代表”之基。福克納的《八月之光》比《最藍的眼睛》更殘酷,僅僅因為傳言的黑人血統,白皮膚的青年就必須背負種族主義沉重的枷鎖,與社會隔離。
福克納是回望過去的作家,作品中更多的是昔日榮耀不可挽回的哀歎。莫裡森則是看向未來,她著力於黑人自我意識和身份的重建,自覺追尋黑人文化;福克納以白人眼光觀照莊園、黑奴、解放運動,莫裡森則以黑人女性身份探索隱秘心理,揭示雙重弱勢的黑人女性心中潛藏的自卑感。
福克納的悲憫為莫裡森所繼承,但莫裡森不願止步於此,她衝出了福克納小說晦澀的迷霧,為世界文學打開了一扇黑人女性奧秘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