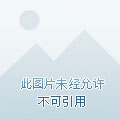今年是知名建築學家童寯誕辰120周年,作為20世紀的同代人,他見證了現代性如何以建造的形式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童寯是第一批赴美學習的建築師,歸國後,在三十年代加入上海華蓋建築事務所,以建築實踐來參與中國城市的現代化進程。四五十年代,他著手西方現代建築的系統性研究。與此同時,面對傳統園林的式微,童寯遍訪江南名園,以畢生精力完成細致而凝練的記錄和理論分析。
“澎湃新聞·藝術評論”近日專訪了童寯之孫、東南大學建築學院教授童明,在他看來,童寯對於今天的意義不只存在於建築學界的專業領域,在今天,他和當時一批擁有自由獨立人格的學人,就像一面鏡子,讓人反思未來的方向。
童寯(1900-1983),中國當代傑出的建築學家、建築師、建築教育家。他曾設計過南京原國民政府外交部大樓、上海大戲院等100多處建築,所著的《江南園林志》是研究中國傳統園林藝術的經典著作。1930年代,自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留學歸國後的童寯任教於東北大學、中央大學建築系,與楊廷寶、陸謙受、李惠伯並稱為中國建築師中的“四大名旦”。

童寯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照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澎湃新聞:很多人對於童寯先生的了解是基於建築,但是他從早年開始,就在繪畫、包括中國畫與西方油畫、水彩畫上都頗有造詣。他對於繪畫的興趣是如何形成的?繪畫與他的建築實踐有怎樣的關係?
童明:童寯從小開始學習繪畫,他的繪畫造詣是非常高的,他不僅具備一般建築師繪畫的那種精準刻畫,也有像畫家那樣寫意的狀態。建築的繪畫實際上更多是偏工程性,強調準確性,比如說透視、比例、尺度關係等。在這方面他是毫無問題,因為他完全是科班出來的,但是,他又不像那種工程化的畫法的“匠氣”和呆板。他是在這麽一種很嚴謹的狀態裡面,又加入了很多精神性的因素。所以你看他當時在歐洲旅行的時候畫了大量的創作,實際上都是非常傳神的,對於歐洲的中世紀古城,以及剛剛興起的現代建築,他的那種靈魂刻畫都入木三分。
所以繪畫是童寯的一個天賦。他學習繪畫的時間加起來並不是特別長,但是他可以非常快地掌握,這些都是他個人的素養和天賦。作為一名建築師,這種素養和天賦是應該要具備的,建築師本身就是半個藝術家;另一方面,我覺得這種繪畫造詣和他的精神世界是相關的,他整個人的精神領域,實際上更多偏向於人文主義色彩。

童寯繪畫作品,威尼斯聖馬可廣場

童寯水彩畫,拙政園香洲
澎湃新聞:童寯在清華讀書時學習的是多學科的綜合性知識,當時國內還沒有成立專門的建築系。這種學習體系給他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童明:童寯是一個非常自明而慎獨的人,他在精神上的自由可能與他早年接受的教育有關聯。他接觸了古代中國的哲學思想,並師傳於王國維,後者更多是吸收了從叔本華等來自德國的哲學家思想,所以我認為童寯的思想之根實際上是滲透著這種非常扎實的對於世界的觀念和理解,在這樣的哲學基礎之上,他很早就形成了這麽一種體系和脈絡。這麽一種精神力量可以延伸為陳寅恪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也是對於當時清華在精神上的傳承性的描述。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文化氛圍與精神狀態之下,會給他帶來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完全是專業知識層面,更多的是一個人的精神內涵。童寯的一生都可以用這種自由獨立的精神來描述,他的身上一直散發著多重光彩的人格魅力,可以說他首先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人,其次才是一個建築師。
澎湃新聞:童寯在上世紀30年代加入上海華蓋建築事務所,他對於上海的建築做了哪些貢獻?
童明:實際上個人很難對於一個城市帶來巨大的影響,因為一個城市實在太大了。但是我覺得他們那一批人,包括他本人,的確對於這座城市的現代化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成立於1931年的華蓋建築事務所不是最早的華人建築公司,但是他們最具明確的目標和意識。20世紀30年代的這批華人建築師帶動了上海現代建築的第二波轉型發展。關於這波轉型的內容曾出現在2018年我們在PSA策劃的展覽“覺醒的現代性——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中國第一代建築師”中,這個展覽的命題在我看來有很深的含義,它不是簡單的“文化殖民”,而是種子的發育,這種“種子”的成長基於上海融合性的背景。第一波轉型和發展基本上可以追溯到1843年上海開埠至20世紀20年代左右,這個時期可以稱為“古典時代”或者“複古時代”,更多的是對西方建築的移植,因此你在那個時代所看到的大量建築、特別是沿著外灘一線的這些建築,都是西方古典主義的。這些建築本質上基於外國資本,由設計洋行的建築師所作。20世紀30年代是一個分野,上海的建築設計迎來了第二階段。我覺得這源於兩大因素,其一是現代建築在世界範圍的興起,現代工業化催生的新技術、新材料和新方法引發了建築革命,古典主義已經被“淘汰”了,這是一個大背景。其二,像童寯這批留學國外的本土建築師開始歸國,在中國民族資本的推動下,他們加入了這種城市發展與建設中。於是,我們看到外灘的第二界面後有大量建築並非由外商所作,反映的不是帝國主義的殖民烙印,更多的是一種內在的、自發的、滲透著現代精神的發展。

1928年, 童寯獲全美大學生設計競賽一等獎作品,新教教堂

1932年大上海大戲院設計圖紙
所以,童寯當時主導設計的一些建築,像大上海大戲院、金城大戲院(今黃浦劇場),還有很多辦公樓住宅樓,和古典主義的建築是不一樣的,它融合了現代主義的發展潮流,然後把它引入到中國的這種經濟文化中間,促成了上海的一種現代性的轉型,並引領了中國的城市發展,對全國產生影響。因此,如果要說童寯對上海做出了哪些貢獻,我覺得這就是其中之一。迄今為止,當代的很多建築師也很難像他們這批人一樣做出兼具精神高度和高品質的建築。
澎湃新聞: 上世紀50年代,童寯就停止了建築實踐,專注於建築教學,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轉變?
童明:50年代,中國有很多的變革,包括公私合營等,對於童寯來說,他所習慣的那種工作體系、那種建築事務所的工作方式就不成立了。當時主導的是部門體制比較僵硬的操作流程,沒有利於建築師創作的社會土壤。1947年,童寯舉家搬到了南京,之後就專注於建築教學與寫作。
與園林的精神同化
澎湃新聞:童寯的著作《江南園林志》《東南園墅》等都是對於中國園林的研究,在當時忙於現代建設的中國,為何會執著於對傳統園林的研究?
童明:我認為這也是同他的獨立精神有關,正是這種獨立人格促使他在當時的語境下做一些比較有開拓性的事情。他對於園林的研究始於他剛到上海的時候。“九一八”事變後,童寯舉家遷到上海,在進行繁忙的建築實踐工作同時,他被從來沒有見識過的江南園林所吸引了。園林和他自己在根源上的同質性一下子把他“抓住”了。園林承載的文化氛圍和他自己身上的那種精神力量有著一種天然的契合關係,我想這是他著手園林研究的一大原因。
園林在中國江浙一帶如此普遍,但是幾乎沒有人把它當做一個凝聚中國傳統精神文化的載體,而童寯實際上開創了這種意義上的研究。江南園林可以說是中國建築領域裡最具特色的一種類型。其他建築討論的都是梁柱體系,或者從台基、主體結構到屋頂的這種構造系統,這是一個普遍性的話語,不僅中國建築可以這樣來區分,西方建築同樣可以。世界各地的房子基本上都是按照功能和需要來進行塑造。但是園林是獨特的,你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找不到類似的對應物,它的這種根源上的發展是與世世代代的以社會來歸納的精神世界是息息相關的。所以如果從這個含義上來講的話,園林應該是中國建築最為典型和最為獨特的一種化身,它所呈現的是一種生活世界。童寯幾乎把大半生的經歷都投入到園林的研究中,我們透過他的視域,可以打開一扇很不一樣的門,對於我們的精神家園、我們的本土性發起新的討論。

童寯繪製的園林草圖《東南園墅》

童寯繪製的園林草圖
澎湃新聞:童寯在寫《東南園墅》《江南園林志》這些著作的時候,對於園林是抱著一種怎樣的心情?
童明:他抱的是一種搶救的態度。他在《江南園林志》開篇就這樣寫道:吾國舊式園林,有減無增。著者每入名園,低回欷歔,忘饑永日,不勝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吾人當其衰末之期,惟有愛護一草一椽,庶勿使為時代狂瀾,一朝盡卷以去也。在他眼裡,園林就像是一個遲暮的美人,一顆失去光澤的珍珠,在30年代的時候,園林以及孕育它的這種土壤已經在消退了,正在被一種不一樣的生活方式所取代。所以童寯是抱著搶救和擔憂在研究園林。當時,中國尚有大量的園林存在,在園林的這種荒棄和倒塌的過程中,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去做這樣的事情。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動機,我想這可能是他開始研究園林的初始目的。隨後,我認為更重要的是,他被園林所“同化”了,因為精神世界太相近了,或者說,他本人的精神世界深深受到園林這種對象的影響。
除此之外,他還想要在廢墟般的園林狀態中間去發掘更多寶貴的內涵,所以他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比較遺憾的是,他沒有太多的機會和條件去把它發揚出來,因為到了50年代之後,園林建築實踐的這塊內容就已經戛然而止了。與他同時代有一位日本園林家重森三玲,同樣對園林做了大量研究和梳理,但是他比童寯幸運,他有自己的實踐,他在京都做的東福寺方丈庭院就是一種現代和傳統相融合的園林設計,類似重森三玲這樣的人還有很多,在那個時代和圖景上,他們起到了橋梁的作用,把古典世界和當代生活銜接起來。所以,在日本,你可以看到古典園林到現代園林的發展,但是在我們這裡基本上已經成為一種文物古跡了。這對於童寯本人、對於中國城市的現代化轉型都是一個遺憾,這可能也是我們當下要努力的一個方向,就是既要讓時代持續發展,又不能隨意地喪失這種本源性的力量。

《江南園林志》
澎湃新聞:園林在今天會被複興嗎,還是說它應該以已有的形式被盡可能地保存起來?又或者園林的某種“精神”能夠以現代建築的語言表達出來?
童明:我覺得很難。當整座城市都有一種園林的基本單元、由一個個具有獨立思想的家庭和社會單元構成時,園林才會成立。今天我們的城市更多的是被機制化、或者機器化了,每個人生活得就像一個機器零組件一樣,基本上沒有獨立的世界。各方面的條件都很難去支撐園林這樣一種設想。
我們今天在學校裡仍然有園林專業的學生,也有園林局,但是今天所討論的園林和童寯在《東南園墅》裡討論的園林已經不是一回事。園林變成了居住區裡的綠化,整個價值評判標準都不一樣了。園林的要點在於人。今天還存在像沈周、文震亨這樣的人嗎?外在的世界實際上是附著於人的,這些性格和精神世界沒有之後,外在世界只是一個軀殼而已。
澎湃新聞:前面說到了童寯與傳統中國園林在精神上的契合,也說到了他對於中國建築現代化的貢獻,怎麽理解這兩者在他身上的統一?
童明:從狹義來說,現代化的進程是伴隨著17、18世界工業與產業革命而來的市民社會的變革,但是從更加廣義的角度來講,現代性實際上早在文藝複興時期就已經開端了,它更多的表現為一種人文主義,人的精神性的自我覺醒。之後,人脫離理宗教束縛,進入了自我獨立的啟蒙(Enlightenment)時代,當人的精神世界被打入了一束光之後,就會機甲狂潮出無數的創造力,所以,後來的工業革命、包括現代化進程都是這種創造力所帶來的。
從15、16世紀以來,精神之自由、思想之獨立是人類總體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變革。童寯身處這種變革的語境中,當然也受益於他早期的教育以及他本人的性格和智慧。這些影響了他的建築創作,園林理論以及更為廣泛的理論寫作。
今天的一面“鏡子”

童寯夫婦攜子童詩白在園林中

童寯代表作之一,南京首都飯店,華蓋建築師事務所 圖片來源:《中國建築》第三卷第三期 1935
澎湃新聞:據說童寯曾說過“建築就那麽一點事”,怎麽理解他對於建築的這種看法?
童明:這句話大概是他五十年代在南京工學院建築系教書的時候,在一個研討會上說過的話。它針對的是當時的時代背景:對於學科的體制性梳理和介入在當時是比較重要的,但是童寯自己有不同的理解。我認為他說的並不是建築不重要,而是建築不是“上綱上線”的一件事,而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間,是生活的一部分。對於這樣一種社區性的事務,沒必要在精神層面把它看得這麽“嚴重”。如果你不把建築當作一個宏大的目標、歷史的使命,而是為了生活的情趣,那建築相對就會變得比較輕鬆了。
今天我們看到城市建築的很多奇怪現象,往往是因為發力過猛,又或者一座城市到處都是呆板的方塊樓,沒有色彩。建築在本質上屬於生活領域,更多地強調人的精神愉悅性,城市實際上由多樣性和複雜性所構成。
澎湃新聞:童寯還說過“情趣”之餘園林的重要性要遠甚於“技巧和方法”,怎麽理解他所說的“情趣”?如何通過童寯的這些觀點來反思今天中國的建築?
童明:從童寯的觀點看來,實際上我們今天有很多的研究或者做法都走偏了,並沒有觸及到很本質、很靈魂性的地方,而只是停留在一種外表。
可以想見,100年前像蘇州這樣的地方就是一座園林城市,家家戶戶除了自己的居住空間之外,周圍還有一片非常美妙的自然,每個家園都像一個自然的生命體。但是在今天,我們的生活更像是“機器的寄生蟲”,每天都被各種各樣的事物或者機制所捆綁,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相應地,這種問題也折射在今天大量的城市發展和建設中。當這麽多樓房住宅建完了之後,它只是一堆混凝土構建,實際上我們的生活質量、我們的精神世界並沒有得到很明顯的提升。
這就涉及到童寯所說的情趣遠勝於技巧和方法,後者實際上是一個外果,而非內因,內因更多地應該是一種精神性的力量。我們今天過度地重視了技術、方法和工具,在這些方面精益求精,又在數量上加緊加快,但實際上你的目的性並不是特別明確——也就是說我們到底要為世界或者為人營造一個什麽樣的生活,這個目標並不明確。與之相反,情趣的概念是回歸人本。海德格爾引用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話,指出人應該“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而人存在於世界,實際上是要通過建造這種行為來實現的,否則你就是流浪在大地上,像一個原始人一樣。江南園林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反映了精神世界在生活領域的凝聚。在整個世界的這種發展史上面,它都是獨樹一幟的。童寯非常精準地抓住了這一點,所以他的園林研究方法跟現在絕大多數的這些園林研究不一樣。大家還是普遍把它當成技法工具,當成普通的住宅或建設項目來看待,而不是把它當做是一個精神世界的塑造。由此來進行反思的話,其實警示我們今天的人應該要能返回到世界的本源之中,去審視我們的所作所為。

童寯,1930年於德國法蘭克福
澎湃新聞:除了園林,童寯對於西方現代建築也有系統性的研究,怎麽看待他在這一方面的貢獻?
童明:除了園林,他還有一大重要的貢獻就是在於現代建築的研究。早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他就向中國的專業領域引入了西方現代建築的體系。從園林和現代建築兩種看似不相關的研究視角裡,體現了他想要把不同的文化根源進行融合的意圖。我就覺得從另一種角度理解,就是思考如何讓中國融入世界,融入當下,如何讓傳統的元素在現實的領域中煥發出新的生命特徵,這可能也是他那個時代的人總體上的理想和抱負。當然,這樣的理想放到今天來看,也絲毫不過時。

童寯晚年在清華
澎湃新聞:今年是童寯先生誕辰120周年,作為現代意義上中國的第一代建築師,談論他在今天有怎樣的意義?
童明:我覺得意義就在於他是多重線索的一個聚焦點。童寯兼具非常扎實的西方教育背景和理論技法,以及非常本源和地道的中國精神世界的內涵。一方面他個人的技能技巧非常高超,你能從他的建築作品和繪畫作品中看到,他在文字上也有很高的造詣。《江南園林志》是用文言文寫的,非常優美和優秀。他自小的教育系統是比較西化的,可以想見,為了進入園林研究,他可以在兩三年的時間裡就精通一門語言。同時他的英文的造詣也是極高的,他20多歲寫的日記就體現出母語性。
童寯是一個極具天分的一個人,但是他思想或者精神世界實際上並沒有什麽複雜之處,只是一種本能性的發揮。他既有高層次的內涵力量,又不妨礙他成為一個具體的、有著工匠精神的人。另一方面,他是一個極其開放的人,否則也不可能成為一個交匯點。他不拘泥於建築專業,而是以更加宏大的視角來著眼視界。
在今天,恰恰是對於這麽一種具體的人格的關注正在淡忘和消失。所有的人都像是嫁接到一個龐大的機器系統裡面,茫茫而不知道目標和目的,很多人都被功名所“綁架”,無法實現自我精神的釋放,精神世界的力量蕩然無存。所以我覺得童寯對於今天是一面鏡子,讓我們去反思,我們的這艘船要往什麽方向去繼續行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