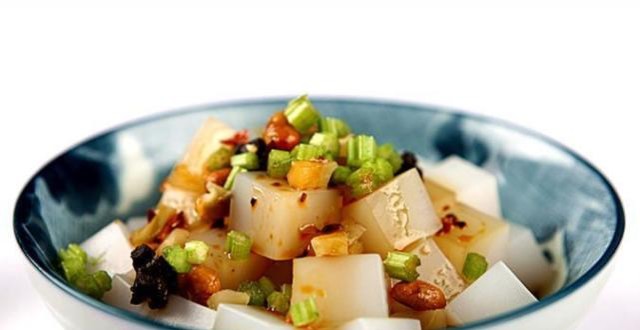論詩的平淡美:濃妝淡抹總相宜
作者:劉勇
人問:詩,是平淡點的美,還是華麗點的美?
我說都美。你有旅遊之雅興否?你注意過大山的自然美麽?
古人說:“山有四時之色:春山冶豔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洗,冬山慘淡而如睡。”(郭熙《林泉高致》)
春山鳥語花香,妖豔嫵媚;夏山蔥蔥鬱鬱,蒼蒼翠翠。——可歸於華麗。
秋山氣韻幽幽,空靈明淨;冬山曠達邈然,沉靜健穩。——可歸於平淡。
然,或華麗之於山,或平淡之於山,均不失其美。山之美,是謂“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王充)
看來,蘇東坡還是比較唯物主義的。他來到杭州,發現了西湖的美,雲:
欲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
西湖的美是瞬息萬變,千姿百態的。詩人似乎奈何不了它了,於是請出了西施,即以西施比譬西湖。
西施究竟有多美?無從考證,也毋需考證。蘇軾說她,平淡的裝束也美,濃麗的粉黛也美。這算是把西施的美寫絕了,把西湖的美也寫絕了。
從藝術美學上看,平淡與華麗屬一對矛盾範疇。它形似矛盾,實則各有千秋。
魯迅喜歡簡練樸實,主張“少雕琢,去粉飾”,但他也說,“其實暢達也有暢達的好處,正不必故意減縮。”
還有李白。李白有雄放奇麗的《蜀道難》,也有平樸質實的《贈汪倫》。
還有杜甫。杜甫有色彩瑰麗的“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也有文采平實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這裡先談詩的平淡美。
平淡,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謂之“衝淡”。
這是一株脫盡浮豔的花,它不裝腔作勢,不弄姿色,不爭奇鬥豔,而每以其天然資質之色,和素樸純淨之美,為人稱是。
蘇東坡說:“漸老漸熟,乃早平淡。”(《竹坡詩話》)
王夫之說:“平淡之於詩,自為一體。”(《古詩評選》卷四)
姚鼎說:“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淡。”(《與王鐵夫書》)
元代詩人房皞論詩絕句雲:“吐語操辭不用奇,風行水上繭做絲。眼前景物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辭。”這首詩論本身就頗具平淡美。
等等,都道平淡的好。
這是因為,平淡,不是單調平庸,不是浮泛淺顯。相反的,而是詩人的藝術修養和思想修養同時成熟後,才能具有的一種氣斂神藏、內蘊外樸的藝術特色。 這是因為,這“平”,是平中有奇的;這“淡”,是淡中見濃的。這是一種爐火純青的美,返璞歸真的美。
對了,這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蘇東坡)。
對了,這平淡,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
原來這平淡之中還有許多不平淡呢,個中消息,前人亦早有窺探。
南宋葛立方《韻語陽秋》雲:“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絢麗中來,落其華芳,然後可早平淡之境。”
清人袁枚《隨園詩話》雲:“詩宜樸不宜巧,然必須大巧之樸;詩宜淡不宜濃,然必須濃後之淡。” 清人薛雪《一瓢詩話》雲:“古人作詩,到平淡處,今人吟繹不盡,是陶熔氣質,消盡渣滓,純是清真蘊藉,造峰極頂事也。”
駱賓王有一首《詠鵝》詩:
鵝,鵝,鵝 曲項向天歌。
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這首小詩,可以說是一首兒歌,平淡極了。然而它有味,耐品。
全詩四句,均系眼前物的實攝。首句摹聲,將鵝的叫聲錄於紙上;次句繪形,把鵝引頸高歌的姿勢勾勒逼真;三四句著色彩,傳動態:羽毛潔白,鵝掌鮮紅,浮在水中,悠悠撥劃,緩緩遊弋——鵝之怡然自得的呆憨情態,委實可愛。
這樣的詩真算平易近人,平易到連我的兩歲娃都可聞後成誦,且亦能摹其聲其形呢。
古代有一首民歌:
東邊一棵樹,西邊一棵樹,南邊一棵樹,
樹,樹,樹,挽不住郎舟住。
前三句指物辨向,平實單起。接下,一連三聲“樹”,音調鏗鏘,節奏急促,內蘊激情難按。於此,活脫脫跳出一個癡情女子.她留不住離去的丈夫,只得把希望寄托給眼前的拴船的大樹了.每棵樹,都曾寄托她挽留丈夫的深情,可又沒有一棵樹能幫她的忙,反過來,她卻對樹發出深沉的怨怒了.這首小詩,也可算夠平淡了,但其中愛多濃,情多深!此正謂"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
當代大詩人艾青的美學主張即追求詩的平淡樸素,追求語言的口語化。他稱詩的平淡之美是“擲給空虛的技巧的寬闊的笑”。他認為“深厚博大的思想,通過最淺顯的語言表演出來,才是最理想的詩。”(《詩論》)因此,艾青寫詩盡可能用口語,盡可能地做到“深入淺出”。
比如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從語言傻瓜看全用口語寫成,算是平淡極了。但這平淡之中蓄有多少至性深情,半個多世紀以來它撼動了多少人的心呢!
“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這是宋人梅堯臣的慨歎。
應該說,詩的平淡美,屬於一種更高級的美。因此,它要求詩人必須有至性深情,又有驅譴錘煉語言文字的功力。
清黃子雲《野鴻詩的》雲:“縱極平常淺淡語,以力運之而出,便勃然生動。”黃氏強調的“力”,即作詩之功力。
清施補華《峴俑說詩》雲:“凡作清淡之詩,須有沈至之語,樸實之理,以為之骨,那可不朽,非然,則山水清音,乃流於薄。”
當然,這沈至之語,這清淡之詩,是要詩人費一番錘煉功夫的。袁枚說:“求其精深,是一半功夫。求其平淡,又是一半功夫。”就是這個意思。張向陶在《船山詩草》中也說:“敢為常語談何易,百煉工純始自然。”
不過,這種錘煉,不是往富麗華貴處煉,而是以平淡的審美原則,在遣詞用字上,盡可能地深入淺出一些,平白質樸一些,做到蘊藉深衷,銜旨遙遠,而又平易清淡,出語如話。亦即劉熙載所說的:“要往活處煉,非往死處煉也。”
所謂往“活”處煉,就是結合煉意,既煉形體,又煉精神;所謂往“死”處煉,就是隻追求字句的修飾和雕琢,為煉句而煉句。清人賀子翼說;“煉字煉句,詩家小乘,然出自名手,皆臻化境。蓋名手煉句如擲杖化龍,蜿蜒騰躍,一句之靈,能使全篇俱活。煉字如壁龍點睛,鱗甲飛動,一字之譬,能使全詩皆奇。若煉一句只是一句,煉一字只是一字,非詩人也。”這裡也是強調煉意。現在我們有些同志寫詩卻不大注意煉意,而隻講究語言的“奇麗”,認為常見的字句太平淡,要煉就煉“奇句”。殊不知,那些膾炙人口的千古佳句,大都是深入淺出,明白曉暢。如大家熟知的“桃花依舊笑春風”的“笑”字,平常嗎?但它點活全境。我國著名大詩人白居易的詩所以流傳甚廣,原委之一就在於他作詩“不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而力求通俗平易。所以劉熙載讚:“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古詩如此,新詩亦然。請看,“長江黃河淚兩行”,可謂平白如話,但其中多少悲慟,多少情思!
蘇軾有雲:“好奇務新,乃詩之病。”的確,若以“奇語”為佳,一味追求奇語,而忽視煉意,其詩句職能象臃腫的胖子一樣“色厲內荏”。賈島的“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兩句,寫了三年,詩人自鳴得意,大發感慨:“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但由於意境不高,他人卻覺平常。
劉熙載在《藝概·詩概》中說:“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這裡的“常語難”,就難在“用常得奇”上。
沈德潛說:“古人不廢煉字法,然以意勝而不以字勝。故能平字見奇,常字見險,陳字見新,樸字見色。”沈氏是主張從平淡入手以煉意。
記不清什麽時候在什麽地方讀過這麽兩句民歌,那是一位婦女痛悼她已故親人的悲歌:
山在水在石頭在
人家都在你不在
這貌不驚人的兩句,實則表現了平淡美的兩個重要特徵:一是情真意切,二是平白質樸。
山,水,石頭,人家,你。四個“在”,一個“不在”。用字也真是太平常不過了。然而,你再品品那“在”與“不在”之間,包孕著,起伏著多麽驚心動魄的至情。這就是平淡美的力量。
最近讀到杜運燮的一首《只因為》(見1985年5月9日《人民日報》,《詩刊》1985年第8期予以轉載),堪稱新詩中頗具平淡美的典範之作。且看詩的前幾節:
你身旁有陰影
只因為你自己
擋住了陽光
不能把陰影甩到後面
只因為你沒有
朝著太陽的方向走
你看耀眼的陽光
仍然是一片黑暗
只因眼睛剛睜開
你看不清好景色
一切是一樣的模糊
只因眼淚未擦乾
你聽不見牆外
火車告訴奔跑聲
只因你關了門窗
......
詩人的面前好象坐著一個人,那是他的知心朋友,作者和他直面相照,促膝而談。全是口頭語,家常話,娓娓道來,平平說出,和風徐徐,其間多少情味,多少哲理,又給人多少深警 的啟智啊!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王安石)平淡,作為一種歸真返樸的美,它不是一開始學詩,就能把握的。而需要有雄厚的生活基礎,和一定的藝術功力。不然,“火候未到徒擬平淡,何啻喜丸?費盡咀嚼,斐然滿口,終無氣味”。(薛雪《一瓢詩話》)
梅蘭芳談他表演,在動作上有過少——多——少(精)的經歷。
華羅庚也說,讀一本書有一個初讀增厚,再讀漸薄的過程。
劉熙載在談到書法藝術時指出:“學書者始由不工求工,繼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極也。《莊子·山水篇》:‘既雕既琢,複歸於樸。’善夫!”(《藝概·書概》)
這叫否定之否定。
就作詩而言,追求平淡之美,也往往有這個過程。
陸放翁雲:“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繪;中年始少悟,漸若窺宏大。”(《示子遹》)
蘇東坡雲:“大凡為文,當使天氣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竹坡詩話》)
這些都是經驗之談啊。
蘇東坡自己寫詩追求平淡之美,也這樣教育後生。一次,有個青年人帶著詩稿請教於蘇軾,蘇軾看完詩稿後,針對那青年人好奇勿實的弊病,隨即寫了兩首五言小詩與他。其一:“字字覓其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其二:“衡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第一首是批評,批評那後生寫詩患在“覓奇險”;第二首是引導,引導年輕人寫詩應追求“常言”的平淡之美,這些無疑地也是值得借鑒的。
本文來源網絡,平台僅為傳播知識,無意侵權,請告之並刪除。
本文摘於網絡,版權歸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