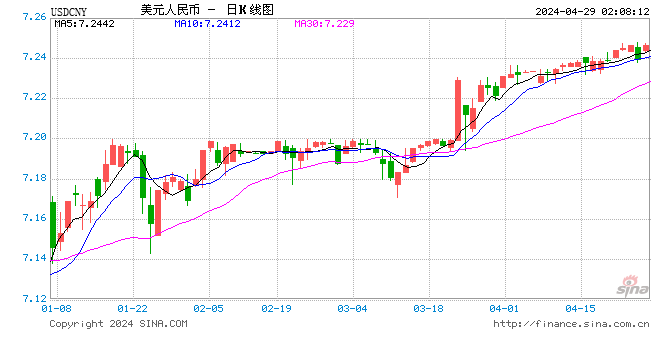來源:前沿觀察
作者:譚翊飛
編前語:他一路思考什麽才是真的馬克思主義。他會成為中國的格林斯潘嗎?看完下文,也許你會有自己的答案。
1.第二故鄉
易先生歸國那年,他那些熟悉的華人教授朋友們在感恩節聚會的話題變成了易先生和易太太,他們不明白易先生為什麽要回國。
這是一群80年代就出國留學的華人教授群體,他們住在印第安納州波利斯城西北的一個叫塞多布魯克的小區,互相聯繫緊密,經常串門聚會。易先生和易太太是其中的一家,在他們這群人中易先生最先拿到美國的終身教職,一周上兩天班,每個月稅前可以拿到5000美金。用他們的話來說,他們在那裡買了房子,安家落戶,美國夢已經實現了。
不過,易先生剛到美國時也過得很辛苦,最窮的時候身上只有2美元,一周三次去餐廳打零工,為的只是填飽肚子再賺些零花錢。大學結束後,他的成績本來可以去更好的大學,但是伊利諾伊大學可以承擔全部的學費,於是他就去了。畢業後,他在印第安納大學經濟系謀到了一份教職。
聚會的朋友們記起了易先生曾經問過他們,你們覺得我們的生活像不像鄉下的農民?
 (IAAT)
(IAAT)
當時易先生36歲。在美國過著安逸、平靜的生活,太太和孩子都在身邊。但是,大洋的彼岸,中國的改革正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熱火朝天地展開。
易先生雖然生活在美國,但研究的都是中國問題。現在能查到易先生的英文文章最早在1987年,他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計量經濟學家George Judge共同署名,他署第二作者,當時他博士剛畢業。
到了1990年,他就開始獨立發表文章,許多文章發表在《China Economic Review》雜誌上,另外還有《Journalof Asian Economics》和《Economics of Planning》等。
1990年,他的第一篇獨立署名的文章《Inflation and price instability: Anempirical stud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發表,他運用1953年-1988年的數據研究中國的通貨膨脹和價格波動的關係。通貨膨脹一直他後來所關注中國經濟問題的重點。
1992年、1993年他寫了多篇文章研究中國的貨幣需求問題,他將貨幣化和通脹預期加入貨幣需求函數,解釋了改革開發初期為什麽貨幣超發嚴重但卻並沒明顯的通脹。這項研究他持續了十年,到2003年,出版了一本專著《中國貨幣化進程》。
他們的那些朋友可能不知道,作為研究經濟和金融問題的副教授,易綱的心早已和大洋彼岸連在一起。他本來準備大學一畢業就回國,但是北大的校長告訴他,要了解美國的教育必須在那工作。於是,他多留了幾年。但到了1994年,即使他的妻子當時沒同他一同回國,他也義無反顧。
回國前,他與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留學生圈子聯繫越來越緊密。1985年,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在紐約成立。7年後易先生成為了這個學會的會長,當時方星海是理事,後來方星海也擔任過會長。至今活躍在國內的一大批經濟學家都曾是這個學會的會員,包括錢穎一、陳平、林毅夫、海聞、楊小凱、許小年、田國強等,名字可以排得很長很長。
1993年6月,夏日炎炎,“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變國際研討會”在海口舉行,這是留美經濟學會首次在中國大陸舉辦活動,易先生是當時的會長,開了先河,後來成為了慣例。他們當時還聯絡了中國留英經濟學會聯合舉辦,張維迎從英國來到海口,林毅夫那時已經回國,在農研室工作,老王是他的同事。林毅夫從北京來到海口。
他們匯聚在一起。據後來的報導說,在這次會上,他們都決心回國,創辦一個中國經濟的研究機構。
1994年8月初,北大杓園5號樓的106房間,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易先生已經從海外回國,成為創辦的六君子之一。
多年後,易先生回到他教書的學校接受榮譽博士學位授予時,校長派專人去機場接他。在演講中,易先生說那裡是他的第二故鄉。當年的系主任Juillerat教授說,“招聘易綱是我做系主任期間做出的最聰明的決定之一。”
2.劉鶴主持的那場爭論
易先生回來的時候,國內經濟已經走出了1990年整頓的谷底,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帶動下,全國都在大乾快上,熱火朝天。於是,經濟很快由緊縮變為過熱。
那個年代,中國的巨集觀調控經驗很不成熟,經濟的波動性很大,跌跌撞撞,在過熱和過冷之間劇烈震蕩。
易先生在國外的學問恰好是中國那時候最需要的,他學的計量經濟學和金融理論,研究的重點是貨幣問題。
1993年,中國的物價已經開始明顯上漲,通貨膨脹的壓力很大。在1994年1月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朱老闆說的第一點就是“繼續整頓金融秩序”,並且反覆強調控制住“發票子”的問題,他說,“嚴格控制信用總量,這是國家的利益,是人民的利益,大家一定要嚴格地按計劃執行。”
當年,銀行的貸款被嚴格控制,現金也管理得很好。按照貨幣學派的觀點,“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種貨幣現象。”那麽,為什麽還會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呢?當年CPI最高達到了27.7%。
易先生發現了新情況,原來貨幣擴張主要來自於外匯儲備,當年的外匯儲備增加了304億美元,1991年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放出外匯佔款隻佔17%,1994年卻急劇增長到佔70%。易先生在1995年接受《山東金融》采訪時分析了這一問題。也就是說,央行想盡辦法控制基礎貨幣,可是外匯佔款卻在“跑冒滴漏”,增加了基礎貨幣釋放。
後來,外匯佔款劇增成為尾大不掉的問題,周小川用“池子”圈住這些被動超發的貨幣,央行大量發行央票,但當年易先生就提了許多解決辦法,這是後話。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當時朱老闆已卸下了行長職務,讓戴XL來當行長。易先生到央行擔任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副秘書長。這場危機對中國金融改革影響深遠,之前開放的思路受到抑製。
1998年初,易先生和方星海一起寫了一篇文章,分析拉美國家債務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當時方星海在世界銀行工作。他們提出了幾點政策建議:1,經常账戶赤字不容忽視;2,資本市場開放要漸進;3,資本市場開放要有順序;4,金融監管一定要加強;5,實行有彈性的匯率政策。
對於中國經濟學界來說,內部整頓外部衝擊之下,那幾年是困難而又迷茫的時期。1997年年底CPI只有0.4%。1998年二季度增速只有6.9%,而1993年一季度是15.3%,增速腰斬。
從1978年算起,1998年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二十年了,中國已經高速增長了20年,這被認為是高速增長的“物理極限”。林毅夫和蔡昉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中國改革》就是解釋這一奇跡。奇跡既然已經發生,未來增長還有多大的潛力?經濟學界較為悲觀。
1998年底,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與管理世界雜誌社主持了一場“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學術研討會,國家資訊中心主任劉鶴第一個發言,易先生第二個發言,其他參與討論的還有宋國青、鄭京平、樊綱、王小魯等。
劉鶴發言開宗明義:1998年以來, 隨著中國通貨緊縮現象的出現, 不少學者提出了較為悲觀的看法,認為長達20年的高速增長階段已經完結, 中國將進入一個低速增長的結構調整期,而不太可能“突破 20 年高速增長的物理極限”。
劉鶴堅持認為,城市化、市場化和國際化將為高速增長創造物理太空、動力機制和運作慣例。他直接批評“懷疑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同仁在兩個問題上有動搖”,這兩個問題是指:把短期的周期現象與長期的結構現象相混淆;把結構性選擇的誤區與結構調整的太空相混淆。
易先生接著發言,他同樣主張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還有五大太空:城鄉結構轉換太空、所有製結構調整太空、產業結構調整太空、區域結構轉換太空和中小企業發展太空。
他並沒為自己所擅長的貨幣政策鼓與呼,相反,他認為,以財政和貨幣政策為主的巨集觀調控是在給定的體制和結構條件下進行政策調整,熨平經濟波動,是經濟生活中的“短期問題”。而從中長期的角度來看, 必須通過深化改革, 調整經濟結構來解決中國的中長期發展問題 , 以保障中國經濟高效可持續地增長。
易綱是一個堅定的改革派。雖然當時的銀根已大為放鬆,但是還是有不少人認為仍不夠松,易綱同意要增加貨幣供應量,緩解緊縮的形勢,但他也回擊許多不合理的要求,比如他說,“社會保障問題已經超出了貨幣政策的範圍。”“通貨緊縮的深層原因是信用制度的破壞, 建立並完善中國的信用制度才是治理通貨緊縮的根本。”他是讀書人,但不是書齋裡的人,對中國的現實他有深刻的認識。
 (2010年12月,北京凱恩克勞斯經濟研究基金會)
(2010年12月,北京凱恩克勞斯經濟研究基金會)
這場爭論早已結束,答案也早已明了,在經過世紀之交的築底徘徊之後,中國加入WTO,重啟了新一輪高速增長。2003年,《財經界》刊登了易先生在中國投資環境論壇上的演講,文章標題是:“克魯格曼真的錯了!”克魯格曼此前對中國增長前景抱有悲觀的態度。
主持那場爭論的劉鶴現在是個重要的人物。新周期開啟時,2003年,他到了中財辦擔任副主任,分管巨集觀經濟政策方面。2013年3月,他轉正為中財辦主任。一年後,2014年4月,易綱和他到了一起,擔任中財辦副主任,即使卸下了外管局長職務,這個職務至今仍在。
 (2013年3月,葛衝)
(2013年3月,葛衝)
相似的爭論在十多年後又一次發生。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四兆”刺激政策實施後,中國經濟再度持續下行,中國不是不是到了新的“增長極限”,還是等待開啟一個新的周期,經濟學界又一次陷入了紛爭。
不過,這場爭論很快結束了。林毅夫振臂高呼“8%增長還可以持續20年”引來了陣陣笑聲。官方給予了蓋棺定論:中國經濟處於“三期疊加”時期,增速要換擋、經濟正處於新常態。
2017年6月底的夏季達沃斯論壇,施瓦布提問總 理關於經濟增速的問題,李再次以“年輕人翻跟鬥”的比喻來回答,也就是說,超高速增長一去不複返成了高層的共識了。
3.這是他的舞台
當1995年易先生發現前一年中國基礎貨幣放量主要是由於外匯儲備增長過快引起時,朱老闆也在掐指頭來計算中國需要多少外匯儲備。
1994年底,朱老闆在央行的講話說,按三個月進口支付能力來計算,他用兩種數據計算都得出,“現在的外匯儲備水準比合理儲備水準大體多100多億美元。”
當時的外匯儲備是516.2億美元。但到了2009年,易先生擔任外管局局長時,外匯儲備將近2兆美元,而在他的任內,外匯儲備一度接近4兆美元。
雖然早在1997年他在《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因素及走勢分析》一文中就提出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應對建議:適當增加進口、藏匯於民、利率市場化和開放資本账戶。但顯然這並沒有阻礙外匯儲備的急劇上升。
2009年,易先生在央行的職務得到實質性提升,他開始擔任外管局局長,執掌兩兆的外匯儲備。
他面臨嚴峻而複雜的挑戰:一方面,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需要保值增值,但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元貶值,外界甚至傳言中國購買的數千億兩房債券打了水漂,可以想象外管局壓力巨大。2009年3月全國兩會後的記者會,溫家寶借回答《華爾街日報》記者提問時直言,“我們把巨額資金借給美國,當然關心我們資產的安全。說句老實話,我確實有些擔心。因而我想通過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國保持信用,信守承諾,保證中國資產的安全。”如何保證中國巨額資金的安全,這個具體任務落到了易先生頭上。他需要嘗試新的辦法。
另一方面,外匯改革停滯多年,資本項的開放也基本停滯,他需要強有力的推動改革。國務院批準的《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要求“逐步實現資本項可兌換”。這個任務也落在易先生任內。
第三,易先生上任那年初,周小川發表了一篇影響力巨大的署名文章《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元這個全世界穩定的錨變得不穩定,周小川也提出了對全球貨幣體系的“中國方案”。這個任務同樣落在新任的外管局局長易先生的肩上。
易先生上任之初就提出了“五個轉變”,這是順應整個行政管理體系改革的潮流而進行的,從重審批向重事後監管轉變。他提出了從“有罪假設”轉變到“無罪假設”轉變,逐步從“法無明文授權不可為”轉為“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等法治思想。他是一個堅定的改革派。
針對嚴峻的挑戰,他打了幾場硬仗,雖然有些成敗未有定論,但至少可以看出,他並非書齋裡的學者,而是有力的改革者。2010年2月,在易先生的力邀之下,朱長虹辭去全球最大債券基金,“債券之王”格羅斯(Bill Gross)長官的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的職務,加盟外管局。多元化投資要推進,但外管局人才缺乏,需要從外面引進。
當時,中國的外匯儲備多元化投資受到全球的關注。中國的外匯儲備過去主要都是美元資產,多元化意味著要拋售美元資產,買入日元或歐元資產。這是一個大膽的舉動。
在2011年兩會期間央行的記者會上,易先生指出,“外匯儲備投資的多元化,一是在幣種上是多元化的,是一籃子貨幣,主要的可兌換貨幣、儲備貨幣、新興市場的貨幣,同時在資產上,也是推進多元化的,有各種各樣的資產。”外匯儲備多元化投資是那幾年的熱點問題,海外也高度關注,日本媒體不斷渲染中國增持日本國債的消息,雖然其實中國購買量在總佔比中並不高。歐債危機在發酵,他們希望中國加大對歐元區的投資,增強歐元的穩定性。
在多元化投資的戰略方向下,中國投資美元資產的比重降低了,多元投資一度也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是到了2014年1月朱長虹離職時,輿情開始爆發。市場將之解讀為外匯多元化投資的失敗,原因是他沒有預料到日本推出瘋狂的量化寬鬆政策,進而導致在日元投資上的重大失利。這段“公案”至今沒有厘清,因為沒有相關的數據公布,外界很難知曉真實情況,是非功過仍有待後人評說。
當時,財新的報導引用知情人的話評價說,朱長虹把很多“市場化的玩法”介紹進來,帶來了很多市場化的東西,包括系統、模型、技術、人員等,可以說讓外匯儲備投資上了一個台階,這是他的主要貢獻。
與外匯儲備多元化投資更重要的是一件事是,易先生任內推動了8·11匯改。中國的匯率市場化改革很慢,1994年匯率並軌、2005年參考一攬子貨幣,易先生任內先擴大了匯率的日波動區間,終於在2015年推出大變——中間價一次性貶值2%。
可是,為何選擇在2015年8月推進匯改?當然有外匯市場技術面的因素,但當時可能確實不是一個改革的好時機,一方面股災剛過,市場還在慘痛之中沒有醒來;另一方面,當時經濟仍處於低迷期,為此不得不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多次降準降息,穩定經濟增長,但這些政策和穩定匯率相衝突。再者,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不斷下跌,導致出口進口增速都大幅下降,外貿形勢嚴峻。
8·11匯改全球為之震驚,國內也完全沒有準備,習慣了穩定或升值的國內民眾也被嚇慌了,國外投機力量又不斷推波助瀾,貶值預期不斷強化,到2016年底人民幣匯率一度接近破7。但“(匯改的)窗戶打開了,不可能再關上了”。

8月13日央行舉行匯改吹風會,易綱在會上作出堅定的表態,“一個僵化的、固定的匯率是不適合中國國情的,也是不可持續的。”對於傳言,“所謂人民幣要貶值10%,要刺激出口,還說這是官方意圖,完全是無稽之談。”他反覆強調,“要相信市場,要尊重市場,甚至要敬畏市場,要順應市場。”
除了外匯投資多元化、匯改之外,易先生任內還積極推進資本項的開放,資本市場和債券市場的開放度都大大提升,雖然至今仍然沒有完全實現。同時,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得到極大提升,2015年人民幣納入SDR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
但是,“不可能三角”也開始發揮更大的魔力。匯改後,當維持匯率穩定在短期內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是排在第一位的任務時,國內的貨幣政策就不得不受到製約。為了保持人民幣的穩定,央行不得不謹慎使用利率或存準工具,2015年10月之後,央行未再動用這兩個“大殺器”。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年為了應對外匯佔款急劇增長,央行發行大量央票回籠貨幣。而今這些年,為了應對外匯佔款的下滑,央行創新了“各種粉”用於增加貨幣投放。央行的基礎貨幣釋放一直處於被動的狀態,未來如何作出轉變則考驗著小川和他的繼任者們。
4.真假馬克思主義
易先生生在北京,長在北京,文革中他的家庭遭到了很大衝擊。在初中和高中的時候,少年的易先生總想搞明白:什麽是真馬克思主義,什麽是假馬克思主義,什麽是修正主義。
這種炙熱的思考一直帶到國外,他還試圖學習德文和俄文的語法,“理解原著是怎麽寫的”。
在一次接受提問時,有人問他怎麽看國家資本主義。他說,他的理想是“小政府、大社會”,“對政府的權力有一個清楚的法律界定,政府對經濟的介入應當是非常有限的。”
在一次讀書會上,他推薦了《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分析了在長期愚昧,實行愚民政策,或者極端制度的國家是如何產生大革命的。”同年年底,老王邀請學者座談,也向學者們推薦了這本書。
在他離開塞多布魯克15年後,當年熟悉他的朋友說,再過幾年,易先生也許會成為中國的格林斯潘。(新浪財經注:本文首發於2017年7月2日)
相關報導:
責任編輯:杜琰 SF007